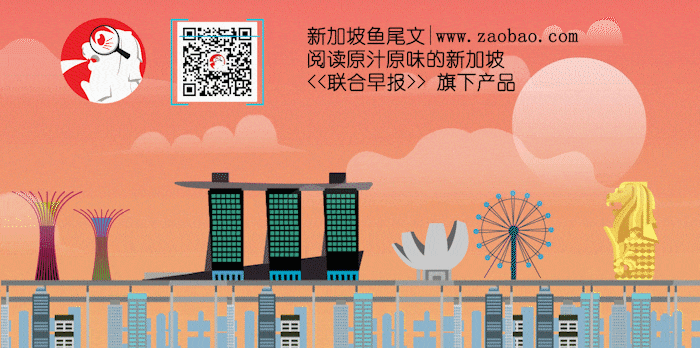1817年,萊佛士的巨著《爪哇史》付梓,引起當時學界的關注。遺憾的是,在他返回倫敦的航程中,船艙起火。他在東南亞各地收集的史料,包括大量的手抄文獻,皆毀于祝融。他曾記述,其實還想編撰一部《新加坡史》。日後《新加坡史》並沒有寫出來。如果萊佛士的《新加坡史》成書,書中對開埠前和初期的華人史會作怎樣的論述?曆史沒有假設,新加坡開埠初期的華人史,實際上是廖內柔佛王朝華人貿易史的延續。因爲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廖內群島與柔佛等地,曾是柔佛王國(Johore Empire)的疆域。
開埠初期新加坡地圖上顯示新加坡河流域已經有甘蜜園存在。
望加錫與武吉斯人
1511年,葡萄牙擊潰滿剌加王朝,占領馬六甲,掀開歐洲列強東來的序幕。當葡萄牙人控制馬六甲海峽後,伊斯蘭、印度及中國商人之間的中西交通航線受阻,被迫改從加裏曼丹,轉入巽他海峽,或者從菲律賓的蘇祿海進入望加錫海峽,再往西航。
位于蘇拉威西南部的望加錫(Macassar,舊稱西裏伯),遂成爲中西交通要沖。望加錫還是爪哇與摩洛哥群島的中轉港口,商業繁盛。 談柔佛王朝的曆史,離不開武吉斯人。武吉斯人源自望加錫,是個骁勇善戰的海上民族。曾經在馬來群島各地稱霸,並左右廖柔王朝的政治。直至18世紀末,荷蘭人將武吉斯人的勢力驅除,廖內遂淪爲荷屬。
古幣解密廖柔王朝 甘蜜貿易史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廖內民丹島的河岸陸續出土數以萬計的古代錢幣,當時的這個發現,並非通過考古發掘,因此出土的古錢幣,大量被轉售到新、馬的古幣收藏市場。
部分珍貴的品種,還被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的錢幣博物館購藏。
對于這些大量出土的古錢幣,當時學界並沒有作太多的論述與研究。 出土的錢幣種類豐富,以錫鑄幣爲主,另有金、銀及銅幣。出土量最大的錫幣,錢文皆鑄有回文“真主是偉大的”(Kali Malik Al Adil)字樣。這類錢幣應是廖柔王朝的鑄幣。
其他尚有來自馬來半島各地、蘇門答臘、爪哇的馬來王朝錢幣,此外還發現大量中國清初銅錢、安南銅錢,及微量的西班牙銀元。更重要的是,出土錢幣之中,同時發現鑄幣模具——錢範。這表明錢幣的出土地點,也是鑄幣地所在。
這些出土錢幣的種類與鑄幣年代表明,其流通時間應該在17世紀至18世紀之間,究竟這些流通于18世紀的錢幣爲何被遺棄在民丹島的河岸呢?故事要從一部馬來文獻《珍貴的禮物》(Tuhfat al-Nafis)談起。
1980年代印尼廖內民丹島出水的各種18世紀錢幣。 馬六甲被葡萄牙人占領後,末代蘇丹不斷往南遷,曾經遷都柔佛河流域,繼遷往廖內,史稱廖內柔佛王國。曆史上柔佛王國並不強盛,日後甚至受武吉斯人牽制。《珍貴的禮物》成書于1885年,由廖柔王朝皇室編撰,內容記載柔佛王國與馬來群島的曆史。
據《珍貴的禮物》記述,廖柔王朝副王鄧哲剌(Daeng Chelak,?-1745),把甘蜜引入廖內民丹島,並鼓勵華人種植。至少在18世紀中葉,甘蜜貿易成爲廖內最重要的經濟支柱。除了馬來群島的土著帆船,閩、粵的紅頭與綠頭船,紛紛到此貿易。新加坡開埠前,廖內是本區域重要的貿易站,馬來群島的商舶與歐洲商船,聚集于此貿易。據英國人記述,19世紀初民丹島上的華人約有1萬3000人,且以閩南和潮州籍爲主。甘蜜與胡椒則是廖內、新加坡及柔佛三角貿易圈的主角。
18世紀以來,荷蘭人與武吉斯人在馬來群島因商業與政治利益而沖突不斷。
1784年,荷蘭人擊潰武吉斯人的政權占領廖內。民丹島河岸的繁榮景象,幾乎皆毀于這次的戰火。岸邊民居的錢財,隨戰火沉入水中,記憶逐漸消失。直至1980年代大量的18世紀錢幣才重見天日。
荷蘭與清初文獻載嚼槟榔
甘蜜不只有食用價值,尚有工業價值,充作染料。
18世紀的荷蘭文獻記載,甘蜜不單在廖內大量種植,也曾被荷蘭人引進馬來半島的笨珍地區種植。這當然是由于甘蜜在馬來群島與中國市場有一定的經濟價值。爲了保護自身的利益,華人極不願意讓荷人知曉甘蜜的種植與生産技術。
清初中外交通史文獻《海錄》(謝清高口述,楊炳南撰),對新加坡出産的甘蜜曾作如斯記述:嘉慶年間,英吉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國商民在此貿易,耕種,而薄其賦稅,以其爲東西南北海道四達之區也。數年以來,商賈雲集,舟船輻辏,樓閣連亘,車馬載道,遂爲勝地矣。蕃人稱其地爲息辣,閩粵人謂之新州府。土産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
槟榔膏即甘瀝,可入藥。 《海錄》裏這段記載,是嘉慶庚辰年(1820)補充的。文中透露槟榔膏有入藥功能,並說槟榔膏也稱甘瀝(甘蜜)。實際上清初時,中國廣東的粵海關早對來自南洋的甘密征入口稅。廣東海關文獻《粵海關志》裏,就將甘蜜歸于藥物類別,並注明其入口稅則。
前述荷蘭文獻亦曾記載,土著在咀嚼槟榔時,除以荖葉包裹,尚混搭兒茶(Catechu)與小豆蔻(Cardamom)。由于兒茶價昂,便以甘蜜代之。中國閩粵地區咀嚼槟榔之曆史悠久,唐宋以來文獻記述甚多。清初黃叔璥《台海使槎錄》記載台灣地區食用槟榔時,需要配加蛎房灰,用孩兒茶、柑仔蜜染紅、合浮留藤食之。
文中所說的“柑仔蜜”即甘蜜。顯而易見,台南與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之間的貿易,是甘蜜的來源。 同時期,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對于嶺南人嗜食槟榔之記載尤詳。並曰盛放槟榔的用具極爲講究:廣人喜使槟榔,富者以金銀、貧者以錫爲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務極精麗。中分二隔。上貯灰臍、蒌須、槟榔。下貯蒌葉(即荖葉)。食用時先取槟榔,次蒌須、次蒌葉、次灰。凡四物各有其序。此外,書中也記述在咀嚼槟榔時佐以石灰及烏爹泥,並說:有灰而槟榔蒌葉乃回甘。灰之于槟榔蒌葉,猶甘草之于百藥也。灰有石灰、蚬灰。以烏爹泥(兒茶的別稱)制之作汁益紅。字裏行間,槟榔咀嚼方式與味道躍然紙上。
由于兒茶與甘蜜相類,洋人曾將源自印度的兒茶與甘蜜混淆記載。早年來自海南島的曆史學者韓槐凖曾撰有《兒茶考》一文,細分兩者之差異。從上述文獻可知,甘蜜又稱柑仔蜜、甘瀝、槟榔膏。這些名稱最早大概出現于清初。
新加坡開埠前的甘蜜種植
甘蜜園通常開辟于河道流域,方便運輸。閩粵方言稱河道爲“港”,河道盡頭或交彙處俗稱“港腳”。廖內、新加坡與日後的柔佛皆是如此。萊佛士登陸新加坡時,曾記述島上已經有華人甘蜜園。第一任駐紮官法誇爾信函(收錄在海峽殖民地檔案裏)記載,當時已經有約20處甘蜜園丘。這些甘蜜種植園分布于福康甯山的西南面及東南面。開埠後,有幾個華人將甘蜜園售予英國商人,包括Tan Naun Ha(陳銀夏?)、Tan Ah Loo(陳亞魯?)、Heng Tooan(王端?)。
重新移植于福康甯山的甘蜜樹。 開埠初期的新加坡地圖顯示,華人曾經聚居于新加坡河南岸,地圖上標示這一帶是一處華人聚落。在聚落不遠處,就標示有甘蜜園(Gambier Plantation)。說明聚落的部分華人與甘蜜種植業有關,甘蜜種植業除了需要園丘工人,也需要運輸與貿易。華人聚落的房子,主要是木屋,而且有些是沿著岸邊而搭建的浮腳屋。
開埠前的華人,極可能早在1784年荷蘭擊垮廖內的武吉斯政權後,陸續從廖內移居到本島。開埠後華人逐步增加。今天如果到廖內或周邊島嶼的河岸,相類的水上木屋依然存在,當地華人稱之爲水厝。相同的居住形態,200年前同樣存在于新加坡河沿岸。
開埠初期華人甲必丹 從事甘蜜貿易
當年東印度公司決定在馬六甲海峽以南,尋求一個適合英國商船中轉的貿易站時,選址舉棋不定。法誇爾曾提議在吉利門島(Pulau Karimun,今吉裏汶島),然而吉利門與曆史擦肩而過,獨具慧眼的萊佛士選擇了新加坡。 開埠後新加坡河南岸的華人聚落房子激增。聚落裏的這些住戶,構成開埠初期最早的華人社群。開埠之初,華人社會有甲必丹管理。然而按萊佛士計劃,新加坡河西南岸要開辟成爲商業地段,供商號與倉庫之用。
1822年10月萊佛士第三度到新加坡,並擬定市區發展計劃,下令聚居于新加坡河西南岸的華人遷離。 海峽殖民地檔案裏有一份文檔,是當年居住于此處130間木屋的111居民,向第一任駐紮官法誇爾面呈的陳情書。他們請求合理的賠償,在這份陳情書上簽字的還有當時的一位華人甲必丹陳浩盛(Tan How Seng)。陳浩盛亦是一名甘蜜商,擁有多處甘蜜園。逝世後地皮賣給洋商約翰麥士威(John. A. Maxwell),可是麥士威發現那裏竟然還有華人在種植與提煉甘蜜。檔案中雖沒有透露陳浩盛從什麽地方移居新加坡,顯而易見,陳浩盛來自廖內,且還應該是潮州商賈。
海峽殖民地檔案裏,新加坡河南岸華人請願書。
倫敦條約 撕裂柔佛王國版圖 萊佛士的《爪哇史》透露,爪哇的甘蜜依賴淩加(Lingga)與廖內入口,每年的進口介于二至三萬擔。開埠後,英國人宣布新加坡爲自由港,這直接影響東南亞其他港口的競爭力,例如巴達維亞與馬尼拉。以廖內出産的甘蜜等土産爲例,也從向南運輸巴城轉爲北上運往新加坡。這時大量的廖內舢舨船,往來于新加坡與民丹島,運來甘蜜、胡椒、稻米和各種群島土産,運走鴉片及各國商品。
英、荷長期在東南亞的勢力糾紛,終因新加坡的開埠,于1824年3月17日在倫敦簽訂倫敦條約(亦稱英荷條約)。條約中,英國與荷蘭劃清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英荷互換蘇門答臘的明古連與馬來半島的馬六甲。兩國以新加坡海峽爲界線,北爲英國勢力範圍,以南則歸荷屬。在船堅炮利下,歐洲列強無視廖柔王朝權益及疆土範圍,一紙條約下,古老的馬來王國就此崩盤。
倫敦條約原件。(攝于國家圖書館特展)
風帆時代的廖內甘蜜貿易
開埠前,新加坡島屬柔佛王國的領土範圍。與民丹島的情況大致相同,這時期的甘蜜制成品皆運往廖內或巴達維亞,再轉運中國及東南亞各地。第二任駐紮官克勞福曾說,最適合本土種植的農作物是甘蜜與胡椒。只是比起其他商品,甘蜜的需求量與利潤不如其他土産。加以甘蜜種植極爲耗費土地資源,因此隨著自由港的迅速發展,甘蜜種植只能往內陸拓展,然而其東南亞的運銷量依然維持。
以1826年爲例,甘蜜出口總值達2萬8000西班牙銀元。由于本地的産量有限,主要還是依靠廖內供應轉出口,每年約有五六百艘小船運載甘蜜來本島。新加坡也取代廖內,成爲甘蜜與胡椒的貿易中心。與此同時,中國帆船南來貿易,船上運載大量華工。這些華工在新加坡靠岸後,有一大部分輾轉前往南洋各地的甘蜜園與錫礦區。
1829年的《新加坡紀事報》報道當年華人激增時指出,園丘工人需求是主要原因。1834年以後,因英國關稅降低,加上工業革命以來,紡織與染料供求不斷提高,甘蜜價格節節攀升,成爲重要的海峽土産。並從本島移植柔佛,且帶動日後柔佛的發展。
甘蜜商的天後與玄天信仰
早年華人南來,謀生經商之余,也把家鄉的信仰帶來。媽祖崇祀在中國堪稱是全國性的,由于其信仰功能,海運與漕運無不信奉媽祖。來往于新加坡與廖內的船戶,面對大自然與海盜的威脅,天後宮自然是心靈寄托之處。而玄天上帝卻是潮汕地區最重要的神祗。從銘刻文獻可知,廖內天後宮的創建年代,不晚于乾隆乙亥年(1779)。
廖內的天後廟與玄天上帝廟,無論是建築風格或信仰背景,與新加坡的粵海清廟有著某種的曆史淵源,更與甘蜜貿易商賈,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今天粵海清廟尚存有兩個香爐(現藏于義安公司)。一方銘刻落款爲:乙卯年(1819)元月吉旦、天恩公、沐恩金協成喜敬。金協成亦可能是閩籍,廈門地區舶商皆以金字代“合”;大多文獻表明,廖內同時有閩商與粵商,即潮州人。另一個銘刻爲:道光六年(1826),玄天上帝,曾四合敬。曾四合,似乎非獨自一人,或是四個人合敬;在曼谷,潮州人的公司多以某某兩合爲名稱,當是一種商業合作俚語或名詞。這兩方香爐上的銘刻,可說是新加坡最早的華人銘刻文獻,且與甘蜜貿易史關系密切。
開埠前史觀需撇開國界
今天如果從國界與一貫的曆史觀,一般將新加坡、柔佛與廖內三地曆史分開論述。然而在1824年以前,這三個地方,皆屬于廖柔王朝之疆域。在談論這個時代的華商、甘蜜貿易及日後柔佛港主制度下,影響新加坡早年最重要的兩項貿易大宗(錫米與椒蜜),如將三地切割分述,所得到的曆史圖像將是片面的。 要更加理解新加坡開埠前的曆史,需稍微跳出一個曆史框框——英荷條約。英荷條約的簽訂,不只將柔佛王國的版圖撕裂,也將我們對于這段曆史的思維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