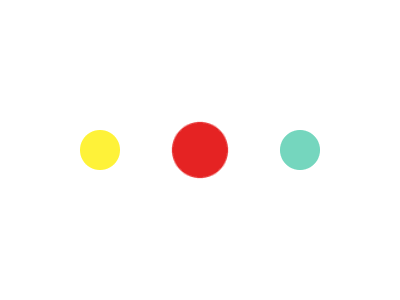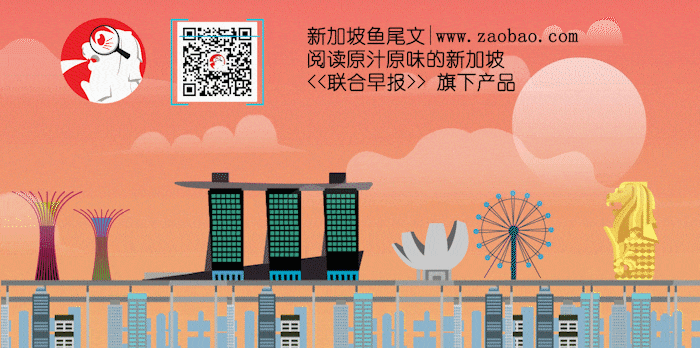今年的冠病疫情尚未緩解,諾貝爾獎領獎典禮以線上方式舉行。文學獎方面,諾獎評委會已將獲獎證書與獎牌寄給得主美國詩人露易絲·格麗克(Louise Gluck),格麗克也寫了一篇獲獎演說提交給評委會,諾貝爾獎網站于12月8日刊登格麗克的演說。《文藝城》的格麗克演說譯稿轉載自《新浪讀書》,由李琬翻譯,柳向陽、陳歡歡審校。
————
格麗克演說全文: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大概五六歲吧!我的腦子裏上演著一場競賽,一場能夠選出世界上最偉大詩作的比賽。有兩首詩進入決選名單: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小黑孩》(The Little Black Boy)和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斯旺尼河》(Swanee River)。
我祖母的屋子坐落于紐約長島南岸的西達赫斯特村,當時我就在屋子的次房裏來回踱步,像我習慣的,在腦中默默地背誦布萊克令人難忘的詩,同樣也在腦中默默地哼唱福斯特那首沉痛、淒涼的歌。
我爲什麽會讀布萊克還是個謎。我想在我父母家,除了常見的政治、曆史書和大量的小說,還有少量詩集。但我總是把布萊克和祖母家聯系起來。我的祖母不是個好讀書的女人,但她那兒有布萊克《天真與經驗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還有一本小書,彙編從莎士比亞戲劇中選出的歌詞——有不少我都能背誦。我格外喜歡《辛白林》(Cymbeline)中的歌,或許當時一個字也不懂,卻能清楚地聽到那語調、格律、铿锵的祈使句,這令一個膽怯恐懼的孩童格外興奮。“墓草長新,永留記憶。”我也希望如此。
被選中的聆聽者
這類爲了榮耀和至高獎賞而開展的比賽,對我來說是十分自然的;我啓蒙時期最早讀過的神話裏充滿這類比賽。即使在我很小的時候,在我看來,世上最偉大的詩就是高級榮譽中最高級的那種。這也是父母培育我和我妹妹的方式,我們要去拯救法國(聖女貞德),要去發現鐳元素(居裏夫人)。後來,我開始認識到這種等級制思維中的危險和局限性,但對于幼年的我來說,發獎這件事卻非常重要。會有一個人站在山巅,從很遠處就能看見,那是山上唯一引人注意的東西。站在下面一點點的人就看不見了。
或者,我說的人在這裏也可以換成詩。那時我非常確信,不知爲何,布萊克一定知道我腦子裏的這場比賽,而且對結果十分關心。我知道他已經死了,但我覺得他還活著,我能聽到他對我說話的聲音,被僞裝起來,但依然就是他的聲音。我感到他只在對我說話,或是專門對我說話。我感到自己被選中,非常幸運;我也感到,我格外渴望和布萊克說話,和莎士比亞一道,他已經成爲我交談的對象。
布萊克獲勝了。但後來我意識到那兩首詩多麽相似;那時和現在一樣,我都被出于哀傷或渴望的孤獨的人類聲音吸引。隨著長大,我不斷重讀一些詩人,在他們的詩中,我自己曾作爲被選中的聆聽者,扮演重要角色。親密的,誘惑的,往往是幽暗的、秘密的。不是那些站在露天競技場上的詩人。不是那些自說自話的人。
我喜歡這種協定,我喜歡這種感覺:一首詩說出的東西不僅必要,而且私密,它們是神父或心理醫生會聆聽的話語。
我祖母家的次房裏進行的授獎儀式,因其秘密性,仿佛就是一首詩創造的強大關聯感的延伸:一種延伸,而不是違背。
布萊克通過黑人小男孩對我說話;他是那個聲音的隱秘源頭。他隱而不見,正如黑人小男孩,在漠然、輕蔑的白人男孩那裏,也是看不見的,或者看不真切的。但我知道他說的是真的,在他暫時的、必死的身軀中,包含著他閃閃發光的純潔靈魂;我知道這一點,因爲黑人小孩所說的,他對體驗和經驗的描述,不帶有任何指責,也沒有想要複仇,只是傳遞著這樣的信念:在他死後將要去的完美世界,人們會按照他真正的本質認識他,他會帶著莫大的喜悅保護更脆弱的白人小孩,防止他被過多的陽光曬傷。
這個信念不是一種現實的期望,它忽略了現實,讓這首詩令人心碎,同時也爲它賦予深刻的政治性。黑人小男孩不允許自己體驗的傷害和正當的憤怒,他的母親希望爲他遮擋的傷害和憤怒,卻被讀者或聽者體驗了。即使那個讀者也還只是個孩子。
狄金森選中我
但公共的榮譽是另一回事。
那些我畢生都狂熱迷戀的詩,是我之前描述的,包含私人的選擇、密謀;包含讀者或聽者的重要貢獻,他們傾聽著詩中的一個秘密或一聲怒吼,而且有時也參與。“我是無名之輩”艾米麗·狄金森說,“你也是無名之輩嗎?/那我們就是一對了——別聲張……”或者艾略特:“那麽我們走吧,你我兩個人,/正當朝天空慢慢鋪展著黃昏,/好像病人麻醉在手術桌上……”艾略特不是在召集童子軍隊列,他在向讀者發言。與之相反的是莎士比亞的“我能否將你比作夏日”:莎士比亞並不是把我比作夏日。我在這首詩中,有幸偷聽了炫目的精妙樂音,但這首詩並不要求我在場。
在吸引我的藝術中,由集體發出的聲音或裁決是危險的。親密言詞的不確定性增強這種言詞的力量和讀者的力量,而正是讀者的存在,鼓勵著這種聲音表達急迫懇求或傾訴秘密。
當一個集體開始對這類詩人鼓掌、頒獎,而不是在放逐和無視他/她,這樣的詩人會遭遇什麽呢?要我說,這個詩人會覺得受到威脅和操控。
這是狄金森的主題。並非全是,但常常是。
我十幾歲時,讀艾米麗·狄金森最有熱情。通常是在深夜,在上床時間之後,在客廳沙發上。
我是無名之輩!你是誰?
你也是無名之輩嗎?
還有我當時讀的,至今更喜歡的那個版本寫著:
那我們就是一對了——別聲張!
他們會把我們趕走,你知道……
當我坐在沙發上,狄金森選中我或者認出我。我們惺惺相惜,在不可見處相互陪伴,這是僅有我們知曉的事實,我們的觀點在彼此那裏得到確證。在這世界上,我們是無名之輩。
不信任公共生活的性格
但對我們這樣生存的人,安居于原木下面自己的安全地帶的人來說,什麽會構成一種驅逐?驅逐就是當木頭被移開的時候。
在此我談論的不是艾米麗·狄金森對青春期少女的惡劣影響,而是一種性格,這種性格不信任公共生活,或者認爲公共生活領域就意味著概括會抹去精確,片面的真相會取代坦率的、充滿感性的揭露。舉個例子:假設這密謀者的聲音,狄金森的聲音,被特別法庭的聲音所取代。“我們是無名之輩,你是誰?”這種斷言一瞬間就變得險惡。
今年10月8日早上,我驚訝地感受到剛剛描述的這種驚慌。光線太明亮了。聲勢也太浩大了。
我們這些作家大概都渴望擁有許多讀者。然而,有些詩人不追求在空間上擁有衆多讀者,他們設想中的擁有衆多讀者,是時間意義上的,是漸次發生的,許多讀者在時間流逝中到來,在未來出現,但這些讀者總是以某種深刻的方式,單獨地到來,一個接一個地出現。
我相信,瑞典學院把這個獎頒給我,是想要獎勵那種親密的、私人的聲音,公開表達可能有時會增強、擴展這種聲音,但絕不會取代它。
我是無名之輩!你是誰?
——艾米麗·狄金森
我是無名之輩!你是誰?
你也是無名之輩嗎?
那我們就是一對了——別聲張!
他們會把我們趕走,你知道。
成爲有名人物,多麽可怕!
多麽乏味啊,像只青蛙,
整日把你的名字
向那仰慕你的泥沼念誦
一只愛生活、文藝範的小魚尾獅帶你了解新加坡原汁原味的風土人情領略小島深處那些鮮爲人知的文化魅力~ 新加坡《聯合早報》旗下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