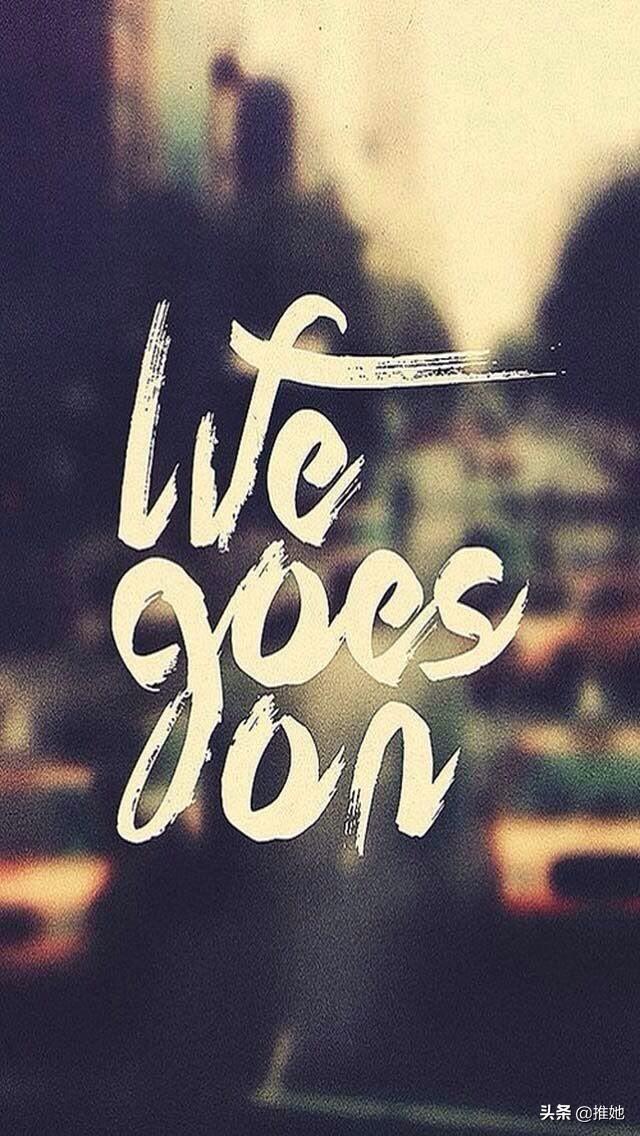我是黃泰勒,含著鑲滿鑽石的金鑰匙出生,今年23歲,坡縣最有錢的年輕富豪之一,卻有著一付悲催的命。
我的父親和母親大人,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所以,我成了百億家産的唯一繼承人。
故事要從我小時候講起。
女仆把我養大
我在英國倫敦著名的富人區——騎士橋長大,站在家中臥室的窗前,可以俯瞰海德公園。
騎士橋也就那麽回事兒吧,有不少頂級餐廳、奢華商場,房價嘛,買一套像點樣的公寓430萬美元(約2700萬元人民幣)。
我長大後,有了兩張美國運通百夫長卡。一張是老媽給的,說兒子你遇到緊急情況時用,另一張是老爸給的,給的時候什麽也沒交代。
無所謂了,小時候我也沒怎麽見過他們,身邊都是伺候我的人:女仆、管家、保姆,是他們把我撫養大的。
你們的童年是怎樣度過的?有小朋友和你們一起玩嗎?
我的童年生活在一個大大的房子裏,現在想想看,有點像個籠子,雖然是黃金的,可還是個籠子。
就是那種與世隔絕的感覺吧。
我每次被帶出去,都是乘坐豪車和私人飛機,我也沒怎麽玩過玩具,我爸爸收集古董汽車,我是在老爺車的陪伴下長大的。
家裏的廚子最喜歡用“和牛”做西餐,我嫌他做得不好,經常自己去餐廳吃,已經吃膩了。
記得有一次,我想吃冰激淩,但父親不讓我自己去買,他叫一個隨從去買給我,因爲安全第一。
我的司機接受過特殊訓練,萬一遇到綁匪什麽的,他能保我安全。不是說他的身手有多好,而是他能幫著我逃跑。
羨慕嗎?這太可怕了好不好,我甯肯自由自在的生活。
上學時,我交了一些朋友,父親馬上啓動了一個預案——對我的朋友及他們家人進行背景調查。
這些無時無刻地都在提醒著我,我是多麽的與衆不同。
三逗號俱樂部
當十幾歲的你們還在努力讀書,或者懵懂在花季時,那年15歲的我,正陪伴在父親身邊,看著他收購一家英國足球俱樂部。
如果父親和母親願意的話,他們可以在世界各大城市,擲骰子購買房産。
錢對于我家來說,只是數字,可以轉換成各種資産罷了。
就說我那兩張百夫長卡吧,這絕對是一種特權,但是,將一張沒有限額、無限透支的卡片,交到青少年手中,是個好主意嗎?
我對錢沒有概念,因爲要什麽有什麽,真希望我不是帶著這些卡片長大的,那樣我就能夠明白,錢的真正意義,和人生其他的一些東西。
16歲時,有一天早上,宿醉不醒,手機響了,我掙紮地爬起來,是父親打來的電話。他說,兒子,周末在做什麽,花什麽錢了。我當時腦子一片混沌,記不太清楚了。
然後我突然發現,自己在一艘豪華遊艇裏,原來我前一天晚上,在曼谷租了一艘遊艇。
我還記得父親在電話那頭開心的笑聲,現在回憶起這件事,我毫無滿足感,反而感覺羞愧。
你們可能會認爲,買東西時要是不用看價簽該多好,但對于一個孩子來說,這很可怕。
從小我就注意到自己的家有很多監控探頭,周圍有很多保镖。我的父母不喜歡引起注意,但他們總有一種危險感。
像我這樣的年紀,成爲“三逗號俱樂部”的一員是非常罕見的。
普及一下:三個逗號表示 10 億美元,在顯示金額時,1,000,000,000 美元需要用 3 個逗號間隔。加入三逗號俱樂部意味著成爲億萬富翁。
想過如果你一年掙10萬美元(約65萬元人民幣),需要多久能成爲一個億萬富翁嗎?
一萬年!
我經常需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當全世界有這麽多人在爲生存而掙紮,爲了擺脫貧困而陷于絕望時,我擁有這麽多錢是否合乎道德?
這個問題我考慮過,擁有巨大財富的人,有義務爲社會、爲那些需要的人提供更多幫助,這也是一種巨大的壓力,說的好聽一點,社會責任感,或者,共同富裕。
畢竟,這不是我的錢,而是我父母的錢。
人們說我太幸運了,一下子繼承幾十億美元(幾百億人民幣),擁有了別人幾輩子掙不來的錢。
你們說得沒錯,我擁有大多數人夢寐以求的生活。
這種生活聽起來像是一場夢,我總感覺自己是在夢遊。的確,財富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但卻無法解決我的問題。
那些繼承巨額財産的人通常會不知所措,他們得到了幾乎每個人都想要的,內心卻會感到內疚,甚至有的人會産生罪惡感。
他們會想,“爲什麽是我?”那一瞬間,一大堆錢就像一堆磚頭一樣,毫無意義。
上了世界上最昂貴的學校又怎樣?
上學的時候,母親主要通過我的學業成績,來衡量我的人生價值。
由于擔心我在學習上三心二意,她想出了個方法,可能只有我們這種富豪家庭的媽媽,才想得出來的方法。
她把我送到精神科醫生那裏,讓醫生測試我的精神有沒有問題。
結果很喜人,我被診斷出患有抑郁症、孤獨症和自閉症,那年我才十幾歲。
但母親絲毫沒有被嚇到,她認爲,兒子有孤獨症是他“有天賦”的表現,抑郁症正好解釋了兒子“懶惰又難相處”。
在我被確診三大“精神疾病”之後,母親把我從倫敦送到瑞士的羅西學院,這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寄宿學校。我上學的時候,每年的學費是11萬3千美元。
每年1月到3月,學校會將學生安置在格斯塔德雪山上,一個特殊的冬季校園,學生每周上四次滑雪課。
羅西學院有大型音樂廳、航海中心和馬廄。一個班不到十個孩子,大一點的學生會被安排品酒課程。
每天晚上,羅西的學生都會坐在貼有個人餐巾紙的座位上,由學院廚師把晚餐送到每個人面前。
盡管上了最昂貴的學校,我還是未能達到父母的期望值,于是我再次被轉校。我回到了新加坡,就讀于英華自主中學,這是新加坡富家子弟紮堆的學校。
由于父母動用了關系,我不用參加入學考試。我上著全世界最好的學校,可是我的精神狀態卻沒有改善的迹象。
我總是感到自己讓父母失望,我的抑郁症愈發嚴重。
在我們這個圈子裏,抑郁症已經不是秘密,許多富裕家庭的孩子都有某種程度的抑郁,我們的父母也一樣,但很多人會隱瞞。
哪個父母會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精神疾病的記錄?以後想參政怎麽辦?
在富人圈,這是一種整體的羞恥感,可是我不這麽想,至少我敢于面對自己,這再好不過了。
在英華學校,“我們努力學習,我們盡情玩樂”成了一句口頭禅。一瓶瓶唐培裏侬香槟王被偷偷帶進宿舍,司機則被我們派去購物。
今天你過生日,明天他過生日,派對成爲了生活的一部分,日子過得雜亂無章。
我的許多同學會站在大廳裏,看著那些授予他們父親、祖父和曾祖父的牌匾和獎勵。這些男孩兒生來就是家族繼承人,他們只能沿著父母設定好的路,學習生活。
我家被詛咒了
當我完成學業後,開始在新加坡軍隊服兵役,這讓我的抑郁症有所好轉。然而,19歲時,醫生在我的腦子裏發現了腦腫瘤,我只能退役。
當所有人以一種異樣的眼光,看著我走出軍營的大門時,他們都認爲,我是靠著家人的關系,得以逃避服兵役。
我只能默默地接受這一切,因爲我不想告訴任何人我長了腦腫瘤。
經過治療,我出院了,我開始在建築業施展手腳,這是我喜歡的領域。我的身心健康再次向著好的方向發展。
但接二連三的厄運開始降臨到我的家庭。
先是在2017年,我的弟弟在一場車禍中喪生。
接著是我的母親,那麽堅強的母親,2020年癌症把她帶走了。
而我的無所不能的父親,在今年2月的一場車禍中喪生。
我家一定是被詛咒了,我們究竟做了什麽?財富的詛咒嗎?
我痛苦萬分,抑郁症嚴重到想自殺。我無法工作,無法生活,最熱愛的建築業我也放棄了。
我的日常活動每天都差不多,當我醒來時,喜歡離開家去外面,街上的喧囂、熙來攘往的人群,會驅散我黑暗的思緒。
我喜歡去屋頂酒吧,我坐在那裏,帶著筆記本電腦,生活和笑聲環繞著我,只有這時我才不會感到孤獨。
那麽有錢,爲什麽痛苦?
一天傍晚,我坐在酒吧給朋友打電話,桌子上是牡蛎、扇貝、香槟酒瓶和一盤薄薄的牛肉片,這盤牛肉片擺放地如此精心,就像是餐桌上的裝飾品。
就在我們通話的時候,太陽正在新加坡的上空落下,在我看來,這是度過一個夜晚的最佳方式。
孤獨可以籠罩財富,金錢就像火箭助推器,把我的病情推到了雲巅。我得到了億萬家産,我也失去了一切。
我的朋友們無法理解我,一個每周花幾千美元買衣服的人怎麽會痛苦呢?
我喜歡擁有美好的東西,但紀梵希的襯衫帶不來任何意義。
一想到父母,我經常會下意識地抽搐。如果我每天面對他們的死亡,我會崩潰。我給了自己一個心理暗示,假裝我的父母在度假。
說實話,我和他們不親,我經常把母親稱爲“虎媽”,把父親稱爲“支票父親”。
我的生活被奢華包裹著,但我真正想要的是父母的擁抱,一種傳遞愛和親情的東西,這讓我心碎。
對我來說,時間比勞力士值錢。我努力敞開心扉,分享自己的真實感受。
母親在世時曾說,抑郁症代表了我的弱點,一個應該用盔甲覆蓋的弱點。
我一直帶著一堵牆,面對周邊的人,隱藏我的情緒。多年來,我已經習慣帶著這道牆,當父親去世時,整個牆塌了。
下一個被詛咒的人是我自己,我的癌症已經到了晚期,我仍在接受治療,但腦子裏的腫瘤是一顆定時炸彈,我不知道自己能撐到什麽時候。
也不知道,這篇文章,是否是我留給這個世界最後的話。
在這個世界上,我是一個人——我一直都是這樣。
我想說,以一個人擁有多少錢,來衡量他的價值和幸福感是不對的。從小我就擁有整個世界,23歲便成爲幾十億美元家産的繼承人。
但是我沒有得到父母陪伴的愛,沒有與其他孩子共同成長的快樂,孤獨是我最好的朋友,幸福是可望不可及的遙遠。
當我泰勒·黃寫完這篇文字的時候,希望你們可以體會到生命的可貴,體味到家庭的溫暖,體味到父母的愛。
要記得,金錢能讓你買到一條最好的狗,但是只有愛才能讓它搖尾巴。
“推她”以專注的態度,聚焦海外名人故事、明星八卦,國際風雲。閑暇閱讀之余,還能學習時尚、曆史、文化的知識,喜歡就關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