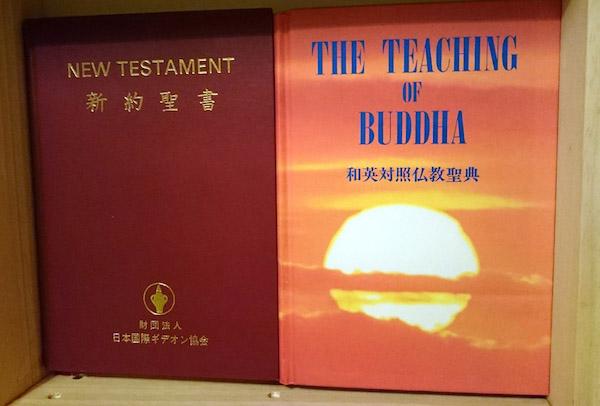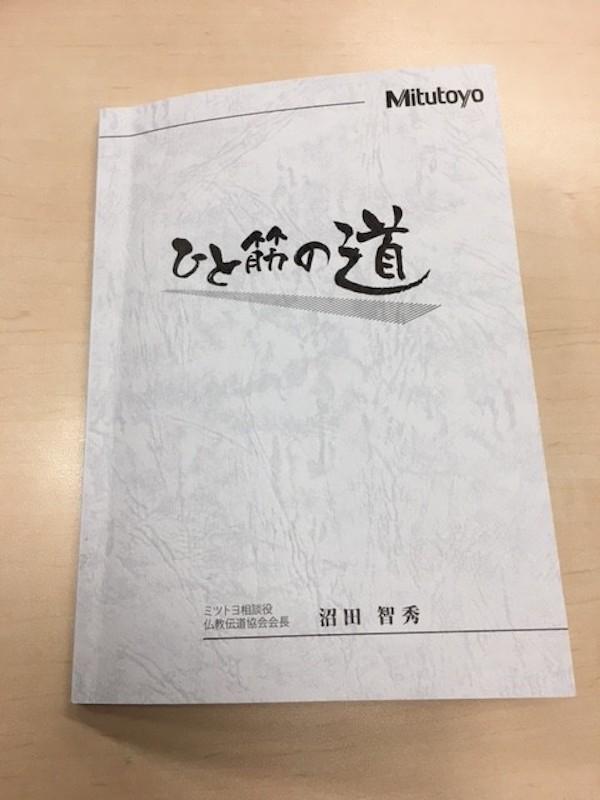2006年10月9日,朝鮮進行了史上首次核試驗。這對日本來說無異于又一顆原子彈發射升空,不同的只是未知何時可能掉落何處。三天後的10月12日,一名“右翼分子”開著自己的“馬路宣傳車”一頭撞進了位于東京近郊川崎市的三豐股份公司(株式會社ミツトヨ,Mitutoyo)的大門,抗議該公司向朝鮮出口了可轉用于核開發的“三次元測定器”(三坐標測量機)——當年8月末,日本政府以三豐股份公司違反“外彙交易及外國貿易法”爲由,逮捕了包括當時的公司總裁在內的四名高管,並暫停公司進行任何出口業務。
2012年4月底,當我坐在日本佛教傳道協會(BDK)總部的會客室,聽會長沼田智秀(1932-2017,Numata Toshihide)先生略顯沉重地談及上述往事:“……只有謝罪和反省,2010年7月2日行政制裁期滿後,總公司和各分社都設立了誓言碑以杜絕類似事件再發生……現在公司恢複得不錯,佛教傳道協會也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又可以很好地支持全球的佛教學術研究了!”竟一時無法想象佛教研究會與朝鮮“核問題”直接挂鈎!
沼田智秀
我只見過沼田智秀先生這一次,三十分鍾左右。寫一篇紀念文章似有攀附之嫌,好在沼田先生對中國來說並不是家喻戶曉的名人。
沼田智秀是三豐股份公司的創始人沼田惠範(1897-1994,Numata Eihan)的長子,曾任公司總裁、董事會主席以及日本佛教傳道協會會長。2012年,在該協會獎學金(BDK Fellowship)的資助下,我獲得了赴東京大學從事爲期一年的訪問研究的機會。出于對無償資助的感恩之心,到東京後我就聯系了負責獎學金事務的江口女士,表示想去協會總部拜訪致謝,沒想到江口女士當天回郵件說,“沼田會長很想見一下第一位來表謝意的中國學者”。于是,一個星期後,我在位于東京都港區的協會總部見到了沼田智秀先生,聽到了與朝鮮“核問題”有關的“不正輸出”(違法出口)的故事。如今,除此以外的會談內容大都已模糊,但古稀之年的沼田先生繼承家族誓言大願,立志以實業傳道、以學術弘法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令我終身難忘。
沼田惠範
“三豐”與“三菱”、“豐田”兩大路人皆知的日企毫無關系,與武當派道人、太極拳宗師“張三豐”更無因緣,而是取義自“天時、地利、人和”與“智慧、慈悲、勇氣”是實現“事業繁榮、人格養成、世界和平”之“豐收”的關鍵因素這一理念,是一家致力于“技術的開發和人心的開發”、專注于制造精密量儀的科技制造類企業。三豐公司生産的千分尺(螺旋測微器)、顯微鏡等精密量儀,在日本長期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場份額;但因與民衆的日常生活無關,故並不是可以在地鐵街頭見到其廣告的公衆企業。然而,正是這家規模並不大、低調務實的家族企業,自創立起,始終堅持以營業額的百分之一用于“佛教傳道”事業,以獨家之力促成了半個世紀以來(日本)佛教在世界各國的傳播與研究之盛勢。沼田家族兩代人的精進與守持,實現了幾乎所有中國近現代佛教大士都曾發願卻始終無法得償的理想——興實業以傳道、資學術以弘法。
1897年,沼田惠範出生在廣島縣淨蓮寺,是屬于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的僧侶人家。同年,正好最早在歐美宣揚禅法(Zen)的臨濟宗僧釋宗演(1859-1919)派遣其著名弟子鈴木大拙(1870-1966)遠赴美國弘法。而十九年後(1916年),比鈴木大拙小二十七歲的沼田惠範獲得了大本山西本願寺的派遣,作爲“開教使輔”赴美布教。
經過十七天的太平洋航行,十九歲的惠範達到洛杉矶,作爲“生徒”寄住在好萊塢附近的一戶美國人家庭,每天早晨上學前和傍晚放學後都要做飯洗碗,周末兩天也排滿了家務活,以賺取一個星期兩美元的薪水來維持在好萊塢高中的學習。生活的貧困、勞作的繁重再加上學業的緊張,兩年後,惠範患上了結核病。這在無藥可治的年代,相當于被醫生宣告了死亡。
“無錢回國,在無親無故的異鄉,過著牛馬般的生活,連死了都不知道會被扔到哪裏……”惠範後來在回憶文章裏寫到,“救我于悲苦的瀕死之境的是從小聽聞的親鸾聖人的話,‘一人居有喜,當作二人想;二人居有喜,當作三人想;那一人便是親鸾。’”
在淨土真宗初祖親鸾的“陪伴”下,惠範用母親所贈之真宗聖典、念珠以及父親所書“南無阿彌陀佛”名號,把居住的黑暗潮濕的地下室布置成了佛堂,開始每日做“功課”(日課,淨土真宗的念佛儀軌),以此爲精神支柱與心靈慰藉。“不可思議的是,身體慢慢恢複了健康。”
完成高中學業後,惠範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數學。四年本科畢業,考入了研究生院學習統計經濟學。比原定的十年早一年完成了留美學習計劃。
在加州求學時,惠範經常感到美國人強烈的“排日”情緒,被同學叫“Jap”而受欺淩。惠範認爲,只有佛法可以改變美國人的這種心性。1925年,在加州日裔和親日美國人的資金支持下,惠範創辦了面向美國人傳播佛教的英文雙月刊《太平洋世界》(The Pacific World),表面上是介紹茶道、劍道等東方文化,實際則是宣揚佛教思想。每刊印刷約四千部,免費寄贈給美國各大學及其圖書館。
然而,雜志發行不到兩年就出現了資金困難。惠範趁回國探親之際,向西本願寺以及被稱爲“日本資本主義之父”、創設理化學研究所的澀澤榮一(1840-1931)求助。獲資後又支撐了兩年,終于1929年不得不停刊。從二十九歲起就全身心地投入這項弘法事業,僅四年即夭折無果,彼時三十三歲的惠範似有頓悟——“無論多麽高尚的事業,在經濟社會沒有錢就是不行的!爲了實現佛教傳道的使命必須要賺錢!”這句話後來成了三豐企業與沼田家族的“初心”(日文“不忘初心”一語——初心忘るべからず——出自室町時代早期的能劇大師世阿彌的《花鏡》一書。“初心者”即“新手”,這句話最初的意思是“不要忘記自己還是初學者時的謙虛、緊張的心”,即不忘最初的難堪困苦,才能不斷精進自己的技能。後世逐漸多用來表達“不忘最初之志”的意思,常與表驕傲自滿的“慢心”相對。)
1930年,三十三歲的沼田惠範回到日本,以伯克利大學經濟學碩士的學曆在內閣資源局謀得了統計官的職位。戰亂年代,中央政府公務員的收入雖足以保全家衣食有靠,但存不下一文錢,更談不上賺大錢來實現“佛教傳道”的使命。正如日本諺語所說的“蟹隨身掘洞”,惠範認爲應該根據自己的身份和力量來行事,于是,在將近不惑之年,考察了日本國內外的經濟狀況與産業結構後,不顧周圍所有人的反對,辭去了高級公務員的“鐵飯碗”,選擇以實現千分尺的國産化爲切入點,“下海”做實業,在東京武藏新田創建了一個研究實驗室。
問題是,惠範本人乃經濟學出身,根本不懂千分尺這種當時屬于被美國壟斷核心專利的高科技。他的辦法是自己借錢貸款,然後雇傭技術人員來做研發。1937年,惠範的千分尺實驗成功,而當時的海軍拿著國家經費都未能研制出來。雖然日本市場充斥著美國進口的名牌,但“國産化”確爲惠範攢下了實現初心所需的第一桶金。1944年,在栃木縣宇都宮市開設了新工廠,後來成爲三豐公司的主要基地。
三豐公司生産的千分尺
對沼田惠範來說,精密量儀的研發與生産經營只不過是他要貫徹初志的手段,並不是目的。所以,1965年,當企業形成穩定的收益鏈時,以佛教傳道爲使命的惠範設立了“日本佛教傳道協會”,發願用所賺取的錢財(淨財)把包括普及佛教典籍、繪畫、音樂等在內的所有傳道事業組織化、體系化,向全世界傳播。此舉得到了當時諸多學界巨擘與教界長老的支持,如中村元(東京大學教授)、松本德明(大正大學理事長)、來馬道斷(曹洞宗宗務總長)等都出任協會成立的發起人。
日本佛教傳道協會成立之初的主要活動是普及《佛教聖典》。所謂《佛教聖典》,其實是一本選取佛教的主要教義編集而成的簡單易懂的精要書,而不是很多經典的集成,出版發行後無償贈送給任何想要了解佛教的人。最初是基于木津無庵爲代表編纂的、由新譯佛教聖典普及會于1925年出版的《新譯佛教聖典》,由山邊習學、赤沼智善爲主導,邀約諸多佛教界人士參與監制、編輯,耗時五年完成出版。後來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斷增減修訂,最新版由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前田專學任編集委員長。至今,《佛教聖典》已翻譯成了四十六種語言,並有點字版(盲文)和手語版DVD,寄送至六十二個國家和地區,共計九百萬冊。特別是無償寄贈旅館酒店和醫院,常與基督教的《聖經》一起並列在床頭,開啓了佛教主動傳道的一種新方式。
日本酒店常見《佛教聖典》與《新約聖經》並列擺放在抽屜
隨著三豐公司的精密量儀在全球各國的銷售,《佛教聖典》也被“三豐人”帶到了世界各地。如,1978年,設立了(加州)美國佛教傳道協會、夏威夷佛教傳道協會;1980年,在巴西設立了南美佛教傳道協會。實業與傳道,于沼田惠範來說是“一車兩輪”之相互協作、共進互贏的關系。
沼田智秀則出生在三豐制作所創立前兩年。從小便有“子承父業”想法的智秀原本打算學習經濟學,以便將來成爲一名出色的企業家;但在嚴父“去學佛教”的命令下,進入了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系佛教學專業,主要指導教授是設立日本道教學會的道教權威、後任大正大學校長的漢學家福井康順(1898-1991)先生。
大學畢業後即進入三豐公司,從一線車間技術員到總裁,把企業做大做強,智秀顯然是一位極智慧優秀的實業家。“別人也可以把公司做好,但佛教傳道事業非血親之子不可。”1985年,沼田智秀接替父親出任日本佛教傳道協會會長,在繼續普及《佛教聖典》的同時,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舉措加強在全球的傳道事業,如設立外國人獎學金制度和專項研究資助制度,先後在墨西哥、加拿大、英國、新加坡、德國、中國台灣等地設立了佛教傳道協會的海外分支機構。從沼田惠範曾經留學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設立“沼田佛教講席”(教授職位)開始,至今已在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英國牛津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德國漢堡大學等十五所世界名校開設了長期或短期的“沼田佛教講席”,通過支持學術研究及其傳播來弘揚佛教思想文化。
沼田智秀先生在佛教傳道協會成立五十周年紀念式致辭
六十五歲時,沼田智秀在淨土真宗西本願寺“得度”爲僧,法名“釋智秀”。在日本,取得僧籍需要通過嚴格的考試,因此“得度”前,智秀在位于京都的本願寺西山別院進行了爲期十一天的“習禮”。至于“出家”的原因,他在自傳《一筋之道》(非賣品)中說:“妻子、父親、繼母在三年內相繼去世,愛別離的精神傷痛是巨大的,支撐自己的只有從小親近的佛教,即使六十五歲開始學佛也不晚。”另外一個理由是,作爲日本最重要的“無宗派”佛教組織的掌門人,經常有機會與佛教界的高僧大德接觸,秀智總是慚愧于自己非僧侶(無僧籍)的身份。
沼田智秀先生的自傳《一筋之道》(非賣品)
2017年3月,我在北印度旅行時,收到了日本佛教傳道協會與三豐股份公司聯合發出的訃告:會長、前董事長沼田智秀先生于2月16日安詳往生,已舉行了唯有近親參加的“通夜”與“密葬”,將于3月30日在東京築地本願寺舉行“本葬”。因爲曾受過佛教傳道協會的獎學金之恩、與沼田智秀先生有一面識之緣,更因爲先生曾希望“有朝一日在中國發展佛教傳道事業”之未竟成(日本佛教傳道協會曾在1982年授予趙樸初居士“傳道功勞獎”,1986年授予隆蓮法師“傳道文化獎”),從那爛陀轉道蒲甘、曼谷,赴東京參加葬禮,既是最後的告別,亦見證沼田家族行“實業”與“傳道”之兩輪的承續,以及初志貫徹生命始終的“一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