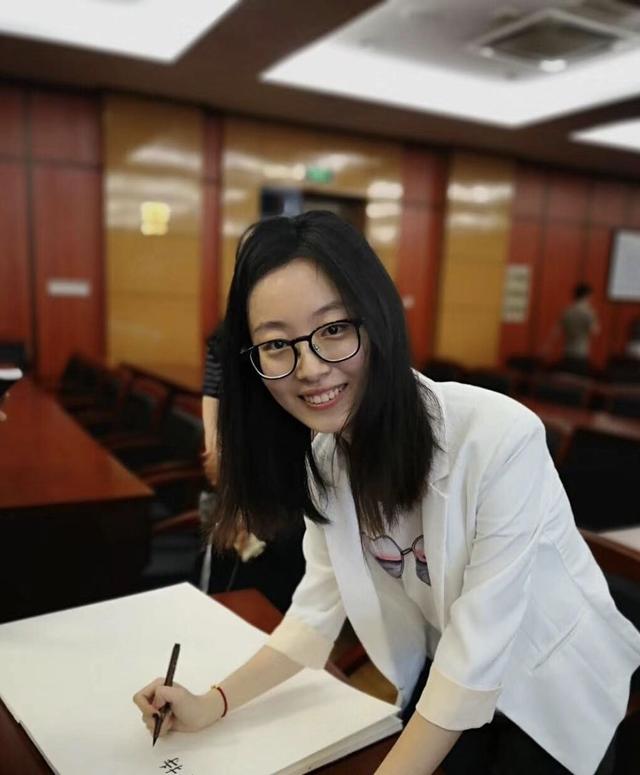王海納,2013年留學于新加坡國立大學,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王潔供圖
炭原美玲和我是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化學系的同屆同學,我們一起選了計算化學課。很慚愧,像我的很多朋友一樣,我忘了究竟是怎麽認識她的。在我現存的記憶裏,我們只是第一天上課正好坐在機房相鄰的位置,于是就像已經認識多年的老鐵兒一樣自然而然地聊起來了。
我甚至不記得我們有過自我介紹。選修同學名單上只有一個日本名字,她又是教室裏唯一一個穿著寬松飄逸的和風長裙的同學,所以人和名字也就自然而然地對上了。
這門計算化學是招牌難課,因此只有十幾個同學選修,大家很快能混熟。混熟了以後大家就開始閑聊,問起美玲姓名的含義。聽了她的解釋,我們很好奇這姓氏爲何帶一個化學元素。
“碳原……爲什麽不是硅原、硼原?”
“你是因爲你的名字才選了化學專業啊?”
“哈哈哈!”她笑道,眼睛彎成很可愛的曲線,口音已經是純正的新加坡英語。“總有人問我這個!我也不知道耶。可能我的祖先是煤礦工人?煤老板?鑽石老板?我真的不知道啊哈哈哈!”
“碳是生命元素,美玲無敵!”我說。
不過美玲在這個小班真正引人注目的原因是這樣的。
班上還有個同學叫蘇乙。他身高兩米,頭發稀疏,每次都穿同一件文化衫來上課,一看便知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天才。他確實思維敏捷,學習刻苦,攻讀化學和計算機雙學位,來到這個課堂可謂如魚得水,可唯一的問題就是太話唠了。每堂課的討論環節,蘇乙都和教授們沒完沒了地爭論問題,導致課堂氣氛不佳,教授們爲了和他爭論,根本沒時間顧及其他同學。我有時候氣得不行,就提醒他兩句:“大家明明一起上課,怎麽就變成聽你蘇乙專場了?”
我們發現全班好像只有美玲從來不生氣,總是嘻嘻哈哈地在課堂討論中接蘇乙的話。比如有時候蘇乙連飙一串計算機科學中的算法術語,美玲就很感興趣地問:“哇!太厲害了吧!你是在哪兒學的算法?”
我們一開始猜測他們是不是互有好感,不過很快就統一認定,是美玲太善良了。
後來臨近期中一節課上,蘇乙突然發現和我爭論問題也是一樣的,于是美玲、蘇乙和我就成了教室最嘈雜的角落。但是這樣很好:課堂討論的時候,教授們終于可以照顧到其他組了。
我們三個同學像國大所有的互幫互助小組一樣,一起約自習、交流思路、交換課題報告。實在忙起來了也會一人做三分之一的作業,然後來個“互相參考”。
美玲和我也漸漸地像新加坡所有好朋友一樣,吃遍了我們能想到的所有飯店,喝遍了我們覺得有趣的所有咖啡館(特別是養了貓的咖啡館)。有一次喝著咖啡的時候,我說我很羨慕她爽朗大方的性格:“我呢,整天想問題,有時候想得太多,擔心太多,會被誤認爲是悲觀啊,多愁善感啊,不自信啊什麽的。”
“哈哈哈哈,你這是科學家性格啊。”美玲大笑道,“你該爲自己驕傲!”
“原來如此,哈哈哈哈。”我說。
後來我發現,美玲其實也有難得不笑的時候。
那是我們參加一個化學系活動後的自助餐,我不記得之前聊了什麽,只記得一位師兄突然感慨道:“女生到後來在科研上可能就趕不上男生啦。你看這幾年諾貝爾化學獎,都是大叔嘛。”
我甚至還沒來得及感到什麽情緒,就見美玲很嚴肅地擡起頭看著師兄說:“你這是歧視啊師兄。女生當然可以得諾獎——我相信 Nora 就可以。”
大家瞬間紛紛鼓掌,爲美玲豎起大拇指,並紛紛責怪師兄說話不注意。
“就是,Nora 當然能得諾獎!”
師兄紅著臉拍著腦袋頻頻道歉:“對哦對哦,我咋就忘了時代變了呢!”
我突然被大家公認要得諾獎,自知遠沒有這個水平,因此有點尴尬,但同時無限地感激美玲。師兄這類話我平時也聽得挺多,好像已經麻木——已經失去對抗的積極性了。那天以鬥士形象出現的美玲,可能讓我永遠無法忘記。
我一直以爲日本有著很嚴重的男尊女卑思想,因此並沒想到日本也有如此進步的女生。這大概是上大學最重要的意義之一:消滅偏見,刪減標簽,從個體的角度了解每一個人。
國大的老師們常說的上大學的另一個意義是體驗文化的融合與貫通。而如此抽象的概念,同樣也是因爲美玲,才變成實在的東西,在心中落地生根。
那天我們聊起日本和中國的詩歌。我背了我知道的唯一一首俳句。
“我知這世界本如白露般短暫,然而,然而 ”
“我們日本也背唐詩。”美玲說,“李白的、杜甫的。”
我吃了一驚。
“是的,我們高中要學中國的古詩詞,因爲俳句受到過它們的影響。我們老師說,要理解俳句,先要理解唐詩。”
“用日語背?”
“用日語,但日語的唐詩裏面有很多漢字了——我記得有一首詩,講的是李白坐船,在一條河上要出發……”
“是說……一個叫汪倫的朋友送別他嗎?”
“一點兒沒錯!”美玲猛地一拍手,激動地說。
那時我們是在新加坡河畔的維多利亞廣場,河上有五彩斑斓的遊船。
我覺得那是生命中最詩意的瞬間之一,幾乎觸發了所有直覺中的感動,而它的意義則要過後用很長時間才能解讀。
我意識到唯有文化能真正地超越時空;我意識到偉大的作品終將比國家之間的分歧活得長久;我意識到即使在這陌生的土地,孩提時代背的那些詩依然有意義。今後回憶起這個片段,我可能會意識到更多東西。
即將進入大四的時候,我們都要選畢業課題,選計算化學的只有美玲、蘇乙和我。我很開心地想到我們還有一年時間吃喝玩樂,然後,不出意外的話,都有光明的前程。
然而,然而。
一天晚上我突然收到美玲的信息:Nora,特別抱歉,我說過要和你們一起做畢業設計,一起畢業的,但是我的奶奶被診斷出了阿茨海默症,我決定回日本陪奶奶,在那裏工作,不拿榮譽學位畢業了。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是——歡迎你們以後來日本玩呀!
我很震驚,第一反應居然是想勸她留下。
然後才慢慢說服自己,挽留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的。
和美玲的最後一次約飯沒有踏歌聲,美玲還是一如既往地哈哈大笑,並打電話和另一群朋友約晚上的另一個聚餐。我的腦海則間斷性地閃過“白露般短暫”那樣的詩句,我想到夢想和雄心的脆弱,想到自己的幸運——今我何功德,尚沒有被命運突然改變人生軌迹,仍然可以整天自由自在地想我的分子模型。
美玲回日本以後,我又和不同的人因爲不同的事去過維多利亞廣場。有時候我希望這個城市國家能夠慢下來,不要總是讓我們看到美好的東西,然後又莫名其妙地讓他們離開——不過,也許應該是上帝需要慢下來。
但這恐怕又是我的多愁善感了,況且我不該總是將自己的願望強加于他人。
我覺得美玲,以她的善良、開朗和勇敢,自能創造她美麗的世界。
來源:嘉興在線
申明: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