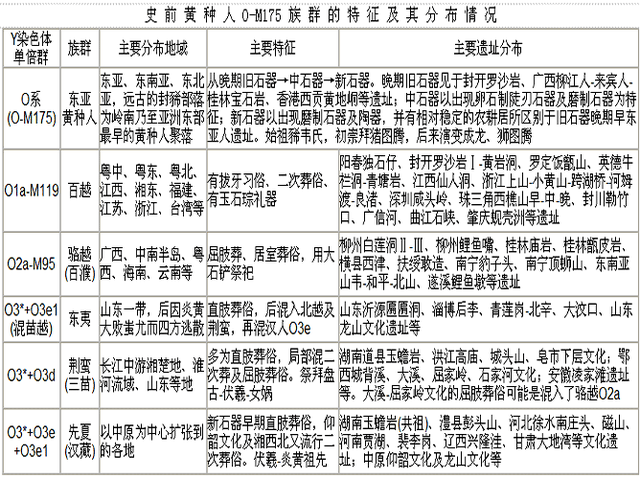一、嶺南的瓯越源流
因古越人缺乏文字,對嶺南瓯越的記載是在漢人到來之後並以漢人的眼光開始的,之前上萬年的情況只能根據古人類活動遺存進行推測。封開的古人類活動遺迹最早、最多,延續性最好,封開是嶺南土著文化最早、最重要的發源地。封開曾和廣西梧州合稱爲廣信。
曾居封開的原始氏族部落-“封豨”,以豬爲圖騰。賀江古稱封溪、封水,郁水(廣義的郁水包括西江)一稱“豚水”(郁水之南稱郁南)。“狌狌”,在舜葬西,封豨之西有桂林八樹。南朝宋元嘉29年(452)曾于今封開的北部置有狌狌縣,此爲佐證。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滅吳,嶺南四國歸越,幹國改名幹越,禽人中的番禺改名百越(廣州、清遠、佛山、中山、珠海、深圳、香港、東莞),雕題與黑齒改名臨越(湛江、茂名、陽江以及雲浮、江門的一部分等);但漚深與倉吾卻一直未被吳、越所占。西瓯是以封豨的原始人群爲中心,融合其周邊的蒼兕、桂國、漚深、黑齒、雕題等形成的嶺南最早、最大的母系氏族部落聯盟。西瓯、駱、番禺三大古文化後來則成爲廣府文化的載體。
公元前257年,被秦滅國的蜀王制(原居四川)輾轉遷到此地,征服雒將,立駱國,其子蜀泮,稱安陽王;其後,安陽王吞並的地盤相當于秦朝的象郡範圍。秦亡,趙佗立南越國;安陽王攻占桂林郡封溪並以其地爲首府;趙佗聯西瓯滅駱國立蒼梧國,蒼梧王趙氏,桂林郡監佐之。西漢末,西瓯、雕題、駱諸部族的遺民大量融合到漢族中,未融合部分東漢時造反。西瓯遺民變爲烏浒蠻(蒼梧蠻),雕題遺民變爲鲛人,駱國遺民則稱蠻裏、俚子。自公元前323年立西瓯至前111年趙光降漢,其間共212年,當中屬楚101年,禦秦抗秦8年,屬秦4年,被瓯駱占封溪3年,立蒼梧國96年。
古越人常以所在地的“田、地”作地名,從而形成相應的地名群。表示“田、地”的讀音,西瓯人念“羅”,而駱越念“那”。因此,古越人留下叫“羅*”的地方曾爲西瓯居住地,而叫“那*”的地方曾爲駱越居住地。羅*地名的主要分布,從廣東東部而西,經肇慶地區達廣西的來賓、上林、邕甯。在廣東寶安、東莞、花都、南海、三水、高明、高要、雲浮、德慶、廣甯、陽山和廣西的蒼梧、平南、賀縣、平樂、柳城一線以北無那*地名;在廣西的武鳴、扶綏、上思、淩雲一線以西和廣東徐聞等地無羅*地名;兩者之間雜居區兩種地名均有。
以上兩段的內容摘編自譚元亨主編的《封開-廣信,嶺南文化古都論》一書。
①廣東漢族除三大民系外,尚有人口不多的其他民系和身分不明的群體,如陸豐、惠東一帶操軍話的和粵北韶關等地操系屬未定的韶州土話的群體等,兩者合計人口不足100萬。參見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又據《廣東年鑒·1998》(廣東年鑒社1998年版),至1997年末,廣東省總人口爲7051.15萬,其中少數民族86.7萬,其余爲漢族。漢族中廣府人3800萬,潮汕人1600萬,客家人1400萬,三民系占漢族總人口的97.64%。
②這裏的土著是指從新石器時代起就一直生活在當地的原住居民及其後裔。
一、廣東三大民系的出現及其發展
(一)廣府民系的出現及其發展
廣府民系的先民是由粵地土著南越和西瓯即百越的部分族人融合于漢族而出現的。其發展,經曆六朝至唐初和兩宋等兩個階段。
廣東自古爲百越聚居之地,已爲考古學、語言學、地名學等資料和文獻記載所證實。學術界也已有共識。至秦漢,他們創造出以種稻和制造並使用有肩石器、扇形青銅钺、幾何印紋陶和舟楫,以及鑿齒、斷發文身、雞蔔等爲主要特征的百越文化。秦代前後,廣東百越各支的分布大致是:南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爲西瓯所居,粵東潮、梅地區是閩越的世居地,而粵西高、雷一帶則爲駱越地。
中原華夏族(漢代之後稱漢族)入粵約始于西周中期。在粵東浮濱文化遺址,不僅出土了分別與河南商代中期和鄭州二裏岡文化相似的平內長援石戈和大口尊,而且發現了三座行中原葬俗二層台的墓葬,①從而大體上確定中原人入粵的上限。②其後,南來的中原人不斷增多。他們帶來了先進的生産工具、生産技術、生活用器以及中原的語言和禮俗。
秦始皇爲平嶺南,“使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守五嶺,與西瓯戰。③這些軍士除戰死外,全部留戍嶺南。統一嶺南後,秦推行“移民實邊”政策,先後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和三十四年(前213)兩次將“嘗逋亡人、贅婿、賈人”和“治獄吏不直者”強徙嶺南,④“與越雜處”。其後,其又應帶兵官趙佗之請,將15,000名“無夫家”之女子徙至嶺南,“以爲士卒衣補(妻子)”。⑤秦末,南海尉任囂臨終前跟趙佗分析形勢時,有“南海僻遠,東西萬裏,頗有中國人相輔”之語,可見當時在廣東的中原人不少。
漢武帝平南越後,亦仿效秦始皇將罪犯遷至嶺南。⑥新莽時期,也曾兩次下令將各種罪人“投諸四裔”,⑦恐怕也有到嶺南的。
南越國時期,趙佗鑒于暴秦滅亡的教訓,推行民族和睦政策:尊重百越風俗,任用越人爲官,提倡越漢通婚等等。越漢關系融洽,有漢族融合于百越者。趙佗“椎結箕踞”,自稱“蠻夷大長”即是一例。⑧
秦漢兩代入粵的中原人,不僅爲粵地的開發和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其所帶來的語言、文化和禮俗對粵地的文化變遷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並爲越漢融合鋪平了道路。從西漢中期至東漢末年,番禺的南越、廣信的西瓯等相當部分族人逐漸融合于漢族,成爲漢朝的編民。
①參見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饒平古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八輯,1983年;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大埔縣古墓群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第11期。
②浮濱文化的年代,爭議頗大。邱立誠的《從普甯牛伯公山遺址談起》(《廣東省博物館集刊》1996年,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文認爲,經碳14測定,浮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1440—公元前920年之間,“下限不會晚至西周後期”。據此並參考地層及出土器物的年代,將其定在西周中期似較穩妥。
③《淮南子》卷18《人間訓》。
④《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
⑤《史記》卷118《淮南王安傳》。
⑥參見《三國志》卷53《薛綜傳》。
⑦《漢書》卷24《食貨志》。
⑧參見《史記》卷97《陸賈傳》、卷113《南越傳》。
越漢融合的結果,一方面是南越、西瓯等族稱逐漸不見于史,另一方面是發生越漢融合的南海、蒼梧二郡編戶大增。從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到東漢順帝永和五年的138年中,兩郡戶口分別猛增364%和457%。①如此高速的戶口增長,決非自然繁衍所能達到。這些新增編戶除部分爲入遷者外,大多數恐與越漢融合有關。
這些新增編戶的多數即南越、西瓯融合于漢族的融合體,就是廣府民系的最初先民。從地望來看,新增編戶不可能是客家民系和潮汕民系的先民。而最重要的證據是他們的語言。據西漢揚雄的《方言》看,當時粵方言已經萌芽。它的某些詞語如“睇”(看)、“西服”(庸賤)等已經出現,其讀音與今日粵語相同。②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詞語,在《廣東的方言》一書中已有專門論述。③粵方言系粵地土著百越族的古台語不斷接受漢語的影響並融合于漢語而形成的一種漢語方言。它的出現既是越漢融合的結果,也是越漢融合的標志。現代粵語仍保留著若幹古台語的語音、語法的特點和某些詞語,即足以證明廣府人與古越族的關系。有關這些特點和詞語,羅香林、徐松石和李新魁等已有成論,此從略。
廣府民系的先民是由南越、西瓯等融合于漢族而出現的。廣府民系是廣東漢族最早的成分,出現于西漢中期。也就是說,廣東漢族始見于西漢中期。有學者把前此徙居廣東的“中縣人”也作爲廣府人的先民或廣東漢族,似有不妥。因爲其所操之中原漢語不屬于今日廣東三大方言中任何一個。廣東漢族就是以廣府民系的先民(當然還有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的先民)爲基礎,繼續融合百越的後裔俚人及廣東境內其他少數民族或其他種族,以及不斷吸納來自全國各地的漢族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兩漢之交至南朝末年,又有不少漢族進入嶺南。他們當中有精通經史的中原士人,但更多的是逃避戰亂、賦役的“流人”和農民。道光《廣東通志·輿地略十》載,“自漢末建安(196—219)至東(西)晉永嘉(307—312)之際,中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嘉靖《廣東通志·事記》引晉黃恭《交廣二州記》也雲,“建興三年(315),江、揚二州經石冰、陳敏之亂,民多流入廣州。诏加存恤”。陸路之外,還有從海道來的。《晉書·庾亮傳》雲,“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南朝,北燕馮業率族人300集體浮海南下歸劉宋,占籍新會(《舊唐書》作番禺)亦是例證。④以上入粵漢族多到今珠江三角洲一帶。他們的入住不但增加了廣府民系先民的人口,而且其所帶來的中原漢語進一步加強了對正在形成中的粵方言的影響。“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指唐代)能晉語”。⑤粵方言至此基本形成。⑥對廣府民系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廣東的第二次民族融合即俚漢融合。在越漢融合之後,史籍出現“俚”的記載。俚是百越未融合于漢族者的後裔。⑦俚人數量甚多,僅粵西古高涼一帶即有“部落十余萬家”。⑧其分布幾遍全省,其中西江流域和古高涼一帶爲其聚居中心。
①據《漢書·地理志》和《後漢書·郡國志》,西漢元始二年,兩郡的戶口分別是19,613戶和24,379戶;東漢永和五年,其戶口是71,477戶和111,395戶。
②(漢)揚雄著、周祖谟校:《方言校箋及通檢》二,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
③參見李新魁:《廣東的方言》,第47—48頁。
④參見《隋書》卷80《谯國夫人傳》。《北史》本傳亦同。
⑤《張籍詩集·永嘉行》,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⑥參見李新魁:《廣東的方言》,第57—59頁。
⑦《隋書·南方人傳》曰:“南方人雜類……曰蜒,曰,曰俚,曰僚,曰人也……古先所謂百越是也”。
⑧《隋書》卷80《谯國夫人傳》。
從三國初年至隋代中葉的300多年中,他們多次起義,以反抗封建王朝的統治。①由于其人口占社會總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在整個社會生活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羅州(今化州市)刺史馮融雖“三世爲守牧,然他鄉羁旅,號令不行,乃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婚于郡大姓冼氏”,借重俚人首領冼夫人的力量,“俚人始相率受約束”。②南朝陳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擁冼夫人,號爲“聖母”,嶺南晏然,足見俚人勢力之大。隋仁壽(601—604)初,番(廣)州總管趙讷貪虐,激起俚人反抗。隋炀帝敕委冼夫人招慰亡叛,“所至皆降”,平定嶺南,不費一卒一箭。③另外,漢族朝廷命官爲取得俚人的支持,也多依從俚俗。故馮融被稱爲“都老”(俚人對首領的尊稱)。其族裔如馮盎、馮子猷、馮智戴等均被目爲“蠻夷”或“南方人酋長”。④
由于各地漢族湧入,促進俚漢文化交流,加上冼夫人“戒約本宗,使從民禮”,加速俚人對漢文化的吸收,于是廣東出現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俚漢融合,衆多的俚人紛紛融合于漢族。俚漢融合,始于晉,發展于南朝,隋唐之間進入高潮,而結束于唐初。《隋書·南方人傳》載,“南方人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曰俚,曰僚,曰也人……稍屬于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複詳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高州府部彙考三》“風俗”條雲:“自隋唐之後,漸襲華風,休明之化,淪洽于茲。椎跣變爲冠裳,侏亻離化爲弦誦;才賢輩出,科甲蟬聯,彬彬然埒于中土”。俚人聚居中心的西江流域和古高涼地區,隋代戶口比劉宋初年成倍地增加。⑤至唐初,兩地戶口又在隋代的基礎上大幅攀升。從隋大業五年(609)至唐貞觀十四年(640)的31年間,高涼郡的戶口增長率高達541.1%。⑥這些新增的戶除部分爲自然增長和入遷的漢族外,大部分應與俚漢融合有關。另外,俚人的著姓如高涼之冼氏、化州之龐氏、新會之馮氏和番禺之王氏等均爲今日該地漢族習見的姓氏,亦不失爲其佐證之一。
俚漢融合較之于越漢融合,規模更大、範圍更廣、人口更多。經過這次融合,土著百越族的遺裔已爲數不多。由于大量俚人融合爲漢族,廣東民族的結構因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只占人口少數的漢族一躍而成爲占人口的大多數,反客爲主,成爲廣東人口最多的民族。這種態勢即使元明兩代瑤族大量入遷亦未能逆轉。除粵東之外,俚人基本上都融合到廣府民系之中。其對廣府民系的作用,主要表現在由于人口的增加、分布範圍的擴大和確定,以及語言的大致形成,使廣府民系成爲較爲穩定的自成一體的民系。其分布格局已隱約可見。
兩宋之交和宋元之交,又有大批漢族進入廣東,使發展中的廣府民系人益多、地更廣。金兵和元兵南下都觸發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史載“中原士大夫避難者多在嶺南”。⑦不僅士大夫如此,一般漢族群衆亦如是。由于他們入粵時多取道大庾嶺,途經南雄縣珠玑巷,或者在珠玑巷稍住然後繼續南下。于是入粵各姓均稱來自南雄珠玑巷。據黃慈所輯《珠玑巷民族南遷
①參見拙作:《試論廣東俚漢民族關系》,《中國民族關系史論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道光《廣東通志》卷268《馮融傳》。
③《隋書》卷80《谯國夫人傳》。
④《資治通鑒》卷194《唐紀十》。
⑤據《宋書·州郡志》和《隋書·地理志》,劉宋大明八年(464),古高涼地區的高涼、宋康和海昌三郡共4666戶、21,328人。隋高涼郡轄境與上述三郡相當,大業五年(609),其戶口9917戶(未著人數)。西江流域,劉宋時設蒼梧、晉康、新甯三郡,共13,793戶、39,977人。隋時蒼梧、信安和永熙三郡轄境與上述三郡相當,共36,684戶。其增長率分別爲212.5%和266%。
⑥隋高涼郡,唐初析爲高、潘、辯、羅、恩、春等六州,據《舊唐書·地理志》,貞觀十四年,六州凡53,662戶,爲隋時9917戶的541.1%。
⑦(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紹興三年三月癸未條。
記》,南遷漢族有羅、湛、鄭、張、尹等70多個姓氏,落籍在今珠江三角洲及其鄰近地區約30個縣市,其中以南海、番禺、順德、中山、東莞和新會等縣市人數較多。②
其實,早在北宋初年即已有衆多遷民進入珠江三角洲。太平興國五年(980),廣州有主戶16,059戶(客戶不詳),至元豐二年(1079)有主戶64,796戶,客戶78,645戶。近100年間,僅主戶即增加48,737戶,增長率爲403.5%。③這顯然與移民入住有關。他們在開發珠江三角洲的過程中,逐漸融合爲廣府人。珠玑巷及其他遷民的融入使廣府民系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其語言已與現代粵方言相去不遠,其語音、詞彙已奠定現代粵語的基礎。
(二)潮汕民系的出現及其發展
潮汕民系同廣府民系一樣,其先民系由百越一支即閩越融合于漢族而成。粵東由于蓮花山-陰那山山脈自東北向西南斜貫其中,將其東南部之潮汕地區與珠江水系隔斷。而其與毗連的福建省則無山川阻隔,卻兼有水陸之便。因此,其與福建的關系遠較其與粵中的關系密切。考古資料表明,新石器時代,潮汕地區與閩南同屬一個文化系統。④其末期的浮濱文化即是如此。⑤其土著居民,學術界已公認與閩越有關。故潮汕地區古爲閩越地已無可置疑。雖說潮汕地區與珠江三角洲交通不便,但它與南越乃至中原地區的交往仍然十分頻繁。浮濱文化的典型器物如大口尊等在香港、深圳、珠海和南海等地均有出土就是明證。其後,兩地聯系日益加強。秦于粵東置揭陽縣(治今揭陽市西),南越國及西漢均因之。漢武帝平南越,揭陽令史定降漢,被封爲安道侯。⑥揭陽縣之置給潮汕地區帶來更多的中原文化。
粵東閩越何時融合于漢族,也就是說,潮汕民系先民何時出現,目前尚無可靠的證據以資證明。江浙一帶的于越,春秋時期便已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即吳國和越國。戰國前後,其族人已完全融合于華夏族,其所操之語言古台語亦融合成華夏語(漢語)的方言之一即吳越語,簡稱吳語。浙江的東瓯和福建的閩越,由于其首領搖和無諸秦末率族人從諸侯滅秦,佐漢有功,分別被封爲東海王和閩越王,建國東瓯和閩越。兩國分別于建元三年(前148)和元封元年(前110)爲漢武帝滅掉。雖《漢書》明載兩地越族已全部“徙處江淮間”,⑦但實際上兩地的古越族遺民仍然不少。至昭帝始元二年(前85),分別于其故地置回浦縣(治今浙江臨海市東南)和冶縣(治今福建省閩侯縣北)予以統治。⑧此後,這些遺民中的多數已逐漸融合于漢族,少數僻居山區者,東漢靈帝(168—189)之後稱爲“山越”,活躍于粵、閩、浙和台灣省等地。⑨如此觀之,粵東閩越融合于漢族很可能在漢靈帝前後即東漢中晚期,比廣府民系先民出現的時間稍後。這與語言學家對潮語研究的結果基本吻合。
①參見《南雄珠玑巷人南遷記》,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②參見曾昭璇等:《宋代珠玑巷遷民與珠江三角洲農業》,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③參見《太平寰宇記》卷157、《元豐九域志》卷9。
④參見曾骐:《潮汕史前文化的新研究》,《潮州學國際研討會文集》上冊,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⑤參見邱立誠等:《從普甯牛伯公山遺址談起》,《廣東省博物館集刊》1996年。
⑥參見《漢書》卷95《南粵傳》。
⑦《漢書》卷95《閩越傳》。
⑧。《宋書·州郡志二》載:“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武帝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于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屬會稽”。(明)王應山《閩大記·閩記》雲,漢昭帝始元二年,閩越遺民自立冶縣,屬會稽郡南部都尉。《太平禦覽》引《吳地記》曰,昭帝始元二年,以東瓯故地爲回浦縣。
⑨山越首見于東漢靈帝建甯二年(169),見《後漢書·靈帝紀》
(10)《廣東的方言》(第269—271頁)載,潮語的萌芽階段在戰國至三國東吳之前。
潮汕民系先民出現之後,雖然發展緩慢,但漢末至南朝都不斷有漢族移入。蕭梁侯景之亂時就有不少逃到潮汕。①東晉義熙九年(413),析東官郡,于揭陽縣地置義安郡,領海陽(今潮安縣)、潮陽、義招(今大埔縣)、海甯(今惠來縣西)和綏安(今福建省漳浦縣西南)等五縣。潮汕地區由原來的揭陽一縣增至爲一郡三縣。遷入潮汕的漢族以徙自福建者居多,但亦有相當數量來自中原。據調查,今澄海、潮州等市的著姓林氏和潮陽的黃氏等即有稱彼時由福建遷來的。建國後,在揭陽、潮陽一帶發現多座東晉至南朝的墓葬,尤其是揭陽的一座南朝墓,其結構之複雜、規模之大爲廣東所僅見。這些墓主無疑是中原漢族。②
中原和閩南漢族入潮,不僅使潮汕民系人口增加,而且也使潮語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潮語一方面繼續接受來自閩語的影響,另一方面直接接受中原漢語的影響日漸增加。兩者交織在一起,使潮汕地區原來所使用的方言逐漸成爲漢語方言的一支。③
唐宋時期是潮語分化的決定性階段,也是潮汕民系發展的關鍵階段。入唐之後,一方面是粵東俚人融合于漢族,另一方面是遷入潮汕地區的漢族日見增多。入潮的漢族,以零星遷徙的農民、商人居多,但也有軍旅性的集體移民。唐初總章二年(669),泉、潮間“蠻僚”起義,朝廷命光州固始(今河南省固始縣東)人陳政父子率“府兵三千六百將士”討之。由于其不敵起義軍,朝廷繼命政兄陳敏、陳敷“領軍校五十八姓來援”。④後來這些官兵全部留戍當地。天寶十一年(752),潮州戶口已由隋大業五年的2066戶增至4420戶,增長率爲213.9%。⑤
兩宋時期,由于航海業的發達,漢族移民從水陸兩路湧入,令潮州戶口驟增。據載,在太平興國五年至元豐二年的99年中,潮州戶口由5381戶猛增至74,682戶,增長率爲1387.9%。⑥至南宋理宗端平(1234—1236)時,其戶口又增至135,998戶,淨增6萬多戶。⑦這些遷徙活動在今日潮汕人的族譜中多有記載。⑧
元代,福建漢族繼續徙居潮州。“他們從福建帶來的閩南話,進一步與原先本地居民所操的方言彙合,逐漸形成後來的潮州話”。⑨潮汕方言最終形成。
在福建遷民入潮的同時,有一些遷民則越過潮州繼續沿海岸線南下,落籍南恩州(今陽江市)、電白和雷州半島的海康、徐聞等粵西沿海各縣乃至海南島,使這些州縣的人口大增,其中以雷州爲最。該州由天寶十一年的4320戶到元豐二年增至13,984戶,增長323.7%。
《輿地紀勝·南恩州》雲:“(南恩州)民庶僑居雜處,多瓯閩之人”。北宋蘇轍曾任海康令,他在《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的引言中說:“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
這些遷民落籍後大都聚族而居,保留原有的語言和習俗,成爲雷州人的祖先。至此,潮汕民系居廣東東西兩翼的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
(三)客家民系的出現及其發展
客家民系的出現與發展都較前兩者簡單。雖然客家民系與其他民族(如畲族)和民系都有密切的關系或融合關系,但其基本上是集團性移民群體曆史積累的結果。其語言,由于其恪守“甯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的祖訓,基本上也是集團性的人群遷徙而形成的“移民集團”的方言。①
就迄今所見,客家先民在兩晉之交已經出現。義招縣之置,事在東晉末年,然置縣的基礎爲“昔流人營”。《輿地紀勝·潮州》“古迹”條引《南越志》雲:“義安郡有義招縣,昔流人營也。義熙九年立爲縣”。晉代流人肇因于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緊接著的“永嘉之亂”更使其有增無已。于是便爆發了以流民爲主的流民起義,如長江流域的李特、張昌、王如和杜等的起義即是。流民何時出現于粵東,雖史無明載,但大體可以將其定在永嘉稍後即兩晉之交。數量足以置縣的流民在粵東東北一帶立足,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保留著原有的語言和文化,形成最早的純客家人聚居區。此後,客家民系便以此爲生長點,隨著中原漢族的不斷入遷而發展壯大。至五代,客家先民已有所發展;北宋初,發展速度明顯加快,中葉之後更有飛躍的發展。其集中表現在州縣的析置和人口的增加。後梁貞明三年(917),徙唐循州于龍川,領龍川縣;于原循州置祯州(宋改曰惠州),將唐循州一分爲二。南漢乾和四年(946),析潮州置敬州(宋改曰梅州),領程鄉縣(今梅縣)。此新建兩州均爲北宋及其後所沿襲。北宋熙甯四年(1071),又析興甯縣置長樂縣(今五華縣)。至此,今粵東純客區已有二州四縣之置。一般來說,州縣的建置以一定數量的戶口和賦稅爲依據。五代,戶口缺載。據《太平寰宇記》載,太平興國五年,梅州戶1568戶,循州戶8339戶。99年之後,兩州戶口分別增至12,372戶和47,192戶,增長率爲788.9%和565.9%。與循相鄰的韶州,戶口增長率(534%)也與循州相仿。②這些編戶不少就是客家人。南宋寶慶三年(1227)成書的《輿地紀勝·梅州》引《梅州圖經》(該書久佚)雲:“郡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借汀、贛僑寓者耕焉”。顯然,彼時在梅州土地上勤勤懇懇“業農”者正是來自汀、贛的客籍人士。今客家人的族譜多稱其由福建甯化和江西甯都等地遷來,與此正合。語言學家認爲,“客家話的最終形成,大約出現于宋代”,③也有力地支持上述推論。
元軍破臨安後,繼續尾追宋軍,中原士大夫及各地郡衆或逃避戰亂,或參與勤王,紛紛自東南沿海南下。宋亡之後,他們大都落籍粵東各州縣,其中不少進入客家地區,成爲充實客家民系的新鮮血液。
至元代,廣東三大民系基本形成。他們的分布,由于“客家人進入之時,廣府、潮汕兩大民系已基本形成東、西分布的態勢,留給客家人的,只有粵北、粵東的兩片相連的山區地帶。因此,這兩塊相連的地區也就成了廣東境內客家的基本分布地”。④
二、廣東的第三次民族融合與廣東漢族的最終形成
明清二代,廣東出現第三次民族大融合,世居山區的瑤、壯、畲三族的大多數陸續融合于廣府、潮汕和客家民系之中,使三大民系也就是廣東漢族的主體得以最終形成。
非粵地土著的瑤族,其主體系六朝後期至明中葉間陸續從湖南遷徙而來。其直系祖先莫徭于南朝梁陳時期逾嶺入粵,散居于粵北今連南瑤族自治縣和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一帶,直至五代。
入宋之後,湖南瑤族大量南徙。他們不僅活躍于粵北的連、韶、英等州一帶,而且已深入到廣東腹地西江流域的端州(治今高要市)。至南宋,瑤族向東、南、西三方向推進。東北的南雄州,西北的懷集縣和粵中的新州(今新興縣)、德慶州及珠江三角洲的廣州都已有瑤族的蹤迹。及元,其更進一步拓展至粵東的循州和南海之濱的南恩州、化州、雷州。明代,又在元代分布的基礎上再向四鄰州縣滲透,進入其繁盛時期。明代,今廣東轄境共九府70州縣,嘉靖(1522—1566)年間,除瓊州、潮洲二府分別爲黎、畲所居外,其余七府44州縣均有瑤族分布。其中清遠、四會和廣甯一帶,西江流域以羅旁(今雲浮市一帶)爲中心包括鄰近各縣,以及粵西信宜、茂名(今高州市)一帶等是瑤族的三個聚居中心。
當時廣東瑤族的人口,至今尚無法統計。元大德(1279—1307)年間,程钜夫在《羅璧神道碑》謂,“洞蠻”(其中瑤族居多)二十萬,負固奪民田以食”。①元末,守韶州劉鹗又說,“廣東一道,地方數千裏,戶口數十萬,瑤僚(即瑤族)半之”。②不管是“洞蠻二十萬”,抑或是“戶口數十萬,瑤僚半之”,都只是個約數,並非實指。不過,據此可知瑤族人口之衆。
明代,瑤族人口又有較大的增長。嘉靖間瑤山918座,③遍布上述府州縣,有“無瑤不住山,無山不有瑤”之諺。
壯族(古作僮),與嶺南土著百越有淵源關系。廣東壯族系由粵地土著百越演化而成的“主僮”和由廣西而來的“客僮”爲主,融合少量瑤族和漢族而形成的人們共同體。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始見于史。④明嘉靖年間,僮分布于廣州、肇慶、高州和廣西梧州(今懷集縣時屬本府)等四府的19州縣。⑤其中封川、開建、懷集和連山等縣即粵西北一帶是其聚居中心。
廣東畲族均在粵東。畲族亦非廣東土著。其入粵時間與莫徭相仿佛。六朝後期,畲族從湖南遷徙到粵、贛、閩三省結合部一帶,唐初定居于泉(州)、潮(州)間。⑥粵東畲族以潮州爲中心向四方擴散,向西發展至惠州府,與向東發展的瑤族相遇。惠州府遂成畲、瑤的雜居區。畲族有少數越過惠州府進入廣州府之增城縣,而瑤族則無法越潮州府雷池半步。其具體分布爲,潮州府之海陽、潮陽、揭陽、大埔、饒平、澄海、程鄉、平遠,惠州府之歸善、博羅、海豐、興甯、長樂、永安(今紫金縣)和廣州府之增城等三府15縣。⑦
廣東壯、畲二族的人口及分布範圍都稍遜于廣東瑤族,但其總人口亦不少。兩族在明代都曾發動過多次規模巨大的起義,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封川壯族蘇公樂起義和隆慶五年(1571)惠州畲族藍一清起義等。這兩次起義明王朝分別調集漢達土兵48,000人和40,000人前往“鎮壓”。據此即足知兩族人口之盛。
明中後葉至清初,三族發生了幾乎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分布區域驟縮,人口銳減。至清末,瑤族由原來的七府44州縣減爲兩府四直隸州(廳)7縣,即廣州府之新會縣,韶州府之曲江、樂昌、乳源等縣,南雄直隸州之始興縣,連州直隸州之陽山縣,羅定直隸州之東安縣(今雲浮市雲安縣)和連山綏瑤直隸廳。壯族更甚,原來分布的四府19州縣僅余連山直隸廳及其毗鄰之懷集縣。畲族亦如是,其原有的三府15縣只剩下圍繞鳳凰、蓮花和羅浮等三山的豐順、饒平、潮安、海豐、惠東、博羅和增城等7縣有少量的分布;至建國初期,其總人口已不足4000。①引起這種急劇的變化的原因很多,封建王朝野蠻的“征剿”和民族的遷徙無疑都是其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應與民族融合有關。
這次民族大融合即第三次民族融合始于明洪武(1368—1398)、永樂(1403—1424)、嘉靖至清康乾之世爲其高潮,而結束于清之季世。少數民族融合于漢族系通過文化的涵化而實現的,文獻多稱之爲“向化”、“同之齊民”、“入籍當差”或“新民”。現按族別分述于下。
民國《陽山縣志·事記》雲,洪武初,“太祖命赍榜招(瑤)陳滿陽等三百八十六戶入籍當差”。這是瑤漢融合的最早實例。
永樂十四年(1416),“高要瑤目周四哥來朝,籍其戶八十有七,則十四年之前爲瑤僚可知矣。厥後,隸尺籍爲編民,散處市廛中,長子孫至讀書取青衿,是不特被漸于化,其爲瑤僚,名謂形似,久將漫然,不複有存”。②
據《明實錄》載,在永樂至正統(1436—1449)的近50年中,先後有高州、肇慶二府屬縣天黃、大帽、曹運、茶峒、石栗諸山,德慶州新落山等處,懷集縣西家等處和連州連山縣黃蓮、大羅諸山等處有數量不等的瑤民“向化”,傳版籍,供賦役。③
萬曆十年(1582),陽山知縣趙文祯招撫稍陀、老鴉、白芒等三坑瑤爲編民,出籍供賦,編爲永化都,名其爲“新民”。
入清之後,融合速度進一步加快。有阖縣瑤族融于漢者。如新甯縣(今台山市),“(瑤民)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招撫歸順,分隸各州縣。其在新甯者,居縣之大隆峒,言語服飾漸與內地習染,同齊民一體,編戶輸糧。婦女髻環衣飾,亦與齊民無異”。⑤
又如新興縣,“今(指乾隆年間)國家升平日久,瑤人欣欣向化,衣食動作與齊民無異”。
四會、恩平、陽江、開建等縣亦有類似記載。
此外,有的縣系部分瑤族融合于漢者。如乳源、曲江、連山、陽山等縣即是。
乳源瑤,“或耕山,或耕畝。耕山者花麻而不賦,耕畝者田糧戶口與齊民同”①等等。
姓氏亦可爲證。今日居住在原瑤區中的漢族,其姓氏每每與昔日瑤姓相同。如新興縣共成鄉一帶,據乾隆《新興縣志·瑤人》載,清初仍爲瑤區。其瑤民多馮、何、李、陳、黃、滿、藍、田、梁等姓。在該鄉肥水坑村前至今尚有“東瑤西民”之界碑,而今日世居這一帶的漢族,其姓與上述頗同。又羅定市新榕等鄉明代爲瑤區,而今日世居該地的漢族,其姓氏不少與曆史上這一帶的瑤姓如盤、藍、雷、駱等同。此又不失爲瑤族融合于漢族的一個有力佐證。
壯融于漢者多在明代。其中以德慶州爲最早。正統四年十月,“德慶州雷鄉諸山僮、瑤何應山等順化隸籍,率類朝貢”。②次爲懷集縣,弘治六年(1493),知縣區昌到今藍鍾、下帥等鄉“開誠招谕”,瑤僮“各立牌甲者”可萬余。③其余開建、東安、西甯(今郁南縣)等縣僮亦漸次與漢族融合。
壯的聚居中心之一今高州、信宜一帶竟無一字提及,可見方志亦有遺漏。筆者在1986年的社會調查中意外地發現了壯融于漢的融合體———漢族“標話”集團,可補史之遺阙。該集團系以其所操之語言自稱爲“標話”而得名,分布在封開、懷集兩縣之交昔日的僮區即今南豐、金裝、長安、詩洞、永固、橋頭和大崗等鄉鎮一帶,人口約30萬。④其語言“標話”,語言學家已一致肯定屬于壯侗語族的一種語言。由于其跟該語族諸語言關系都十分密切,語支歸屬尚未確定。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標話”約有1/3詞彙僅其本身所獨有,爲壯侗語族其他語言所不見,這顯然是它繼承壯侗語族古老語言即古台語底層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獨立發展的結果。這種語言現象表明,“標話”集團的前身是自古以來就一直生活于這一帶的古越族的後裔。
此外,其姓氏、族譜和文化等亦尚有若幹僮的特征,與語言資料吻合。
畲融于漢始于永樂初。《明太宗實錄》載,永樂五年(1407)八月,“潮州衛總旗李和招谕斜(畲)人頭目盤星劍等一百余戶向化,和就率之來朝”。⑥《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也雲,“畲客(即畲族),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爲名者也。衣服言語,漸同齊民”。
瑤、壯、畲三族融合于漢族的成分,從地望來看,多數融合于廣府民系,少量融合于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經過這次民族融合,三大民系由于人口大幅增加、分布範圍進一步擴大而最終形成。
最後,還需說明的是,廣東漢族在其出現、發展和形成的曆史過程中,不僅融合了嶺南土著百越及其後裔以及瑤、畲等族,而且還融合了若幹非蒙古利亞人種的血統。廣東自漢至清一直都有非蒙古利亞種族在生息勞動。其中數量較多的是來自南海諸島的棕色或黑色人種。東漢楊孚《異物志》載其“齒及目甚鮮白,面體異黑若漆,皆光澤。爲奴婢”,稱爲“甕人”。這種人隋之後稱昆侖、昆侖奴或鬼奴,近世稱“小黑人”或“矮民”。唐之《嶺表錄異》、宋之《太平廣記》、《萍洲可談》,明之《廣志繹》和清之《廣東新語》等都有關于他們的記載。他們人數不少,或爲家奴,或爲自由人。隋大業四年(608),隋炀帝派兵攻打流求(今台灣省),自粵東義安郡出發的軍隊中就有昆侖人。①唐中宗嗣聖元年(684),憤怒的昆侖更將廣州都督路元睿殺死:“元睿暗懦,僚屬恣橫。……群胡怒,有昆侖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②迨至清代,粵西北懷集縣和雷州半島一帶仍有關于他們活動或遺俗的記載。③人類學家從海南島黎族的個別掌紋特征,發現“曆史上存在著黎族和某些黑色人種混血的可能性”。④這種“混血的可能性”恐怕不僅存在于黎族,而且還應存在于廣東漢族。
另外,廣東古代還有白色人種在生活。廣州、順德、三水和高州等地出土的漢代陶俑燈座和陶質舞俑,從其深目、高鼻、兩顴較高,胡須和體毛發達等體質特征看,似是歐羅巴人種,來自當時與番禺有貿易關系的印度(北部)和西亞。唐以降,有聚居于廣州“蕃坊”(今廣州光塔路一帶)的西亞商人“蕃客”。至五代,廣州更有西亞人雜居民間,以致被征召入宮。據載,南漢主劉伥“與官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複出省事”。⑤這些人種包括與廣州回族有淵源關系的蕃客,也應與廣東漢族有融合關系。
三、廣東漢族也爲瑤、壯、畲等族所融合
融合關系是雙向的。在百越及其後裔以及瑤、畲等族融合于漢族的同時或前後,漢族也爲他們所融合。
部分漢族由于種種原因進入少數民族地區久之,融合于當地的少數民族,曆史上屢見不鮮。嘉靖初,“廣東新甯、新會、新興、恩平之間,皆高山叢箐,徑道險仄,奸民亡命者辄竄入諸瑤中,吏不得問”。⑥嘉靖七年(1528),廣東分巡李香到陽春縣“招出投瑤二千余人,還新興、陽江、新會等處複業”,⑦但並未盡數招出。後來這一帶的瑤族起義,便推舉他們當中的陳以明爲首領便是明證。明末清初,“有明朝遺老多人,慨漢族之淪亡,憤腥膻之滿地,多徙族入排(即村寨),雜瑤而居,曆史既久,遂與同化”。⑧先哲亦已有見及此。顧炎武道:“特二種(指瑤、僮)有真赝、主客之分,不可不辨。大率盤姓爲真瑤,他姓爲赝瑤”。⑨稍後,屈大均說得明白:“諸瑤(指羅旁瑤)率盤姓,……其非盤姓者,初本漢人,以避賦役,竄潛其中,習與性成,遂成真瑤”。
民國《陽山縣志·輿地志》也謂:“老鴉坑瑤,原土著人(指漢族),以效瑤所爲,故亦曰瑤”。民族系以文化(非姓氏血緣)爲基礎的人們共同體。將有共同文化的瑤族按姓氏分爲真、赝,當不足爲訓。不過這是曆史的局限,不可苛求于前人。
據調查,連南縣南崗鄉的鄧姓(部分族人)、大麥山鎮馬嶺墩和廟應崗一帶的許姓、內田鄉的方姓,乳源縣遊溪鄉子背村的鄧姓、柳坑鄉薯莨坑的馮姓、龍南鄉藍廠的邝姓等,都是由漢族入住瑤區而融合于瑤族的。
另外,曆史上還有不少漢族的兒童被瑤族收養,或漢族女子嫁入瑤山而成爲瑤族的。據連南縣油嶺排瑤唐姓的族譜,其始祖唐郎白公之曾孫唐一公收養一漢族養子,法名爲天保七郎,又稱唐七公,俗呼“漢人公”。他的後裔繁衍成今日該排的小唐(唐姓內部分大唐、小唐)。
漢族融合于壯族者亦多。這種現象有學者稱之爲“壯化”。①據調查,今連山縣壯族有相當部分族體系外地漢族遷入壯區後而融合成爲壯族的。如該縣福堂鎮以及與其毗鄰的懷集縣下帥鄉和廣西賀縣南鄉鎮等地的莫姓;該縣加田鄉之梁姓、謝姓,上帥鄉之陸姓,小三江鎮之朱姓、陸姓,永豐鄉之郭姓、文姓等壯族均是。其中以莫姓人口最多,約30,000。漢族女子嫁入壯區的亦不少。
畲族與客家民系的關系密切,已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廣東畲族居住分散,與周圍漢族保持著各方面的密切聯系,使得兩族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促進;加上兩族間長期的相互通婚,更促進了畲漢民族文化的交融”。②如語言,目前多數畲族操的是近似客家方言的畲話。③而客方言也受到畲語的影響,兩者“曾經起過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作用”。④又如精神文化方面,畲族的民間信仰和客家人一樣,是佛、道結合,多神崇拜。在命名、排輩和取郎名、法名等方面,畲族和部分客家人也同。又如在婚喪節慶等習俗方面,兩者亦多有相同之處,等等。⑤這種文化互動關系必然會有利于或促進兩族的相互融合。部分漢族融合于畲族不足爲奇。
另外,據研究,畲、漢通婚在清初已較爲普遍。不少漢族通過婚姻而融合于畲族之中。⑥
二、從一些Y染色體信息推測瓯越的族屬
複旦大學李輝等以廣州爲取樣點,得出廣東漢族Y染色體單倍群比例,有20%的M119和7%的M88。文波《Y染色體、mtDNA多態性與東亞人群的遺傳結構》(2006年全國優秀博士論文)中的數據,北方漢族有8.0%的C-M130、2.2%的D-YAP、5.7%的P*-M45;南方漢族有6.8%的C-M130、1.4%的D-YAP、1.5%的P*-M45;廣東有32.5%的M122、30%的M95和15%的M119。
鑿齒(黑齒)好食槟榔,與熱帶馬來人有近緣,因此,廣州周邊的鑿齒(黑齒)及禽人(符婁、番禺、番陽)應屬百越O1a-M119;百越可能是在4~3萬年前在越南的占城與馬來支分開後,沿古海岸進入到珠江水系的下遊及中遊地區,然後又在約1.2萬年前經粵北向贛浙方向發展,部分從桂東北的賀江源頭進入湘南、贛西。(新觀點見:黃種人O系的遷徙、分化與擴張)
鑒于李輝等在鄱陽湖西南面的吳城遺址(3500~3100年前)取得的古DNA主要爲O2a型,按古越人的遷徙路線,駱、桂國、漚深可能屬駱越O2a-M95;他們從滇南、桂西南進入到西江的上、中遊地區,然後有經桂東北的漓江源頭過湘南。
居郁水之南,有文身習俗的雕題氐人可能混有或屬早東亞人D,氐人源出巴蜀,遷居九疑之南而有文身之俗。另有一分支夫余族群O2b可能是在追逐(殺)早東亞人C3過程,沿古海岸遷徙到東北-朝鮮半島-日本等地。
早期駱越O2a在桂中、桂北的溶蝕平原及溶洞分布區有較好發展;而百越O1a在粵北-湘贛擴散較早,後來在江浙一帶獲得巨大發展;封豨、蒼兕居兩遷徙線路中間,屬何族系?尚有疑問。
三、古蒼梧的族屬
封開作爲嶺南土著文化最早、最重要的發源地,有必要搞清賀江流域的古蒼梧(即封豨+蒼兕)是屬百越O1a-M119、駱越O2a-M95還是荊蠻-揚越O3系。在了解百越O1a、駱越O2a大致遷徙路線的基礎上,再只能在出土文物上尋其蛛絲馬迹。
玉琮、玉璧、玉钺等被視爲江浙百越民族良渚文化(5.3~4.2kaB.P;O1a-M119)中的特殊禮器,粵北曲江的石峽文化(5~4.5kaB.P)也出土了玉石琮6件及玉璧、石钺各1件,此說明沿粵北-贛-浙,百越交流路線的存在,有幸的是,在封開杏花的祿美村遺址(4kaB.P)也出土了與石峽、良渚遺址相似的1件玉石琮及1件小石钺,由此可推斷,此期封豨所居應爲百越O1a。另在杏花河畔山崗遺址(4kaB.P)的152件斧锛中,發現有36件的石料屬霏細岩,霏細岩是南海西樵山石器制作場制作有肩石器的主要石料,在未發現封開本地有開采霏細岩的情況下,可推定霏細岩石器是從西樵山運來的,這種“親緣”來往,爲封豨與西樵山一帶在四、五千年前同屬百越O1a的地盤添加了佐證。
百越人活著時喜歡拔牙(鑿齒),傳說吃槟榔及拔牙是爲了消除瘴氣,對死者有二次拾骨葬葬俗,杏花烏騷嶺二次葬公墓中的111座墓葬(4.3~3.9kaB.P)說明封豨在大約四千年前所居爲百越O1a。沿百越遷徙路線,早期的拔牙遺存見于珠三角西樵山文化(5~4kaB.P)、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4.5kaB.P)及山東大汶口文化等;早期二次葬見于粵北石峽文化、封開杏花烏騷嶺、江西新余拾年山(6~4.5kaB.P)及湘鄉岱子坪(5~4.5kaB.P)等遺址。相比,數千年前駱越O2a的葬俗多爲屈肢葬,早期的有9~7千年前的桂林甑皮岩、橫縣西津、扶綏敢造、邕甯長塘、南甯頂蛳山及東南亞和平-北山文化等遺址,晚些的有粵西遂溪鯉魚墩(7~3.5kaB.P)、肇慶蚬殼洲(5.1kaB.P)及鄂西大溪(6.4~5.3kaB.P)-屈家嶺(5~4kaB.P)文化遺址等。蚬殼洲遺址又見拔牙遺存,有雙手反綁于背的俯身屈肢葬,被葬者也有可能屬俘虜而非駱越O2a;荊蠻大溪-屈家嶺文化有40%左右的屈肢葬可能意味著其較深地混合了駱越O2a。
有研究認爲,進入商周青銅器時代,大石鏟退出了實用舞台,但在駱越則演變爲祭祀天地、祈求豐年的農業祭祀禮器,這種沒有使用痕迹作祭祀用的鈍刃大石鏟在駱越的活動中心-廣西的左、右江發現最多,然而,在封開縣內多地也發現共有十多件形制奇特、磨制精細的雙肩大石鏟(更多>>>)[1],由此推測,大約在3千年前的商周時期,有駱越O2a融入古蒼梧;據李輝等,3.5~3.1kaB.P江西吳城遺存Y染色體主要爲駱越O2a,或也能說明,駱越大約在4~3.5kaB.P有一個由西向東向北的擴張過程,給粵西、湘、贛等地帶來駱越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古蒼梧地域的腰坑墓葬特色及所出土的青銅器屬揚越類型,說明隨著北方青銅文化的傳來,源自湘地的揚越O3*文化占了主導。二、三千年前,揚越主要居湘地,部分居鄂、贛,由原先居長江中遊湘楚地域荊蠻族群演變而來,而當今的瑤族可能是揚越後裔,演變關系也則:荊蠻族群→荊楚、揚越→苗、瑤族。偏北楚地的荊楚O3*+O3d主要演變爲苗族;偏南湘地的揚越O3*與駱越O2a-M95融合較深,常混有O*,部分混底層小矮黑D,部分演變爲瑤族,畲族是瑤族的分支。苗、瑤族或多或少都混有O3d-M7(據文波,684個樣本平均爲6.7%)。瑤族曆史上在嶺南分布很廣,據嘉靖《廣東通志·外志·夷情》載,明代廣東還有很多瑤寨,分布33個州縣,其中肇慶府約有540處,占全省900多處瑤寨的60%左右,西江與粵北一樣,爲瑤族的大本營(-據司徒尚紀)。不過,可能並非所有的瑤族都源于湘西,兩廣北部除本地起源的百越O1a及駱越O2a外,可能還存在本地起源的類瑤人群O3*,如在高頻的O3譜系中未出現O3d-M7及O3e-M134的封開-懷集講標人有可能屬本地起源?(相關見:封開一帶果然有O3系祖型族群)
四千多年來,封豨或古蒼梧作爲嶺南土著文化的發源地,在不同時期,成爲蒼梧越(蒼兕+封豨,O1a,四千年前)、駱越(駱越,O2a,商周)、荊蠻-揚越(O3*,春秋戰國)、秦漢中原漢人(O3e)的移居及文化交流場所。
南方新石器晚期遺址自北而南、自西而東先後大約是在4500~3500年前出現了中斷,這意味著原始社會出現了動蕩、出現了轉折,還意味著可能出現了族群的更替。東南地區新石器晚期流行二次葬、有拔牙(鑿齒)習俗、以玉琮作爲特殊禮器,應屬百越(O1a),當今江浙人群就有較高比例的O1a-M119。但廣東漢族主要爲O3系,次爲駱越O2a,而百越O1a比例相對較低,出現了南粵越民少這種奇怪現象,推測應與荊蠻族群被黃帝集團打敗後的南逃有關。荊蠻雖敗,但其文化的先進程度還是在嶺南百越之上,荊蠻的到來,對百越來說是個災難性的打擊,他們不得不逃離原先的居所,因此遺址就出現了中斷,而後又經曆了春秋戰國湘地揚越的滲透,揚越-苗瑤的O3系統就取得了優勢地位。苗瑤族O1a-M119低頻,說明百越很少融入到苗瑤之中,揚越-苗瑤可能是通過消滅或驅逐方式取得對百越地盤的更替。先秦,大規模漢人到來之前,廣東西江-珠江以北大多已成揚越或荊楚人的地盤,而粵西湛江-茂名-陽西一帶應爲駱越-俚僚的地盤,或許,珠三角西面至羅定-陽江一帶還是百越O1a的地盤?但目前相關數據欠缺。東亞人群O1a-M119頻率排行:台灣高山族50-100%>海南黎族30-60%>上海馬橋原住民30-55%>廣西貴州仡佬族、仫佬族20-60%>印尼原住民20-50%>部分侗族35%>浙江漢族27%>上海漢族26%>安徽漢族18%、江蘇漢族18%、廣西水族18%、廣西壯族18%>湖北漢族17%>廣西漢族15%>江西漢族14%>湖南漢族13%>廣東漢族12%(據李輝、石宏、文波等)。
四、廣府民系的形成,兼對比客家民系、潮汕人群
漢民族可分北方民系、江浙民系、廣府民系、福佬民系、客家民系、湖湘民系和老表民系七大民系,分別操北方語、吳語、粵語、閩語、客家語、湘語和贛語。漢民族約占全國人口的92%。原始漢族起源于黃河中上遊的華夏族群,後與東夷及荊蠻發生融合,形成漢人齊語支及漢人楚語支,再經戰亂遷徙,與當地土著或少數民族發生融合,形成漢族的七大民系。在父系Y染色體單倍型方面,華夏漢人父系Y-SNP頻率O3e-M134>O3*,O3*主要爲M122,K-M9有較高比例;漢人齊語支O3*>O3e-M134,O3*中M324有較高比例,O3e*中O3e1-M117有較高比例;漢人楚語支O3*>O3e-M134,有O3d-M7,O3*爲M122。
廣府民系講粵語,以廣州地區爲代表,分布于兩廣,由偏北的北方華夏漢人南遷,與越人土著融合而成,在廣東廣府人當中,源于北方漢族的M9+M122+M134三項占60.5%,M134>M122。廣府人父系DNA,宋朝漢人血統占50%、秦漢漢人血統占10%(似偏小?)、越人血統占40%;母系DNA,越人血統占80%、漢族血統占20%。北方漢族血統父系的貢獻要比母系高得多;廣府民系所融合的越人土著,西部爲西瓯,東部爲南越(黑齒、禽人),南部爲臨越(雕題),西南爲駱越;廣東北部還融合了比漢人更早到來的揚越荊楚人。若按廣州、廣甯的幾份檢測數據分攤估算,肇慶-廣州人的構成大概是:越人土著M119+M95占17%、春秋戰國入粵的揚越荊楚人M122+M7+M95占23%(包括後來瑤畲漢化)、秦漢北方漢人占17%、唐宋以降北方及江南漢人占38%,其他占5%。嶺南最早漢化始于舜帝時期的賀江流域,兩廣大規模漢化始于西漢,其從西江中遊廣信(封開)開始,並沿水系向東、向西、向南推進,再在唐代以來經粵北融入大量北方或鄂湘贛江南漢人。粵語來源于秦漢時北方華夏族群的“普通話”-雅言,屬漢語秦語支,漢武帝平定嶺南並在廣信設立交趾部,並依上述路線融入漢人不斷推廣,而在此之前,越人各部落還缺乏文字及統一的語言,粵語化有可能是標准的、革命性的。
客家民系特點有:①.形成時間較晚,大致與宋朝大量北方或鄂湘贛江南漢人經南雄珠玑巷驿站南徙珠三角時間相當。兩宋中國積弱,河南等地的中原漢人首先雲集江西,後在贛南閩西形成客家大本營(據譚元亨)。②.客家人的父系DNA,宋朝漢族血統占30%、秦漢漢族血統占10%、苗瑤族O3d血統占30%、越人血統及早東亞人各占10%(總數怎麽只有90%?似越人偏低、秦漢偏高,估計粵客秦漢漢族占5%,越人占25%);母系DNA,越人、漢族、苗瑤族血統各占30%、早東亞人血統占10%。據李輝等,福建長汀客家Y染色體漢族結構占80.2%,客家人主要融合了當地苗瑤族群中的畲族,類畲族結構占13%、類侗族結構占6.8%,如數表>>>;與廣府民系相比,客家人O3e-M134頻率較低,有4%的O3d-M7,說明客家漢人祖源河南,南下過程混入楚語支漢人,後又在贛閩粵混入當地的畲族及百越土著。據文波、張有隽等684個苗瑤族樣本,M122/M7=7,按4%的M7,可算得客家人混入苗瑤M122+M7的比例爲32%。③.客家民系在不停地遷徙。宋元之交,客家民系在抗擊元兵中遭受大浩劫,大本營被打散打亂,並向粵東北、湘東等地逃散;明初,朱元璋與陳友諒爭帝,粵北原居民遭屠殺驅趕,後遷贛南、閩西、粵東之客家人來填補,在明朝,客家民系再次凝聚成形(據譚元亨)。
潮汕人群從閩南遷來,屬福佬民系,福佬民系的形成與東漢末至南北朝河南-山東一帶的漢人南遷有關,潮州話屬漢語齊語支閩南方言。閩語支人群O3系占大部分,其中O3e1-M117有較高比例,符合齊語支漢人的特點,可能爲傳說中東夷少昊集團的後裔。與潮汕人有親緣關系的有雷州半島、海南、台灣、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地的閩南語人群。潮汕人混合的土著主要爲苗瑤中的畲族,畲族的始祖聚居地就在潮州的鳳凰山,O3d-M7頻率在粵東閩南一帶全國最高,潮州人中較高比例的O2a*應源自畲族。
惠州話屬客家話、粵語,或是另種粵方言?爭議甚大。惠州話比唐末-五代經粵北進入梅州一帶的“早客家人”年代還要古老,真正客家人大量進入惠州則更晚,所以惠州話應不屬客家話。從博羅橫嶺山遺址300余座春秋戰國墓出土的青銅器、銅甬鍾、編鍾和青銅鼎等判斷,其應屬荊楚文化類型,此說明在漢人到來前,東江中下遊符婁古國的百越原住民曾被來自于楚地的荊蠻所替代,荊楚文化成了主導。到了漢代,漢文字夾帶著古粵語沿東江水系推進,“城”居荊楚人及鄉下百越原住民在學習漢文字的過程也就實現了古粵語在東江流域的傳播,惠州話或惠(州)河(源)方言因此形成。盡管東漢末(公元217)交州已東遷番禺,但估計進入三國時,白話的強勢推廣可能就中止了,因此,東莞話、惠州話等差異大的面貌未獲根本性改變。對照《楚辭》,惠州話殘留有古楚語底層用詞,如睇(看)、掏(綁)、督水(告密)、桶笃(桶底)、一笃屎(一堆屎)、揞(遮掩)、戆(傻)、仡失(吝啬)、低D(知道)、谷(乳房)、奶(媽媽)等(據吳定球)。白話人大概能聽懂三四成惠州話,惠州話應屬粵語方言。惠州話與客家話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分,是因爲都混融有古楚語成分,古楚語是惠州話的底層,而客家話中的古楚語成分應源于其融合的畲族語言。
五、白話-粵語
西漢時漢武帝平定了南越國,在公元前106年至公元217年有三百多年在西江中遊的廣信設置管轄嶺南九郡的交趾部及交州治所,並沿西江水系的上遊及下遊兩個方向開始了兩廣白話的推廣,上遊白話區到達南甯甚至進入越南境內,下遊到達東莞、深圳及香港。東漢末(公元217),交州東遷番禺,而廣府民系的粵語化在交州東遷前已基本定型。
當今的白話,如果以廣州西關口音爲標准,白話的差異大概是:廣州<香港-澳門<肇慶-佛山<梧州<南番順-中山-珠海<封開羅董(漢代活化石)<懷集-廣甯-清遠-從化-增城<羅定-雲浮-新興<湛江-信宜-高州-化州-吳川-廉江<東莞<南豐(西漢活化石)<岑溪-容縣-貴港-南甯-北海-欽州-玉林<合浦-靈山<陽春-陽江<新會-台山-開平-恩平-鶴山-鬥門<惠州。白話的推廣與西江水系的交通便利有關,潭江及漠陽江流域因不能與西江直接溝通,且人口多于南宋以來經粵北珠玑巷驿站南遷,造成四邑話差異較大;在融入廣府民系方面,鑒江流域之茂名-湛江地區,古時屬高涼俚僚土著,也因不能與西江直接溝通,晚至唐初才完全融入廣府民系;珠三角的順德等地雖近鄰廣州,但可能是由于成批成群的入粵定居者多在宋朝以來,所帶入的語言與唐前中原已有較大差異,在粵語化不徹底的情況下,所形成的當地土白話與廣州話也有一定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