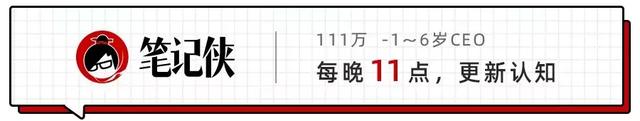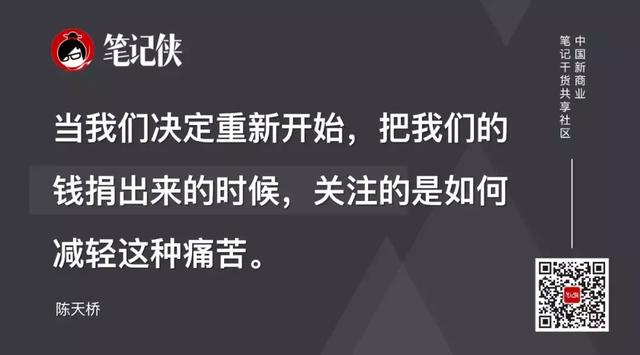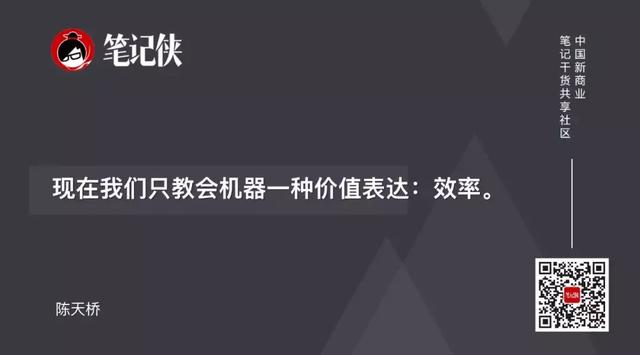內容來源:內衆生皆苦,不如自渡。創業邦(ID:ichuangyebang)首發,筆記俠經授權發布。封面設計 & 責編 | 麗麗第 3877 篇深度好文:7128 字 | 18 分鍾閱讀
精選筆記·科學
本文優質度:★★★★★+ 口感:紅豆
筆記君說:
26歲白手起家,創立盛大,31歲公司上市,成爲“中國最年輕的首富”,陳天橋在事業如日中天時突然長時間消失,現在專注于腦科學研究的公益事業。
緣何做出這樣的選擇,他對創業、科學、宗教、心理又有何看法?
以下,enjoy~~
作爲盛大網絡董事長兼CEO,陳天橋是中國互聯網史上繞不過去的重要人物。
1999年白手起家,他和妻子、弟弟等人在上海一套三室一廳的公寓裏創辦了上海盛大網絡發展有限公司。
陳天橋和妻子雒芊芊
2004年,盛大獲得軟件銀行集團4000萬美元的融資(這是當時互聯網領域最大的投資),同年,盛大在納斯達克上市,陳天橋也以88億資産在《胡潤2004IT富豪榜》中排名第一,當年,他31歲。
當時,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還不是阿裏巴巴或者騰訊,而是陳天橋的遊戲運營公司——盛大網絡,在這個位置上,盛大甚至保持了近5年時間。
不過,陳天橋“志”不在遊戲,之後,盛大奇襲新浪,折騰“迪士尼互動娛樂傳媒帝國”和平台戰略。但盛大的基因裏實際上就沒有平台,哪怕把旗下遊戲、文學、視頻等業務用戶全部打通,也只是一個個分散的Zynga,而不Facebook。
之後,盛大定位從內容公司專爲技術驅動型公司(支付、雲計算、精准廣告投放),2009-2011年又沖上了一個小高峰,但2011年後業務整體下滑。
拼盡全力推出的盛大盒子被廣電一紙文書叫停,文學板塊賣給了騰訊,遊戲也慢慢拼不過網易、騰訊。最核心的原因是:陳天橋生病了,患上了“驚恐發作”。
這種病的英文名叫Panic attack,爲急性焦慮症狀之一,患者會突然出現強烈的恐懼症,感到“死亡將至、大難臨頭”或“失去自控能力”的體驗,同時伴有呼吸困難、心悸、胸痛或眩暈、嘔吐、出汗、面色蒼白、顫動等。
每次可持續發作幾十分鍾,過程非常痛苦。有些人甚至會連續不停地發作。
Panicattack在長期工作壓力過大的創投圈或剛剛失去親人的人群中發生概率不低,但很多人對這種病症缺乏了解,發作後被送到醫院也不知道自己其實經曆了驚恐發作。
輿論導向這塊石頭更是亞得陳天橋喘不過氣。那時候發生了傳奇玩家玩遊戲致死事件,還有玩家因爲裝備問題跑到盛大公司自焚,數以千計的中學生因玩遊戲荒廢了學業,連人民日報都以頭版批評盛大。
這對從小就是學霸,對遊戲無感的陳天橋來說,心裏十分委屈。
他內心十分渴望大衆能夠承認自己,而不是被貼上“電子鴉片販賣者”的標簽:“我年納稅過億,卻沒辦法昂頭挺胸的向大家說出這件令人自豪的事”。
2010年,陳天橋攜家人移居新加坡,將盛大私有化,同時出售其在子公司的股份。
之後,陳天橋又被檢查出癌症,他開始賣掉盛大所有運營業務,轉型做投資,並將“腦研究”作爲了事業的下一站。
爲此,2016年陳天橋捐助10億美元致力于神經科學的研究。
據統計,這筆錢捐贈是中國富豪在全球著名學府前沿科學領域的最大筆捐贈,陳天橋計劃捐贈十年,每年捐贈一億美元,希望幫助那些和他一樣遭受過痛苦的人。
筆記君注:其中,包括他和妻子雒芊芊用于建設陳氏研究院向加州理工學院捐贈的1.15億美元,這1.15億美元,是人類在基礎學科研究方面獲得的最大一筆捐贈。
自此,陳天橋和妻子雒芊芊從新加坡搬到了硅谷,監督其捐款的使用,並在San Jose買了兩百畝地的一個校園作爲研究基地。
陳天橋在外媒Medium的采訪中,談到了他投巨資成立“陳天橋和雒芊芊腦科學研究所”推動腦科學研究的種種心路曆程,也談到了佛教信仰和大腦研究之間的關系,科技造成的問題需要科技來解決的邏輯,以及他對人工智能的看法。
涉及創業、科學、宗教、心理及哲學。
以下是陳天橋接受Medium(以下簡稱M)采訪的訪談要點:
一、壓力
M:隨著盛大的出現,你很快就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你也談到,在管理企業時感受到了強大的壓力。
陳天橋:我在1999年創辦了公司,我們花了三年的時間專注于業務。剩下的時間裏,我一直在壓力下掙紮。
即使是在2008年,當時我們的股價達到了曆史最高點,我也並沒有感覺好一點。在2009年,我們籌集了12億美元把遊戲業務分拆出來。公司發展很好,但我想我心裏一定有什麽東西積累起來了。
當然,我的妻子總是一直在陪伴我,這對我幫助很大。但我還有1萬名員工,他們都指望著我。
我還記得有次正在睡覺,大早上,我的一個同事打錯電話,給我撥了過來。
然後,我突然驚醒,心跳也變得很厲害,砰,砰,砰。還有一次,在飛機上,我突然覺得自己心髒病發作了,但這不是,而是一種驚恐發作。
所以我意識到,我身上可能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2010年,在我的驚恐症發作後,甚至癌症也被診斷出來之後,我們決定搬到一個新的環境中去。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我想我的整個人生都開始改變了。
M:離開自己建立的公司,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嗎?
當然,這對我來說非常難。在我搬到新加坡後,我們至少花了2到3年的時間來適應。
我會回頭看看中國,看看這些競爭對手,那時候我把他們看作是第二梯隊的參與者。他們逐漸地來占據我們的市場份額。你想回去,即使你知道你不應該回去,所以我內心非常掙紮。
但我一直在跟我的妻子討論,她也一直在鼓勵我。她說,大多數人只能爬上一座山,但也許你可以爬上第二座、第三座。我可以開啓我的人生新篇章。
許多人沉溺于過去的成功,他們認爲這就是他們擁有的一切。
所以我總是和我們這一代的企業家交談,告訴他們,“你的生活不僅僅是這家公司,請擡頭看,你可以看到許多有趣的東西。”
但我能看到,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在掙紮,因爲競爭,因爲各種壓力,他們的生活非常緊張。
二、宗教
M:現在你是一個佛教徒,這是你重新選擇的一部分嗎?
陳天橋:坦白說,在此之前,我並沒有真正相信宗教。
我的妻子會和一些佛教大師交談,我總是說:“不要浪費時間。”但是當我36歲的時候,我被診斷出癌症,那時候我意識到佛陀說的是對的。
我有很多錢,我擁有我想要的一切,包括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但是,爲什麽我總是感到不快樂呢?爲什麽我有恐慌症?爲什麽我總是沒有滿足感?
佛陀說,我們必須在內心尋找答案。
事實上,生活中的每個人都在受苦,這也是佛陀教導的基本原則:生命是痛苦的。
許多人不相信這一點,但生命的確是一場苦難,因爲即使你有了快樂,有了漂亮的房子,也終究會失去這一切。最後,你必須面對死亡。最後,你必須經曆這種痛苦。即使在這一刻你是快樂的。所以我說,“這是對的。”
所以,當我們決定重新開始,把我們的錢捐出來的時候,我們關注的是如何減輕這種痛苦。
當我們選擇這樣做的時候,一些人說:“不,不,不!你爲什麽選擇痛苦?疼痛是一種症狀。你應該治愈疾病,因爲沒有疾病,就沒有痛苦。
我告訴他們,“不,疾病也是一種症狀。”疾病是死亡的征兆,疾病是通往死亡之路。死亡是我們生命中唯一的疾病。我們必須承認,死亡不是我們能治愈的。即使在硅谷,也沒有人敢說能夠做到。
所以我認爲,如果你能治愈生命的痛苦,這是治愈死亡的最好方法。如果死亡沒有痛苦,那就像人睡著了一樣,而治愈它的方法就是學會接受它。
最後,我們認爲,死亡和痛苦是我們未來應該關注的焦點。之後我們去見了許多科學家——到目前爲止,幾乎有300名科學家。
三、科學
M:你知道科學研究的重點是神經科學嗎?
陳天橋:神經科學是理解我們大腦的瓶頸,但這並不是唯一的部分。
我一直告訴人們,盡管我們關注的是神經科學,但我對這個研究所的看法是,這是一個與大腦和精神相關的不同學科的垂直綜合研究所。
所以不僅包括神經科學,還有精神病學,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神學等等。我想把所有這些不同的學科結合在一起,但到目前爲止,我看到了神經科學的瓶頸,因爲我們試圖通過科學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方式。
幾千年來,我們一直問自己:我們是誰?我們爲什麽痛苦?真正的幸福是什麽?意識是什麽?我認爲自上而下的方法來自于宗教,哲學,社會學,以及所有這些。
甚至在幾千年前,哲學家們也問自己這些問題,沒有人能阻止你這樣想。但是自上而下的方法面臨著一些問題,因爲現代人總是說,“給我看看。”
M:是的,他要看證據和數據。
陳天橋:是的,“告訴我確切數字”,神經科學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學科。
讓我們以精神病學爲例,到目前爲止,精神病學診斷仍然主要依賴于面談,它仍然是主觀的。
我和精神科的院長交談:“你什麽時候可以安裝成像?什麽時候可以安裝某種生物標記來檢測抑郁症?”我覺得我有一些精神障礙,我相信一定有什麽不對勁的地方,一些化學物質或者我大腦裏的東西。
舉個例子,當我坐飛機的時候,我其實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我知道這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我還是很害怕。
但我吃了一片藥後,恐懼感就不見了。這就是所謂的恐懼,精神抑郁,你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來檢測它,但它就像精神科疾病一樣停在那裏,沒有進展。
神經科學是理解我們大腦的一個瓶頸。
我對此非常失望。我們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檢測到癌症。但到目前爲止,大腦和精神方面的研究仍然和50年前一樣,沒有進展。所以我認爲,這是我們做這件事的合適時機。
四、慈善
M:爲什麽通過慈善的方式?10億美元是一大筆錢。爲什麽選擇這種方法而不是進行投資?
陳天橋:我們研究了不同的方法,來改善一些慈善投資的方式,但我認爲對于大腦和精神領域研究來說,必須選擇一個非盈利性的方式,因爲我們缺乏對大腦的一些基本方面的理解,這是一個瓶頸。
所有這些研究都還在大學或研究所,這些都是非盈利組織。
舉例來看,埃隆•馬斯克曾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初創公司Neuralink能夠實現將芯片植入大腦。我們和加州理工學院的神經科學家談過,他們說不可能,那是50年以後的事了。
我們想要給科學家提供基本的支持,我們想要解決根本問題,不是只有賺錢能讓我們滿足。
五、投資
M:關于大腦和神經科學領域,你也參與了風險投資。在這些領域,哪些領域你看到是在增長的?是藥物嗎?還是腦機連接?
陳天橋:就像我說的,這是基礎研究,這是由人類的好奇心引發的,人類喜歡尋求真理。但是,在基礎研究發現的基礎上,我認爲它可以滿足人類的三種需求。
第一個我們稱之爲大腦治療,處理一些快速增長的精神障礙疾病,我認爲這將是未來的一大挑戰。
不僅是精神障礙,還有神經退行性疾病。隨著我們的年齡越來越大,老年癡呆症和帕金森症,這些類型的疾病總有一天會到你身上。
抑郁症已經成爲頭號疾病,我想我們可以幫上大忙,我們真的相信,在未來的10到20年裏,基礎研究將爲這一領域做出很大貢獻。
下一階段是“黑客大腦”,只有當你這樣做的時候,才能顯著提高滿意度和幸福感。
第二個問題我們稱之爲大腦發育。我認爲,如果我們真的想要造福人類,我們必須了解我們自己,然後讓汽車,房子等一切事物能夠讀懂你的想法,讓這個世界滿足你。
可以通過基因編輯改變你的身體,我認爲這些都是未來的殺手級應用。
第三個是我們的終極願景。我們試著回答這些比較大問題,比如什麽是意識?我們是誰?什麽是真實的,什麽是虛擬的?這似乎太學術化了,但對我和許多人來說,這真的很重要。
幾千年來,這些一直都是全人類的終極問題。我想我們這代人可能會發現這個真理,也許我們是幸運的。
六、哲學
M:世界只是感知?
陳天橋:這是另一個哲學問題。世界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我真的相信世界是虛擬的。
因爲如果我們的眼睛,我們的肉眼,能有顯微鏡那樣的功能,當然,顯微鏡比我們肉眼更真實,對吧?
當我看到你的時候,應該看到的是細胞裏的原子,我可以在空氣中看到有多少個水分子,這裏有多少氧原子在周圍漂浮,這是真實的。但我看到的是經過我們的肉眼編輯的東西,這是知覺。
另一位科學家,我們的導演大衛·安德森,他可以操縱老鼠的情緒。當他打開一個按鈕時,鼠標突然變得非常平靜;當他打開另一個時,老鼠突然就會打架。
所有的攻擊行爲都是由一組神經元控制的,這是我的另一個假設——我們是化學機器人。
在未來,也許我可以戴上頭盔,下載一些軟件,這個軟件可以激活神經元——也許我可以爲你創造一個世界,這是有可能的。
M:你認爲這是一件好事嗎?
陳天橋:我只說事實,沒有好壞,沒有價值判斷。當然,好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現在我想告訴你們的是技術,尤其是神經科學技術,在未來會有多麽強大。
七、人工智能
M:我們看人工智能,目前的方法似乎是收集和挖掘盡可能多的數據。但這不是人類認知的工作方式,而且似乎已經遠離了人類大腦的模式,把人類從這類工作中移除是一個錯誤嗎?
陳天橋:人工智能已經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比如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沒有人否認這一點,但我們不應該僅僅滿足于這些。
我總是用我兩歲大的兒子舉例子,他總能在街上認出這是一個叔叔還是阿姨,他永遠不會叫錯,但是一台電腦必須經過數百萬次的訓練才能知道“這是一只小貓,這是一塊餅幹。”
現在我們只教會機器一種價值表達:效率。
機器提高了效率,機器總是知道如何快速找到最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機器統治世界,它會說,“殺死所有的老人和病人,因爲他們對于資源是一種負擔,對吧?”
所以我們必須教會機器公平和同情,但是當我們都不知道如何定義的時候,如何教會機器呢?
M:有些人擔心人工智能將成爲一種威脅,你害怕機器人統治世界嗎?
陳天橋:我認爲可能存在有兩種威脅。
一是機器人會搶奪人類的工作,但我不認爲這是一個很大的威脅,科技將爲人們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可能會有一些痛苦,他們可能需要時間來接受教育或訓練,但對人類來說,我們會適應。
第二個擔憂是,機器人可能會進化出意識,然後超越我們。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因爲它們已經計算得比我們快得多,但他們仍然沒有任何意識,一定存在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奧秘,就像一台沒有裝對軟件。
也有些人說,機器有機器的權利,就像人類有人權一樣。他們有變得更聰明的權利,我們不應該讓機器實現人類的價值體系。也許有一天,機器會變得有自我意識,他們也應該有自己的權利。
我認爲,可能是,但那將是一個新物種。爲什麽我們要煞費苦心去創造一個新的物種呢?地球上有如此多的人仍在遭受痛苦和饑餓,許多物種仍然面臨滅絕,爲什麽要去創造新的物種呢?我認爲目前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是非常混亂的。
八、虛擬現實
M:你剛剛提到對虛擬現實非常感興趣,作爲一個在數字娛樂領域發家致富的人,你如何看待塑造未來的方式?
陳天橋:我一直說虛擬現實的終極版本是夢想。我們的大腦足夠強大,可以創造出一個虛擬的現實,可以模仿現實的聲音和感覺,這是最令人驚歎的。
所以我想,爲什麽我們必須依靠谷歌頭盔?我們對自己的大腦知之甚少,如果我們能控制自己的大腦,繼續做夢,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感受?每當我從一個好夢中醒來時,我總是很感到很低落。
如果我能在晚上繼續我的夢呢?如果你能繼續做夢,那將是一個巨大的産業,我一直說那將是娛樂産業的終結者。
我已經請教了科學家,包括我的研究所,是否能模擬感覺。
目前,你只能模擬聲音和視覺效果。如果你能感覺到什麽,那麽大腦就可以模仿一切。所以我認爲虛擬現實的最終版本應該來自我們的大腦本身,因爲它是如此強大。
M:我們已經討論了技術對我們的幸福可能帶來影響。如果我們能在虛擬現實技術上做到這一點,是否會有風險?會使情況變得更糟嗎?
陳天橋:我認爲這只是增加了趨勢,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比如,我年輕的時候,在中國的開放和改革之後,很多電影都是從香港和美國引進的。它開辟了一個新世界。
那時候我是個好孩子,我媽媽唯一一次責罵我的時候,是我在朋友家裏看電影的時候。
她說,“你爲什麽看這些東西?他們會讓你沉迷,他們會讓你……。電視連續劇,電影,他們會給你介紹壞的東西,讓你不去學習,不去上班。”
然後,在我們這一代,每個人都做了同樣的事情。當我在盛大的時候,我的用戶的父母,他們每天都批評我,說我們的産品讓人上瘾。
我認爲,如果技術更加生動,這一趨勢將會得到加強。你總會發現有些人對它上瘾,就像一個藥物。這種藥物是如此的強大,它可以控制你的大腦,讓你感到快樂。
但如果它和藥物有同樣的效果,我們的政府可能已經有了監管了。我認爲,即使VR能産生更多讓人上瘾的東西,我們也可以把藥物監管作爲基准,我認爲它可以被監管。
總結
M:最後,你對我們的技術和腦科學的發展方向感到樂觀?你認爲我們能讓自己變得更健康、更快樂嗎?
陳天橋: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這就是爲什麽我有點悲觀的原因。
我認爲技術産生了很多問題。我所能做的就是嘗試用科學的方法來減輕這種技術的可能後果。但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可能會導致非常糟糕的後果。
*文章爲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加入筆記俠官方圈子,與牛人一起交流進步,付費圈子&免費圈子 都有好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