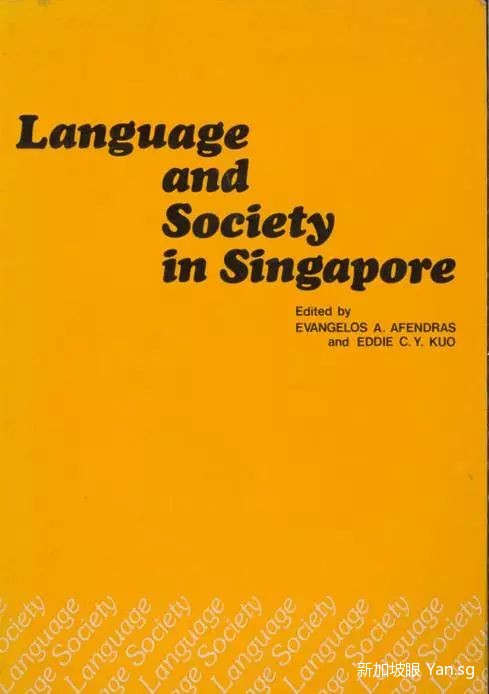前言
1973年我應聘到新加坡大學(當年簡稱新大)任教,最初簽了三年聘約,後來續約三年,之後又續約三年,然後就留下來。如今算來竟是45年了!這45年來,一直在教學研究的學術園地裏努力做個盡職的園丁。70年代加入第一代社會學的團隊,從當年的武吉知馬校區到改名爲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肯特崗校區,開拓新加坡社會基礎研究。1992年應南洋理工大學詹道存校長之邀,西遷雲南園,創辦傳播學院。2003年又應南大第二任校長徐冠林之請,籌劃成立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協助南大轉型爲綜合性大學。2008年加盟新躍大學(現稱新躍社科大學),于2012年成立“新躍中華學術中心”,開始回歸文化原鄉的尋根之旅。
回顧這45年的學術生涯,自覺很幸運,一直有機會開拓學術園地,從墾荒,破土,到播種,灌溉,最後還能和一批一起出汗出力的朋友,收獲豐碩的果實。人生有此機遇,不能不感恩。
感恩之余,老園丁“鬓已星星也”,是到了安坐杏壇、置身學園綠蔭下聽雨的時候了。當然,南國的赤道雨,不似南宋江南春雨,“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蔣捷,詞《虞美人》】。回首前塵,有風雨相伴的日子,更不缺那雨後的彩虹。南國杏壇聽雨,有回音,有回響,仔細聆聽,或許還有羽音陣陣、余音袅袅。
初識新加坡
(一)
1973年6月,我和妻兒一家四口,告別美國威斯康辛州清水市(威斯康辛大學清水校區所在地Eau Claire ),啓程回歸亞洲。第一站到蒙坦那州波茲曼(Bozeman),探望海菲妹一家,也一響夙願,暢遊黃石公園;然後經過洛杉矶,檀香山,舊地重遊,探望老友。最後經東京回到台北,停留兩周,拜望雙親四老以及老同學老友。六月底經香港于六月29日飛抵新加坡巴耶裏巴機場。(當年沒有長途直航客機,短程轉機乃是常態。)
代表學校來接機的是社會系同事陳壽仁,是系裏一位資深(也是當時唯一的)本地學者,後來共事多年,也合作了幾個研究項目。
當晚壽仁把我送到校園旁Nassim路口的大學招待所,那是二戰前的老建築,相對簡陋,晚上挂蚊帳點蚊香,在蛙鳴和蟲聲中入眠。次日早起推門而出,頓覺青天白雲鳥語花香,好一片南國風光。原來這武吉知馬校園,緊鄰新加坡植物園(2017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名錄),而社會系館所在,就在隔Cluny Road山坡上獨立的House 11(11號樓),是一棟1920年代的老建築。據說這曾是萊佛士書院時代副校長的住宅,是座獨立洋房,屋後有仆人(想來包括幫傭,司機,廚子等)住處以及廚房車庫等,看來風水不錯。只可惜這片舊校區多年前已經劃歸給植物園,第11號樓也早已拆除,不見蹤影了。
武吉知馬校園
7月2日星期一,我依約到社會系報到。按在美國工作的習慣,我准時8點到校,第一個見到的是同事簡麗中。據她後來的回憶,我當時穿了一件紫色無領的T恤。她批評我說:哪有人第一天到大學報到這樣穿著的!我回想起來,也不能了解當年爲何如此隨便。其實我無意冒犯,只是在美國校園隨意慣了,真沒有用心。
簡麗中來自香港,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社會學博士。當年柏克萊是美國自由主義大本營,新大聘用她,我覺得是開放的象征。在第11號樓,我和簡麗中辦公室相鄰,牆上開了小窗口,共用一個電話分機。我們又都主修家庭社會學,曾經合作開課,又合作多項研究計劃,出版專書和論文。她先生黃朝翰是新大經濟系同事,兩家都住大學College Green 外來教師宿舍。兩家稚齡小孩,年齡相近,在大雜院一起長大,可說是通家之好,如今算起來是45年的情誼了。她在80年代從政,當選國會議員,90年代被延攬擔任官職,曾官至教育部和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巧合的是,2010年我從南大退休,到新躍大學(現在的新躍社科大學,簡稱躍大)擔任學術顧問,和同任顧問的麗中再次同事,而且辦公室又是毗鄰而處。她後來榮任躍大名譽校長(Chancellor),是新加坡各大學中第一位女性名譽校長。我這老友與有榮焉。那是後話。
(二)
新大的社會學系創立于1965年,和共和國同年。創系系主任Murray Groves,來自澳大利亞,是位文化人類學者。原來在英國學術傳統中,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密不可分,和美國二者泾渭分明情況大不相同。新大社會學第一年基本必修課是Soc101社會學概論和Soc102人類學概論。我也開始和人類學同事交流學習,接觸到他們“接地氣”的田野研究,有別于社會學偏重調查及統計分析的做法;讓我大大開拓了視野,獲益良多。
我1973年加入新大社會系時是第二任系主任Hans Evers當家。Evers來自德國(當年還是西德),主修發展社會學和東南亞研究。他1971年到任,大刀闊斧擴展社會系陣容,從原來5,6人,增加到10人,其後幾年大約維持在10-15人之間,其中不少是短期(一到三年)訪問學者。Evers自己也只來三年,1974年就另有高就,回西德了。他多年來還是活躍于學術界,經常來訪。
當時的社會系非常國際化,除了英美澳德之外,還有來自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及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的同事。只有兩位是新加坡本土學者。和早期(1970年以前)純然“西方”學者主導的情況相比,到了70年代,有本土和港台及大馬學者加入,或可說是“去殖民化”的第一步。不過嚴格說起來,系裏同事都受過歐美(特別是美國)一流大學社會學的完整訓練,教材內容以及理論體系,基本上都來自歐美,嚴苛說起來,是“代理殖民化”。要“去殖民化”,談何容易。真正本土化的落實,至少要經過一個世代的反思覺醒之後,才看得出成效。
新加坡大學原屬大英聯邦教育體系的一部分,學制和美國大有不同。首先,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本科采用三年制,學滿三年畢業,可獲得學位。少數優秀學生(約20%)可繼續進修榮譽學位,一年畢業後依成績可以獲得一等,二等,或三等榮譽學位。畢業後就業職位薪金高低通常依學位成績而定。因而學生對考試和分數非常重視,因爲這關乎一輩子的事業前途。新加坡社會一向重視考試和成績,早年申請工作,甚至還要求小學會考成績!當年的學制和文官制度如此,如今教育當局要“翻轉”觀念,不以學位和成績定終身,只是積習難改,遺毒難消,“翻轉”還需努力。
英國學制還有另一驚奇。大學課程采學年制,學生每年選8門課,每門課上足上下學期,30-35周課程,一年一次學年考試,學生必須8門全數及格,通過年級考試,才能升級進修下一年度課程。只要有一門課不及格,就要重修所有8門課程!我初來時非常不解,詢問之下,才知道在此一制度下,所謂考試及格,指的是通過整個學年考試,包括所有課目。通過學年考試,全數及格,大一學生才能升爲大二學生!
(三)
我當時教一門大二必修課“社會研究法”,是要求較多難度較高的一門課,每年總有幾位學生被“當”掉。每年決定最後成績,我總是猶豫再三,非常不忍,因爲“當”他們一科,他們就要多讀一年。這個不合理的制度,要到1990年代,新加坡兩所大學步向“美國化”,改采學分制之後,才糾正過來。
談到我教的研究法,由于課程性質,內容偏于抽象枯燥,但是這又是一門訓練邏輯思維基本功的必修課程。我接受挑戰,在課程中強調推理邏輯,也要求學生實際操作,要能發掘研究課題,設計研究方法,進行田野觀察訪談,分析資料,最後完成研究報告。多年之後,偶遇早年學生(如今多已退休!),談起這門社會研究法,還得到回饋說印象深刻。看來這門課還算教得成功,很覺欣慰。
我那個年代教的學生,資質都很優秀,原來那時大學生人數只占同年齡人口的百分之三,根據人口智商常態分配曲線,都是“精英”,和今日努力培養25%年齡層進大學的“普及”模式,大有不同。然而,更讓我訝異的是,有不少學生來自普通甚至弱勢家庭,學生中有母親爲洗衣婦,父親爲司機者,辛苦培養優秀子女上大學,令我印象深刻。那個時候新加坡社會發展剛起步,各方急需人才,這段時間應該是新加坡社會流動性最大的年代。到今日,40年後,社會階層趨于定型,甚至僵化,世代間的流動性反而緩滯了。
談到社會研究法,當年還有一個難忘的經曆:1976年9月9日,“偉大舵手”毛澤東過世,我當即指派學生進行一研究項目,調查民衆信息來源及傳播路線:從何處得到此一消息?何種媒體?何時何地?是否轉告他人?這是效仿早期美國總統肯尼迪受刺身亡後,傳播學一個經典研究。我想借毛氏之死,探討新加坡社會人際信息傳播的模式,或可做比較研究。當時我指定學生采用quota sampling(配額選樣),到烏節路等公共場所面訪公衆。三天之後,系主任陳壽仁找我談話,問起此事。原來“有關當局”發現新大學生的這項調查活動,表示“關注”。看來我是踩到了紅線,不過關切之余,倒沒請我去喝茶,想來這位郭某還算動機純良無不良記錄,給過了關。至于有沒有留下什麽檔案記錄,就不得而知了。我這份曆史性的調查資料,終究沒有發表,現在還埋在書房某處的資料檔案中,見證第一次和“有關當局”的邂逅。
當年我教的另一門課是榮譽班的“大衆傳播和社會發展”,是當年當紅的發展社會學中一個重要課題。據我所知,這應該是新加坡的大學首開大衆傳播課程。而19年後,1992年,我應邀在剛成立的南洋理工大學創立傳播學院,在當時是無法想象的。
(四)
新大社會學系當年在系主任Evers領導下,建立了社會學的研究傳統,也成就了他立志要建立一個“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強社會系”的豪語目標。
當年具有影響力的一項新傳統,是每周三下午的“學術研討會”(Research Seminar),除了本系教師和研究生輪流做研究報告之外,也邀請過境學者以及其他學系同仁分享研究心得(當時經濟系的林崇椰和政治系的陳慶珠都曾前來做報告) 。那時社會系的研討會很受重視,每周三來自其他學系的旁聽人士不少。這樣的聚會,一方面讓大家交換研究心得,另方面也無形中對一些年輕學者施加壓力,要努力准備上台報告。更重要的是在系裏建立一個非常正面的研究文化研究風氣,大家能坦然分享心得,互相切磋。或許是70年代80年代大學校風學風較爲純良,我很懷念那時同仁問學問道的樂趣。
那時學術研討會有兩件事讓我印象深刻。一是有位研究生提出Hawker centre(小販中心)的研究報告。她在開場白之後,很慎重地努力在黑板上寫了兩個中文字:“小飯“,說明原意是little rice,是販賣食物(小吃)的地方。這是我初次接觸體會(新大)大學生如此中文水平,令我心驚。
還有一次是一位人類學學者在研討室討論演化論,只見窗外幾只猕猴探頭探腦,似在探班。一時傳爲“佳話”,是社會學系口述曆史常提到的一個“都市傳奇”(urban legend)。其實第11號樓緊鄰植物園,經常有猕猴來訪,只是那次探訪碰上演化論討論,自由自在的猴子,對比關在窗內的人類,難免令人有種時空錯亂的感覺。
(五)
我們這批第一代社會學者當年教學時首先面對的挑戰是新加坡社會基本資料的匮乏。無論是人口,婚姻,家庭,宗教,種族,教育,社區組織,社會階層,等等社會學課題,都有待搜查(原始)資料,進行分析。有了這些基本資料,才能進一步深入探討社會快速現代化,都市化,工業化發展過程中面對的挑戰。早期同仁各憑自己專長,努力研究發表論文,可以說是邊教邊學邊研究。
以我個人而言,除了教學以外,作爲一位初學者,也非常自覺地努力做研究,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到新大的第二年(1974),我的第一篇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在美國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社會心理學學刊》)。那是我根據博士論文其中一章改寫的研究報告,主題是家庭和兒童雙語發展,用的是美國案例,卻非常吻合新加坡情況。系主任Evers很表贊賞,我自己也大受鼓舞。
我的新加坡研究,重點有二:一是家庭社會學,二是語言社會學。經過幾年的努力,終于在1979年和簡麗中(Aline Wong)合編出版The Contemporary Family in Singapore(《當代新加坡家庭》);1980年又和Evangelos Afendras 合編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 (《新加坡的語言與社會》)。前者收集了12篇論文,我署名的有三篇;後者包括論文11篇,我署名的也有三篇。兩本文集都由新加坡大學出版社出版。(Afendras來自希臘,當時在“區域英語中心”RELC任教,是當年少數研究語言社會學的同好。)
有了這兩本著作,基本上奠定了我在社會研究領域的基礎,自認對新加坡社會有了初步認識,可以自稱爲第一代新加坡社會學者而無愧了。
來源:怡和軒俱樂部
作者:郭振羽 南洋理工大學終身名譽教授、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
本文原題《初識新加坡》,發表于2018年10月27期的《怡和世紀》。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