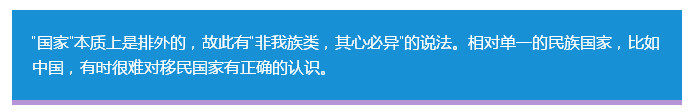上月中旬,應中國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邀請,參加了“外國文化官員訪華團”。此行15人,只有我一人是華人,其他14人,各色人等,基本不谙漢語,對中華文化認識也不深。此行下來,有幾點有趣的觀察。
在活動的第一天,大家作自我介紹,要簡單介紹自己的國家、職業。輪到我的時候,循例介紹自己所屬單位及職務之前,很自然地就先自報家門——“100年前,祖父因生活艱苦,從福建的一個叫‘金門’的小島下南洋,當時在新加坡謀生的除了中國人,還有印度人、馬來人、阿拉伯人等;我昨天從赤道100公裏邊上登機,飛了六小時抵達北京。”
爲何得先報家門?原因有二。首先,我是華人,但我卻不是中國人,而是與其他人一樣,是中國人邀請來的朋友,所以我有必要說明我與中國的關系,即:我的先輩是中國人,我是新加坡華人。其次,我的介紹簡單扼要說明了新加坡地理位置和人口概況。其他團員作了自我介紹之後,都由中方進行翻譯,我則選擇了漢英雙語發言,不需翻譯。
此後,團員凡有什麽事都愛找我,讓我幫忙跟中方溝通,反之亦然。到了一些文化場所,好爲人師的我也很樂意充當義務翻譯兼講解員。剛開始我還蠻享受這個角色,覺得自己有價值,但到後來,有時卻出現了一些尴尬場面。
一天中飯,坐我旁邊的尼日利亞代表跟我說,你幫我向服務員要筷子。我看了他一眼,說:“你不是能說‘筷子’了嗎?爲何不自己說?”他說:“我不是主人家啊,不好意思開口。”我哈哈一笑,他才反應過來,忽然醒悟我也不是主人家。
還有一次,有個團員自行脫隊,沒有參加活動。中方人員一臉嚴肅告訴我,你得跟他說,不能隨意脫隊。我也哈哈一笑,她才反應過來。我與那位仁兄同爲團員,自然無權對他作此告誡。無論中方或外方,有時難免誤把我當作中國人。責任在我,因爲我得意忘形,忘了保持距離。
這令我想起十多年前,在上海擔任駐滬商務領事時的一件事。爲了方便,我給中方發的所有公函都用中文,我見地方官員時也全程使用漢語。有一次上司訪華,他強調了兩點:第一,聯系工作的普通公函可以用中文,但是重要公函必須用英文;第二,平時聊天或談談簡單的公務可以用漢語,但是官方會見和重要談判得用英語。他的道理有二:首先,英文是我們的行政語言,我們要是選擇使用中文,如果辭不達意造成誤解,責任在我方;其次,在重要場合使用英語,除了避免前文所述風險,也有利于減少對方把我國當作華人國家的誤會。其實,李光耀1976年第一次訪華時,刻意帶上非華族部長,也是出于這個目的。
“新加坡人”這個身份認同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來的。我祖父母那一代人的青壯年時代是僑民身份,他們認同的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唐山”——中國。一直到我祖母晚年,她到老家金門探親總是稱之爲“回唐山”。
到了我父母這代人,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的是在新加坡本地,他們的情感歸屬和政治效忠,也自然是對新加坡。他們一直到晚年才有時間和余錢到中國旅遊,在此之前,“唐山”一直只是存在于他們想象中的帶點浪漫色彩的故鄉。
當然,我父母這代人當中還是有不少是第一代移民,仍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我記得念小學時,我的華文老師就說:“我們的國父是孫中山”。“國父”是什麽?“孫中山”是誰?我當時當然不知,但正是因爲不知而好奇,好奇而把這句話記得牢固至今。
第一代移民在政治身份認同上是尴尬的。一方面你已經宣誓效忠新加坡,另一方面,無論情感上、生活上、工作上,卻很難也沒必要與祖籍國割舍。兩國相安無事時當然左右通吃,但兩國鬧得面紅耳赤時,第一代移民又站到風口浪尖,本地人要說你的祖籍國幹嘛這樣?祖籍國的親戚朋友則說你投奔的那個國家幹嘛這樣?大有腹背挨箭之感。
大部分國家源自民族,從先民時代的民族部落發展壯大而成國家,之後再相互統合而成今日之列國。“國家”本質上是排外的,故此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說法。相對單一的民族國家,比如中國,有時很難對移民國家有正確的認識。最近羅家良大使與胡錫進總編輯的論戰中,就有中國人指責羅:“別忘了你是華人”。有趣的是,作此指責的人忘了,中國的五十六個民族中有朝鮮族、俄羅斯族、哈薩克族、蒙古族等。現在中國因爲薩徳問題指責韓國,那麽韓國是否能指責朝鮮族中國公民:“別忘了你是朝鮮族”?當年中蘇交惡時,蘇聯人是否能喊一聲:“別忘了你是俄羅斯族”?
儒家講“天下大同”。終我一世不會有機會見到這個理想的實現。但是,未來如果真實現天下大同了,料想屆時人們關心的是你這個人,而不會過于關心你的國籍和民族。
▼吃飯中
▼參加書法和國畫啓蒙班
(文:許振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