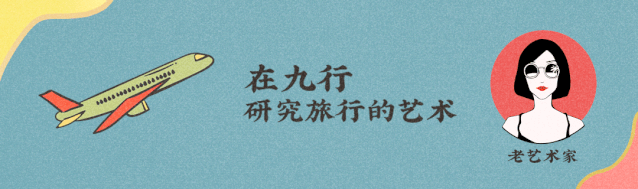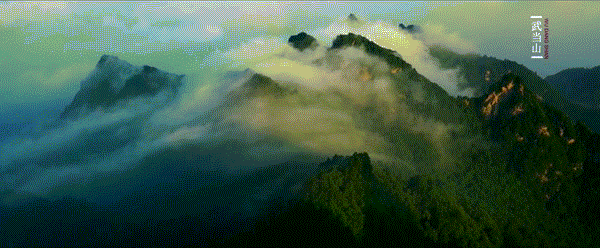有的人想“修仙”,有的人想逃離現實生活,有的人想回歸生活的節律感……
這些問題,並非上一趟武當山做義工就可以解決的。
到武當山道觀當義工,你要准備一份簡曆。
姓名、性別、身份證號和健康證明,這是最基本的,余下的你可以自由發揮:
英語四六級考試的分數,微信公衆平台運營的熟練程度,跑800米所用的時長,認識簡譜或五線譜,會洗菜和切菜,心態穩定到即使登上1612米的天柱峰也不會恐高,等等。
或者幹脆什麽都不點綴,道長會根據特長一欄的空白,“因地制宜”地分配給你技術含量要求不高的工作——去紫霄宮或太和宮的某一片區域掃地。
△紫霄宮 / 圖蟲創意
和武當山道教協會紫霄宮管委會主任王芳道長通過QQ聯系上、定好上山日期以後,你需要買一張火車票或者飛機票,准備足夠的衣服和驅蟲藥水。
秋冬季還要多准備一些熱水袋——武當山有著與海拔匹配的寒冷。
而道觀因易燃的木質結構,屬于特級防火單位,取暖設備難以令適應暖氣的城市人滿意,甚至你的Kindle和電腦都會被凍得開機困難。
△紫霄宮 / 圖蟲創意
跟看重學曆的企業單位或者看重經驗的NGO(非營利組織)不同,道觀錄取義工的標准是“隨緣”。
因此大多數申請者最終都能順利踏入義工宿舍,除非床位已滿——那只能說明你實在無緣。
“來一起開啓修仙之路啊”
1月24日,因爲新冠病毒肺炎的暴發,位于疫情重點地區的武當山封山,十堰封城。去年10月來武當山大嶽太和宮做義工的行李因此滯留。
在豆瓣和B站上持續更新“武當山修仙日常”的行李,經過6個月的適應,已經將在道觀的作息穩定下來:用道家養生早餐冰糖水煮蘋果開啓一天,偶爾侍奉觀內靈獸(流浪貓);
研習笛、箫、樹葉等多款民間樂器,制止衆多逃票、在觀內燒紙、亂丟硬幣許願的遊客“作妖”,參與冬季特有的“冰雪奇緣”鏟雪活動,還能免費領取鐵鍬一把,無限次體驗在風雪中禦鍬滑行。
△武當山的修仙日常 / 微博截圖
去年,人類學專業畢業的行李辭去做了5年的出版社編輯工作,在北京的胡同開了一個“快閃式”小賣部,用短短幾個月時間從令他感到迷失的工作狀態回歸柴米油鹽的生活。
作爲一個喜歡觀察不同群體、時常切換生活模式的人,行李從朋友謝九那裏聽說了武當山招募義工的信息,在他看來,這是想象之外的一種身份。
同時,在國內衆多招收義工的道教場所之中,相對于其他背景繁雜、難以分辨專業與否的道觀,武當山招募信息更公開透明,流程和管理也更正規、安全。
△紫霄宮招募義工的官方微博 / 微博截圖
一開始,行李憧憬這樣一座幽密的“人間淨土”式道觀:與世隔絕,道長們仙風道骨,在蒼松古刹裏靜聽晨鍾暮鼓,閑看雲聚雲散;日子清淡如水,彼此之間老死不相往來。
他甚至幻想會不會有高人教他掐訣念咒,或碰上奇幻際遇。
就連武當山太玄紫霄宮官方微博也在2020年武當山道教學院招生簡章的宣傳語中寫道:“來一起開啓修仙之路啊。”
由于武當道觀的被動曝光量大多來自武俠、玄幻作品,而主動曝光又相對低調,這種源于武俠小說和影視的斑斓想象,成了部分上山做義工的人的“誤會”。
有些義工去紫霄宮(紫霄宮是武當山道觀行政中心,也是招募義工的主要場所)體驗,有一種免費旅遊的心態。
武當山是5A級風景名勝區,道觀裏包食宿,齋堂的素食三餐還算豐盛,有免費的公共浴室和衛生間供使用,除了日用品要自己購買,基本可以承包所有生活需求。
愈熱情的人有時愈容易放棄。
隨興而至的太極功夫愛好者、看過金庸或梁羽生小說有“修真”想法的中二年輕人,以及從事教師、醫生等體面工作的人來到這裏,覺得每天掃地幹體力活兒很委屈,同時又要受觀裏規矩的制約,就會提前下山。
“像回到了農村老家,很鄉土”
提到“千層樓閣空中起,萬疊雲山足下環”的武當道觀,會默認它擁有落後于山下的生活節奏:網絡不夠穩定,硬件設施不夠宜人,需要種菜挑水自給自足,沒有過度社交。
用義工姑娘芋圓的話來說,“像回到了農村老家,很鄉土”。
芋圓是中國傳媒大學的大四學生,喜好古風文化。很久以前,她讀過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的《空谷幽蘭》,書中講述了作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親身探訪隱居在終南山等地的中國現代隱士的故事。
因此,芋圓想象中武當山的道士們也過著“隱士”般的生活。
△在山岩間隱隱約約 / 圖蟲創意
從霧霾陰沉的北京跨越1000多公裏的地理距離來到武當道觀後,眼前的情景卻讓她深感熟悉:台階上的涼席曬著藥材,黝黑的道長坐在低矮的板凳上聊天,陽光燦爛,糧食曝曬,像回到了鄉下老家。
義工的生活每天都遵循著相似的節奏,日複一日。
早上六七點起床,和道長們一同上唱腔優美但聽不太懂的早課,上午和下午分別進行3個小時的勞動:有時是掃地,把道觀裏的落葉、灰塵掃在一起;
有時是清理垃圾,可能會在某個香爐底掏出某個遊客虔心上供的猕猴桃;有時負責值殿,引導遊客們安全進出並合乎禮儀地跨越門檻;有時是采摘藥材(比如黃精),或者給午飯用的100斤蘿蔔擦絲。
△義工的活其實並不輕松 / 微博截圖
“上山下鄉”的農活重複了幾天,過慣了豐盛日子的芋圓覺得太無聊。
她在制作紀錄片《白日夢想家》時被工作夥伴指責“不懂真正的純粹是什麽”,因而賭氣上山,抱著“逃離原有生活”和“想看真正純粹的人到底是什麽樣”的目的而來。
她問道長爲什麽要安排自己做這些事,對方回答:“把你內心的事情掃一掃,還能增強體力。”
忽然有了大量閑暇時間,芋圓“閑得發慌”,還是選擇把時間托付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上山兩天後,她在手機上重新下載了VOA英語App,一邊除草,一邊聽有關特朗普的新聞——在遠離城市的陌生環境裏,仍要尋找一些熟悉的事來做。
從較低的工作強度和寬松的監督制度上來說,義工勞動更像一種戶外健身和放松。逐漸適應以後,芋圓發現,農活帶來的美的感受大于它帶來的疲勞。
在大殿工作時,她能注意到陽光微弱的偏移,周師兄吹笛子和高師兄伴唱的聲音會時不時飄進來。
“生活變得非常簡單”
最初跟行李提到武當山義工招募信息的謝九,也持有和芋圓一樣“逃離原有生活”的想法,在去年5月到紫霄宮做了一個月義工。
2014年,“全真道士梁興揚”成爲微博網紅,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大衆對道教的刻板印象,引發社會對該群體的關注。
和行李一樣也是人類學專業出身的謝九,從那時開始關注國內的道教組織,“在當代,這樣一個非常有曆史的組織會以什麽形式存在?我實在是有點好奇”。
△這位博主打破了大家對道士的印象 / 微博截圖
去年,負責一個“費心費力”的品牌公關項目的謝九因爲工作特別辛苦,自覺失去了對生活的掌控,早上起不來床,晚上睡不著覺,時間上的豐儉不再由人。
在無盡的事務讓她難以招架的時候,她思考究竟能不能找到一種生活方式,讓自己更關注生活的“節律”,“我希望自己(至少)有好的生活表象,不想混混沌沌”。
當時,她關注的紫霄宮官方微博每天都發清晨日出的照片,讓她覺得山上的生活是有秩序、有要求的。“比如早上6點你就是要起床,就是要去做事情。”
盡管市面上有很多治愈效果明確的禅修班,但在她看來,短期內人爲幹預的課程不太可能達到某種目的。
“比如我去山裏走一趟就升仙了?不可能嘛。”
到武當山道觀做義工,謝九想親身嘗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不只是截取其中的一個顯著片段,而是接受它完整的面目,“不是一種我刻意營造的實驗室般的小環境,而是本身真實存在的一種生活狀態”。
做義工後,一度在工作裏承受多方壓力的謝九感到“生活變得非常簡單”。
平時的生活裏,除去用手機主動獲取的信息,光是所處的主導環境和主導力量分配給每個人的信息就已經飽和了,也會發生大量社交活動,“面對社會這個龐大的信息體,我處于被大量信息規訓的狀態”。
而紫霄宮給予謝九的信息量,只有她平時生活的20%—30%。
△武當山風景 / 圖蟲創意
每天清早起床洗漱,謝九會聽到位于紫霄宮大殿右側那面大鼓傳來“咚咚咚”三通鼓聲,意味著早課即將開始。
穿好衣服出來,她會看到毫無遮擋的天空、朝霞、險峻的山脈,有些道長會很自然地搬起自己的腿,放在欄杆上壓腿——她感受到了久違的生活節律和秩序感。
掃地,也成了她每天投入、專心、視爲使命的工作。“掃地能讓你知道前一天晚上發生了什麽故事。”謝九說。
遊客沒來之前她已經拿起了掃把,因此頭一天晚上刮的風,被風刮來纏在樹枝上的風筝,野鳥打架後留下的幾根羽毛,松鼠留下的糞便,等等,這些發生在昨夜的故事都被她率先得知。重要的是,在井然有序之下,她重獲一種有余力關心生活細節的閑暇。
△紫霄宮的魚,也是自由自在 / 圖蟲創意
除了信息量顯著減少,在工作裏常要和人打交道的謝九體察到了另一重“簡單”:社交壓力簡直爲零。
這裏有更多的空間讓她可以用想要的表情生活。
以前她負責一個項目時,臉上要調動豐富的表情以應對各方關系,“社會生活不允許你沒有表情啊”。但在道觀裏,面無表情就是被允許的,想笑的時候可以笑,不想笑的時候不用笑。
△紫霄宮前的道士們 / 圖蟲創意
這裏的道長和義工們不會勉強自己社交,即使冷如冰山也無妨,形成了比較自我的狀態。
受此感染,曾經在田野調查裏喜歡抓著每個對象問一大堆問題的謝九也減少了好奇心和窺探欲,更專注于自身——對于那個每天到山頂獨自練功的外國男人,她一個字也沒問過。
“道長們照此生活,
義工們只是短暫經過”
盡管大家每天都一起上早晚課,一起勞動,芋圓坦言:“義工跟道長們的生活始終隔著距離,我只是體驗了其中的一部分生活。”
山上忌諱問道長們從哪裏來的問題,因此不能進一步了解他們;芋圓看到他們認真上經文課的樣子很棒,但因爲並不感興趣,她自己不會去上課,“我只是選擇性地接受有關道教的東西,體驗到的道觀生活是很淺的”。
道長們常常會練琴、練劍、練習如何使用拂塵,晚上的書法課會研究《周易》《道德經》,義工如果願意的話,可以一起學習。
“但即使我們跟道長們一起聊cosplay,聊微博熱點,聊二次元,做差不多的事情,也只是短暫的過客。他們是真心向道,以此爲業。”
相對新道徒來說,義工的招募要求並不嚴格,要的只是對道教文化感興趣、有閑暇時間的社會人士。因爲心向修行,道長們更能從根本上長久地實行這種簡單樸素的生活。
在短暫的道觀居民角色扮演裏,芋圓發現表面上自己和大家的生活節奏趨于一致,可是世界觀和圈子完全不同:“我和同住的義工同樣都喜歡看一個綜藝,我們對這件事的思考方式相似,可爲什麽她會相信用一個打坐的姿勢就能得到身心的升華呢?”
△道觀的生活/行李
這座道觀的現代化進程裏,摻雜著住在這裏的人彼此矛盾的生活觀,仿佛時空錯置,既現代又複古。
作爲接待大量遊客的風景區,山上電網全通,纜車解放腳力,物資與山下無異。
宮觀管委會裏的管事道長也會被稱爲主任、副主任,開微博、豆瓣賬號,玩抖音和《王者榮耀》,在App上預訂機票飛往新加坡交流道法。在今年的“太和宮小型春晚”上,還有人演唱了《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
但同時,他們仍然采草藥治病,在陋室裏節食苦修,用經書或神話解釋自然現象,八九點就上床休息,不像城市人那樣熱衷熬夜。
看到在殿前玩日漫cosplay的年輕人,道長們也會好奇地問道:“他們在拍《霹雳布袋戲》嗎?”——那是上世紀80年代播出的一部台灣木偶劇。
△其他道觀的一位道士 / 圖蟲創意
隨著上山的人越來越多,來道觀體驗當義工會不會更普遍?
謝九認爲這不會成爲一個流行化的選擇,“因爲主動權不在我們手裏,而是取決于道長們。對于這樣的機構,是想變成一個盡可能開放交流的場所,還是更看重有限度的傳播,可能不是完全取決于公衆意願的”。
上山給她帶來的變化是:走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看到落葉她會突然有想掃一掃的沖動。
因爲道長們的熱心而退過一次回京火車票的行李,目前的身份還是“李小道”。
最近因爲常常需要鏟雪以及疫情封山期間物資緊缺,“每當一鐵鍬鏟下去,都覺得像奶油蛋糕,越看越餓”。
△“李小道”鏡頭中像奶油蛋糕的武當雪 / 微博截圖
6個月過去,在B站上傳的“武當山修仙日常”視頻裏,面對窗子漏風、房頂漏水的宿舍,他仍會調侃一句,這是風水很好的房間,順便極爲“入戲”地跟關注他的朋友們發一聲問候:“祝大家生活愉快,逍遙自在!”
他仍然舍不得下山。
你想去道觀修仙嗎?
劉江索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562期
原文標題
《找個道觀躲起來》
編輯 | 周芷若
排版 | 薯片
封面圖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