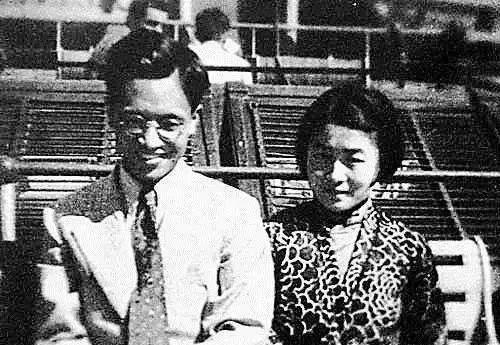錢鍾書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撫養,因爲伯父沒有兒子。據錢家的“墳上風水”,不旺長房旺小房;長房往往沒有子息,便有,也沒出息。伯父就是“沒出息”的長子。他比鍾書的父親大十四歲,二伯父早亡,他父親行三,叔父行四,兩人是同胞雙生,鍾書是長孫,出嗣給長房。伯父爲鍾書連夜冒雨到鄉間物色得一個壯健的農婦;她是寡婦,遺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現成的好奶媽(鍾書稱她爲“姆媽” )。姆媽一輩子幫在錢家,中年以後,每年要呆呆的發一陣子傻,家裏人背後稱爲“癡姆媽”。她在鍾書結婚前特地買了一支翡翠鑲金戒指,准備送我做見面禮。有人哄她那是假貨,把戒指騙去,姆媽氣的大發瘋,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終沒見到她。
鍾書自小在大家庭長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輸親兄弟。親的、堂的兄弟共十人 ,鍾書居長。衆兄弟間,他比較稚鈍,孜孜讀書的時候,對什麽都沒個計較,放下書本,又全沒正經,好像有大量多余的興致沒處寄放,專愛胡說亂道。錢家人愛說他吃了癡姆媽的奶,有“癡氣”。我們無錫人所謂“癡”,包括很多意義:瘋、傻、憨、稚氣、淘氣等等。他父母有時說他“癡顛不拉”、“癡舞作法”、“呒著呒落”(“著三不著兩”的意思–我不知正確的文字,只按鄉音寫)。他確也不像他母親那樣沉默寡言、嚴肅謹慎,也不像他父親那樣一本正經。他母親常抱怨他父親“憨”。也許鍾書的“癡氣”和他父親的憨厚正是一脈相承的。我曾看過他們家的舊照片,他的弟弟都精精壯壯,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憐相。想來那時候的“癡氣”只是稚氣,還不會淘氣呢。
鍾書周歲“抓周”,抓了一本書,因此取名“鍾書”。他出世那天,恰有人送來一部《常州先哲叢書》,伯父已爲他取名“仰先”,字“哲良”。可是周歲有了“鍾書”這個學名,“仰先”就成爲小名,叫作“阿先”。但“先兒”、“先哥”好象“亡兒”、“亡兄”,“先”字又改爲“宣”,他父親仍叫他“阿先”。(他父親把鍾書寫的家信一張張貼在本子上,有厚厚許多本,親手貼上題簽“先兒家書(一)(二)(三)¨¨”;我還看到過那些本子和上面貼的信。)伯父去世後,他父親因鍾書愛胡說亂道,爲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的意思。鍾書對我說:“其實我喜歡『哲良』,又哲又良——我閉上眼睛,還能看到伯伯給我寫在練習簿上的『哲良』。”這也許因爲他思念伯父的緣故。我覺得他確是又哲又良,不過他“癡氣”盎然的胡說亂道,常使他不哲不良——假如淘氣也可算不良。“默存”這 個號顯然沒有起克制作用。
伯父的“沒出息”,不得父母歡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陰富戶 ,做顔料商發財的,有七八支運貨的大船。鍾書的祖母娘家是石塘灣孫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響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進門就挨他父親一頓打,說是“殺殺他的勢氣”;因爲鍾書的祖父雖然有兩個中舉的哥哥,他自己也不過是個秀才。鍾書不到一歲,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終不喜歡大兒 子,鍾書也是不得寵的孫子。
鍾書四歲(我記年都用虛歲,因爲鍾書只記得虛歲,而鍾書是陽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周歲當減一歲或兩歲)由伯父教他識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鍾書成天跟著他。伯父上茶館,聽說書,鍾書都跟著去。他父親不便幹涉,又怕慣懷了孩子,只好建議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學。鍾書六歲入秦氏小學。現在他看到人家大講“比較文學”,就記起小學裏造句:“狗比貓大,牛比羊大”;有個同學比來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師一頓罵。他上學不到半年,生了一場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學,籍此讓他停學在家。他七歲,和比他小半歲的堂弟鍾韓同在親戚家的私塾附學,他念《毛詩》,鍾韓念《爾雅》。但附學不便,一年後他和鍾韓都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對鍾書的父親和叔父說:“你們兩兄弟都是我啓蒙的,我還教不 了他們?”父親和叔父當然不敢反對。
其實鍾書的父親是由一位族兄啓蒙的。祖父認爲鍾書的父親笨,叔父聰明,而伯父的文筆不頂好。叔父反正聰明,由伯父教也無妨;父親笨,得請一位文理比較好的族兄來教。那位族兄嚴厲得很,鍾書的父親不知挨了多少頓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讓兩個弟弟都由他教。鍾書的父親挨了族兄的痛打一點也不抱怨,卻別有體會。他告訴鍾書:“不知怎麽的,有一天忽然給打的豁然開通了。”
鍾書和鍾韓跟伯父讀書,只在下午。他父親和叔父都有職業,家務由伯父經管。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館喝茶,料理雜務,或和熟人聊天。鍾書總跟著去。伯父花一個銅板給他買一個大酥餅吃(據鍾書比給我看,那個酥餅有飯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麽大,還是小兒心目中的餅大);又花兩個銅板,向小書鋪子或書攤租一本小說給他看。家裏的小說只有《西遊記》、《水浒》、《三國演義》等正經小說。鍾書在家裏已開始囫囵吞棗地閱讀這類小說,把“呆子”(豈+犬爲繁體的呆字——編者注)讀如“豈子”,也不知《西遊記》裏的“呆子”就是豬八戒。書攤上租來的《說唐》、《濟公傳》、《七俠五義》之類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家裏不藏。鍾書吃了酥餅就孜孜看書,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後便手舞足蹈向兩個弟弟演說他剛看到的小說:李元霸或裴元慶或楊林(我記不清)一錘子把對手的槍打的彎彎曲曲等等。他納悶兒的是,一條好漢只能在一本書裏稱雄。關公若進了《說唐》,他的青龍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敵得過李元霸的那一對八百斤重的捶頭子;李元霸若進了《西遊記》,怎敵得過孫行者的一萬三千斤的金箍棒。(我們在牛津時,他和我講哪條好漢使哪種兵器,重多少斤,曆曆如數家珍)。妙的是他能把各件兵器的斤兩記得爛熟,卻連阿拉伯數字1、2、3都不認識。鍾韓下學回家有自己的父親教,伯父和鍾書卻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兒”。伯父用繩子從高處挂下一團棉花,教鍾書上、下、左、右打那團棉花,說是打“棉花拳”,可以練軟功。伯父愛喝兩口酒。他手裏沒多少錢,只能買些便宜的熟食如醬豬舌之類下酒,哄鍾書那是“龍肝鳳髓”,鍾書覺得其味無窮。至今他喜歡用這類名稱,譬如洋火腿在我家總稱爲“老虎肉”。他父親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機把鍾書抓去教他數學;教不會,發狠要打又怕哥哥聽見,只好擰肉,不許鍾書哭。鍾書身上一塊青、一塊紫,晚上脫掉衣服,伯父發現不免心疼氣惱。鍾書和我講起舊事,對父親的著急不勝同情,對伯父的氣惱也不勝同情,對自己的忍痛不敢哭當然也同情,但回憶中只覺得滑稽又可憐。我笑說:痛打也許能打得“豁然開通”,擰,大約是把竅門擰塞了。鍾書考大 學,數學只考得十五分。
鍾書小時候最樂的是跟伯母回江陰的娘家去;伯父也同去(堂姐已出嫁)。他們往往一住一兩個月。伯母家有個大莊園,鍾書成天跟著莊客四處田野裏閑逛。他常和我講田野的景色。一次大雷雨後,河邊樹上挂下一條大綠蛇,據說是天雷打死的。伯母娘家全家老少都抽大煙,後來伯父也抽上了。鍾書往往半夜醒來,跟著伯父伯母吃半夜餐。當時快樂得很,回無錫的時候,吃足玩夠,還穿著外婆家給做的新衣。可是一回家他就擔憂,知道父親要盤問功課,少不了挨打。父親不敢當著哥哥面管教鍾書,可是抓到機會,就著實管教,因爲鍾書不但荒了功課,還養成不少壞習氣,如晚起晚睡、貪吃貪玩等。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家由北京回無錫。我父母不想住老家,要另找房子。親友介紹了一處,我父母去看房子,帶了我同去。鍾書家當時正租居那所房子。那是我第一次上他們錢家的門,只是那時兩家並不相識。我記得母親說,住在那房子裏的一位女眷告訴她,搬進以後,沒離開過藥罐兒。那所房子我家沒看中;錢家雖然嫌房子陰暗,也沒有搬出。他們五年後才搬入七尺場他們家自建的新屋。我記不起那次看見了什麽樣的房子、或遇見了什麽人,只記得門口下車的地方很空曠,有兩顆大樹;很高的白粉牆,粉牆高處有一個個砌著鑲空花的方窗洞。鍾書說我的記憶不錯,還補充說,門前有個大照牆,照牆後有一條河從門前流過。他說,和我母親說話的大約是嬸母,因爲叔父嬸母住在最外一進房子裏,伯父伯母和他住在中間一進 ,他父母親伺奉祖父住最後一進。
我女兒取笑說:“爸爸那時候還不知在哪兒淘氣呢。假如那時候爸爸看見媽媽那樣的女孩子,准摳些鼻牛來彈她。”鍾書因此記起舊事說,有個女裁縫常帶著個女兒到他家去做活;女兒名寶寶,長得不錯,比他大兩三歲。他和鍾韓一次抓住寶寶,把她按在大廳隔扇上,鍾韓拿一把削鉛筆的小腳刀作勢刺她。寶寶大哭大叫,由大人救援得免。兄弟倆覺得這番勝利當立碑紀念,就在隔扇上刻了“刺寶寶處”四個字。鍾韓手巧,能刻字,但那四個字未經簡化,刻來煞是費事。這大概是頑童剛開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現。後來房子退租的時候,房主提出賠償損失,其中一項就是隔扇上刻的那四個不成形的字。另一項是鍾書一人幹的事,他在後園“挖 人參”,把一顆玉蘭樹的根刨傷,那顆樹半枯了。
鍾書十一歲,和鍾韓同考取東林小學一年級,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學。就在那年秋天,伯父去世。鍾書還未放學,經家人召回,一路哭著趕回家去,哭叫“伯伯 ”,伯父已不省人事。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的傷心事。
伯父去世後,伯母除掉長房應有的月錢以外,其他費用就全由鍾書父親負擔了。伯母娘家敗得很快,兄弟先後去世,家裏的大貨船逐漸賣光。鍾書的學費、書費當然有他父親負擔,可是學期中間往往添買新課本,鍾書沒錢買,就沒有書,再加他小時候貪看書攤上伯父爲他租的小字書,看壞了眼睛,坐在教室後排,看不見老師黑板上寫的字,所以課堂上老師講什麽,他茫然無知。練習簿買不起,他就用伯父生前親手用毛邊紙、紙撚子爲他訂成的本子,老師看了直皺眉。練習英文書法用鋼筆。他在開學的時候有一支筆杆、一個鋼筆尖,可是不久筆尖撅斷了頭。同學都有許多筆尖,他只有一個,斷了頭就沒發寫了。他居然急中生智,把毛竹筷削尖了 頭蘸著墨水寫,當然寫得一塌糊塗,老師簡直不願收他的練習簿。
我問鍾書爲什麽不問父親要錢。他說,從來沒想到過。有時伯母叫他向父親要錢,他也不說。伯母抽大煙,早上起得晚,鍾書由伯母的陪嫁大丫頭熱些馊粥吃了上學。他同學、他弟弟都穿洋襪,他還穿布襪,自己覺得腳背上有一條拼縫很刺眼,只希望穿上棉鞋可遮掩不見。雨天,同學和弟弟穿皮鞋,他穿釘鞋,而且是伯伯的釘鞋,太大,鞋頭塞些紙團。一次雨天上學,路上看見許多小青蛙滿地蹦跳,覺得好玩,就脫了鞋捉來放在鞋裏,抱著鞋光腳上學;到了教室裏,把盛著小青蛙的釘鞋放在擡板桌下。上課的時候,小青蛙從鞋裏出來,滿地蹦跳。同學都忙著看青蛙,竊竊笑樂。老師問出因由,知道青蛙是從鍾書鞋裏跑出來的,就叫他出來罰立。有一次他上課玩彈弓,用小泥丸彈人。中彈的同學嚷出來,老師又叫罰立。可是他渾渾沌沌,並不覺得羞慚。他和我講起舊事常說,那時候幸虧糊塗,也不覺得什麽苦惱。
鍾書跟我講,小時候大人哄他說,伯母抱來一個南瓜,成了精,就是他;他真有點兒怕自己是南瓜精。那時候伯父已經去世,“南瓜精”是舅媽、姨媽等晚上坐在他伯母鴉片榻畔閑談時逗他的,還正色囑咐他切莫告訴他母親。鍾書也懷疑是哄他,可是真有點擔心。他自說混沌,恐怕是事實。這也是家人所謂“癡氣”的表現 之一。
他有些混沌表現,至今依然如故。例如他總記不得自己的生年月日。小時候他不會分辨左右,好在那時候穿布鞋,不分左右腳。後來他和鍾韓同到蘇州上美國教會中學的時候,穿了皮鞋,他仍然不分左右亂穿。在美國人辦的學校裏,上體育課也用英語喊口號。他因爲英文好,當上了一名班長。可是嘴裏能用英語喊口號,兩腳卻左右不分;因此當了兩個星期班長就給老師罷了官,他卻如釋重負。他穿內衣或套脖的毛衣,往往前後顛倒,衣服套在脖子上只顧前後掉轉,結果還是前後顛倒 了。或許這也是錢家人說他“癡”的又一表現之一。
鍾書小時後喜歡玩“石屋裏的和尚”。我聽他講的津津有味,以爲是什麽有趣的遊戲;原來只是一人盤腿坐在帳子裏,放下帳門,披著一條被單,就是“石屋裏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麽好玩。他說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裏的和尚”,玩得很樂。所謂“玩”,不過是一個人盤腿坐著自言自語。這大概也算是“癡氣”吧。
鍾書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畢業了。鍾韓成績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個癡頭傻腦、沒正經的孩子。伯父在世時,自愧沒出息,深怕“墳上風水”連累了嗣給長房的鍾書。原來他家祖墳下首的一排排樹高答茂盛,上首的細小萎弱。上首的樹當然就代表長房了。伯父一次私下花錢向理發店買了好幾斤頭發,叫一個佃戶陪著,悄悄帶著鍾書同上祖墳去,把頭發埋在上首幾排樹的根旁。他對鍾書說,要叫上首的樹榮盛,“將來你做大總統。”那時候鍾書才七、八歲,還不懂事,不過多少也感覺到那是伯父背著人幹的私心事,所以始終沒向家裏任何人講過。他講給我聽的時候,語氣中還感念伯父對他的愛護,也驚奇自己居然還有心眼爲伯父保密。
鍾書十四歲和鍾韓同考上蘇州桃塢中學(美國聖公會辦的學校)。父母爲他置備了行裝、學費書費之外,還有零用錢。他和鍾韓同往蘇州上學,他功課都還不錯,只算術不行。
那年他父親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寒假沒回家。鍾書寒假回家沒嚴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說世界》、《紅玫瑰》、《紫羅蘭》等刊物恣意閱讀。暑假他父親歸途堵塞,到天津改乘輪船,輾轉回家,假期已過了大半。他父親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命鍾書鍾韓各做一篇文章;鍾韓的一篇頗受誇贊,鍾書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親氣得把他痛打一頓。鍾書忍笑向我形容他當時的窘況:家人都在院子裏乘涼,他一人還在大廳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嗚嗚地哭。這頓打雖然沒有起“豁然開通”的作用,卻也激起發憤讀書的志氣。鍾書從此用功讀書,作文大有進步。他有時並不按父親教導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骊,倒也受到父親贊許。他也開始學著作詩,只是並不請教父親。一九二七年桃塢中學停辦,他和鍾韓同考入美國聖公會辦的無錫輔仁中學,鍾書就經常有父親管教,常爲父親帶筆寫信,由口授而代寫,由代寫信而代作文章。鍾書考入清華之前,已不再挨打而是父親得意的兒子了。一次他代父親爲鄉下某大戶作了一篇墓志銘。那天午飯時,鍾書的姆媽聽見他父親對他母親稱贊那篇文章,快活的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風報信,當著他伯母對他說:“阿大啊,爹爹稱贊你呢!說你文章做得好!”鍾書是第一次聽到父親稱贊,也和姆媽一樣高興,所以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時商務印書館出版錢穆的一本書,上有鍾書父親的一篇序文。據鍾書告訴我,那是他代寫的,一字沒有改動。
我常見鍾書寫客套信從不起草,提筆就寫,八行箋上,幾次擡頭,寫來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鍾書說,那是他父親訓練出來的,他額角上挨了不少“ 爆栗子”呢。
鍾書二十歲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華大學,秋季就到北京上學。他父親收藏的“先兒家書”是那時候開始的。他父親身後,鍾書才知道父親把他每一封信都貼在本子上珍藏。信寫得非常有趣,對老師、同學都有生動的描寫。可惜鍾書所有的 家書(包括寫給我的),都由“回祿君”收集去了。
鍾書在清華的同班同學饒馀威一九八六年在新加坡或台灣寫了一篇《清華的回憶》,有一節提到鍾書:“同學中我們受錢鍾書的影響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詣很深,又精于哲學及心理學,終日博覽中西新舊書籍,最怪的是上課時從不記筆記,只帶一本和課堂無關的閑書,一面聽講一面看自己的書,但是考試時總是第一,他自己喜歡讀書,也鼓勵別人讀書。¨¨”據鍾書告訴我,他上課也帶筆記本,只是不作筆記,卻在本子上亂畫。現在美國的許振德君和鍾書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鍾書奪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頓出氣,因爲他和鍾書同學之前,經常是班上第一的。一次偶有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鍾書向他講解了,他很感激,兩人成了好朋友 ,上課常同時坐在最後一排。許君上課時注意一個女同學,鍾書就在筆記本上畫了一系列的《許眼變化圖》,在同班同學裏頗爲流傳,鍾書曾得意地畫給我看。一年 前許君由美國回來,聽鍾書說起《許眼變化圖》還忍不住大笑。
鍾書小時候,中藥房賣的草藥每一味都有兩層紙;一張白紙,一張印著藥名和藥性。每服一副藥可攢下一疊包藥的紙。這種紙幹淨、吸水,鍾書大約八、九歲左右常用包藥紙來臨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園畫譜》,或印在《唐詩三百首》裏的“詩中之畫”。他爲自己想出一個別號叫“項昂之”——因爲他佩服項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項羽的氣概。他在每幅畫上揮筆署上“項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約常有“項昂之”的興趣,只恨不善畫。他曾央求當時在中學讀書的女兒爲他臨摹過幾幅有名的西洋淘氣畫,其中一幅是《魔鬼臨去遺臭圖》(圖名是我杜撰),魔鬼象吹喇叭似的後部撒著氣逃跑,畫很妙。上課畫《許眼變化圖》,央女兒代摹《 魔鬼臨去遺臭圖》,想來也都是“癡氣”的表現。
鍾書在他父親的教導下“發憤用功”,其實他讀書還是出于喜好,只似饞嘴佬貪吃美食:食腸很大,不擇精粗,甜鹹雜進。極俗的書他也能看的哈哈大笑。戲曲裏的插科打诨,他不僅且看且笑,還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奧的哲學、美學、文藝理論等大部著作,他象小兒吃零食那樣吃了又吃,厚厚的書一本本漸次吃完 。詩歌更是他喜好的讀物。重得拿不動的大字典、詞典、百科全書等,他不僅挨著字母逐條細讀,見了新版本,還不嫌其煩的把新條目增補在舊書上。他看書常做些筆記。
我只有一次見到他苦學。那是在牛津,論文預試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門課,要能辨認十五世紀以來的手稿。他毫無興趣,因此每天讀一本偵探小說“休養腦筋”,“休養”得睡夢中手舞腳踢,不知是捉拿凶手,還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結果考試不及格,只好暑假後補考。這件補考的事,《圍城》英譯本《導言》裏也提到。鍾書一九七九年訪美,該譯本出版家把譯本的《導言》給他過目,他讀到這一段又驚又笑,想不到調查這麽精密。後來胡志德(Theodore Hu ters)君來見,才知道他向鍾書在牛津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聽來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錢鍾書》裏把這件事卻刪去了。
鍾書的“癡氣”書本裏灌注不下,還洋溢出來。我們在牛津時,他午睡,我臨帖,可是一個人寫寫字困上來,便睡著了。他醒來見我睡了,就飽蘸濃墨,想給我畫個花臉。可是他剛落筆我就醒了。他沒想到我的臉皮比宣紙還吃墨,洗盡墨痕, 臉皮象紙一樣快洗破了,以後他不在惡作劇,只給我畫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鏡和胡子,聊以過瘾。回國後他暑假回上海,大熱天女兒熟睡(女兒還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畫一個大臉,挨他母親一頓訓斥,他不敢再畫。淪陷在上海的時候 ,他多余的“癡氣”往往發泄在叔父的小兒小女、孫兒孫女和自己女兒阿圓身上。這一串孩子挨肩兒都相差兩歲,常在一起玩。有些語言在“不文明”或“臭”的邊緣上,他們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鍾書變著法兒,或作手勢,或用切口,誘他們說 出來,就賴他們說“壞話”。于是一群孩子圍著他吵呀,打呀,鬧個沒完。他雖然挨了圍攻,還俨然以勝利者自居。他逗女兒玩,每天臨睡在她的被窩裏埋置“地雷”,埋得一層深入一層,把大大小小的各種玩具、鏡子、刷子,甚至硯台或大把的毛筆都埋進去,等女兒驚叫,他得意大樂。女兒臨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裏的東西一一取出。鍾書恨不得把掃帚、畚箕都塞入女兒被窩,博取一遭意外的勝利 。這種玩意兒天天玩也沒多大意思,可是鍾書百玩不厭。
他對女兒說,《圍城》裏有個醜孩子,就是她。阿圓信以爲真,卻也並不計較。他寫了一個開頭的《百合心》裏,有個女孩子穿一件紫紅毛衣,鍾書告訴阿圓那是個最討厭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圓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鍾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遊戲。後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裏去了。
鍾書的“癡氣”也怪別致的。他很認真地跟我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圓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麽對得起阿圓呢。”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爲了用情專一而只生一個。
解放後,我們在清華養過一只很聰明的貓。小貓初次上樹,不敢下來,鍾書設法把它救下。小貓下來後,用爪子輕輕軟軟地在鍾書腕上一搭,表示感謝。我們常愛引用西方諺語:“地獄裏盡是不知感激的人。”小貓知感,鍾書說它有靈性,特別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別的貓兒打架。鍾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裏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和我們家那貓兒爭風打架的情敵之一是緊鄰林微女士的寶貝貓,她稱爲她一家人的“愛的焦點”。我常怕鍾書爲貓而傷了兩家和氣,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打狗要看主人的面,那麽,打貓要看主婦面了!”(《貓》的第一句),他笑說 :“理論總是不實踐的人制定的。”
錢家人常說鍾書“癡人有癡福”。他作爲書癡,倒真是有點癡福。供他閱讀的書,好比富人“命中的祿食”那樣豐足,會從各方面源源供應。(除了下放期間,他只好“反刍”似的讀讀自己的筆記,和攜帶的字典。)新書總會從意外的途徑到他手裏。他只要有書可讀,別無營求。這又是家人所謂“癡氣”的另一表現。
鍾書和我父親詩文上有同好,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鍾書常和我父親說些精致典雅的淘氣話,相與笑樂。一次我父親問我:“鍾書常那麽高興嗎?”“高興”也是 錢家所謂“癡氣”的表現。
我認爲《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鍾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鍾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癡氣”旺盛的鍾書。我們倆日常相處,他常愛說些癡話,說些傻話,然後加上創造,加上聯想,加上誇 張,我常能從中體味到《圍城》的筆法。我覺得《圍城》裏的人物和情節,都憑他那股子癡氣,呵成了真人真事。可是他畢竟不是個不知世事的癡人,也畢竟並不是對社會現象漠不關心,所以小說裏各個細節雖然令人捧腹大笑,全書的氣氛,正如小說結尾所說:“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傷感,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腸蕩氣。
鍾書寫完了《圍城》,“癡氣”依然旺盛,但是沒有體現爲第二部小說。一九五七年春,“大鳴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詩選注》剛脫稿,因爲父病到湖北省親,路上寫了《赴鄂道中》五首絕句,現在引錄三首:“晨書暝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碧海摯鯨閑此手,只教疏鑿別清渾。”“奕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應褪淨,夜來無夢過邯鄲。”“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懑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鸠忽噤雨將來。”後兩首寄寓他對當時形勢的感受,前一首專指“宋詩選注”而說,點化杜甫和元好的名句(“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摯鯨魚碧海中”;“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泾渭各清渾”)。據我了解,他自信還有寫作之才,卻只能從事研究或評論工作,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念了。《圍城》重印後,我問他想不想再寫小說。他說:“興致也許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會有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只有後悔了。遺恨裏還有哄騙自己的余地,後悔是你所學的西班牙語裏所謂『面對真理的時刻』,使不得一點兒自我哄騙、開脫,或寬容的,味道不好受。我甯恨毋悔。”這幾 句話也許可作《圍城》《重印前記》的箋注吧。
我自己覺得年紀老了;有些事,除了我們倆,沒有別人知道。我要乘我們夫婦都鍵在, 一一記下。如有錯誤,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圍城》裏寫的全是捏造,我所記的卻是事實。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壹點號難忘秋月
找記者、求報道、求幫助,各大應用市場下載“齊魯壹點”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點情報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體記者在線等你來報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