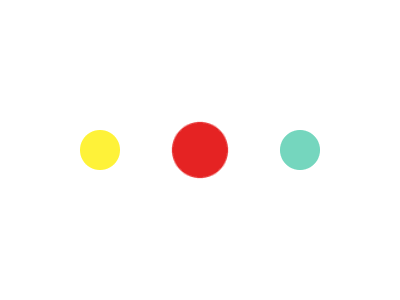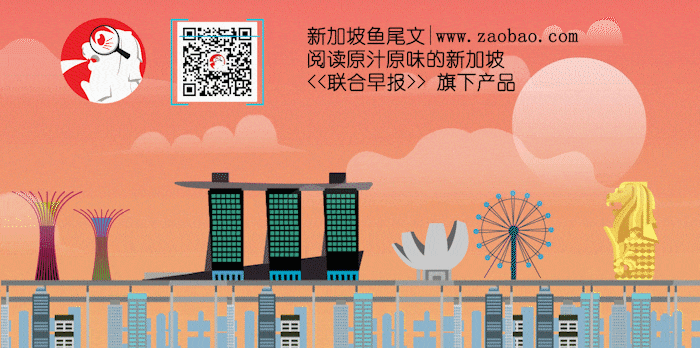丹戎禺尾是早期木炭與火炭集散中心。(互聯網)
曾是造船廠與修船廠,以及木材、火炭集散中心的丹戎禺,也曾是“歹仔區”……
建國初期,新加坡政府爲了發展工業,征用土地。我家從加冷河畔的福順甘榜,搬到由建屋局在芽籠河畔新蓋的丹戎禺組屋。
丹戎禺(Tanjon Rhu)地名早在1604年已出現在新加坡地圖上。這裏曾經是一片淺灘,稱爲沙地坊(Sandy Point)。丹戎禺(Tanjong Rhu)源自馬來語,丹戎(Tanjong)是岬角的意思,Pokok Rhu則是木麻黃樹。
船廠與木材集散中心
萊佛士在19世紀初就計劃把丹戎禺發展爲造船與修船廠專屬地段,到了1880年,船塢、造船廠與修船廠林立,後來更成爲船運與漁船停泊中心;許多木材廠、火炭廠應運而生。這裏的街名都與人們從事的行業有關,如火炭村(Kampong Arang)、木頭村(Kampong Kayu)、舢板坊(Sampan Place)、舯舡坊(Tongkang Place)與大舟古坊( Twakow Place )等。
一些外國公司如Vosper Thornycroft等,也陸續設廠與建造貨倉。1964年由于水路運輸方便,本地公司康元面粉建廠,隔年本地品牌泛電(Pan-Electric)也設廠;這些公司爲丹戎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
居民包括1962年芽籠大火的災民,多爲藍領工人和小販等;有搬木材扛火炭的,有賣肉賣魚的,也有在夜市擺地攤的流動小販。男人出外討生活,女人也沒有閑著。有些大嬸早上在樓梯口賣炒米粉或糯米飯,下午賣木薯糕或Ondeh ondeh(番薯丸)等;更多婦女是忙完家務後“車水貨”(衣服),剪線頭或折紙皮盒等,家中老人和小孩都會幫忙。
有些樓下人家商住兩用,把客廳開成雜貨店或賣粥、面及粿汁的小鋪等,印象中沒有“地牛”(稽查員)來掃蕩。那時生活艱苦,男女老少都得靠雙手勤奮工作,賺取微薄收入過活。
不跟老人搶飯碗
年輕的舅舅和表舅剛從馬來亞來新加坡時失業,只好去丹戎禺尾扛火炭,每天都“黑頭黑臉”回來。有一次表舅的臉出現一條黑線,原來他用手抹汗時黑炭留在額頭,兩道眉毛連成一條。
一天兩人回來時臉色不對。原來在那裏打工的都是些年紀大的“老阿哥”(潮州大叔),他們譏諷年輕人識字有力氣,不該跟老人搶飯碗,哥兒倆此後不敢再去扛火炭。
舅舅後來到“紅沙厘”(實龍崗花園)打洋雜。表舅則因找不到工作常眉頭深鎖,母親鼓勵他不要灰心,告知不介意他一起吃粗茶淡飯。後來表舅成爲羅厘司機,在同一家運輸公司忠心服務至退休。每逢華人新年他必定和表舅母來拜年送禮,感謝母親當年鼓勵他並提供瓦遮頭。
富婆抛金鏈賞花旦
1960年代初在丹戎禺興建的政府組屋。(互聯網)
樓下那家人有五個小孩,卻不見蹤影,母親說他們去“綁戲”了。原來這家人太窮,讓小孩加入戲班包吃包住;平時受訓打雜,上台則跑龍套演小兵丫鬟等。他們偶爾回家,說在戲班常挨罵與籐鞭,日子很苦,羨慕我們有書讀。
真的感恩!我家也窮,但父親在堂叔的“坊廊”(鋸木廠)當管工,母親勤儉理家,車衣服幫補家用,家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兄弟姐妹都有書念。我還常有機會看“大戲”(傳統戲曲),只是從沒見過樓下的小朋友粉墨登場。
每年農曆九月初九是九皇爺誕辰,從初一至初九在勞動公園(Kallang Park)有酬神戲。我每晚都會拎著小凳子,跟鄰居大嬸走路去看戲。不論上演的是福建或潮州大戲,是“新賽鳳”“筱鳳”,還是“老賽桃”戲班,我都照看不誤。我常爲花旦小生臉上的彩妝與絢麗戲服著迷,會跑到後台看他們化妝與穿戲服。戲台周圍燈火通明、人頭攢動,有販賣各種食物與飲料的小販,非常熱鬧,簡直是那個年代的嘉年華會。
在火炭村路與炮台路交界處(今加東民衆俱樂部),從前爲四層樓的私人公寓。有時園地內會搭起戲棚,敲鑼打鼓上演廣東大戲,我們隔著籬笆觀賞也很開心。有一次花旦出來謝幕,一個富婆抛了條金鏈上台獎賞她,我們都看呆了。聽說花旦乃香港粵劇名伶,獎賞方式非獨創,是我們少見多怪。
兩所母校空間重疊
從加東民衆俱樂部朝火炭村路方向,經大牌12號組屋就是德明政府中學。
今天的德明校園曾經屹立著三所老學校:德儒小學(Tanjong Rhu Primary School),丹戎禺男校(Tanjong Rhu Boys’ School)與丹戎禺女校(Tanjong Rhu Girls’ School)。
我是德儒的學生,小六畢業後就讀于德明政府華文中學(德明路舊址)。第一次踏入德明在丹戎禺的新校園時,心情是複雜的,兩所母校竟然在空間上重疊,一時仿佛時空交錯,校園因增加了時光厚度與曆史層次感。
六年小學時光是快樂的,師長的疼愛與教誨令人感激難忘。
便衣警探追捕嫌犯
今日的丹戎禺不但有名校,也是個高級住宅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卻非如此。
記得有個晚上,突然聽到樓下有急促的跑步聲,原來有個“暗牌”(便衣警探)在樓下追捕嫌疑犯,他大聲警告那“歹仔”(私會黨徒)再跑就開槍,歹仔果然停住腳步束手就擒。姐姐說,我們家曾因大門開著,有歹仔跑進來要求躲藏,以後就常關門避免惹麻煩。
後來姐姐拍拖男友要她外出約會,說這裏是有名的“歹仔區”,常有流氓、地痞和私會黨徒出沒,外人不敢進來。也許基于江湖上不吃窩邊草的潛規矩,我們住在這裏卻不覺得受到地痞流氓幹擾;或許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吧?
我們在1970年代末搬離丹戎禺。爲了清理嚴重汙染的芽籠河,政府在1980年代將造修船廠等遷移他處;後來更打造成私人公寓林立的住宅區、水上運動與康樂活動中心。丹戎禺華麗轉身,風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記者:尹玉
一只愛生活、文藝範的小魚尾獅帶你了解新加坡原汁原味的風土人情領略小島深處那些鮮爲人知的文化魅力~ 新加坡《聯合早報》旗下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