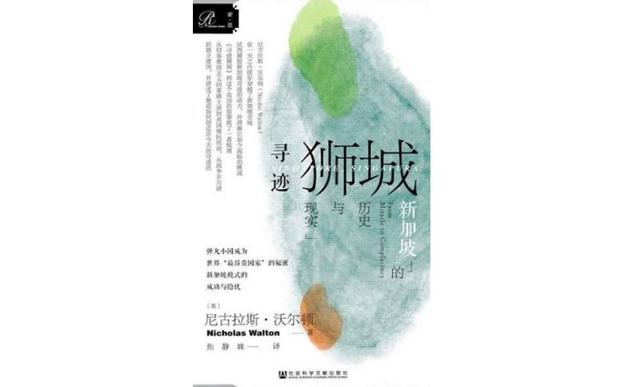上周,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再次聲明,保留李光耀故居是父親李光耀的決定,“我身不由己。”實際上,有關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故居是否保留的爭論已延續幾年。在2015年李光耀去世後,李顯龍主張保留故居,其弟弟妹妹李玮玲和李顯揚主張拆除故居,以免成爲“供人崇拜的遺迹”。李玮玲和李顯揚認爲,李顯龍保留故居是借李光耀的光環扶持自己的兒子進入政壇。但李顯龍稱,其兒子對政治並無興趣,而且認爲所謂“借李光耀的光環”是可悲的。
李光耀故居之爭在表面上是李氏家族內部的矛盾,實際上也反映出新加坡所面臨的不平等挑戰。新加坡從一個彈丸小國快速發展成爲發達國家,新加坡普通居民能夠負擔得起交通、食品和住房,這一切堪稱奇迹。但是,這一“社會契約”越發遭到貧富分化和相對剝奪感的挑戰。英國記者尼古拉斯·沃爾頓在新加坡生活多年,他在《尋迹獅城》中寫出了新加坡的奇迹之處以及其將面臨的挑戰。沃爾頓認爲,新加坡在新世紀所面臨的挑戰不會比其獨立以來的五十年更輕松。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中,新加坡社會將如何解決不平等的挑戰?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尋迹獅城》,小標題爲編輯所加。
原作者 | [英]尼古拉斯·沃爾頓(焦靜姝 譯)
摘編 | 徐悅東
《尋迹獅城:新加坡的曆史與現實》,[英]尼古拉斯·沃爾頓 著,焦靜姝 譯,索·恩|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8月。
新加坡公民生活的三大“社會契約”:交通、食品和住房
就在尼爾街(Neil Street)將與廣東民路(Cantonment Road)交會的地方,我路過吉祥紅龜粿(Ji Xiang Confectionery)。這家甜品屋位于一座醒目的、桃紅加奶油色的巨大組屋的底層,門面也就比牆上的洞大一些。但別看它其貌不揚,其實聲名遠揚。它的特色甜品是一種用糯米粉、椰奶和糖制成的發亮並帶有圖案的黏嘴小甜點。新加坡人從四面八方前來,選購一份被精美裝盤的禮盒,其中傳統的口味有花生味、玉米味、芋頭味和鹹豆沙味。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這東西實在不好吃:太甜、太黏,簡直就是爲了塞牙而設計的。但排隊購買的新加坡人絡繹不絕。這種食品就像一個黏稠的提示器,提醒我作爲一名外籍人士,我的生活與口味和廣大新加坡人之間有一道鴻溝。
普通新加坡公民的生活是圍繞該島社會契約的三大支柱構建的:帶空調的地下捷運網、樸實簡陋的小販中心和高高聳立的HDB組屋。由于該國的居民忙于發財致富,他們期望生活的這三個基本層面——交通、食品和住房——可靠且能負擔得起。
但這一社會契約似乎不如以前那麽堅實了。矛盾的是,隨著新加坡一躍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她的大部分居民卻開始有相對不富裕的感覺。一捆捆1000新元的鈔票也無法阻止全球有關不平等的討論沖上她的熱帶海灘。這一討論在新加坡尤其火爆,一方面是因爲該島相當富裕,另一方面是由于整個國家建立在明確的精英主義基礎上。
而一連串關于金融巨頭炫耀財富的報道也加劇了這種緊張局勢。2017年4月,當地一家餐廳的老板蓋瑞·林曾被指控嘲諷一名出租車司機的財富狀況,當時司機拒絕了他抛出的1000 新元的鈔票。“你看看,誰叫我這麽有錢,我也沒辦法啊,”他在視頻裏說道,“你是成不了大事的。你知道你爲什麽是個出租車司機嗎?因爲你成不了大事。”社交媒體上輿論沸騰。林的餐廳在網上成了衆矢之的,遭到了網友一連串的憤怒攻擊。蓋瑞·林爲了適當地表示懊悔,也爲了緩解局面,讓自己的餐廳爲出租車司機們提供免費的飲食。1
盡管如此,引發人們對不平等現象感到不安的,不只是一些超級富豪的粗魯行爲。它還涉及社會契約的三大支柱——交通、食品和住房。盡管新加坡人被告知自己已經實現了真正的富裕,但這三個方面恰恰代表了實現這一願景道路上的玻璃天花板。
先從交通說起。捷運系統運行良好,公共汽車也都准時運營。當你下了交通工具,通常有一個有遮蔽的步道爲你阻擋傾盆大雨,直到你的組屋或鮮貨市場門前。而且交通費用很便宜。與其他富裕的城市相比,連出租車的費用都很低廉。市民也許會抱怨捷運列車的機械故障妨礙了列車的平穩運行,但這裏的大多數人並沒有與倫敦足以塑造人個性的公共交通對抗過,更別說在高峰時段在雅加達或曼谷出行了。盡管當地人會抱怨,但新加坡的公共交通除了空調溫度調得太低,確實廉價且高效。像Grab或者優步(Uber)這樣的打車軟件又讓打車出行變得更加便宜。
新加坡。
但不是所有的外籍人士都對這裏的公共交通系統表示贊賞。倒黴的英國人安東·凱西(Anton Casey)就是一個例子。他覺得公共汽車對于他兒子來說太髒太亂了,而且他很討厭有些出租車司機的特有習慣。盡管如此,新加坡人不但沒有接受凱西先生有建設性的批評,反而將他驅逐出境,而他的老板也解雇了他。這不公平嗎?公平得很。
安東·凱西是全球最令人反感的一類人的典型代表。他不但是個銀行家,而且引用一個金融業同行在《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的話說,還是一個“白癡”。他和他的兒子之所以會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因爲他的保時捷暫時上不了路。他把一張公交車的照片放到社交網絡上,然後加了一個標題:“爸爸,你的車去哪兒了,這些窮人都是誰?”他抱怨說,他不得不下車洗掉“公共交通工具的惡臭”。他將一位出租車師傅稱爲“智障人士”。隨著他奢華而自鳴得意的生活細節逐漸被曝光——包括他與前新加坡小姐的婚姻——死神針對他的審判開始了。他匆忙乘坐飛機(經濟艙)逃往澳大利亞。盡管他低聲下氣地向受辱者及公衆道歉,仍然無法平息衆怒。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裏,人們對銀行家普遍缺乏同情,即使是在熱愛金融、對貿易開放的新加坡。尤其是當這個銀行家的所作所爲完全符合那種煽動者可能畫出的漫畫形象的時候,更是如此。
安東·凱西的行爲讓人們注意到,新加坡存在一條巨大而幾乎不可逾越的鴻溝,這條鴻溝橫貫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大多數人和擁有私家車輛的少數人之間。德意志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一輛中型汽車在美國或者英國可能賣到24000美元,但在新加坡要賣到90000美元。當你看到一輛勞斯萊斯或者法拉利經過時——在新加坡的某些區域豪車相當常見——你大概可以推測出車主爲此花費了上百萬甚至更多。
外籍銀行家不是唯一受到責難的人。有錢有勢的新加坡本地人也像土狼一樣,懷著對同胞的同情之情照舊開著自己的邁凱倫(MclLarens)和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s)飛馳而過。而公衆最大的憤怒則朝向該地區來自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超級富豪。民衆的憤怒情緒被2012年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點燃。在羅徹路(Rochor Road)附近的紅燈路口,一輛法拉利599GTO以每小時178公裏的速度側面撞上一輛出租車。
出租車司機和車上的乘客——一名日本婦女,連同肇事的跑車司機馬馳,當場喪命。新加坡的汽車所有權制度建立在擁車證(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COE)的基礎上。事實上,擁車證是爲期10年的汽車駕駛執照,可以隨著車輛的出售進行轉讓。當一輛車車齡達到3年,那它的執照就只剩7年,而車的價值也會相應降低。10年之後,執照過期,不管車有多花哨多昂貴,都不能再上路了。然後它會被運到其他地方出售。10年期的擁車證每年都會進行拍賣,而價格也一路飙升。早在2009年1月,B組車(1600cc或者97kw 以上的車輛)的擁車證價值200新元,到2017年11月8日,同類擁車證的價格漲至57414新元。2017年的金額與2013年1月的峰值(96210新元)相比,已經算是很便宜了。
一方面,擁車證控制了新加坡人擁有汽車的數量。這裏很少出現嚴重的交通堵塞,而且絕對不會像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新興城市那樣,路上尾氣熏天、摩托車劫匪頻繁出沒。TomTom導航儀公司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雅加達位列世界最擁擠城市的第二名,曼谷位列第三,新加坡則位列第55名。另一方面,由于只有11%的新加坡人可以擁有自己的代步車,對大部分新加坡人而言,私家車的擁有權越來越明顯地成爲一塊玻璃天花板。用新加坡英語來說,這叫“可望而不可即”。新加坡的交通服務當然很優質,但當大衆高爾夫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代表著一種無法獲得的奢侈品時,難免會讓人産生挫敗感。
社會契約的下一個支柱是食物。鮮貨市場和無處不在的小販中心是大多數新加坡人就餐的主要去處。你可以用紙巾占個座位,對著海南雞飯、菜頭粿或是一盆營養豐富的牛蛙粥大快朵頤,吃完後還有一個70 多歲的服務員來收盤子——他想在退休之後明智地存些錢,而所有這些勞動也就能賺幾個零錢。除此之外,吃飯貴得離譜。一想到要在外面吃飯,而且要開瓶酒,能讓你在冷氣十足的房間裏冒出汗來。我在超市裏看到,一小籃(日本)草莓能賣到70 新元;我也曾帶著負罪感喝過20 新元一瓶的啤酒;如果發現一瓶不錯的紅酒售價在40 新元以下,那簡直是撿到大便宜了。這樣的價格讓現實扭曲,讓遊客驚訝。誠然,這樣的招待標准可能會符合不少外籍人士對飲食的期待,但這畢竟是少數人的標准,與一個典型的當地公民能負擔起的標准之間有很大一段距離。
社會契約的第三個支柱就是住房了。新加坡大約85%的人口居住在公共住房裏(通常擁有時長99年的租約),而少數富人喜歡類似高檔度假村的私人別墅,這些別墅擁有無邊遊泳池以及像“皇家角”和“納西姆攝政王”這樣的名字。華彬漢美登頂級公寓可以將嶄新的蘭博基尼通過電梯運到你位于15層的公寓裏,讓坐在客廳裏的客人,以及樓下171路公交車上的可憐“窮鬼”們都看到。翠城新景是由31棟、每棟6層高的住宅樓組成的樂高叢林:實話說,與其說它是相互連接的格局,不如說它就是一堆摞起來的積木,但那都是小細節。無論如何,這座令人矚目的巨大建築群于2015年榮獲了世界建築節的年度最佳建築大獎,它的風格和它獲得的名望可是一個四方形的混凝土HDB組屋可望而不可即的。
新加坡組屋。
私有房産的業主們不但可以住在夢幻般的建築裏,享有網紅度假豪宅,還能因地産價格的通貨膨脹獲得巨額收益。新加坡安全港灣的地位讓亞洲其他地區的熱錢像潮水般湧入當地的房地産市場,這也是因爲其他國家的法治沒有那麽牢靠,而貨幣的波動像季風一樣。那些有幸擁有私人房産的人的銀行賬戶,因此增加了幾百萬收益(其中一些很快流入保時捷和法拉利經銷商的口袋裏)。HDB組屋的價值也有所上升,但其租賃者卻被擋在玻璃天花板的另一邊。
在新加坡,真正的貧困是罕見的,但相對貧富差距仍然很大
這與西方世界經曆的社會不平等不甚相同。在新加坡,人們顯然正活在夢中。曆經50年,這裏從一個叢林密布的後殖民地國家變成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年的數據,新加坡位列人均國內生産總值的全球第三名,僅次于卡塔爾和盧森堡,領先于文萊、挪威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而這個國家沒有從地下挖掘大量的碳氫化合物,也沒有爲那些從人民手中竊取財産的盜賊們提供零稅收的便利。一個典型的新加坡人所擁有的經濟保障和物質財富,遠遠超出他父母輩的想象。在這裏真正的貧困是很罕見的。
然而這個典型的新加坡人也很憤怒。因爲大衆所能期待的物質水准和無法穿透的玻璃天花板另一邊的少數人所能享受到的物質水准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新加坡反複強調自己的教育系統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衆多高級職位卻由外籍人士和在國外鍍過金的本地人占據,這也讓新加坡人難以接受。這些人可以享受普通人買不起的汽車、公寓和餐廳服務。而這種不平等的感覺還與世代更叠有關。對于建國一代而言,工作、財富和安全都代表了一個值得爲之奮鬥的烏托邦。如今的年青一代穿梭在令人眼花缭亂的購物中心裏,黏在他們方寸大的屏幕前,從沒有面對過與上一代相同的困難。因此他們想得到更多的東西,但沒想到一頭撞上了玻璃天花板。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Unit)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2017年,新加坡已是連續第四次入選全世界“最昂貴的城市”。這樣的調查結果通常會在當地媒體上刊登,並傳達出官方對外籍居民喜好葡萄酒和公寓生活的半否認態度。2014年在國會就預算案辯論時,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明確指出,下列消費屬于外籍人士的特有開支:“進口奶酪、菲力牛排、博柏利雨衣、劇院裏的最佳四連座、四人份三道菜的高端晚宴。”言外之意就是,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並不高,只要新加坡人能滿足于公共交通、小販中心和HDB組屋。但我不確定這個信息在公民中的反響達到了尚達曼的預期。
如今不但在社會契約的三個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玻璃天花板,作爲新加坡社會基石的精英主義管理機制也開始受到質疑。“國民的素質決定了國家的産出,”李光耀曾說,“區別就在于,你如何挑選國民,如何訓練、組織並最終管理他們。”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你足夠優秀,你就能找到工作,而言外之意是,在這樣一個狹小的國家裏,沒有無用之人的容身之地。
然而,即使沒有富裕的西方外籍人士和超級有錢的亞洲人,研究也證實了一種印象,即新加坡社會只有在某個不可滲透的社會頂層之下,階層才是流動的。新加坡雖然有85%的人居住在公共住房中,但一項研究表明,那些住在私有房屋、在頂尖大學讀書的人,更願意和跟自己條件差不多的一小撮人親近。上層人士的特權不斷被他們所處的社交圈強化,而上層以外的人則感覺受到了排斥。這一現象在當今世界並不罕見,但在新加坡尤其具有破壞性,因爲這個國家如此之小,而且它對流動性和精英管理做出過公開承諾。一項調查表明,60%的年輕人考慮移居國外以尋求工作機會,並使自己可以負擔得起生活開支。
在李光耀去世後的幾年中,媒體上出現的一段插曲加劇了人們對新加坡精英主義文化的擔憂。這段插曲以李光耀遺囑中的一項條款爲中心,表現爲李氏家族的不睦。遺囑規定,家宅必須在李光耀死後拆除。這一要求一部分出于隱私考慮,但另一部分,也是值得贊賞的部分,是他害怕死後圍繞自己形成個人崇拜。雖然大多數新加坡人對于他們這位前領袖抱有極大的尊重,但新加坡鮮有街道或雕像紀念他。李光耀也許是一位偉人,但他的家族不應該因此沾光。
李光耀故居。
李光耀的住所是一座可愛的(盡管是被腐蝕的)五居室平房,位于歐思禮路的黃金地段,那裏曾經是一片種植園。(報紙估計,這塊地皮如今價值超過2000 萬新元。)2017 年,關于這處房産的處理問題以一種頗爲轟動的方式登上新聞頭條。李顯龍總理的弟弟和妹妹聯合發表聲明,稱自己的胞兄“將自己對權力和個人聲望的欲望與李光耀的遺産牢牢結合在一起”。如此一來,他試圖違背父親拆除家宅的遺願(李光耀年邁後一直照顧他的女兒李玮玲已經不在那裏生活了),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形象。他們還稱,李顯龍試圖建立一個政治王朝,並表示“不管是以兄長還是領袖的身份,我們都不信任顯龍”。而李顯龍總理在國會面前則明確否認了這些指控。他說自己的兒子對政治沒有興趣,並開玩笑說,如果他在13 年的總理生涯後還需要通過一座房子來借用父親的“光環”,“我也太可悲了”。
不管這些聲明和總理的反駁是否屬實,這場內讧能在公衆面前展開本來就已非同小可。這件事情隨後主要通過Facebook的帖子形式繼續發酵,很有可能進一步削弱公民對新加坡政治權力與利益無涉以及精英化本質的信心。這也就意味著,公衆不再相信新加坡社會中政治權力與利益無關,並且保有精英化本質,甚至開始質疑政治階級的合法性。
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憤怒正在對新加坡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産生影響,博客和社交媒體成爲新加坡人發泄不滿的最常用和最新的方式。一些人對外來人口的敵意越來越大,無論這些人是外籍專家、家政工人還是亞洲“那些在Instagram上炫富的富二代”。有人抱怨說,西方的外籍人士占有了最好的工作,家政工人把公共交通工具弄得亂哄哄的(你試著坐一下174 路公交車,該車往返于武吉知馬和菲律賓人周日的多功能會面場所幸運商業中心)。新加坡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都不是本地人,要平衡三個階層——本地公民、高技能的外籍人士和低技能的移民——之間的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國人爲先黨(Singfirst)的網站(口號是“公平社會、強大家族、自信人民”)指出:“在過去的50年中,新加坡人淪爲了不斷追求經濟增長的附屬品。”這是在明確地指責人民行動黨的“精英主義”政策將新加坡變成了財富和收入高度分化的不平等社會,而且這一政策還使介于貧富之間的中産階級人數不斷減少。指責羅列出的事項還沒有結束:一方面,稅率旨在扶植外來的跨國公司和外籍員工;另一方面,壓榨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造成人口過度擁擠。此外,國民服役的要求對新加坡本國男子不利。它宣稱,新加坡如今亟須將整個經濟增長模式與“跨國公司和外國勞工”分離開來。與此同時,成功申請到“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國人人數大幅下降(永久居民擁有大量福利待遇,但沒有正式公民身份)。由于申請條件中要求“充分融入當地社會”,而且對申請資格做出評判的評委會由當地人組成,2016 年76% 的申請被拒,而在2009年申請失敗的比例僅爲30%。
從政治層面來看,國民日益增長的不安定感引發了戲劇性的後果。在2011 年的新加坡大選中,人民行動黨的支持率從75.3%下降到60.1%,而人民行動黨總統候選人在五個選區中只贏得35.2%的選票。人民行動黨在2012年和2013年的補選中再度失利。在新加坡人看來,這無疑稱得上一場大地震。用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的許林珠(Gillian Koh)的話來說,新加坡正演變爲一個“贏家和輸家”的社會,這種模式下的政治就體現爲“人們對于現行政治機構和領導人的信任被削弱,因爲人們認爲是體制造就了他們” 。
如何解決新加坡的外勞問題?
政府的應對策略是提供咨詢,並將經費撥給低收入人群。這一分析思路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不謀而合,大家都意識到,有一群人更能接受一個開放的全球化經濟所帶來的挑戰,而另一群人更想要地方保護,兩者之間存在分歧。在新加坡,低收入人群被稱爲“老街坊”。同時政府還采取一些措施確保新加坡公民享有優先選擇工作的機會。按照所謂“公平考量框架”的規定,該舉措旨在“加強新加坡人爲核心的勞動力隊伍”。2016年人力部部長林瑞生說,爲實現這一點需要雙管齊下。首先,因爲沒有做出適當的努力,強化企業就業人口中新加坡人的比例,100家企業將受到更加嚴格的審查。這其中20%的企業後來對用人政策進行了完善,但剩下的企業仍然處于林先生的嚴格觀察之下。其次,那些以公平和進步的方式在人力資本運作方面起到示範作用的企業,將受到政府優待。
而單純從逸事和個人層面出發,我的很多外籍朋友突然發現,不管他們的資曆有多優秀,也不管他們所在的行業本地優秀人才多麽缺乏,他們都被排斥在了有關職位的競爭範圍之外。每當我們周三晚上聚在一起,在足球訓練開始之前更衣的時候,我那些來自英國、荷蘭和澳大利亞的朋友都會大聲抱怨,自己在招聘時不得不跨越了怎樣的重重障礙。然後他們會沮喪地搖搖頭,說這些公司在浪費了兩到三個月的珍貴時間後,最終還是不得不從國外引進人才。
與此同時,從量化的層面出發,島上的非公民數量經過多年的增長後,突然開始發生逆轉。1970年,新加坡外籍勞工的數量占到全島人口的3.2%;2010年,這個比例則是34.7%。2008 年,外來人口的數量達到每月19萬人,漲幅近20%,而新加坡公民的人數則只增長了1%。盡管這一年的表現尤爲突出,但在其他年份,外來人口的數量每年都在穩定增長(增長率通常在兩位數),直到2012年那次決定性的選舉爲止。外來人口的增長率就此開始穩步下降。到2017年,人數大幅減少,達2.7萬人。
被削減的大多是高技能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不光在新加坡,在全世界都很稀缺。印度軟件和服務業企業行業協會(Nasscom)稱,新加坡簽證的通過率近年大幅降低了。2017年該協會主席R. 錢德拉什卡稱,當前受雇于新加坡的印度技術人員不到1萬人;而過去幾乎每年都要發放1 萬份工作許可證。但事實上勞動力市場對于IT員工的需求是持續上漲的,僅2016 年第四季度,針對該項技能的招聘啓事數量就增長了30%。
盡管在其他國家,也不難找出針對移民的類似政策,但對于新加坡而言,這一人數規模的下降造成的影響比其他國家要大得多。美國在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下開始限制綠卡的發放,但美國本土仍有大量可以使用的內部資源。隨著脫歐進程不斷推進,有些人也許會譴責英國在歐盟的移民問題上和自己過不去。但盡管如此,英國境內仍有6000 萬人口和多元化的經濟。但新加坡就不是這樣了,別忘了,它是漂浮在全球化汪洋大海上的一葉小舟。如果需要船員來修理船帆或者補充航海技能,她未必能在本土居民中找得到這樣的人。新加坡的奇迹顯然離不開跨國公司和國際高技能流動人才。政府很難在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與國民利益、國民感情(因爲在社交媒體的新時代,人人都能發表意見)之間找到平衡點。
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新加坡一直以來假裝自己的面積比實際的要大。確實,它的勞動力市場腹地延伸到了幾個同心圓以外,超越了它的國界:第一個同心圓囊括了來自馬來西亞邊境新山市(Johor Bahru)的日常通勤者;第二個同心圓囊括了特別是巴淡島和鄰近的印度尼西亞廖內群島的工廠的工人,這些工廠實際上是國內工業低成本的延伸。除此之外,還有來自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緬甸的外籍家政工人,以及來自孟加拉國和印度的體力勞動者。印度等地還會輸送高級技工,從事新加坡人如今很回避的重工業一類的工作。最後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專家,處在技能鏈的頂端。
新加坡的外籍勞工。
要改變勞動力市場結構當前的平衡狀態不可能一蹴而就,還需要高度集權的政府用有形的手加以引導。高技能的外籍專家,以及雇用這些人的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一直處在新加坡經濟價值鏈上遊最頂端的位置,因此對這一部分人口數量加以限制,必然會對新加坡高端經濟的維持造成實實在在的影響。而在勞動力技能的另一端,對外籍家政工人數量的限制將會引起極大的爭議,他們默默無聞的勞動對于新加坡家庭的正常生活至關重要。然而正如政治經濟學家琳達·林(Linda Lim)指出的,經濟學規劃師們需要校准勞動力的供求關系,以確保激勵機制不會偏向外國勞工。
這其中包括建築業,(由于新加坡人不願意從事該行業內的工作)外來勞動力大量湧入,並造成該行業長期處于低收入低生産率的狀態。此外,由于引入外籍家政工人太容易,國家從未設立專門照顧老年人的服務部門。馬凱碩教授也認爲,輕松就能獲取的外來勞動力對新加坡經濟産生了不良影響,並加劇了社會壓力。“這就像一種鴉片,”他對我說,“你引入外來勞工,然後外來勞工輕而易舉就增加了你的國民生産總值。但這也造成了社會問題。如果你想早上搭乘火車,卻發現捷運列車裏已經人滿爲患。”
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政府也在努力保護本國移民工人的權利。2016年,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宣布,他希望爲印尼的外籍家政工人提供更好的培訓、資格認證、正常的工作時間和住宿條件,提高他們的待遇標准。不用說,他也希望在新加坡務工的125000名印尼籍的家政工人可以獲得更好的待遇。菲律賓政府也明確表示,新加坡需保障菲律賓務工人員的工作條件。少數新加坡人用惡劣的方式對待自己家中的幫傭,這些話也是說給他們聽的。
2017年3月,林俊宏 和鍾瑞鳳因虐待40歲的菲律賓家傭賽爾瑪而入獄。在15個月的時間裏,他們只給她吃白面包和方便面。在逃到移民避難所之前,賽爾瑪的體重從49公斤掉到了公斤。而另一個案例則是一名中介向一個可能的雇主抱怨說,某個特定的外籍家政工人很難找到工作,原因是她堅持要求每月休假兩天。“她是來工作還是來度假的?”中介如是說。我們身邊辛勤工作的外籍家政工人,每周工作7天,全年無休,包括聖誕節和複活節,而有些家庭的牆上就懸挂著十字架和其他象征基督信仰的標志。
達士嶺組屋:新加坡對不平等現象的反擊?
就在吉祥紅龜粿的對面,穿過廣東民路,有一片在公共政策實驗下誕生的有趣建築直聳雲霄。七座布滿斑點窗戶的建築拔地而起,每一座都像一塊大概50 層樓高的多米諾骨牌,建築與建築之間由兩座灌木叢生的天橋連接。總的來說,在一塊不超過兩個足球場面積的地皮上,這一建築群構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公共住宅建築。達士嶺組屋 內有1858套豪華公寓、數千可移動的輕質混凝土牆體,還被賦予了新加坡政府滿滿的希望。達士嶺組屋項目是政府對日益增長的不平等現象的反擊行動之一,旨在向新加坡公民展示,公共住房也可以令人神往。任何人只需購買一日通票,就能乘坐電梯到達50層的高空天橋,盡情欣賞新加坡乃至印度尼西亞的瑰麗景色(橋的另一半則供樓內居民使用)。正如新加坡其他地方,這裏的天橋也不僅僅是一條步道,而是一座真正的花園,人們甚至可以在這裏找到這樣的標識:禁止露營和賭博。天橋邊緣有兩層圍欄將人們擋在一組軌道後面,用于架設玻璃清潔裝置和防止高空暈眩。
達士嶺組屋。
2010 年8 月,李顯龍總理在達士嶺組屋的55 層向全國人民發表了國慶獻詞。恰如其分的是,在獻詞中李顯龍總理強調了政府的目標是“讓所有新加坡人都能享受經濟增長的果實”。他還提到國民關于移民問題的“合理憂慮”,談起完善服務,包括更有設計感的HDB組屋。
極盡奢華的達士嶺組屋確實滿足了一切設計師的願望。它向世人證明,卑微的HDB組屋可以一點兒都不卑微,它能沖破那層阻隔在85%的居住在公共住房內的人和一小群富豪之間的玻璃天花板。這一點確實令人欽佩。但事實上,這一項目卻無意中強化了一種認識,即一部分新加坡人可以像買彩票中大將一樣得到不公平的獎勵。
在達士嶺組屋剛建成的時候,有5000人繳納了10新元的申請費用希望得到其中一套住房。中了頭彩的人在頭五年裏不允許進行房屋買賣,但五年過後,很多人從交易中獲得相當可觀的收益。這也許正反映出,這個如此優質和重要的樓盤,其初始售價低得多麽不切實際。2004年,5套新出售的公寓售價在345100新元到439400新元之間。2016年,其中一套公寓的售價達到112萬新元,這創造了HDB組屋交易史上的記錄。在此之前,至少有10套達士嶺組屋的公寓售價達到了7位數。事實上一個房地産分析網站在2015年就指出,從達士嶺組屋獲取一套公寓的概率堪比買彩票中大獎。從象征意義上講,這很難用以強調新加坡社會天生具有公平性。
達士嶺組屋是政府美化社會契約的起點,如今整個新加坡都在按照國民不斷變化的期待改頭換面。比如位于小島北部的榜鵝地區。這裏被重新開發成爲熱帶度假勝地,北岸海灣 這樣的時髦HDB組屋與旁邊全設施配套的寶家軒(ATreasure Trove)這樣的私宅比也毫不遜色。雙子瀑布以“新式的行政公寓”爲賣點,其宣介稱,在“風情無限的榜鵝海濱”,“每天早上醒來,眼前都是一個熱帶天堂”。還有一個以狂野西部爲主題的榜鵝牧場,混凝土小屋被塗成馬車的樣子,前面有一個用假草皮填成的馬的雕像。你也可以到疾馳馬廄(Gallop Stables)騎馬,玩一種叫“足球高爾夫”的遊戲。
如果你肚子餓了,可以前往螃蟹之家或梁吉簽名(Leong Ji Signatures)就餐,只需路過兩個渾濁的綠色水滴形池塘——裏面的烏龜仰頭望著天,喘息著。居民們騎著租來的自行車,在海邊的木板上搖搖晃晃地前行,沒幾十米就停下來調節一下手機裏音樂的音量。在榜鵝海灘(Punggol Beach),曾有幾百名華人在日占期間的肅清行動中被殺害,如今這裏被奇異的圓石頭覆蓋著。
而離榜鵝海岸不遠,位于柔佛海峽中間的實龍崗島如今被重新命名爲科尼島(Coney Island)。新加坡政府非常慎重地嘗試更新社會契約,以滿足新一代人的需求,這一代人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習慣于面對各種不確定性。這背後傳達出來的信息是,不只是買彩票中大獎的達士嶺組屋住戶才能實現Instagram 上的豪宅夢:每個人都能享受度假村式的生活方式,不管你是惱怒者還是自滿者。
原作者 | [英]尼古拉斯·沃爾頓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