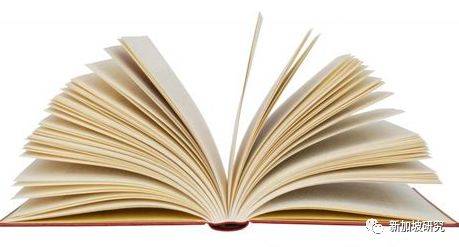自左向右依次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崔峰老師、新加坡新移民社團華源會會長王泉成先生、範磊
作者簡介
範磊,國際政治學博士,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山東政法學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山東政法學院“一帶一路”國別與區域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中國亞太學會東北亞研究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新加坡政治與外交,公共外交,一帶一路,比較政治與社會發展。
內容摘要
有限的面積、多元的族群認同和複雜的地緣環境對新加坡的生存與發展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但是其族群和諧的圖景與出色的管理能力爲其贏得了與先天條件不相稱的巨大影響力。
新加坡建國幾十年來族群治理的成功經驗表明,國家與社會的分層治理結構對于這個有著多元宗教、多元語言與文化的多元族群社會是積極而有效的治理模式。
在其中,國家依然扮演著主導性的角色,族群與宗教社團則成爲新加坡社會和諧與國民融合的重要紐帶和節點,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讓公衆有了參與國家與社會事務的機會。
引言
多元族群的國家中,認同和效忠于本族群的原始情感,並未隨著政治現代化而消退,反而在該進程中被強化,特別是當他們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時,這種受控于族群意識的“逆穩定”力量便成爲一種對既定社會秩序的潛在威脅。出現在時代截面上的多元族群問題在成爲影響本國政治發展進程重要變量的同時,也已經跨越邊界,成爲地區性、世界性的政治議題。只要有族群多元差異性的存在,就會存在族群問題。東南亞作爲世界上族群異質性最高的區域之一,已經讓其成爲族群政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選項,處于該區域中心的新加坡自然不能例外。
新加坡可謂是先天不足最爲典型的一個國家,作爲地圖上的一個“小紅點”,有限的面積、多元的族群認同和複雜的地緣環境對其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但是其族群和諧的圖景與出色的管理能力卻在國際社會贏得了與其先天條件不相稱的巨大影響力。它的存在與發展爲族群政治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且有意思的案例,國家雖小,卻充斥著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斷層線”,不論是從其社區、國家乃至整個地區層面來看,新加坡人口中所包含的族群與社會的異質性、各族群之間所具有的曆史與社會的複雜關系、族群個體之間的社會互動、國家在族群問題與族群關系治理方面的實踐與經驗等,都清晰展示了新加坡族群政治發展的一幅幅生動畫面。
國家與社會關系
國家與社會關系:新加坡族群治理的基本變量
自國家誕生以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博弈便貫穿在人類曆史的發展進程中。有學者曾經將決策與治理的五個層次從微觀到宏觀依次劃分爲個體、角色、政府、社會與體系。從總體來看,不論是國家與個人、族群、社會組織以及其他各層級的行爲體之間的互動都擺脫不了國家與社會的基本框架。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正隨著社會力量的壯大和國家力量的稀釋而逐漸走向融合,進而衍生出一種不同于以往的公共治理模式,其中“治理結構或者秩序的産生並非被額外地強加,而是通過治理的多樣性互動來實現,並在各行爲體之間相互影響”。
目前,治理理論日益強調社會多元主體的合作共治,政府機構以外的非政府性、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已經融入公共治理領域,國家與社會之間通過積極而有效的合作實現了公共資源與權力在全社會的分配與再分配,社會組織與政府共同承擔公共管理責任的同時,也實現了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互構。“隨著執政形式的發展,存在于公共和私人部門之間或者內部的邊界與區隔逐漸變得模糊不清”,國家與社會之間不再是傳統的線性統治關系,而是逐漸轉變爲互動合作的網絡多元治理架構,“政治秩序正在從組織/科層體系向網絡轉變”,實現了縱向垂直的科層體系與橫向水平的社會變量之間的縱橫交叉。
新加坡建國幾十年來族群治理的成功經驗表明,國家與社會的分層治理結構對于這個多元族群社會是一種積極而有效的治理模式。首先,“沒有哪一種競爭性的政治結構……擁有像國家這樣足夠全面的多維能力”,所以新加坡依然將國家視爲是現代社會秩序中具有決定性的組織工具,以政府爲代表的官方治理體系依然在這一公共進程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其次,新加坡特有的族群與文化結構賦予了以地緣、血緣和神緣爲基礎的族群與宗教社團重要的曆史使命,它們的存在成爲新加坡社會和諧與國民融合的重要紐帶和節點。最後,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也爲公衆參與國家與社會事務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公衆正在通過自己的積極參與來影響國家的公共政策和社會發展。
族群治理和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
族群治理和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國家與政府的角色
自1965年獨立建國以來,新加坡國家治理層面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如何處理族群關系。針對當時所處的形勢,李光耀曾說,“種族欺侮和恐嚇事件,使新加坡人情願容忍獨立自主所面對的艱辛。種族暴亂的慘痛經曆,也促使我們更加堅定地下決心建設一個平等對待所有公民,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的多元種族社會”。
面對獨立後國內族群關系的現狀,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政府基于新加坡的族群結構以及周邊地緣環境的客觀事實,通過制定平等多元的族群政策和建立完善的相關配套制度等具體的因應措施,減少了國家與社會資源的內耗,緩和了族群關系,化解了族群矛盾。其中,高效的國家與政府提供了結構性的保障,如福山所說,“集聚合法的權力並運用于特定的目標,這是只有國家和國家集團才能做到的事情”。作爲國民融合與社會和諧的主導性力量,政府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結構,制定了相應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政策,通過國家層面的治理結構來主導新加坡族群關系與社會和諧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通過系統的制度設計來規制多元族群之間的關系,協調各族群之間的互動,並爲少數族群在國家事務中的地位提供切實保障。曆史與現實的深刻教訓讓行動黨政府理性選擇了維護多元平等社會、反對族群霸權和特權的道路,一方面避免給予多數族群以政治特權,另一方面則依法保護少數族群的利益,鼓勵少數族群積極融入社會。在政治領域,主要通過意識形態引領、國會立法、成立相關機構、制定相關制度、發展基層組織等形式來實現在政治領域對少數族群利益的維護。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集選區制度,該制度下的選區需以幾個人組成團隊的方式參與選舉,且每個團隊必須有至少一名非華裔的少數族群參選者。設立集選區制度旨在照顧少數族群,有助于少數族群獲得更高的勝選機會進入國會,是追求族群平等的重要舉措。
組屋分配時所遵循的族群比例配額制度同樣具有代表性。殖民地時期分而治之的族群政策造成各族群之間的隔閡與猜忌,讓新加坡政府意識到跨族群交流的重要性。1989年,國家發展部部長丹那巴南就組屋的分配問題指出,當年3月以後的組屋分配將采取族群比例原則,要求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毗鄰而居,通過這種方式培養各族群之間的互動交流與和諧容忍。2007年,國家發展部部長馬寶山再次強調組屋區的族群融合政策的成果和重要性。政府在具體的族群治理中通過精心設計的制度框架實現了對多元族群關系的協調和整合,推動了國民融合進程的有序進行。
同時,在意識形態的引領和國家認同以及共同身份塑造方面,新加坡建構出一個中性的“新加坡人”概念,早在1966年新加坡成立不久,惹耶勒南就起草了“國民信約”,強調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並爲實現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爲此,還專門成立了“國家意識委員會”,從1988年開始每年都舉行一次“國民意識周”活動,增強公民對新加坡的認同感和歸屬感。1991年,國會發表《共同價值觀白皮書》培植公民的國家意識,要求國民要通過族群的和諧與平等來共創全社會的發展與穩定,強化新加坡的國家認同。
其次,通過有效的政策引導實現族群治理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多個橫向領域與國家與社會這一縱向科層機制下的縱橫交叉,推動網絡化治理的實現。“在凝聚多元族群社會和鼓勵個人與團體參與國家制度方面,語言是無可替代的有力工具。”所以新加坡政府決定制定和執行多元語言與文化政策,既尊重各族群的既有語言文化傳統,避免語言霸權;又通過確立馬來語爲國語,尊重馬來人的土著地位,並將不帶任何族群色彩的英語作爲中性的官方通用語言,既有助于減少周邊馬來國家對這個城市國家的猜忌和敵視,又可通過語言的同質化培養和增進新加坡的社會凝聚力。
新加坡教育制度的目標就是要消除各族群之間的差異,增強國家的共同感,增進對新加坡的認同和效忠。政府通過取消不同語言源流的舊教育體制,推行雙語教育體制,以此來消除各族群之間在社會文化方面的隔閡,增進互動和認知。如杜進才所說,“我們要求各民族的教育與語言平等……我們會繼續支持受英文教育的人學習英文,但是,受英文教育的人也應該跟受華文、巫文、印文教育的人站在同等的地位上……任何人都不應該有特權”。而爲了照顧少數族群,新加坡憲法第152條也給予馬來人特別的優遇,並設立了馬來社區發展理事會(Mendaki),協助馬來族群在教育文化和經濟與社會領域的發展與進步。
同時,政府意識到社會動亂和族群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爲各族群之間明顯的貧富差距,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提升弱勢族群的經濟地位。爲此,成立了少數族群權利總統理事會,通過政策傾斜和制度保障來提升少數族群尤其是馬來族群的經濟地位,後來還專門設立了總統咨詢委員會,集中處理馬來族群的發展及宗教事務。最終政府通過提升馬來人的教育水平來增強其就業和經濟能力,逐漸縮小了與其他族群之間的經濟差距,有效地促進了與其他族群的合作和共處。
最後,建立起完善的組織體系,以自上而下、由內而外的組織機構系統來完成具體的治理實踐,推動族群治理的有序進行。具體來說,主要有基層組織系統和國家組織系統兩個層次,目前已經建立起以政府爲引領、以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爲主體、以社區爲紐帶的基層組織體系,將政府、社團、社區和國民有機地聯系起來。良好的基層社區建設既是人民行動黨政府鞏固其執政地位的重要基礎,也是推動跨族群互動交流,做好族群治理的有效平台。
社區基層組織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公民咨詢委員會、民衆俱樂部和居民委員會。這些組織主要負責向政府反饋不同族群選民的訴求,並把政府的政策和相關具體措施傳遞給民衆;承擔社區具體活動的開展,並根據樂齡、婦女、青年、馬來族群、印度族群等不同的執行委員會劃分來開展不同的活動;協調社區鄰裏關系,通過各種鄰裏之間的互動交流和對話活動來促進鄰裏和睦、族群互助和社會和諧。
除了完善的基層組織系統,新加坡政府還在國家層面設置了統領國家族群議題的組織機構,以此來引領跨族群的交流與互動,提升作爲“新加坡人”的凝聚力。早在1970年,政府就成立了少數族群權利總統理事會(PCMR),政府向國會提交新法案之前,都須交由理事會審查,以確保各項法案的內容不會損害或影響到少數族群的權利,並向總統做出報告。此外還有宗教和諧總統理事會(PCRH)、族群與宗教互信圈(IRCC)、社區發展理事會(CDC)等組織機制,來確保各族群尤其是少數族群的利益訴求可以在國家與社會層面得到切實的保障。比如文化、社區及青年部就設立了總額500萬新元的和諧基金(Harmony Fund),支持互信圈與個人或社區團體合作,推動跨族群和跨宗教交流,增強社會凝聚力。
新移民的增加讓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新加坡逐漸面臨著新的社會挑戰,而如何推動國民融合已經成爲新移民時代的迫切議題。李顯龍總理曾經在很多場合告誡新移民要積極融入新加坡社會,爲此政府特別成立了國籍與人口策劃署(CPU)和國民融合理事會(NIC)等機構來推動融合議程,並通過組織“公民日”“家庭日”等多種既面向本地人也面向新移民的活動來增進國民融合,打造同一的新加坡國家認同。
族群與國家的聯結紐帶和節點
族群與國家的聯結紐帶和節點:社會組織與公民社會的定位
如果說國家和政府在整個的治理框架中主導著族群互動與社會和諧進程的話,社會行爲體則在這一網絡式的治理框架中充當了跨族群的聯結紐帶和互動節點的基礎作用。社會層面的治理主體可分爲三部分:高效而完善的社會組織體系建構,多元化和多樣性的族群間與族群內部活動,以及迅速成長的公民社會。
首先,高效而完善的社會組織體系建構,爲新加坡的族群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作爲多元族群社會,新加坡的四大族群本身都有代表本族群的社團和相關機構,華人有傳統會館,也有新移民社團,馬來人有馬來人協會,也有各類自助和互助組織,印度人和歐亞人同樣有本族群的特色社團,這些帶有不同族群色彩的社團,一方面通過推動本族群內部的活動來傳承優秀文化,另一方面則通過與其他族群組織之間的跨族群交流來推動國民融合與族際和諧;作爲多元宗教社會,新加坡有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等數個宗教派別,完善的宗教管理機構在傳播信仰和善念的同時也在教導信衆要與人爲善,和諧爲本,熱愛新加坡,關愛他人。
對于華人社會而言,以會館爲代表的華社機構是聯結不同方言群和新老移民的有效紐帶。成立于1986年的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在其發展願景中明確提出要“領導宗鄉會館;弘揚華族語文、文化與價值觀;建立緊密聯系的宗鄉會館網絡;促進種族和諧與社會凝聚力;從事一切其他符合或利于促進上述宗旨或其中一項宗旨的活動”。成立20多年來,總會充分發揮華人在地緣、血緣和業緣等多個領域的團結優勢,通過主辦“春到河畔迎新年”、體育文化比賽、資助學術研究以及舉行多元族群同胞交流等活動提升國家凝聚力,推動跨族群互動與和諧。陳振聲部長曾指出,“我們鼓勵宗鄉會館、社團組織以及各基層單位,爲建立起一個更爲包容、相互理解、互相尊重並且充滿活力的多元種族社會而努力”。目前,總會正在與其他多家會館合作推動中華文化中心建設,旨在爲各族群提供一個社區互動的空間,將其打造成推動本土居民和新移民融合的新平台,通過展示與弘揚多元文化,促進社會發展和族群和諧。
作爲傳播信仰和善念的平台,不同的宗教在信仰、價值觀和社會美德等多個方面都有著共通之處,在國家和政府推動全民共同價值觀的同時,新加坡的宗教團體也通過對信衆的影響力,協助各族群的民衆內化這些價值觀,塑造社會品德,推動跨族群、跨宗教的交流與溝通。1968年,由馬來族群推動成立的新加坡回教理事會(MUIS),就旨在爲總統和政府在伊斯蘭教事務決策方面提供相關政策建議,推動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義的認知和理解,維護和照顧信衆在宗教、社會與福利等方面的訴求,將之與國家福祉緊密相連,並將協商與包容作爲工作的核心價值。
爲了推動馬來族群的經濟能力和教育水平,回教理事會設置了回教救濟金(Zakat),2011年該項目曾經讓2000多個貧困家庭受益,而2004年啓動的扶貧計劃和2010年設立的成長基金(Progress Fund)也針對穆斯林貧困家庭的生活與教育提供相應的補助和扶持。理事會的這些舉措一方面使需要幫助的穆斯林家庭得到了及時的救助,另一方面避免了族群內部因爲貧富差距而滋生極端主義,有利于維護族際和諧與社會穩定。
其次,多元化和多樣性的族群間與族群內部活動爲政府政策的推行和社會公共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平台。2013年4月6日,新加坡舉行了首屆“築橋研討會”(Building Bridges Seminar),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代部長黃循財在演講中指出,“新加坡幾十年來所享有的社會和諧以及各族群之間的和平關系與各宗教領袖的獻身精神和積極維護密不可分,跨宗教和諧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一直持續下去,築橋研討會將成爲促進宗教對話、搭建跨族群和跨宗教橋梁的重要渠道”。雖然是馬來社群主辦的會議,但是來自華人和印度族群的新加坡人占了很大比例,會議其他嘉賓包括新加坡十大宗教的領袖以及多位不同族群的學者。每年8月國慶期間,佛教總會還會舉辦仁王護國祈福法會,共創和諧新加坡。
廈門公會林璒利會長指出,當前新加坡人的生活與發展環境有了新變化,訴求也呈現出多元化多樣性的特點,華人社團就一定要利用好春節、中秋等重要節慶來開展豐富的活動,吸引各族群的同胞參與,以期在此基礎上促進國民融合。自2008年以來,以“中秋博餅”爲主題的“國民融合千人博餅慶中秋”活動已經由廈門公會連續主辦了五屆。博餅活動沒有年齡、職業、階層之分,在活動中部長和民衆、老人和孩童、華人和其他族群的同胞共同參與、全面交流,氣氛熱烈而融洽。這個活動作爲重要的溝通橋梁,既傳承了優秀的文化遺産,又構築起跨越族群的交流平台。
除此之外,宗鄉總會還經常聯合其他社團在每年的傳統節慶舉辦跨族群民衆的聯歡活動,促進國民融合與跨族群交流。筆者有幸參加了今年(2013年)的端午節民衆嘉年華,粽子都呈現出既有馬來風味也有印度風味的多元性,文藝表演除了華人傳統戲曲,還有馬來族的鼓樂表演、印度風情的歌舞表演等。作爲嘉年華高潮的旱龍舟比賽,筆者參與到新移民社團天府會龍舟隊中,與來自馬來和印度族群的新加坡朋友同台競技。現場有一位印度裔的老人還拿起毛筆,現場揮毫,寫下“天下太平”四個字。活動主賓環境與水資源部部長維文醫生的中英文致辭也強調了通過這種跨族群互動推動國民融合的意義。
最後,公民社會的迅速成長,各族群國民日漸成爲族群與公共治理進程中的主體力量。以社會公衆爲主體的公民社會在族群治理網絡中是最基層的力量,也是最活躍的參與者,隨著民衆參與意識的增強,他們“希望在自己共同關心的事務中聯合起來,通過他們的存在本身或行動,對公共政策産生影響”。尤其是在與日常的工作與生活密切相關的跨族群交流領域,公民社會的成長更凸顯出其重要的意義。
多年的經驗也表明國民融合與跨族群互動是雙向行爲,不同的族群要積極融入所在的社區,將新加坡作爲國家認同和忠誠的對象,本著平等合作、和諧共處的心態與其他族群同胞建立良性的互動關系。筆者曾經在2013年1~4月間分別在榜鵝東、蔡厝港和阿裕尼采訪,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的受采訪者都表示,其他族群的同胞與自己並沒有什麽不同,大家都是“新加坡人”,雖然膚色、生活習慣、信仰與文化以及政治理念等方面可能存在歧義,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彼此的親近感,有一位華人老者更是將他的印度裔鄰居稱作“兄弟”。
隨著近年來新加坡新移民數量的逐年遞增,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成立的新移民社團,也在新加坡國家發展與社會和諧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成立于1999年的天府會就提出了“從天府走進獅城,從融入邁向投入”的重要使命,天府會署理會長楊建偉教授在談到“新移民的融合之道”時指出,新移民一方面要保持正確心態,做到入鄉隨俗,尊重本土社會,另一方面還要學會欣賞和感恩,學會“爲客之道”,以實際行動來踐行“融入”新加坡的承諾。
由于不同的族群之間有著各異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所以此時各族群之間的包容就顯得更爲關鍵。比如華人習慣于在組屋樓下辦葬禮,而馬來人則習慣于在組屋樓下辦婚禮,兩件事情對于兩大族群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傳統。經過幾十年的磨合,基本都能體諒對方的這種文化傳統。當然也有個別情況,2012年10月張艾美在面簿(facebook)上抨擊馬來族群婚禮的行爲遭到了來自華人社會、馬來人社會以及政府和其他族群的共同譴責,最終以張艾美被辭退公職離境而解決,顯示了公民社會的強大力量,也證明了族際和諧在新加坡人心中的地位。
結論
新加坡的成功引發了學術界對其發展模式的關注和思考,多數學者都認爲新加坡在族群治理方面成績斐然,給相似的多元族群社會處理類似問題提供了借鑒,但是也有學者認爲新加坡“小國寡民”,國家層面的治理相對容易,其經驗不足以推而廣之。其實,如果放眼全球就會發現,不論是族群沖突還是族群和諧,與國家的幅員大小與人口數量並沒有必然的聯系,認爲新加坡國家小人口少好治理的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
學習新加坡,最要緊的不是照抄照搬它的治理模式和現成經驗,而是要學習新加坡的治理思路,學習其作爲一個多元族群國家能通過有效的多元和多層治理實現跨族群和諧與社會穩定的“新加坡精神”內核。可以說,“新加坡已經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成功不僅在經濟方面,而且也在它的社會以及人的性格和成就上,四個偉大的傳統在這裏快樂地和平共處”。這種美好的和諧圖景,對其他同類型國家是一個很好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