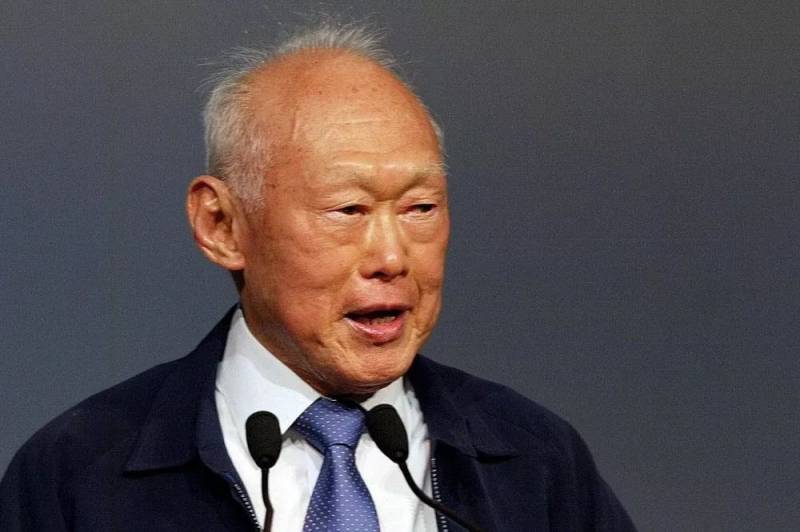本文選自《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美)艾利森、(美)布萊克威爾、(美)溫尼編,蔣宗強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李光耀
(Lee Kuan Yew,1923.9-2015.3)
人性本惡
我認爲: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雖然這樣說可能令人沮喪,但我仍然這樣認爲。
我們已經征服了太空,但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緒,這些本能和情緒對于我們在石器時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時代卻沒有必要。
雖然儒家思想認爲人性可以改良,但我一向認爲人類就像動物一樣,我不確定能否改良,但我認爲可以進行訓練,可以進行管教……你可以讓一個習慣使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寫字,但你無法真正地改變其與生俱來的本能。
人們認爲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或者說應該是平等的……但這種想法現實嗎?如果不現實,那麽追求平等就會導致倒退。
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是沒有任何兩個事物是完全平等的,沒有同樣小的事物,也沒有同樣大的事物。事物從來都不是平等的。即便對于非常相似的雙胞胎而言,出生時也有先後之分,先來者優先于後到者。人類是這樣,部落是這樣,國家也是如此。
人類不是平等的,他們處于極其激烈的競爭中。蘇聯已經失敗了,因爲他們試圖把利益均等化,這樣一來,沒有人會努力工作,但每個人都不想比別人得到的少。
我一開始也認爲人是平等的……現在我知道這是最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因爲人類已經進化了數百萬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絕,獨立謀求發展,種族、民族、氣候、土壤條件都不盡相同……這是我在書本上讀到的東西,我自己的觀察也印證了這一切。
對任何一個社會而言,在1000個新生兒中肯定有相當比例的嬰兒接近于天才,有相當比例的嬰兒是普通人,也有相當比例的嬰兒有點兒愚笨……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終決定了未來的事情……
我們想要一個公平的社會,我們想給每一個人提供均等的機會,但在我們的思想深處,我們從來不會自欺欺人地認爲存在兩個在毅力、動力、敬業程度、內在禀賦等方面一模一樣的人。
在這個問題上,弗雷德裏希·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負》中表達的觀點非常明確,而且具有權威性,與我長期以來的想法不謀而合,但他的書沒有說明一些偉大的知識分子的不明智之處,其中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些偉人往往認爲人類大腦可以設計出一種更好的制度,這種制度比“曆史演進”或“經濟達爾文主義”在過去幾個世紀帶來的“社會正義”還要多。
任何一個政權、任何一個宗教、任何一種思想都無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設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樣化特征太明顯了,不同的種族、文化、宗教、語言及曆史要求各國通過不同的道路實現民主和自由市場。在全球化的世界,各個社會因衛星、電視、互聯網及便捷的旅行條件相聯,因此各個社會就會相互影響。
在某個發展階段,什麽樣的社會制度能最好地滿足一個民族的需求,是由社會達爾文主義決定的。
我會把自己描述爲一個自由主義者
也許按照歐洲的標准,我是一個介于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之間的人。
我會把自己描述爲一個自由主義者。一方面,我倡導機會均等,努力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最好的發展;另一方面,我還有一定的悲憫之心,希望失敗的人不會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讓制度以最高的效率運作,但同時考慮到那些現狀不佳的人,因爲他們的自然條件沒有提供給他們足夠多的資源,或者他們本身缺乏努力奮鬥的條件……
我是名副其實的自由主義者,因爲我不會拘泥于某一種關于治理世界、治理社會的理論。我是務實的,我願意直面問題,說:好吧,什麽才是最佳解決之道?怎樣才能爲最多的人創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長于三世同堂的家庭,這就不知不覺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這種思想會潛移默化地滲透進你的大腦。儒家思想認爲如果人人都爭做“君子”,那麽社會就能實現良性運轉。理想中的君子與紳士有些類似……這意味著不要做邪惡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順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撫養孩子,善待朋友,這樣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
儒家內在的哲學觀念認爲如果想要一個社會實現良性運作,你就必須考慮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會利益必須優先于個人利益。這是與美國文化的主要差別所在,因爲美國文化是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外出旅行和訪問期間,我會注意觀察一個社會、一個政府是如何運作的,會思考爲什麽它們運作得好……人的思想不只來自閱讀,你可以從書本中獲取,但如果你不把書本知識同自己的情況結合起來,書本知識就無用武之地。我自己經常會把讀到的東西同自身情況結合起來……
同博學多才的人展開討論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點一定不要忽略,我認爲這比單純孜孜不倦地閱讀文獻強得多。因爲通過短暫的交流,你就能萃取對方的知識和對方的思想精華。
新加坡的模式是無法輕易複制的,我認爲這是我作出的最大貢獻,也是最有價值的事情。
性格、經曆和思想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還有我的一些生活經曆。當你的整個世界轟然坍塌時,你就會遇到一系列不可預見的、出乎意料的情況。我的人生就是這樣。
如果日本軍隊沒有在1942年發動侵略,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統治或許會再持續1000年,但事實上在1942年就終結了。我從來沒想過日本人會征服新加坡、把英國人趕出去,但他們確實做到了,還用殘暴的方式對待我們,包括我本人也遭受過日本人的虐待……
在毛澤東提出“槍杆子裏出政權”之前,我就深刻地知道了什麽是權力。日本人表明了這一點,英國人卻沒有。
當時大英帝國快要走到盡頭,在技術、商業和知識領域都占有主導地位,已經沒有必要使用殘暴的武力了。他們只是在1868年動用印度的犯人勞工們在山上修建了這座巨大的政府辦公樓,以此統治人民……我從英國人那裏學到了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見識了日本人是如何運用權力的。
日本人對新加坡的侵略給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課,因爲在長達三年半的時間裏,我看到了權力的意義,看到了權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關的,而且我還明白了在強權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們爲了生存會采取哪些應對之策。先是英國人在這裏,他們是固有的、完全意義上的主人,而之後日本人來了,我們一直奚落日本人是矮胖、短視和斜眼。
當我和在內閣中擔任高級職務的同事們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的忙碌歲月時,我們都意識到充滿磨難的學生時代使我們受益良多。我們遇到了街頭惡霸,如果我們沒有體驗過這種磨難,那麽我們就會被打倒。如果我們從未感受過憂患,就像一條狗被圈養在籬笆後面的小屋裏那樣安全無憂,那麽當我們身處危險重重的車流中就會被碾壓而亡……
我們的孩子沒有經曆過那種殘暴侵略下的艱難歲月,較年輕的一代部長們也沒有過這些經曆。激烈的鬥爭造就了老一輩的部長們,我們中間那些身體虛弱、行動緩慢或者容易緊張的人就成爲早期的犧牲品。我們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達爾文所謂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幸存下來的人,我們都有強烈的生存本能。
自1973年以來,我學到了什麽呢?我學到了一些關于人類與人類社會的更加基本的、永恒的道理,學到了如何讓人類和人類社會實現更好的發展,學到了倒退和崩潰的風險是永遠存在的……我意識到了一個文明社會是何等脆弱……我還明白了個人成就的重要意義。
在50多歲、將近60歲時,我意識到,同知識、道德和精神上的滿足相比,塵世的一切榮耀與成功都是轉瞬即逝的,一切感官上的愉悅和快樂都是短暫的……我不禁開始懷疑我所擁有的東西中有多少是先天決定的,又有多少是後天培養的。如果我沒有經曆過艱難抗爭的考驗,我會與現在的自己有所不同嗎?
作出了一個個生死攸關的抉擇,經曆了一次次重大的危機,我的眼光、雄心和辨別輕重緩急的能力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我相信這種變化將對我産生深遠的影響。也許所謂的“硬件”(即我的身體、精神和情緒)並沒有什麽變化,但我的“軟件”(也就是我對上帝、榮耀或金錢的看法)已經受到了人生閱曆的深刻影響。
換句話說,無論“硬件”(由先天決定)多麽好,沒有“軟件”(靠後天培養),“硬件”也不會有多大的用武之地。
嚴峻的考驗是成績,而不是承諾
邏輯與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最終檢驗。
嚴峻的考驗是成績,而不是承諾。數百萬無依無靠的亞洲人不關心也不想知道什麽理論,他們只想過好一點兒的日子,他們想要一個更加平等、公正的社會。
如果我們要創造良好的經濟條件,就必須找到實際的辦法,解決增長與發展問題,而不是尋找這種或那種理論。這也符合理智的要求。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種哲學或某些理論指導的。我把事情辦好,讓別人從我的成功之道中總結理論或原則,我不會搞理論。相反,我會問:怎樣才能做好這項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決方案之後發現某個方案切實可行,那麽我就會努力找出這個解決方案背後的原則。
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在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如果我面對一個困難、一個重大問題或者一系列相互沖突的事情,而初步解決方案行不通,那麽我就會先看看是否存在備選方案。我會選擇一個成功概率比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敗告終,我還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樹上吊死。
我們不是理論家,不會搞理論崇拜。我們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人們要找工作、要掙錢、要買食物、要買衣服、要買房、要撫養孩子……我們可能讀到過什麽理論,也許半信半疑,但我們要保持現實、務實的頭腦,不要被理論束縛和限制住。如果一個方案行得通,我們就實施,這樣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經濟。
面對一個理論,我們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它可行嗎?能給人民帶來利益嗎?當年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理論之一就是跨國公司壓榨廉價勞動力、廉價原材料,會把一個國家壓榨幹淨……我認爲,既然廉價勞動力閑置,那麽如果跨國公司想利用,爲什麽不行呢?我們可以從跨國公司那裏學習先進經驗,沒有它們,我們可能永遠都學不到這些……發展經濟學派認爲這是壓榨,而我們的經曆就有力地反駁了這種觀點。我們只是腳踏實地,絕非故意給高深的理論原則挑刺。
我認爲,一個理論不會因爲聽起來悅耳或者看起來符合邏輯就一定具有現實可行性。一個理論最終還是要放到生活中檢驗,也就是要看現實生活中出現了什麽,要看能給一個社會中的人民帶來什麽。
我認爲美國的制度不一定是理想的或者適用的。我注意到英國人一直在試圖模仿美國人……盲目效仿美國制度的人認爲,只要美國官員開始披露秘密,那麽這種行爲就應該成爲一種時尚,這種行爲表明你的社會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如果有任何部長或法庭壓制真相,你就有義務將其捅給反對派。
這種想法是否合理呢?這還是新事物,還沒有得到實踐證明。如果你損害了社會基礎,就會給下一代或者更下一代人造成不良影響。如果有兩種制度擺在你面前,一種是得到實踐檢驗的,另一種是尚未被檢驗的,而我又是保守派,我肯定會選擇前者,至于後者是否可行,爲什麽不留給其他人、讓他們證明呢?
如果一種制度能推動科技事業大繁榮、能給人民帶來幸福、能解決社會問題,如果因爲害怕引起爭議而放棄這種制度,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行爲……最終的證據是它能給社會帶來什麽。
我崇拜的領導人
戴高樂、鄧小平、溫斯頓·丘吉爾。
崇拜戴高樂是因爲他有巨大的魄力。他的國家被占領了,他是個一星的將軍,而且他代表法國……當英國人、美國人收複北非時,他前往阿爾及利亞和阿爾及爾,他在那裏看到一位四星的法國將軍。于是戴高樂說:“吉羅,你是一位法國將軍,爲什麽還要讓外面的美國士兵保護你?”他是一位意志堅強的人,他有勇氣、有魄力。
鄧小平是一個偉人,他引領貧困的中國發展成今天的模樣,成爲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指日可待。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有可能重走蘇聯的老路。
我崇拜丘吉爾是因爲當時換成其他人可能就放棄了,但他說:“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田野裏、在街巷裏作戰,我們永不投降。”在自己的軍隊吃了敗仗的情況下能說出這種絕不向德國人投降的話是需要巨大意志力、勇氣和決心的。
如果你問美國人他們崇拜誰,他們會說羅斯福。但羅斯福手中掌握著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工業實力。
不會把自己歸入政治家的行列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銘記。首先,我不會把自己歸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認爲自己是一個意志堅定、始終如一、堅持不懈的人,我腳踏實地地做事。我會堅持不懈,直至成功。沒有別的了……任何一個認爲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醫生。
別人會以什麽方式銘記我,我認爲我決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認爲有價值的事情。我從來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師,過上好日子,做一個好的顧問,但由于發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蕩,我無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負著很大的責任,我要負責讓國家正常運轉……
我能做的只是確保當我離開時,各種制度還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確保現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麽,知道搜羅高素質的下屆政府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