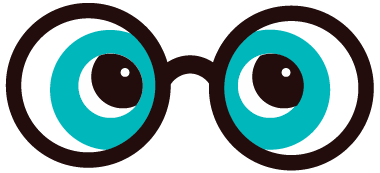
編按:饒宗頤先生(1917-2018)1968年至1973年曾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任教。此事因材料缺失,緣于目前有關饒先生的傳記、事迹、年表、研究等或失之簡略,語焉不詳,或文獻不征,頗有纰漏,或輾轉傳抄,謬誤衍生。
澳門大學曆史系教授楊斌搜尋新加坡本地檔案,梳理有關文獻,相互比較甄別,並尋訪新加坡耆老,問諸遺事,對饒先生星洲事迹著文如下。
緣起
饒宗頤 1968年秋執掌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到1973年秋離開,時間雖短,卻是他盛年時期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曆;也是他研究、創作、國際交流的爆發期之一。因此,有關饒宗頤的各種簡曆、年表、傳記都不能不提到。可是,所有的相關記載,均失之簡略,或一筆帶過,或謬誤間雜。
關于此事,饒宗頤本人距其離開新加坡大學最近的回憶是1976年8月。他在爲《新加坡古事記》記跋時回憶:“一九六六年夏,余在法京,忽接已故星洲大學林大波教授函,以該校中文系首任講座教授見邀,心許之而未敢遽應也,遲延至一九六八年杪始蒞星洲。”
按,當時聘用饒宗頤的是新加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0年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合並成爲新加坡國立大學(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簡稱國大或者新國大,沿用至今。不過,饒宗頤回憶中提到所謂新加坡大學校長林大波純屬誤會。1965年至1967年擔任新加坡大學的校長 (Vice Chancellor) 的是林溪茂,其英文名字爲Lim Tay Boh (1913-1967),被誤譯爲林大波。饒宗頤雖然是林溪茂聘請的,可是兩人之間並沒有見過面;聘請前後的通信以及聘書,按照新加坡的習慣,都是以英文進行,林溪茂的署名爲Lim Tay Boh。因此,饒宗頤1976年的回憶是根據此英文名而被記錄爲林大波,隨後大家都沒有查證,以致訛傳。
爲何南下?
那麽,新加坡大學爲什麽聘請饒宗頤呢?饒宗頤又爲什麽決定離開培育他多年的香港大學南下新加坡呢?
1960年代中期的饒宗頤正當壯年,其學術成就不僅在海外華人世界廣爲人知,在國際漢學界也是鼎鼎大名。1962年,饒宗頤因其大作《殷代貞蔔人物通考》獲得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頒發的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該獎以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命名,于1872年創立,可謂是國際漢學界的最高榮譽。此前此後,饒宗頤遊學日本、印度、歐美,一時交往,都是國際學術界的巨擘,其學問、見識和人脈可謂漸入佳境漸入盛境!而儒蓮獎大大擴大了饒宗頤在國際上的知名度,這應該是新加坡大學聘請饒宗頤的重要考量。須知,新加坡大學承襲英制,一個系的教授只有一兩個,遑論講座教授的頭銜!此外,除了饒宗頤的學術成就,林溪茂還要借重饒宗頤的行政能力、學術資源和人脈,聘其擔任系主任一職,服務行政,爲中文系的教學研究以及人才培養規劃藍圖。以此論之,林溪茂和新加坡大學對于饒宗頤是非常器重的;饒宗頤對于這個職位,應該也是滿意的,認爲自己能夠有所作爲。當時友朋也是這樣期許的。
那麽,具體招聘經過如何?亦不可考。惟德國漢學家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1912-2007) 的回憶或可一窺端倪。1968年,傅吾康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任客座教授。是年9月底,傅吾康途徑新加坡,“拜訪了還不太熟悉的饒宗頤,他現在是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賀光中離職後,新大要重新招聘新主任,曾邀請我去做評審。申請人當中沒有誰的學術資格比得上饒宗頤,他是大學自中文系成立以來聘請的唯一具有國際水平的學者,雖然爲期很短。饒宗頤的學術貢獻尤其得到了當時法國漢學元老戴密微的贊賞。” 以傅吾康的回憶分析,新加坡大學爲中文系這個職位曾經公開招聘,傅吾康是評審委員會委員之一,而饒宗頤遞交了申請;在相關的申請人當中,饒宗頤學術成就最爲突出,因而脫穎而出,被選定聘用。
饒宗頤去新加坡之前,香港的友朋門生爲之高興,特地編寫了《饒宗頤教授南遊贈別論文集》,作者包括羅香林、嚴耕望、羅慷烈等人。羅香林的“序”文可以一窺當時人們對于饒宗頤去新加坡的冀望。羅香林指出,南洋尤其是星馬地區,清末一向是文人南下的首選之地,中華遺風猶在,前賢有康有爲、黃公度等人。而饒宗頤詩書畫學術無一不精,其去南洋,前途自然大有可觀。羅香林遂預測雲:“今饒子不徒以學術蜚聲,自詩古文辭賦長短句,至于繪事雅琴,無有不精絕者。余固知異日南中父老之人物指點相告曰:此疇者饒某居停之所也,授業之壇也,著畫之齋也,題詩之壁也,鼓琴之台也,入畫之樹也。夫豈惟南中之人物山川草木鳥獸蟲魚,有所資於饒子哉!” 羅香林的這篇序,描述了友朋之厚望,也反應了饒宗頤的心聲。然而,結果卻是大相徑庭,令人唏噓。五十年後,不但饒宗頤居停不爲人知,連其執教事迹亦早已鮮爲人知!
因何離去?
不料,在新加坡的幾年卻和期許相背,饒宗頤非常不愉快。最後,原來九年的合約僅五年就黯然終止,而這五年當中,饒先生也小半時間在美國、台灣等地遊學訪問,真正問事不過三年多而已。這其中的原因,饒先生本人有過回憶,大致是對新加坡壓制中國文化不滿。胡曉明采訪時,饒宗頤回憶說,“1968年到1973年,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有五年時間。我在新加坡時心情不大好,那個時候,新加坡政府壓中國文化,所以後來我就跑掉了。新加坡本來請我擔任九年系主任,但是我到了第五年待不下去,因爲我在那裏做唯一的一所大學即國立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而政府卻根本不提倡中國文化,之提倡中國語,沒有‘文’,只學華語就夠了,害怕中國文化,對大陸非常怕。時代的轉變非常有意思。我不能再住下去。《新加坡古事記》是在新加坡時編的,應該在那裏出版年,可是至今才在香港出版。所以我的舊詩集取名《冰炭集》,如冰與炭。這跟當時的心情有關。假如我不以中國文化爲重,而以個人的生活爲重,我就不會這樣了,生活待遇上那是很不錯的。所以我離開之後,反而做了許多事情。我完全以中國文化做主體的。”
饒宗頤對于任教新加坡期望甚高。他去新加坡前後曾經花了很大的力氣整理新加坡的文獻和金石材料,研究新加坡曆史,先後有《新馬華文碑刻系年》和《新加坡古事記》的完成。可是,他個人的這種努力,和整個社會以及大學的氛圍尤其是有關政策導向是格格不入的。對此,饒宗頤在1989年有過側面而尖銳的批評。他在“新加坡古事記引”中說:
“夫河山有表裏,文化亦有表裏。今人之所追逐著,唯富是求,然富之至義,非資財貨殖之爲富也;有內富也,猶人之有內美也。內美爲何?立國之道,有不可動搖者,以文字曆史爲其長久之根柢,國之靈魂系焉。文字,非語言之謂也;必循其聲音形體,反覆其義,進焉以究其道。乃世有外尊語言而內蠲其文義者,有貌崇義理而徒繡其鞶帨者,是存皮而去其骨,買椟而還其珠也。顧體國經野,其塗多端,有好爲長久之遠慮者,亦有喜求一時之炫耀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智者,自擇而已。”
這段話把學華文抛棄中華文化的做法譬喻爲買椟還珠,現在看來,愈見饒宗頤的遠見卓識,令人掩卷長歎。沒有了文化的氛圍,饒宗頤才幹無處可施,郁郁不樂,途中幾次出走外國訪問,可謂興起而來,敗興而歸。
天入西南異我鄉
饒宗頤在新加坡的三五年內,其研究在原有領域如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金石學、書畫繼續高歌猛進,完成或發表了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曾憲通曾經評論說,“香港和新加坡是先生走向世界的舞台。” 此論頗有可斟酌之處。
香港確實是饒宗頤成就其學問、走向世界的基地和舞台;新加坡則不能這麽說。首先,在1968年來新加坡之前,饒在香港潛心學術近三十年,期間遊學日本、印度和法國,獲得1962年的儒蓮獎,已經在國際漢學界享有盛名;1973年秋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四十余年又再創輝煌,奠定一代宗師的曆史地位。應該說,香港這一因緣成就了饒宗頤,所以饒宗頤對于香港感情極其深厚。他在晚年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高屋建瓴地總結了香港在上個世紀在東亞和世界風雲變化中所處的特殊時空位置以及貢獻。“香港這個地方,從地圖上看,只是小小的點兒,但是它和中國的學術關系是在是非常大,跟我今天的成就也有非常大的關系。我經常說,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個饒宗頤。”
早在1953年,饒就有預見性地把香港比作漢末三國的作爲南北交通樞紐和避風港的荊州。如果說,荊州的特定時空孕育了荊州學派和王弼這樣的大學者,香港則孕育了饒宗頤這樣獨一無二的通儒。饒宗頤這樣解釋香港給予他的機遇和栽培,“我這個人總要搞七搞八。香港是破了model 的地方,能讓我的天性自由發揮,這使得我的學術領域能夠破除藩籬,有一定的廣度和深度。我曾經對自己的學問加以歸納,分爲八個門類,分別是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金石學、書畫。從時間跨度上來說,涉及到上古史前到明清,這樣宏大的規模格局,也得力于香港這一破了model 的分割,算是得其地利吧。” 和香港相反,“新加坡不能讓我的天性自由發揮,離開那裏才能有成就。這些問題是‘地利’的問題”。
相較于對香港的感恩,饒宗頤對于當時的新加坡頗有微詞,認爲新加坡壓制中華文化,管理者的條條框框太多,壓抑學術的自由和天性。當時新加坡獨立不久,在冷戰的大環境下,在東南亞強鄰四伺的情況下,經濟上非常成功,是亞洲四小龍之一,是東亞最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又是華裔爲主的國家,饒宗頤也爲之高興。1989年元旦,他作“新加坡古事記引”,就稱贊了新加坡的成就:“自古華人於海外立國,而能廁於強國之林,不以幅員之小而降其聲威,不以人口之少而減其盛美,孰有如今日之新加坡國乎?”
可是,作爲唯一華裔華人爲主的小國,新加坡在政治上采取了割裂與中國聯系的國策,在文化上打壓中國文化,從而使得以中國文化爲主體想在海外(新加坡)做出一番事業的饒宗頤非常苦惱。新加坡雖然以華裔華人爲主,饒宗頤反而覺得其文化氛圍不如日本和法國。他回憶說:“在新加坡生活待遇雖好,但是我呆不下去,只因我是以中國文化作主體的人。那裏壓制中國文華,我覺得很壓抑。在題辭裏寫:‘雖無牧之之後池之蘊藉,庶幾表聖狂題之悲慨’,那真是身無長物,兩手空空的感覺,覺得失去了依托”, “我在日本那麽久,在法國時間也很長,但並沒有寄居海外淪落天涯的感覺,因爲那裏有中國文化的血脈在。像我在日本,與日本友人寫詩唱和,研究敦煌文獻、甲骨拓片;在法國時,和戴老合作研究敦煌曲、研究敦煌白畫,我都覺得心理很安穩。”
在新加坡的五年期間,饒宗頤在美國、台灣訪問大約一年半,和Arthur Wight、楊蓮生、洪業、傅漢思、張充和等學界名人深入交流,固然使先生大名有所增益,但此前先生已經在國際學術界鼎鼎有名,因此無法稱新加坡是饒宗頤走向世界的舞台。不過,公允地說,新加坡是饒宗頤在星洲和南洋(主要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奠定名聲的地方,饒宗頤這幾年雖然心情不愉快,學問卻依然高歌猛進,這樣講並不爲過。
饒宗頤和香港的因緣的關鍵一環是香港的兩所大學。2006年他在九十華誕晚宴的講話中幾次感謝香港的兩所大學: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他說,“我要感謝中大,也感謝港大。港大把我帶到國際上,發生關系”,“ 我的後期能夠學、藝兩個都做,那是香港中文大學培養我這麽做的”。“我今天要感謝兩間大學培養我的人,我是一個最不忘本的人”;“我這個成績是香港大學栽培出來的,得益于Frederick (Ferderick Sequier Draker, 林仰山教授) 當年對我的支持,這是港大對我的影響。我的後期能夠學、藝兩個都做,那是香港中文大學培養我這麽做的。”
本來,饒宗頤可以感謝華人世界的三所著名大學的,新加坡大學失之交臂,令人唏噓。
後記
筆者在研究這個課題時,得到新加坡本地文史前輩如陳榮照、吳振強、杜南發、林利國和友朋如許振義、許齊雄等之指導幫助,獲益良多,特此致謝。
本文刊載于《怡和世紀》2018年4月第35期。作者楊斌爲澳門大學曆史系教授。
《怡和世紀》是新加坡由百年以上曆史的華人社團“怡和軒”,所發行的綜合型文化季刊,含時事觀點、金融財經、人文史地,也設有藝文欄目。
網站:www.eehoehean.org
相關閱讀:
-
新加坡頂級華人俱樂部怡和軒,成立百余年,秘史初次公開
- “新冠橫行之際,黃皮膚猶如過街老鼠,成了宣泄惱怒情緒的箭靶”
- 從古老牛車、三輪車到汽車,新馬交通發展的巨變
- 當年新航遇劫機恐怖襲擊,時任新加坡總理的他卻一夜安眠
編輯:WWT
《新加坡眼》視頻號你關注了嗎?
點擊下面視頻,可以看到更豐富的內容!
或直接搜”新加坡眼“也可以找到我們的視頻號~
新加坡眼 , 李光耀先生回憶自己曾祖父的故事#新加坡#新加坡眼#李光耀 更多精彩視頻關注@新加坡眼 視頻號
新加坡眼推薦搜索關鍵詞列表:怡和軒新加坡曆史
— END —
跟進新加坡時事,點擊文末閱讀原文Read more小坡生活 | 房屋租售 | 二手閑置 | 求職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