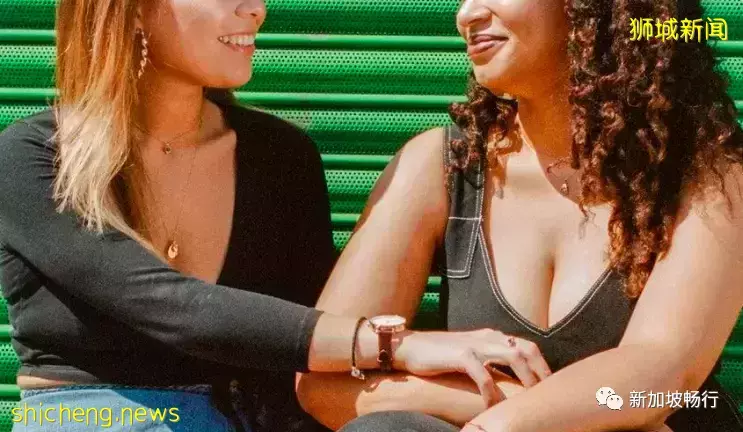去年九月,我的搭檔蕾妮從新加坡搬到了洛杉矶,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開始新的生活了——這是一個盛大而無可否認的浪漫姿態,通常是爲戀人保留的。蕾妮和我絕對不是。
蕾妮和我是柏拉圖式的生活伴侶,這種關系結合了友誼、婚姻和多妻制的品質。我們是彼此的主要伴侶,但我們不發生性關系(甚至擁抱也是零星的和偶爾的),我們約會其他人。我們在洛杉矶市中心共享一間單間公寓,並且是財務合作夥伴。我們還在考慮在法律上承認彼此的直系親屬的選項。
Renee 和我在新加坡的中學相識。從一開始,我們就覺得我們的聯系很特別。我們有共同的興趣和重疊的社交圈,但我們的聯系更深——我們稱對方爲“靈魂伴侶”和“雙生火焰”。我們在假期和家庭假期合並了我們的家庭。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也建立了共同的曆史。我們在彼此關鍵的成年時刻坐在前排:第一個男朋友,早期的職業生涯,以及成爲年輕人的所有成長痛苦。
經過七年的青少年最佳友誼,我搬到了洛杉矶。我們在不同的國家過著不同的生活,但我們仍然很親密。距離甚至沒有給我們帶來太多困擾——直到 2020 年春天,它突然變成了我們需要克服的一個巨大的障礙。
我們得到的最常見的問題之一是“你們兩個是如何決定成爲柏拉圖式的生活伴侶的?” 是什麽讓我們想在我們已經穩固和充實的友誼中加入這種程度的承諾?答案是,在許多方面,彼此靠近很大程度上是我們靠近自己的結果。
Renee 剛剛從新加坡的一所大學畢業,獲得了生命科學學位——她並不打算使用這一學位。她渴望有一個更有創意的職業,並被其他同樣致力于改善自己的思想開放的人所包圍。
她也越來越難忽略她的雙性戀——在同性關系仍然是禁忌的社會中長大的她自己的一個側面。她以前在新加坡看到過她假設的未來,雖然她想像自己在那裏可以過得很舒服,但她知道她不想一輩子都靠自動駕駛。
雖然蕾妮和我知道我們想在不久的將來和遙遠的未來在一起,但在一種比“最好的朋友”標簽似乎更正式和有意的方式中,我們沒有一個標簽來形容我們的樣子然而。
然後,我偶然看到一篇關于波士頓婚姻,這個術語描述了 1800 年代後期的女性如何與其他女性一起生活和“結婚”。其中一些關系很可能是隱蔽的性關系(“曆史書會說他們是室友”)。但他們還有另一個優勢:在那個時代,如果一個女人嫁給一個男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她將不得不用未來的職業來換取家庭生活和母親身份。波士頓婚姻讓希望繼續個人學術追求的女性也有穩定的伴侶關系。閱讀本文時,我記得在想,這些女人有 BBE – 大腦能量。
這個概念立刻引起了蕾妮和我的共鳴。我們都有尚未實現的抱負和自私的欲望,在我們的生活決定中考慮浪漫伴侶將意味著對這些夢想做出妥協。這種夥伴關系的替代方法打破了我們的先入爲主的觀念,即 1)我們應該與配偶一起度過余生,或者 2)只是獨自一人。它提高了我們共同設想的未來的上限,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第三種選擇:與你最好的朋友一起生活。
我們對彼此有著深厚的柏拉圖式的愛和承諾,並且還就重大的人生決定進行了冷靜的討論,以確保它們保持一致。雖然我不熟悉如何浪漫的情侶決定結婚,我想這類似于我們決定建立柏拉圖式的生活夥伴關系。當有人始終如一地幫助你成爲最好的自己,你的未來和他們一起變得更加光明和大膽時,你爲什麽不希望他們永遠在你身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