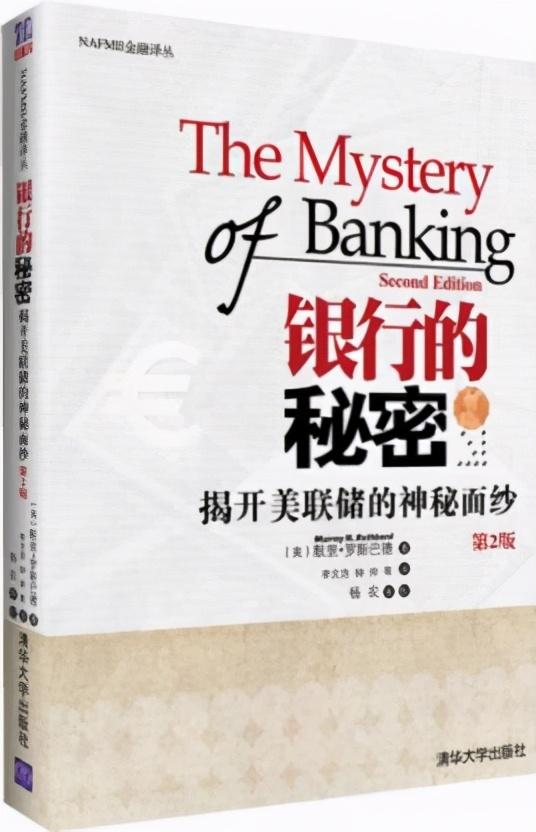周瓊(資深金融從業者)
1816年成立第二合衆國銀行時,共和黨人約翰·倫道夫警告說:“央行將成爲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其在政治和金融上的地位堪比物理學中著名的阿基米德命題中的支點,執政者憑借這個支點可以任意操縱整個國家,甚至造成國家的毀滅。”——轉自羅斯巴德《銀行的秘密》
維爾·羅傑斯:“自從開天辟地以來,曾經有三件偉大的發明:火,輪子和中央銀行。”——轉自薩缪爾遜《經濟學》
央行從一個基本隱形的機構搖身一變成爲世界政治的唯一主導者。——穆罕默德·埃爾–埃裏安《負利率時代》
10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就《中國人民銀行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10月31日金穩委專題會議要求“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完善貨幣供應調控機制,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一直在經濟舞台中心的央行,又引起更大的關注。
中國的情況,和全球類似。圍繞央行的爭論,從300多年前央行誕生就從未止歇。連應不應該設立央行曾經都有很多鬥爭討論,當然現在這已不是問題,問題只在于央行應該如何更好的發揮作用。經過一次又一次經濟金融危機,央行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地位上升。但過于依賴央行並非好事,央行也難堪重負。
全球最重要的央行,曾經是英格蘭銀行,現在是美聯儲,但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産規模,早在2011年就成爲全球央行之冠並保持了9年。2019年末,中國央行資産規模37.11萬億元人民幣,美聯儲資産規模4.38萬億美元,歐央行資産規模4.69萬億歐元。由于疫情後國外央行采取超寬松貨幣政策,2020年9月末,中國央行資産規模37.47萬億元人民幣(基本不變),美聯儲資産規模7.06萬億美元(比2019年末增加了62%),歐央行資産規模6.5萬億歐元(比2019年末增加了39%),美、歐央行的資産規模再次超過了中國央行。這一方面是我國寬松貨幣的工具和歐美央行大規模購買資産不同(易綱行長曾經解釋,中國“央行降准和增加再貸款是雙擴張的貨幣政策工具,但反映在央行資産負債表上則前者是縮表、後者是擴表。這幾年我國央行‘擴表’和‘縮表’在金額上大體相當,所以央行資産負債表規模這幾年基本穩定,這與目前國際上主要經濟體央行資産負債表大幅擴張的機理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也反映我國因爲疫情控制得好,貨幣政策的寬松在經濟複蘇後適時退出,沒有過度依賴貨幣政策來拯救經濟,這是好事。
本文並非系統探討央行,只是撷取了有關央行的幾本書中一些有意思的內容,談點個人看法體會。願能爲今天我們思考央行提供一點參考。
一、反對央行的奧地利學派
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有門格爾、維塞爾、龐巴維克、米塞斯、哈耶克、羅斯巴德等。
以前一直很敬佩哈耶克,主要是他在別的經濟學家還認爲蘇聯計劃經濟有優勢的時候,就能從邏輯上預見到其經濟上的問題和後果。(張維迎的概括:“1930年代,經濟學界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爭論中,大部分新古典經濟學家站在支持計劃經濟的一邊,只有奧地利學派堅決反對計劃經濟。最後,到1990年蘇東計劃經濟徹底崩潰,才證明了他們的正確。”)
但後來發現,奧地利學派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市場萬能論”和“政府有罪論”思想下,奧派的思路都是反政府幹預的,政策措施很少,很難被政府采用作爲主流學說。撒切爾政府和裏根政府算是信奉奧地利學派的,撒切爾夫人把國有企業私有化,但這個做完了好像就沒啥奧派能用的政策了。
2010年米塞斯研究院網站上盧·羅克維爾寫的文章《平行的人生 自由還是權力——羅斯巴德 VS 格林斯潘》,被譯成了中文。羅克維爾是米塞斯研究院的創辦人和主席,羅斯巴德的重要學生和同僚之一。因爲作者的身份立場,當然偏向性明顯。這篇文章盛贊羅斯巴德(我覺得過譽了),批判格林斯潘(批得也太狠了),說“格林斯潘留下的,是一團糟的經濟,和一生的逢迎討好。而羅斯巴德留下的,是用科學統一起來的,廣闊的自由主義視野,一個真正爲長遠打算的範例。”說羅斯巴德“從不曾擁有任何權力。實際上他利用他的教職來反對應用權力,並成爲激進自由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在這個世界上最傑出的代表人物。這個深愛自由的人于1995年去世。自那以後,他的思想傳遍了整個世界,他的全部著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熱賣,如日中天。”熱賣應該是指金融危機後一段時間,一些批判金融體系的書熱賣,從《資本論》到明斯基《穩定不穩定的經濟》等。這本《銀行的秘密》熱賣,應該是契合了大衆批判美聯儲的心情。
奧派從哈耶克到羅斯巴德都是反對中央銀行,甚至建議取消中央銀行的。
“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指出,任何形式的銀行信用“擴張一收縮”都會導致經濟的“繁榮—蕭條”交替循環。羅斯巴德寫道,“經濟周期這一現象從18世紀中後期開始,就讓西方世界頭疼異常。銀行擴張信用並引發通脹,每次經濟周期都帶有這種烙印,甚至成爲了經濟周期開始的導火索。由此,經濟周期的基本框架也就顯而易見了:銀行信用擴張提高了社會中各類物品和服務的價格,造成一派繁榮的景象,但是這一繁榮是基于對後來的貨幣接受者隱蔽且欺詐性的稅收。通貨膨脹越嚴重,銀行越可能淪爲‘坐著的鴨子’,隨後信用緊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這種信用緊縮造成流動性短缺,從而導致投資減少、企業破産以及物價下降。”這有一定道理。
但是,政府需要央行去主導掌控信用的擴張和收縮,而不是無能爲力放任市場自發波動。政府是希望央行能用逆周期調節手段平抑經濟周期,雖然如果政策措施出台時機不當會導致或加劇經濟周期,但央行的調控藝術水平也在提高。伯南克說,“找到恰當時機收緊或者放松政策的確很有挑戰性,這也是美聯儲要擁有如此之多的經濟學家和模型的原因。”
奧地利學派的缺陷就在于對“市場失靈”和“大政府”的必要性認識不足。現代社會,必然是個政治化的社會。王滬甯在《比較政治分析》中指出“中世紀人類是神學化的,現時代的人類是政治化的,政治擴展反映了曆史上不可阻擋的物質運動的進程,政治構成了人類生存的一個基本條件。這個觀念意味著三個前提:整個人類的生存與命運日益與政治相結合,整個人類的政治活動日益成爲一個緊密相關的體系,整個人類面臨的各類問題日益成爲政治問題。”“國家一旦介入經濟領域,與經濟擁抱在一起,其活動和職能就會象洪水決堤一般,一瀉千裏。”“巨型國家形成的原因:現代化、社會化大生産引起的物質生産運動中內在矛盾的擴大和增長。這個基本矛盾促使人們走向通過國家活動來協調和緩和它。”
奧派的意義在于,在國家幹預、參與社會經濟生活越來越深,政府之手伸得越來越長的時候,它的理論和觀念從另一端形成了一種平衡,警惕“政府失靈”以及政府對個人權利的侵害。所以,這種理論的優點也同時是它的缺點。
沒必要把奧派的很多觀點奉爲圭臬,它不是治國之策,解決不了現實困難。
二、羅斯巴德 VS 伯南克
《銀行的秘密》首版于1983年。到1983年,一個國家需要一個中央銀行,還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嗎?而作者通篇就是論證,中央銀行沒有比有更好。這本書可以和伯南克的講美聯儲的《金融的本質》對照來看,從不同的理論觀念出發,對相同的曆史有不同的解讀。幾乎是正方反方,相映成趣。在我看來,雖然羅斯巴德也有道理,但還是伯南克更有道理。
一般都認爲英格蘭銀行的成立有劃時代意義(全球第一家央行是1688年的瑞典央行,但1694年成立的英格蘭銀行是美聯儲之前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羅斯巴德寫道“最早的中央銀行出現于17世紀後期的英格蘭,它是瀕臨破産的政府和利欲熏心的金融集團之間肮髒交易的産物”。羅斯巴德認爲“中央銀行制度的根本目的是,運用政府權力,消除自由銀行制度下貨幣和信用擴張所受到的制約。”當然政府是爲了解決內戰引起的財政問題,金融業也是看到了建立這樣一個機制的好處。但同一件事帶著不同的觀點和感情色彩就會描述得完全不同。
羅斯巴德在書中最後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回歸金本位制,一個不受政府幹預的商品本位貨幣制度。廢除美聯儲,建立自由銀行制度。將國家黃金儲備私有化,每家銀行都擁有100%黃金儲備的穩健經營基石。不僅黃金和鑄幣廠可以非國有化,美元本身也可以非國有化,化身爲不具有信用擴張傾向的私人鑄造的産物。我認爲哪條都沒有可行性,都不可能被國家采納。這和哈耶克的最後一本著作,1976年出版的《貨幣的非國家化》思路也是類似的(被某些人拿來作爲私人數字貨幣的理論支柱了,我覺得在國家存在的情況下都是不可行的)。
羅斯巴德認爲這樣做的好處是“實現國家與貨幣和銀行業的分離。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嚴格受限于黃金供給的增長,通貨緊縮再無機會出現,通貨膨脹定會銷聲匿迹。利率會下降,而儲蓄、投資等將大爲提振。商業周期的噩夢將一去不返。”這把沒有央行的世界太理想化了,但這不是曆史事實。
伯南克的書裏寫了,美聯儲成立前,美國的金融恐慌一直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1893-1914年,就發生了6次比較大的金融恐慌,銀行倒閉,給整個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所以從1907年金融恐慌後,國會考慮籌備央行。伯南克也分析了金本位的問題,金本位下,貨幣總量會受到黃金開采量等因素的變化影響,經濟産出和通脹水平的波動性更大,央行不能靈活調控。而且很多金融恐慌都與金本位制相關,金本位制並不總是能穩定物價、穩定金融系統。到現在偶爾還能看到個別經濟學民粹或不知道是什麽人鼓吹金本位,曆數央行的放水造成貨幣供應量擴大了多少倍,認爲回到金本位才能解決問題,但金本位就是因爲它的諸多缺陷被放棄的,未來也絕不可能回歸。鼓吹金本位和認爲貨幣中性一樣,都是完全脫離這個時代了。
當然,兩種看法都有自己的一套邏輯。羅斯巴德反對中央銀行。他從曆史和央行、商業銀行資産負債表的關系,論證央行帶來了信用擴張(“中央銀行可以挽救陷入困境的銀行,在全國範圍內以一種平滑的、可控的、統一的方式擴張貨幣。”“新的聯邦儲備體系是專門設計出來的信用膨脹發動機,能收縮自如地控制擴張程度,並保持整個體系擴張的同步性。”)。他不喜歡央行的操控/自由裁量權,就喜歡金本位的約束。而伯南克指出,由于“一戰”後工人運動的強大,政府更擔心失業,所以失業情況變得糟糕時央行必須采取貨幣政策進行幹預。這樣就無法采取金本位制。
對于通縮,羅斯巴德寫“縱觀曆史,商品和服務的供給一般逐年增加,由此增加的貨幣需求將不斷地拉低價格總水平。實際上,從18世紀中葉到1940年價格總水平一直在下降。寥寥數次的例外出現在拿破侖戰爭、1812年戰爭、美國南北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紙幣的印制使得當時社會的貨幣供給增加,但較之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史無前例的經濟及商品供給增長,仍無法望其項背。只有在戰爭時期,政府才會開足馬力印制貨幣,以此爲戰爭埋單,這時,貨幣供給的增加才會超越産能的增長從而拉動價格快速上揚。”伯南克寫“19世紀後期,相較于經濟增長,黃金總量出現了相對短缺。黃金不足,導致貨幣供應量開始相對收縮,美國經濟經曆了一次通貨緊縮。”也就是那時的通縮正是金本位制下黃金不能隨經濟而增長造成的問題。
對于大蕭條,羅斯巴德認爲罪魁禍首是美聯儲。“美聯儲的信用擴張政策帶來了20世紀20年代的空前繁榮,同時也讓美國乃至世界經濟在1929年陷入深度蕭條。”而伯南克寫道,“有證據表明,金本位制是導致‘大蕭條’如此嚴重、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的主要原因。”還有“一戰”帶來的影響、股市泡沫等一系列原因。另外,30年代美聯儲信奉“清算主義”(liquidationist theory,這種理論認爲美國經濟在20年代過度繁榮,經濟增長過快,信貸過度膨脹,股價過高,因此需要經曆一段通貨緊縮,把過度發展的部分擠出去),也是對大蕭條應對不得力的重要原因。
一般都認爲羅斯福新政從大蕭條中挽救了美國經濟,而羅斯巴德認爲“蕭條曆時長久的原因是,胡佛總統在美國曆史上首次對蕭條進行大幅幹預,羅斯福總統不僅緊隨其後,而且變本加厲。在1929年之前,一旦經濟發生衰退,政府都允許經濟進行自我修複,通常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經濟就能步入複蘇軌道。然而,在胡佛和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他們對經濟的幹預程度很深:強迫企業維持最低工資率,發放大量貸款勉強維系不健康的企業,提供失業救濟金,擴大公共設施建設,擴張貨幣和信用,支撐農産品價格,實施赤字財政等。政府的廣泛幹預導致衰退無限期地延長下去,使得原本很快就可以結束的衰退演變成爲曠日持久、傷筋動骨的大蕭條。”伯南克認爲羅斯福很多措施是有效的,包括1934年成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廢除金本位制,允許放松貨幣政策,這就結束了通縮,使經濟在1933-1934年間經曆了一個短期的有力反彈。但也有些措施不成功,比如發布《全國工業複興法》,要求企業將産品價格維持在高位。我認爲伯南克的評價更爲客觀。羅斯巴德從奧派角度出發,把政府幹預都一棍子打死了。
羅斯巴德寫道,“銀行家、經濟學家、商人、政治家和政黨都支持中央銀行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是‘與時俱進’的:從19世紀後期的自由放任主義、硬通貨制度和小政府理念,轉變到從德國俾斯麥政府舶來的中央經濟集權和大政府主義。集體主義被冠以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而得以流傳,並被商人和政客廣爲接受。”羅斯巴德對此是持批判態度的。但美國經過反複的鬥爭,1914年還是成立了中央銀行,這是“進入20世紀以來普遍流行的中央集權理念”的産物,更是現代國家管理經濟的現實需要。
三、通脹VS通縮
威廉·格雷德的《美聯儲》主要寫了沃爾克,也有很多對美聯儲曆史的介紹和對美聯儲主席的評價。書裏寫美聯儲主席小威廉·邁克切斯內·馬丁(任期最長的美聯儲主席,1951/4/2到1970/1/31,第二名是格林斯潘,1987/8/11-2006/1/31,都是約19年)“給美聯儲帶來最適合的運行原則,即‘逆風飛揚’,也就是適度貨幣政策應靈活熟練地對抗商業循環周期的方向。當經濟擴張瀕臨通貨膨脹時,美聯儲就要學會緊縮貨幣;當經濟周期處于收縮期,美聯儲又要學會放手。馬丁曾開玩笑地說道:‘美聯儲的工作就是在宴會剛開始時撤掉大酒杯。’實際操作的過程遠比說起來複雜。”“美聯儲主席應該秉承的傳統是:關注美聯儲自身的識別力和敏感性,審慎控制貨幣增長,不屈服于來自白宮或國會的牢騷抱怨和政治壓力。作爲美聯儲主席,除了必須擁有高超的專業技能之外,還需要具備靈活的政治操作能力,要遊刃有余地與其他政府權力核心機構和諧共存,由此才能保住美聯儲最爲珍貴的遺産–自身的獨立性。”
是否“審慎控制貨幣增長”,不光是看取得的短期效果,而且從長期來看當時的決策是否給未來奠定良好的基礎,可能是判斷一個中央銀行家功過最重要的標准。
伯南克在《金融的本質》中也區分了不同的情況:“必須認識到,獨立的央行所扮演的角色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環境下是不一樣的。通脹的環境更多與政府債務的過度貨幣化有關,此時央行的獨立性表現在對政府說‘不’上。在長期通縮的環境下,過度創造貨幣幾乎不是問題,此時就更加需要央行采取合作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短時期內央行和財政部門進行更好的合作並不與央行獨立性相矛盾,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行爲都是與國家主權原則相悖的。”但問題是現在,央行的過度創造貨幣是很大的問題,又和通縮並存,爲什麽超發貨幣並不引起通脹,也有很多分析。
格雷德寫道:“這家中央銀行的自身目標就是傳遞一種男人的責任感:即不受群情激憤所左右並做出艱難且不得人心的抉擇。面對公衆的質疑和辱罵,他們要夠堅強、夠從容。要避免可能會影響判斷或暴露弱點的情緒激動和多愁善感。這位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在公衆面前的形象越發高大,成爲一個令人敬畏、不動感情、不輕易屈服、神秘莫測且學識淵博的人。他似乎並不關心圍繞在其周圍且毫無意義的華盛頓政治壓力,但似乎也不在乎美國平民百姓的痛苦呐喊。在公共舞台上,沃爾克就像是一個嚴厲的父親,他會對犯錯誤的小孩施以懲罰。當孩子開始大哭或抵抗時,他會耐心地做出解釋,解釋那些孩子不能完全理解的原因以及從長遠來看什麽是對孩子有利的。他的行爲方式有些冷漠,他的堅持不懈似乎遠遠高于周圍那些軟弱的靈魂。20年前,國會議員賴特·帕特曼曾抱怨美聯儲就像是‘爸爸做主的家庭’。沃爾克的確履行著這樣的責任,他正是爲家庭制定紀律教條的父親。這樣的職責絕非是一個比喻。許多貨幣經濟學家實際上也會這樣看待美聯儲,他們將其看做是所有人的家長,是必須偶爾用疼痛來懲罰孩子的負責任的成年人。”
我們都叫央行“央媽”。現在的美聯儲,似乎也不再是美聯儲“爸爸”。
四、神秘VS透明
美聯儲成立後的很長時間,決策過程都是非常保密的,保持了在公衆眼中的神秘感。格雷德寫道“馬丁成爲美聯儲憑直覺做出預測和決策的神秘化身,這種決定要統攬經濟事務中的所有因素,然後再逐個階段地判斷出哪些因素才最重要;這種便宜行事的管理風格,無論其正當與否,總之是讓外界評論家幾乎不可能知道美聯儲到底是怎樣確定貨幣政策的。”
雖然格林斯潘以用語含糊而著稱,但實際上從他那時起,已開始美聯儲政策的透明化,伯南克則更進一步。
伯南克在《行動的勇氣》中寫道,“保持決策過程的神秘感是一件利弊兼有的事情。一方面,它有利于讓中央銀行家們顯得無所不知,有利于提高短期政策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它會讓公衆感到困惑,讓市場手忙腳亂,爲陰謀論鋪就了溫床。在當今這個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日益注重透明度和問責制的世界上,我覺得美聯儲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神秘色彩已經過時了。我還相信,神秘色彩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我和米什金曾經在關于通脹目標制的論文中指出,如果央行能夠同公衆和市場進行清楚的溝通,那麽貨幣政策就能夠産生更好的效果。”“貨幣政策要發揮出影響力,98%靠宣傳,2%靠政策本身。”
“我們(伯南克和格林斯潘)的思想在幾個不同的方面存在分歧。比如,我支持將通脹目標制作爲美聯儲的一個政策框架,旨在提高美聯儲的透明度,但他不信任這個框架。他甚至以開玩笑的方式解釋透明度給自己造成的緊張。1987年,他告訴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說:‘自從成爲央行行長之後,我說話時經常會喃喃自語,而且缺乏連貫性。如果你覺得我講的某句話似乎很清楚,那麽你一定誤解了我說的話。’”(這句是格林斯潘的名言)“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與市場溝通的曆程可謂漫長而曲折。在1994年之前,該委員會召開例會之後不會發表聲明,即便例會決定改變聯邦基金利率的時候也不會發表聲明。這樣一來,市場參與者就不得不絞盡腦汁地通過觀察貨幣市場的短期動態去猜測聯邦公開委員會的決定。1994年2月,格林斯潘開始在會後發表一份‘主席聲明’。2003年5月那次例會結束之後發布的會議聲明首次允許委員會成員分別表達自己對于經濟增長和通脹形勢的看法。”伯南克認爲格林斯潘在任期間,“貨幣政策溝通方式的確取得了諸多進步”。
伯南克推動美聯儲實現了更大的透明度。“我早就痛苦地意識到美聯儲主席的每一句話都可能輕易地遭到誤解或過度解讀。”“我們仔細推敲著每一個字:我應該說更多的降息行動“可能是必要的”,還是“很可能是必要的”?我們並非沒有注意到討論這種事情的荒謬性,但我們通過痛苦的經曆學到了一個教訓:措辭往往很重要。我們是目標是向市場傳遞盡可能清晰和強烈的信號,同時保留在必要時改變方向的回旋空間。”
“曾經,(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上)7位美聯儲理事和12位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即興發表看法的。但1994年,爲了回應衆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亨利·岡薩雷斯的要求,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同意發布完整的會議記錄。自那之後,大部分與會者都開始讀預先准備好的講話稿了。這雖然有利于提升會議的透明度,但不利于改善討論的質量和自發性。”
在《行動的勇氣》結語中,伯南克自豪地寫道,“今天,美聯儲不僅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央行之一,也是華盛頓最透明的機構之一。”
我想,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透明化,可能一方面是美國政治“陽光化”的大趨勢影響,另一方面也和全球化、經濟日益金融化,美國的貨幣政策影響越來越大有關。美聯儲如果搞“半夜雞叫”式的政策大拐彎突然襲擊,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因爲影響太大,美聯儲如何與市場溝通真的是需要字斟句酌、拿捏分寸的藝術。
透明度是強有力的約束,參與決策者會有更大的壓力。誰的觀點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不用追責,也有聲譽的壓力。比如伯南克分析了多次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當時的觀點,2008年1月,“關于聯邦基金利率的降幅是否足夠,依然存在分歧。大多數人認爲,如果美國經濟沒有陷入衰退,那麽當前的降息幅度足以爲經濟提供支撐,但米什金嘲笑這種樂觀的看法。事實證明,米什金的直覺是正確的。”但透明度確實利弊兼有。
2019年4月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文章“陽光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Sunlight)討論“陽光議會”。這篇文章指出,“陽光議會”並不是美國從立國之初就有的東西,相反,建國國父們其實認爲保密對善治非常必要。漢密爾頓曾說:“如果當時的討論是公開的,各執一端的喧囂將無法導致令人滿意的結果。”作者說,自20世紀70年代實行“陽光政治”以來,這50年實踐證明了“陽光議會”不是什麽好東西,而是美國政治問題的重要原因。1970年《國會改組法》的理念是,讓辯論公開、投票紀錄有明確檔案,可以讓議員對自己的選區更加負責,公衆也得以參與過去密室開會的一些專門委員會的會議。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許實現了,但實踐中卻帶來了很多導致國家治理敗壞的負面效果。副作用之一是特殊利益團體的院外遊說活動越來越猖獗。過去,議會活動都是密室政治,議員的投票和發言都是秘密的,院外集團哪怕有心要幹預一個議員的投票,他們不知道到底議員在關鍵表決中是什麽態度。現在就不一樣了。公開議會紀錄帶來的另外一個大問題就是公開的辯論和投票讓議會政治成爲一個劇院,兩黨議員根據各自的角色充分表演,導致兩極化越來越嚴重,失去了密室談判中妥協的余地。透明度帶來的問題——不斷的陽光照射,甚至都不偶爾有一點陰涼,會殺死你原本想培育的東西。(基本轉引自沒有人比我更懂杭之馮玥的微博,略有修改)
這對于央行的透明化,也不無啓示。中國央行現在和市場的溝通、引導市場預期的藝術大爲增強,但決策過程還是相當不透明的,是否需要加強透明度呢?也許這種不透明有其好處。
央行有的事情還是需要保密的。比如,新加坡金管局,對新加坡元彙率的合意波動範圍區間(政策帶),就是高度機密。一旦彙率超出政策區間,貨幣當局即買賣外彙,使彙率重新回到政策帶的範圍之內。但不能讓市場完全知道貨幣當局的底線底牌,從中套利。有時有的央行也會突然襲擊,比如2015年1月瑞士央行突然取消歐元兌瑞郎彙率下限同時下調利率,瑞郎兌一攬子貨幣暴漲近20%。當然,這都是較小經濟體、較小的央行,最大的幾家央行一般還是不能這麽幹。
五、央行的T字路口
羅斯巴德生于1926年,于1995年去世。他還沒有看到現在這個負利率的新時代。那時他反對央行主要是認爲央行導致了信用擴張,認爲有央行作爲最後貸款人,采取部分准備金銀行制度,要爲“兩百多年來揮之不去的災難性通脹負責”,他批評央行是“信用膨脹發動機”。但現在的新問題是央行絞盡腦汁都無法刺激經濟、達不到理想的通貨膨脹水平。
取消央行是絕不可能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怎麽讓央行更好地發揮作用。埃裏安《負利率時代》一書是還不錯的探討。
埃裏安總結了曆史:央行的聲譽經曆過劇烈的波動——20世紀90年代中期,央行還被認爲絕對不會犯錯(那時人們還在爲經濟繁榮和金融穩定而彈冠相慶);因爲2008年金融危機,央行“被指責成巨大渎職的無知教唆犯”;渡過了金融危機,央行又被認爲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政策響應方和勇敢且富有創造力的機構”。
金融危機後,以美國爲首,普遍趨勢是加強了央行的權力。美國以多德爲代表的一些國會議員曾要求剝奪美聯儲的監管權力,讓美聯儲專注于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管理。但是,在聽取美聯儲和專家的意見後,形成了加強美聯儲監管權的多數意見和最終的多德弗蘭克法案。中國同樣在加強央行的監管權限。
現在,全球掉入靠央行“流動性輔助增長”的困境。“央行承擔的政策負擔日益沉重,這勢必會對央行未來的信譽、影響力和聲譽造成影響,它們的經營前景正在變得越來越不確定。自從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央行就一直在努力抑制市場波動,並且推出了“流動性輔助增長”的操作模式——這指的是由于特殊的流動性注入而帶來的金融市場的繁榮最終導致的經濟增長。然而,央行的這種不懈努力卻無法足夠迅速地過渡到真正的增長和有序的政策正常化。”
“央行的堅定努力以及對金融資産不容置疑的影響力,已經轉換爲在‘經濟的壞消息就是市場的好消息’這句口號之下的市場運作。令人失望的經濟新聞並沒有導致投資者對基本面評估的下調,而是被解釋爲暗示著央行將會更努力地致力于抑制波動、人爲推高資産價格,以及通過讓人們‘覺得自己變得有錢了’,讓他們進行更多的消費(也包括引導企業去投資以擴大生産規模)。市場早已習慣了寄希望于央行,指望央行可以成功解決所有的問題。”
格林斯潘的“格林斯潘看跌期權”,金融危機後被批評埋下危機的種子,然而現在的央行難道不照樣如此嗎?
雖然“整體來說,投資者們從央行那裏還是分到了極大的利益,但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喜出望外”,央行的行爲扭曲了市場,使得資産“價格和關聯度的變化不再遵循已有的分析和曆史模型,帶來令人沮喪的‘結構突變’,破壞投資者們多年來好不容易積累下來的、用起來得心應手的模式、經驗以及心態。央行不再只是裁判的角色,同時也成了競爭對手——擁有更多、更優質的信息來源以及媒體發布渠道。不僅如此,只要‘裁判’樂意,還可以任意修改規則。擁有‘永久資本’和幾乎不受限制的高彈性的資産負債表,使得各國央行能夠撐得住‘賠錢交易’的時間比大部分對沖基金的資金都要長得多。畢竟,它們不是市場裏的商業玩家。因此,市場的錯誤定價和資産類別間不合理的關聯可以很輕易地拖垮大多數對沖基金的耐心。”“分析表明,非常規貨幣政策,包括量化寬松和前瞻性指引,通過鼓勵某些形式的冒險行爲導致了風險。”“從貨幣流動性曆史看,其調整的隱含類型有可能會帶來破壞:不僅使潛在金融不穩定性增加——與低迷的基本面和高資産價格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也有關系,還面臨著溢出和溢回的風險。”
這確實是現在央行行爲的一個嚴重後果——扭曲了市場。市場參與者都在與央行博弈,分析央行行動的原因和預判央行的下一步舉動。經濟形勢不好時,央行放水,大概率能使金融市場向好。而經濟好轉時,央行收回流動性,使得金融市場可能下行。央行放水力度超過預期,大家會懷疑是不是因爲經濟實際下行程度超過統計數據所顯示的。這使得資産價格更難以反映實體經濟的情況,很可能扭曲資源配置。
“央行已經無法生産出西方經濟——包括世界——最需要的東西:高速、持久以及與真正的金融穩定相結合的包容性增長。”“自上而下的力量和自下而上的力量正威脅著由央行繼續抑制市場波動帶來的長期低增長均衡的一致性基線。原因十分複雜,不只涉及經濟、金融、地緣政治、政治、社會和技術因素等,還包括創新帶來的影響。”
埃裏安認爲央行面臨的T字路口——“一條道路,是通往高包容性增長恢複的道路,能夠創造就業機會、降低金融不穩定性的風險、遏制過度不平等,也能夠緩解政治緊張局勢、減輕政府治理功能障礙、化解全世界的地緣政治威脅。而另外一條道路帶來的是更低的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高失業率以及更嚴重的不平等,包括全球經濟不穩定的複現、政治極端主義的加劇以及對社會誠信和凝聚力的侵蝕。”
怎麽能走向第一條道路呢?雖然央行自身也要繼續探索,但更重要的是國家不能太依賴央行作爲唯一工具。埃裏安認爲,“我們不應該對央行過于苛刻。畢竟,央行也有自己的無奈之處:它們沒有任何政策手段,去通過基礎設施升級、教育現代化、勞動力市場改革等方式推動生産力發展;央行沒有能力去改變過時的財政結構;對于榨幹經濟活力和阻礙新投資的債務負擔,央行也無力消除。”。“在改善國家的增長引擎方面,央行無能爲力。”
央行到底能不能“改善國家的增長引擎”呢?可能不能從根本上,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以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鼓勵銀行以更低的利率、更大的規模給企業貸款來刺激投資,給個人貸款來刺激消費,央行能夠促進增長。但高質量的發展,還是需要更深層次的供給側改革(包括他提到的教育和勞動力市場的改革),而非僅是寬松貨幣的刺激。
埃裏安提出,理想的世界是實現四個全球性的轉變:
·央行從輔助增長,轉變到真正的、更具包容性的增長。
·央行從追求金融穩定和抑制市場波動,轉變到追求經濟更持久穩定的發展。
·從全球經濟中具有系統重要性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轉變爲新的區域和全球安排、積極協調不同意見、調整激勵機制,從而持久緩解緊張局勢。
·從日益惡化的不平等現象(收入、財富和機會上的不平等)和政治機能障礙,轉變爲制度、政治和社會的革新。
央行“在被迫成爲‘唯一玩家’之後,它們現在發現自己已經完全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了。如果政治體系最終能夠承擔起它本應承擔的經濟治理的責任,那麽央行的風險政策就將獲得回報。它們的勇氣、智慧和判斷將被歌頌贊美,它們的政治自治權和經營靈活性將受到保護。但如果政治系統功能失靈,央行的情況會變得更糟。它們不僅不會被視爲解決方案的關鍵組成部分,而且會被當成是引發甚至加劇問題的角色。”“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確保我們在T字路口的轉彎時做出更好的選擇。否則,全球經濟將面臨更萎靡的增長態勢、更嚴重的不平等,以及更動蕩的市場——所有這些都將給社會和政治凝聚力帶來壓力,並且使地緣政治局勢更加緊張。”
中央銀行確實經常承擔了阿基米德支點的作用,以貨幣信貸撬動一切。正如拉詹在《斷層線》中所說,打開貸款的水龍頭是最“速效的解決辦法”——“寬松信貸真是好處多多,它收益大,見效快,受益面廣,而且成本到未來才需支付。讓許多國家都屈從于寬松信貸的誘惑。”今年的新冠疫情,使得央行又不得不應急扛起重任,債務杠杆越加越高。但央行如果作爲唯一的支點確實獨木難支,只有結構性的改革,實體經濟的發展,才能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各國並不是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只是解決問題還任重道遠。
中國,因爲與其他國家相比更早從疫情中走出,同時因爲中美摩擦等看到了根本性的問題,所以中國政府更堅定地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爲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中國在努力走向埃裏安所說的第一條道路。全球是否能共同走上第一條道路,是大家的期盼,還有漫長艱難的過程。(本文轉自公衆號“玉鑒瓊田”,已獲作者授權)
參考文獻:
1.《銀行的秘密:揭開美聯儲的神秘面紗》,The Mystery of Banking,默裏·羅斯巴德著,美國1983年首版,2008年第二版,李文浩等譯,楊農審校,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金融的本質:伯南克四講美聯儲》,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本·伯南克著,美國2013年版,巴曙松、陳劍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3.《行動的勇氣:金融危機及其余波回憶錄》,The Courage to Act: A memoir of a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本·伯南克著,美國2015年版,蔣宗強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4.《負利率時代 貨幣爲什麽買不到增長》,The Only Game in Town:Central Banks,Instability,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穆罕默德·埃爾–埃裏安著,美國2016年版,巨瀾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