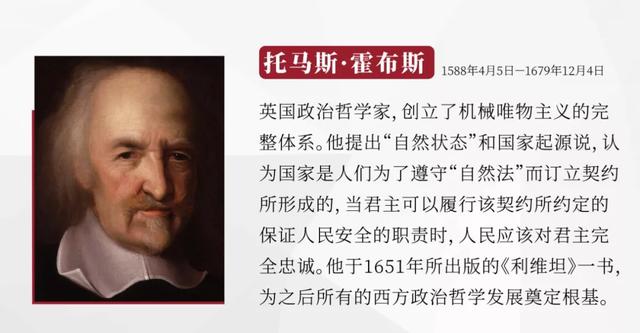2015年,《三體》斬獲“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這是中國科幻小說的一次重大突破。這部巨作講述了地球在三體人的進攻與宇宙“黑暗森林打擊”的陰影籠罩下追求生存的故事。只是與我們習慣的大多數科幻小說不同,這一次,故事的結局異常冷酷。
《三體》的作者劉慈欣,被讀者昵稱爲“大劉”,或另一個印象更爲深刻的稱號——“上帝派來拯救中國科幻的人”。筆者意圖通過此文提供一種不同的視角,來定位劉慈欣的《三體》對于中國科幻,乃至對于世界的意義。
文 | 張笑宇
編輯 | Fan
本文首發于澎湃,經作者授權後轉載
全文約3598字,細讀大約需要8分鍾
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對于奇妙世界的想象就與文學創作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亞歐大陸的最東端到最西端,我們可以看得到《摩诃婆羅多》與《神譜》、《吉爾伽美什》與《荷馬史詩》、《山海經》與《埃達》、《西遊記》與《羅摩衍那》、《亞瑟王傳奇》與《尼伯龍根之歌》……我們的先祖想象巨龜托起大地,太陽神的馬車在雲中疾馳,索爾的巨錘擊出閃電,鲲鵬扶搖直上九萬裏若垂天之雲……想象力使人類文明成爲人類文明。
也許最初,這些不過是人類對于世界的玄妙解釋,是人類天性中對于新鮮事物的好奇興趣所激發的産物。然而最終我們愛上幻想作品,是因爲它折射出關于我們自身文明最本質的東西。因爲,如果一個故事講述的世界我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這個世界中的生活我們一無所知,這個世界中人們的能力超乎我們的認識,然而我們還是會爲這個故事打動,那一定是因爲,這個故事裏蘊含著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就像我們會震撼于孫悟空的反抗天庭,欣慰于奧德修斯與妻子的團聚,擔憂于辛巴達是否能克服下一次的磨難,悲苦于西格弗裏德最終逃不過命運的無常,我們每一次被幻想世界感動,只因爲我們在那些“超人”與“非人”身上,看見自己。
因此,幻想作品與所有人類智慧的偉大結晶一樣,沉澱著人類對自身命運的思考。我們在古希臘的軸心時代有《俄狄浦斯王》這樣的悲劇,我們在文藝複興時期有《巨人傳》這樣的傳奇。而我願意把幻想作品中的一支——科幻作品——看作是《巨人傳》的精神繼承者。
《巨人傳》是拉伯雷的作品,主人公巨人本身力大無窮,然而更重要的是接受人文主義的教育,熱愛知識與體育,尊重愛與和平,對新事物保持好奇心。正因爲此,他們無往不勝,遠渡重洋也能克服種種磨難,最終追尋到智慧的啓示。《巨人傳》以幻想小說的形式爲我們開啓了一扇信念之門,那就是:只要正直的人接受正確的教育,他就會在這個世界中捍衛他珍惜的價值。
在秉持類似人文主義信念的一系列小說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烏托邦》、《大洋國》、《格列佛遊記》等等思想史上耀眼的名字。這些小說背後的政治意味十分濃厚,它們寄托了人類對于公正社會的向往,並且暗示讀者,建立公正社會的前提是接受啓蒙,接受人文教育對美德的塑造。
它們對應的時代是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文藝複興到啓蒙運動,在這段曆史中,歐洲文明一方面與保守勢力全力鬥爭,另一方面以自己的意志發現並改造著整個世界。北京大學李猛教授在其新著《自然社會》中,就將《魯濱遜漂流記》這部小說,看作是關于歐洲人確立這一世界秩序的寓言。
從科幻小說誕生之初,它就在關懷政治問題。這裏的“政治問題”指的並不是那些勾心鬥角的權謀,而是關于人類共同生活的重大問題。而且,科幻作品關心政治,未必是描述美好前景的溫馨童話,未必是用“政治正確”搭建起來的庇護所,未必是以人文主義信念和曆史進步論爲“中心思想”的宣傳作品。它同所有偉大作品一樣,真實地反映人性中的善與惡、黑與白、光與暗,並在情節中對此加以深切的關懷與探討。它需要幻想,因爲幻想能爲這種關懷搭建更宏大的平台;它需要科學,因爲科技與人類文明的關系,已經成爲任何關于人類命運嚴肅探討都回避不開的話題。
爲了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讓我們把視線從科幻小說上稍微拉開,來讀一讀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
霍布斯最著名的理論之一就是“自然狀態理論”。他認爲,自然狀態的人處于悲慘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之中,這個結論是基于三條原則推理出來的:
1)人生存的首要目的是自我保全
2)人的自然能力十分平等
3)人的語言並不代表他的真實想法
首先,人要自我保全,所以自然法規定他必須要對自然世界中的一切擁有所有權,這樣他才能正當地利用一切手段保全自己的生命。
其次,(正常情況下)人的自然能力是平等的,這種平等體現在人可以互相殺死彼此——即使是最弱的人,也可以用偷襲和毒藥殺死最強壯的人。
最後,由于語言無法代表真實意圖,因此一切善意的表述和在此基礎上的契約都沒有意義,能保障契約實現的只有強力的威脅:如不履約,只有死亡。
所以,我們可以設想一種霍布斯式的極端狀態:你的手中有一個蘋果而我已因饑餓而奄奄一息,自然狀態下的我,必然會用盡一切手段來奪取你手中的蘋果以保全我的生命。而就算是我保證我想要的只是一個蘋果,但我的語言在你看來並不可信。你無法判斷我究竟是要從你手中奪取蘋果,還是要幹脆奪取你的生命。
在這種極端狀態下,我們只有對彼此開戰。這個極端狀態無法被“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所消弭,因爲這世界上的蘋果就算産量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排斥我因爲各種各樣的原因陷入一個蘋果都沒有的悲慘境地。
而只要極端狀態無法排除,“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就無法排除。
有趣的是,劉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則”與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理論驚人地相似:人的自我保全對應宇宙中文明將生存視爲第一要務;所有權的排他性對應宇宙物質總量的有限性;人的語言不可信對應猜疑鏈原則;人殺死彼此的平等能力對應“技術爆炸”這個設定;最後,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對應的就是“黑暗森林打擊”。可以說,劉慈欣在宇宙的尺度上展開了霍布斯的理論。
《三體》想說的道理,就是內在于人性中的困境,即使到了人類文明有能力探索宇宙的時候,也依然會繼續存在。而奧克肖特推崇政治哲學家的理由,就是他們有能力超脫于一時一地的事件,從中揭示普遍存在的、內在于人性的困境。
任何時代的人類都需要有懂得政治殘酷性的人來守護真正的價值,這是人類曆史的一條普遍性規律。在《三體》中,劉慈欣以京劇臉譜式的人物塑造,重新講述了這個寓言。你說他集體主義也好,強權崇拜也好,但無論你給他貼上怎樣的標簽,都取消不了這部作品中提出的,人類自身所要面對的真實問題與困境。
中國人向來不乏幻想的傳統,然而科幻傳統卻並不強大。據專家考證,中國最早的科幻小說是著于1904年的《月球殖民地小說》與《新法螺先生譚》。前者模仿的是凡爾納《氣球上的五星期》,寫一個新加坡華人乘氣球曆險的故事;後者則是模仿了德國的《敏豪森男爵曆險記》,講一位“新法螺先生”經曆靈肉分離,又創制“腦電”的故事,頗有些修真小說的味道。
另外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可以稱之爲“政治幻想小說”,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梁啓超。1902年,梁先生在自己的《新中國未來記》中設想了百年後中國革命成功,建立起民主共和政體,人民富裕、國家強盛,甚至承辦了世界博覽會的圖景。不過,科學技術照例在這裏占不到什麽地位。
我們大體可以看到的是,早期的中國科幻小說或者附屬于志怪類小說,或者脫胎于諷喻類小說,大體上依舊是傳統文學的余脈。即使是老舍後來寫出的《貓城記》,也不過是披著科幻的外衣,本質上依然是部《格列佛遊記》式的政治諷刺小說。
這類小說真正的用意是將社會問題暴露在光怪陸離的幻想世界中進行嘲諷,我們從中看不到“科技”這個因素對人類文明邊界的延展。
這並不奇怪。
五千年曆史中,我們這個民族已經經曆過無數殘酷的生存考驗,而且,二十世紀上半葉,它剛剛經曆過可能是最爲殘酷的一次。19世紀誕生的科幻小說那種漂浮在半空的夢幻氣質,相對于這個民族所經曆的、沉重的二十世紀上半葉而言,顯得過于超脫飛揚了。而二十世紀下半葉,相對于這個民族所經曆的狂飙突進,一切科幻小說中的荒誕又顯得不值一提了。
劉慈欣是一位敢于真正面對這種殘酷性的作家,而且,在他的思維裏,這種殘酷考驗中磨煉出的生存智慧,很可能構成了中華文明最本質的要素。
因此,雖然我引用了霍布斯的理論,以指出劉慈欣的政治關懷具有普世性,但我更願意相信大劉的寫作來自本土經驗,因爲我們在《鄉村教師》中讀過那種在極度貧困的土壤上中也要傳遞現代科學知識的沉重責任感;我們在《詩雲》中讀過那種認爲現代科學邏輯亦無法把握中國古典詩意的浪漫主義情懷;我們在《朝聞道》中讀過那種把科學探索精神與“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士大夫情懷連接起來的探索;我們在《西洋》中讀過中國人構建世界秩序的狂想;我們在《全頻阻塞幹擾》中讀過那種爲國犧牲的精神;我們在《球狀閃電》中讀過那種不惜一切代價取得勝利的遊擊戰精神……
這一切經驗都屬于我們這個民族,因爲我們傳承的曆史比所有民族都漫長,我們記取的苦難比所有民族都深刻,我們在生死面前的狡詐與質樸、偉大與渺小、浪漫與現實,這一切的一切,比所有民族都豐富。將這生存經驗進行萃取、提煉,轉而成爲對人性自身的警惕與關懷,這就是在“民族性”中發現“世界性”的過程。
從《三體》中的兩句名言,我們見證了大劉是如何完成這一過程的——在《地球往事》中,他借旁白之口說“在中國,任何超脫飛揚的思想都會砰然墜地——現實的引力實在是太沉重了”,然而到了《死神永生》中,他又借維德之口說,“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
劉慈欣一直在思考許多中國人理應思考的重大問題,比如已經逝去的偉大領袖與當下關系爲何,比如這個民族的過去與未來關系爲何,比如這個民族與世界上其它偉大民族的關系爲何。那時,他心中已有了初步答案。比如權威和曆史所認可的東西,有些並不重要也可以抛棄,有些並不重要但很難抛棄,有些十分重要,但其重要性卻有著被人忘卻的風險。
那一年劉慈欣二十六歲,他以自己的小說,對自己所經曆的曆史、自己的民族和自己面對的世界得出了初步結論。這一結論走在政治權威之前,並比政治權威的宣傳還要來得平和深刻。
二十六年後,他的作品獲得了這個星球上最重要的科幻獎項。
二十六年後,我們看到劉慈欣依然堅持著他當年得出的某些結論。
二十六年後,這個世界已經讓同性戀婚姻在部分地區變得合法,讓動物的權利也受到重視,讓人工智能的曙光出現在人類文明的地平線上。
但劉慈欣不爲所動地認爲,根植在人性深處的生存困境不該那麽輕易地被忘卻,這個文明曆經五千年所積累的生存經驗,不會那麽快地被這個新世界淘汰。也許在他骨子裏面,他認爲自己其實是章北海,從古老的世界中走來,記得一些殘酷的生存經驗,並且早已做好了准備,像個父親一樣把這些舊世界的經驗交到新世界孩子的手裏面,然後坦然地面對死亡。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