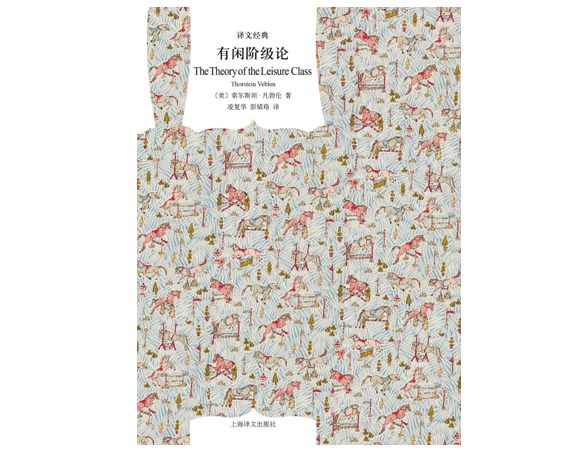古董、珠寶、跑車或華美的服飾等五花八門的人工制品被一些人認爲是奢侈品,但也有人認爲一頓美餐、一段異國之旅或一次讓人放松的貼身護理是奢侈品。年輕一代會說最前沿的科技産品或房價飙升的城市公寓才算得上是奢侈品。其實每個時代關于奢侈品的定義都不一樣,它取決于當時的社會認爲什麽是“超出”人們預期的事物。
奢侈品不僅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和物質實踐,也一直與複雜的情緒感受相伴相生。這使奢侈品的曆史不僅涵蓋經濟發展、社會傳統和文化習俗,還包含了謹慎的投資、各種稀奇古怪的行爲、性別模糊以及光彩奪目帶來的純粹愉悅感。真正的奢侈品要麽難以估計它的價格,要麽是完全免費的。
傳統意義上的奢侈品僅爲富人和貴族所有,但在21世紀廣告營銷的作用下,一些新的奢侈品應運而生,它們價格更爲實惠,用途也更加廣泛,普通消費者也能負擔,這也使得奢侈品的定義發生了新的改變。有人還提出“奢侈品大衆化”這個名詞,並用它來說明奢侈品極大地擴展了它本身的含義和形式這個道理。
在“996”工作制的體驗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時間才是更大的奢侈品。那麽除了時間,還有哪些奢侈品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呢?它們是否凸顯了當今社會財富不平等的議題?《奢侈品史》這本書將帶我們走進一個奢侈品牌和新科技相輔相成的新世界。
《奢侈品史》,[澳] 彼得·麥克尼爾/[意]喬治·列洛 著,李思齊 譯,格致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在媒體聚光燈下,奢侈品變成21世紀的童話
2013年底,兩位30多歲的俄羅斯千萬富翁在倫敦梅菲爾俱樂部進行了一場比賽,看誰在飲料酒水上的開銷更大。在短短的兩個半小時內,他們花費了超過131000英鎊(約20萬美元)的錢,接下來幾天,俄羅斯暴發戶在倫敦的所作所爲在各類新聞上得到了廣泛報道。
對于這兩位千萬富翁來說,醉酒可能是一種恰當的表達,酒精和揮霍金錢的快感一起湧上頭頂。他們絕不是例外:他們的同胞——手機大亨葉甫蓋尼·亞曆山大羅維奇·契克伐金(Yevgeny Alexandrovich Chichvarkin)在定居倫敦後成了一名酒商,在他看來,如果你買得起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遊艇226,那麽和朋友們喝掉一瓶55年窖的格蘭菲迪威士忌(價值約12.3萬英鎊)也就不算什麽過分的事了。
而在現實中,公衆竟然對這種肆意揮霍的行爲感到十分興奮:它是夢想的素材,是21世紀的童話。關于六星級酒店、鍍金豪車和價值3300萬英鎊的手表的故事比比皆是。許多內容與20世紀80年代的享樂主義和電視劇《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産生了共鳴。區別在于,如今可以用iPhone拍攝這種超級消費行爲後通過照片牆(Instagram)迅速發布到網絡上。事實上,這種奢侈的行爲在媒體和網絡報道中無處不在,因此從某種程度來說它們也變得“正常化”起來了。
21世紀人人都在談論奢侈品,因爲大家認爲奢侈品說明了精英階層和我們大多數人之間日益擴大的財富差距:“富人”和“其他人”。在新興經濟體經過一系列增長之後,貧富差距已經成爲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國內爭論的重點,同時它也更新了奢侈品的定義和關注點。英國記者佐伊·威廉姆斯(Zoe Williams)認爲,雖然一位首席執行官的收入是公司底層員工的202倍,但“從來沒有一個人的能力比其他人高202倍的”。
這種收入的不平等還反映在當代消費中:盡管我們大部分人會買一瓶相當便宜的葡萄酒,但還是有少數人買得起價格227成千上萬倍貴的葡萄酒。自20世紀中葉以來,這種消費似乎有所增加。如果你研究一下20世紀50年代社交聚會上的酒水單,甚至是20世紀初一家豪華酒店的菜單,你會發現它們的價格並不是普通酒的數千倍。
有些人可能會反駁說,自2007—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富豪們的日子也不好過了。經濟危機確實嚴重打擊了奢侈品市場的某些部分。2013年年中,希臘唯一一家法拉利經銷商關門了。問題不在于希臘的有錢人再也買不起法拉利了,而在于當希臘經濟面臨崩潰時,再斥巨資購買豪車是很不明智的。尤其是銀行家、股票經紀人和首席執行官,他們處于風口浪尖,因此不得不保持低調。更糟的是,政府開始仔細調查富人,詳細詢問他們申報的收入和他們所購買的汽車、珠寶、別墅是如何一筆一筆對應上的。在意大利,幾位有遊艇的人被逮捕了,因爲他們在納稅申報單上聲稱自己十分貧困。奢侈品制造商和服裝生産業也受到了沖擊:2012年,意大利兩家主要時裝公司被控偷稅漏稅。奢侈品和奢侈品生産商與偷稅漏稅和境外資金有關,他們確實帶著利潤“跑掉了”。
這裏的重點不是指責肆意揮霍的行爲,而是稅收部門意識到,對于非常富有的人來說,有些奢侈品既是享受,也是投資。隨著離婚、法庭訴訟、破産或遺産規劃的出現,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據我們所知,離婚是裝飾藝術市場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之一)。豪宅、別墅、藝術品甚至前文討論的那瓶葡萄酒——人們喝這些酒的頻率比想象中低很多——都屬于這種情況。
電影《珠光寶氣》(2013)劇照。
奢侈品不再只屬于“過得非常好”的那些人
一味地指責富人並把奢侈品視爲分裂社會的力量是不可取的。事實上,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在向往奢侈品。也許我們買不起一瓶標價與一套小公寓差不多的威士忌,但我們可以去買“豪華巧克力”或者“不同口味”食物中的一種。廣告總是告訴我們,我們獨一無二、與衆不同,因此需要買些昂貴但並非買不起的奢侈品犒勞一下自己。這種奢侈品可能是知名時尚品牌推出的香水、精心設計的廚房設備、一種稀有的橄榄油或者一瓶來自法國經典葡萄酒産區的紅酒。
21世紀奢侈品的真正“成就”就是它盡可能多地欺騙了人們,正如戰後西方世界的大衆消費一樣。它代表著我們心中對“更好的東西”的渴望,並且在不斷滋養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影響著我們社會的猖獗的個人主義(虛僞或者自戀?)。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暗暗希望自己也能成爲俄羅斯的小寡頭,能在施泰尼茨買古董並且能直接包下整層整層的酒店。
奢侈品無處不在。社會科學家提出將奢侈品依據收入和社會/文化資本進行分類。這種分類基于物品的價值(以及得到這件物品需要賺多少錢)來區分“頂級奢侈品”(稀缺、珍貴、質量好,而且通常是專門訂做的物品)、“中級奢侈品”(質量上乘、小批量生産的物品)和“買得起的奢侈品”(有時被稱爲“大衆”奢侈品,奢侈品牌的領域)。
還有一種更加精細的分類,把奢侈品分爲四類:“真正的奢侈品”包括那些不受金錢約束的物品,比如高檔汽車、噴氣式飛機和遊艇;“傳統奢侈品”包括時裝、珠寶、香水、高檔葡萄酒和烈酒;“現代奢侈品”指的是通過旅遊、科技、酒店和水療等服務以及線上奢侈品來尋找身份和地位;最後,“生活中的小奢侈品”是由真正的大衆奢侈品組成的,包括平價時裝、鞋子、進口或本地生産的“有機”食物以及身體護理産品。
盡管這些分類實質上是在試圖提煉更複雜的現實,但卻十分有用,因爲它們指出了其實生活中存在著大量奢侈品這個事實。這些奢侈品不一定貴到讓人買不起,但卻幾乎是普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不過這裏也出現了兩個問題。首先是頂級奢侈品(爲超級富豪們量身定制的)市場與其他奢侈品市場的區別,高端奢侈品市場需要變得更加奢侈(或者是更加精英化),因爲現在太多的人買得起一些基礎型奢侈品了。去最好的餐館是不夠的,必須要雇用一名頂級廚師在家裏爲你做飯才行;去最好的度假村度假也是不夠的,必須要買下或者租下整個小島才行。頂級奢侈品追求“走出市場”(要擁有非常罕見甚至獨一無二的東西,比如2014年底邦尼·梅隆那顆栩栩如生的藍鑽以3260萬美元的高價賣出),正是因爲現在大多數奢侈品變得越來越標准化,而且明碼標價。
概念空間和市場潛力的擴大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一些國際知名品牌的生産性質和形象發生了變化。2008年,記者達娜·托馬斯(Dana Thomas)指責奢侈品行業“賤賣”了奢侈品的關鍵資産:它的吸引力。在一本題爲“奢華:奢侈品如何失去吸引力”(Deluxe: How Luxury Lost its Lustre)的極具煽動性的書中,她通過研究奢侈品牌的生産者和消費者揭示了奢侈品牌的膚淺。有些人認爲這是“奢侈品民主化”的勝利,但她卻認爲這是奢侈品牌的一種策略,即通過滿足各種各樣的客戶來實現利潤最大化。
以20世紀六七十年代著名的高級時裝和成衣生産商聖羅蘭爲例,80年代時該品牌推出了一系列較爲平價的奢侈品,比如香水,而聖羅蘭在1979—1989年之間香水銷量增長了16倍。而如今這種較爲便宜的奢侈品有著比過去更高的定位,價格上也有了更高的切入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場真正的“奢侈品通貨膨脹”,幾乎現在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形容成奢侈品。
有時,奢侈品牌還會把含義上完全相反的詞組合在一起,比如那些“買得起的奢侈品”:電影院的座位現在也經常分類,就像過去遠渡重洋的客輪一樣,最好的座位配置了更好的椅子、毛毯,甚至還有酒水服務員。另一個例子和韓國汽車品牌現代有關,該公司制定了一項戰略:要生産“買得起的豪車”;到2015年時,現代汽車成爲加拿大汽車業銷量增長最快的品牌。這一切對于愛德華七世時代的紳士甚至20世紀50年代的白領而言,都是難以理解的。
電影《珠光寶氣》(2013)劇照。
商業把隨處可見的東西也變成了奢侈品
在過去30年裏,我們見證了純粹的商品向奢侈品的轉變。在18世紀,由于仿制品和替代品的出現(比如銀和銀板)還有大規模生産(因此每單位的生産成本降低了),一些原本只有少數人才能擁有的奢侈品變成了大部分人都能擁有的大衆奢侈品。而我們的上一代則經曆了相反的過程,那時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東西到今天搖身一變成了奢侈品。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咖啡(盡管它不會馬上被視爲奢侈品)。20世紀50年代,一杯咖啡只要10美分,是北美生活習慣中再平凡不過的一件東西了;但現在咖啡既是一種商品,也是一種“奢侈品”,走進星巴克或咖世家的任何一家門店,都能看到不同容量和口味的咖啡。這些商品本身可能不是奢侈品,但愈發細化的市場分類爲它們找到了客戶。
那些真正追求品質的人可能更願意在帕多瓦的佩德羅基咖啡館[19世紀的法國作家司湯達(Stendhal)是它的第一個客戶]或威尼斯的弗洛萊恩咖啡店(歐洲的第一家咖啡店)裏喝咖啡,這裏咖啡的價格是星巴克的好幾倍,而且肯定不會裝在寫著你名字的紙杯裏。就算你不喜歡這種精致的氛圍,你也很可能選擇購買一台意式咖啡機和一種稀有的咖啡豆自己研磨。例如,貓屎咖啡就十分受歡迎,它是一種由亞洲野生麝香貓食用並排泄的咖啡果實制成的咖啡。咖啡果實經過麝香貓的腸道,獲得一種特殊的香味。對于那些覺得這樣有點惡心的人,價格說明了別的含義。這種咖啡每年只生産1000磅(約454千克),而每磅的售價超過300美元。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從啤酒到錢包再到鋼筆。一個富裕的社會總能找到新的花錢方式。有社會良知的經濟學家曾警告我們要警惕過度消費,但他們沒有預見到企業所采取的營銷策略之一就是不會在我們只需要2件套頭衫的時候想著賣20件,他們更傾向于賣出2件毛衣獲得相當于賣出20件的利潤。這時售賣的毛衣或者套頭衫就不再會是普通針織品了,而會是一件貼上“名牌”“環保”“做工精良”“合乎倫理”等標簽並投入大量廣告宣傳的奢侈品。這就是時尚研究專家帕特裏齊娅·卡裏法托(Patrizia Calefato)所說的通過廣告、購物、時尚和媒體所進行的“消費奢侈化”。
商品轉變爲奢侈品的過程在科技領域也得到了驗證。2002年,作家、學者詹姆斯·B.特威切爾(James B. Twitchell)認爲,盡管科技産品在我們身邊無處不在(比如微波爐、隨身聽,以及近年來的手機和智能手機),但它們仍然擁有排他性,因此和面向大衆市場的消費品仍有區別。
蘋果公司的産品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些人認爲它屬于奢侈品,而另一些人則認爲它屬于邪教或是大衆文化。盡管蘋果公司生産的iPhone、 iPad和iPod數以百萬計,但它的包裝設計卻頗爲誇張。蘋果公司的商品都是裝在一個可以滑動的精美白色盒子裏,看起來很像香水的包裝盒。它也采取了和奢侈品類似的營銷策略,比如它的店鋪都是極簡主義風格,最著名的一間位于曼哈頓,這家店在第五大道的衆多奢侈品店中十分引人注目。店裏展出的商品很少,訓練有素的銷售人員會告訴顧客這是因爲新産品基本上已經賣光了。威圖(Vertu)和普拉達(Prada)等品牌的門店裏也經常發生類似的事情,這些公司將手機等大衆科技打造成真正的奢侈品,旗下商店遍布香港、曼谷和新加坡的大型奢侈品購物中心。
蘋果官網。
奢侈品不再是一個物件,而是商品標簽以外的東西
在一個奢侈已成爲一種普遍現象的世界中,奢侈品如何保持其吸引力?盡管人們常常指責奢侈品過度放縱物欲,但自21世紀初以來,奢侈品的本質(也包括價值)變得越來越不重要,這聽起來似乎是個悖論。用一名當代評論員的話來說:“今天,奢侈品是一種條件而非一個物件。”換句話說,奢侈品不僅僅和獲取物品有關,它更是一種生活、思考和充滿激情的方式。
奢侈品的目的不是通過提供昂貴的專有商品,而是通過提供一種在獲得和享受此類商品(以及越來越多的服務)方面可能並不特別的獨特體驗來恢複其獨特性。哲學家伊夫·米肖(Yves Michaud)談到了個人需要通過奢侈品來體驗情感強度的需求。他認爲,奢侈品是當前應對一個日益沉悶世界的“真實性”的關鍵所在。
相反,有人可能暗示著世界越來越重視“虛假的”東西:後現代主義鼓勵各種狡猾的人物編造出“可能的”“相對的”並且同“外表”有關身份和職業。這不是我們所說的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和愛德華時代時的感性經濟。今天的優質法國葡萄酒可能會被菜單解釋爲一種“煙熏紫羅蘭”的味道(就像2015年胡拉勒的葡萄酒圖書館所做的那樣),這是因爲消費者缺乏富裕、受過良好教育的愛德華時代食客的審美和感官訓練(他們真的知道他們在聞什麽和品嘗什麽)。
所有這些對于奢侈品牌來說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那些不僅僅想得到物品本身的客戶不太可能被直接使用商標之類的粗略手段所吸引。也許是出于這個原因,普拉達在2014年開始減少對標志性三角形的重視,他們甚至把該標志性三角形印在T恤衫的背面。客戶現在解釋說,他們想要標簽以外的東西。對于這類消費者而言,“真正的”奢侈品意味著拒絕奢侈品和品牌之間的聯系。因此,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我們看到了“無品牌”的出現:看不見任何商標的高端産品。
這種現象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解釋。一方面,客戶希望將自己與奢侈品牌的大衆市場區分開來,並希望選擇一種超出平均水准的産品。一些人還擔心,明顯的品牌標志會給他們帶來一個沉迷享樂的負面形象。因此,“無商標”使産品更具體驗性,這種體驗通常只在真正看到日常包與無品牌商標的奢侈品包之間差異的人中間親密分享。
零售商認識到,要保持較高的銷售水平,他們需要采取更謹慎的品牌塑造方法,所以對“無商標奢侈品”有不同的解釋。因此,他們將更多的精力投資于醒目的零售空間,而不是放置商標的位置。對于消費者而言,這意味著“奢侈品元素”不是來自商標,而是來自從奢侈品商店購買商品的體驗感,這種體驗的價值不亞于産品本身。
營銷專家已經明白,消費者需要的是獨特的感覺而非獨特的商品。一個簡單但形象的例子可能是香水。比起出售知名品牌的香水,少數倫敦調香師現在爲客戶提供了創造自己的氣味的機會。他們模仿花宮娜香水廠(Parfumerie Fragonard)香水的模式,這家公司在離位于埃滋(法國南部城市,離尼斯很近)的工作室中爲客戶提供專業幫助,讓他們創造並購買專屬于自己的獨特香精。在這個例子裏,奢侈品不僅與購買獨特的香水有關,還涉及自己制作香水並成爲一名工匠的機會。不僅與獲得技能和理解香水制作流程有關,還包括了産品的私人定制。
定制的重要性在奢侈品服務中尤爲突出。蓋特威峽谷度假村(Gateway Canyons Resort & Spa)是位于科羅拉多州和猶他州之間邊界的豪華“探索度假勝地”,這裏提供定制牛仔靴和帽子的服務,還有由專業攝影師制作的完整客戶旅遊記錄。蓋特威峽谷由探索頻道的創始人約翰·亨德裏克斯(John Hendricks)建造,只有58個專屬房間和14個“賭場”,並在其衆多定制服務中提供“印第安人教授的串珠課程,夫妻們將自己制作的珠寶帶回家”。
另一種個性化服務的是“隨叫隨到的精靈”:禮賓服務。在所有關于上流社會的電影中,門房都是無處不在的人物。在過去,門房是一間豪華酒店大堂裏的工作人員,經常負責滿足他的富裕顧客各種不可能的要求。 如今,禮賓服務已成爲“生活方式管理服務”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爲了滿足超級富豪的需求。
從事“獨家奢侈品”行業的品牌都深知服務對于其産品聲譽的重要性——即使這樣做是有代價的。這種關于奢侈品的新觀點認爲消費者要付出的並不僅僅是錢。在21世紀的奢侈品概念中,時間和知識十分關鍵。這一觀點並不新鮮。
社會學家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是1899年出版的著名的《有閑階級論》(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的作者,他認爲“區分”——一種想要與其他人不同的需求——不僅僅是通過購買和使用豪華昂貴的物品來實現的。這種區分也是通過支出明顯的時間——我們稱之爲無用的活動——來實現的。那些支付得起這些費用的人只是把錢花在毫無經濟回報的活動中,例如打高爾夫球、參加聚會、開豪華轎車,以及在充滿異國風情的地方度過悠長的假期,而不是去工作賺錢。可能有人反對將這些活動與愉悅聯系在一起,但事實證明,並非所有這些活動都是如此: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無休止的上流社會舞會當然不僅是一種簡單的愉悅,它還可以用來證明社會地位和歸屬、尋找簇擁者,有時還與社會慈善事業有關。如今,花時間在“無用的”活動上可以爲從理發師到高爾夫球童的各種服務行業提供就業機會。
《有閑階級論》,[美] 索爾斯坦·凡勃倫 著,淩複華 / 彭婧珞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休閑和服務活動也需要知識(有時需要非常專業的知識)。當這類活動希望變得與衆不同時,它們必須盡可能地排他。高爾夫的例子很恰當:加入高爾夫俱樂部不僅僅是要付高額入會費的事情;人們還得知道該如何打高爾夫球。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其他休閑運動,例如網球或馬球。奢侈品需要文化。那些不懂得如何舉止得體的人雖然可能和彌達斯一樣富有,但他們在社會上卻走不了太遠。
近年來,受到“奢侈化”影響的“實驗”領域之一是食品。用餐或使用各種食材制作食物是體驗的一部分,這種體驗既非常物質化(涉及所有感官)又很短暫(因爲吃完了就什麽也不剩了)。食物、葡萄酒、烈酒和糖果不僅因爲它們的價格或內在口味而受到贊賞,還因爲它們與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因此,如果不去著名的糕點店拉杜麗(Ladurée)逛逛就不能說自己曾去過巴黎,在這家店裏人們可以品嘗到鎮上最好的馬卡龍。無疑,這家法式蛋糕店的娴熟經驗和人造夾心使這些馬卡龍的口感遠勝于其他任何馬卡龍。
時間和空間才是21世紀最昂貴的奢侈品
分析奢侈品如何在富裕的西方國家已經成爲比簡單的物質消費更複雜的事物,可以更進一步以展示奢侈品的概念如何塑造了我們對時間和空間的看法。索菲亞·科波拉(Sophia Coppola)在她的電影《珠光寶氣》(Bling Ring, 2013年)中講述了一群加州中産階級年輕人闖入好萊塢明星的家中偷竊他們的奢侈品的故事。影片圍繞兩個重要主題展開:中産階級生活的無聊與疏離,以及超級富豪居住的宏偉空間。
至少從文藝複興時期開始,豪宅和宮殿對人們的吸引力就可見一斑了。對空間的追求也許是人類的一種基本需求,而意大利城邦的富裕家庭建造的中世紀高塔所展現出的力量使這種需求得以實現。事實上,它們常常是爲了給平民和外國貴族留下深刻印象而建造的。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這種迷戀越來越強烈,以至于我們不僅認爲房子和公寓是居住的地方,還認爲它是一種資産,一種可以“交易”或“編造”的東西。這是因爲,在所有已成爲奢侈品的商品中,空間或許是最明顯的例子。有個棲身之所是必要的,但對于西方和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物理空間已經成爲一種奢侈品。任何想在倫敦、紐約或悉尼購買哪怕是最小的公寓的人都很清楚這一點。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空間也變得昂貴起來。像布拉格等城市如今也有排他性的房地産市場。
證明空間已成爲終極奢侈品的證據也可以在高端房地産市場找到。在倫敦,海德公園一號的一套公寓將花費大約2億美元。紐約位于曼哈頓第56街和第57街之間的公園大道432號(德雷克酒店舊址)是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樓。
倫敦和紐約的例子或許不能代表總體趨勢,但它們告訴我們,整個房地産市場的價格一直在上升。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買不起房子,房産被視爲奢侈品。這意味著,富人將付出額外的努力,以確保他們有機會獲得頂級豪宅。在一個人口越來越多、聯系越來越緊密的世界,似乎很難找到一個平靜祥和的地方。這就是奢侈品公司會提供無人島、看不到人的足球場大小的公寓,以及去世界最偏遠地區度假遊的原因。城市裏的擁擠現象立刻被消除了,這一行爲與一種非常傳統的觀點異曲同工,即奢侈品是頂級精英所獨有的。有人可能會說這些人居住在象牙塔中,從而對其他人、其他社會問題和集體意識都視而不見。然而,這並不奇怪:在許多國際大都市,當每平方英尺的空間售價高達2000多美元時,許多人做夢也想不到,隱私和寬敞就成了奢侈品。
時間也正在成爲一種新的奢侈品。另一部電影告訴我們爲什麽時間本身可能是一種稀有的商品。賈斯汀·汀布萊克(Justin Timberlake)和阿曼達·塞弗爾德(Amanda Seyfield)是影片《時間規劃局》(In Time)中的主演。影片描繪了一個未來的反烏托邦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人們可以購買時間。人們再也不需要整容手術了,因爲有機會通過購買時間來長生不老、永葆青春。
時間本是唯一非交易性的奢侈品。除了我們能活多久這個問題外,時間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被認爲是一種難得的好東西。然而,對于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和閑暇時間的追求與這樣一個事實之間存在矛盾:那些有空閑時間的人要麽是沒有技能的人(傳統意義上的窮人和社會邊緣人),要麽是失業的人(新的窮人,越來越多的中産階級),要麽是領取養老金的人(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相對貧窮)。這就是爲什麽時間也以“高質量的”強度體驗和短暫的放縱(水療、周末的豪華靜修)等形式被“奢侈化”,以作爲對在辦公室、惱人的老板、嘈雜的車間和其他工作場所中度過的“壞”時間(有壓力、忙碌、令人不悅)的解毒劑。
這讓我們能夠區分那些只是有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的人和那些利用這些時間來做“積極的”“有意義的”活動的人。這是21世紀早期消費與20世紀最後幾十年消費之間的主要區別之一。即使是在澳大利亞沒有像樣的購物設施的偏遠鄉村小鎮上,現在也有一個足浴中心,而這些地方通常由富有創業精神的移民經營——這是奢侈品全球化的另一個標志。他們可能開了一家簡單的印度或中國餐館,但隨著全球食品革命和美食的興起,當地人現在更傾向于要求羊奶酪配上當地植物,佐以有機羊肉和松露土豆。
本文經格致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奢侈品史》,較原文有刪減,小標題爲摘編者所加。
原作者 | [澳] 彼得·麥克尼爾 [意]喬治·列洛
編輯 | 申婵
導語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