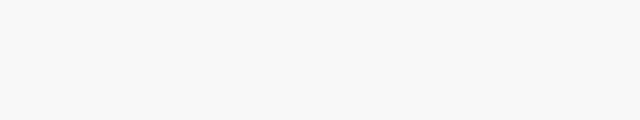袁芳芳第一次見何亞君,是在5年前的北京馬拉松上。
袁芳芳當時200多斤,是個大號女孩。作爲志願者的她,在終點附近,看到一個戴著墨鏡的跑者,怪的是,還有人用繩牽著他跑。
這不是作弊嘛,咋還能讓人牽著跑?
她心生困惑,直到那個人跑過去了,她才看見他的背後印著“視障”兩個字。
袁芳芳也算見過世面,英國計算機博士,互聯網大廠碼農,但盲人跑馬拉松她還是第一次見——他們不應該待在按摩店嗎?
比賽結束後,那個拽著繩子奔跑的背影揮之不去。袁博士查了下資料,中國竟有1700多萬視障人士,比整個荷蘭人口還多。她有點想不通:這麽多人平時都到哪兒去了?還有,盲人跑馬拉松又是怎麽回事?
正處在減肥事業低潮的袁芳芳,決定去看看。她剛開始練習跑步,但實在太重,最好成績是2公裏,幾乎沒人帶她玩。
“我降低起點,陪盲人跑總能跟得上吧。”她想。
後來,朋友告訴她,那個盲人跑者,叫何亞君。他全馬跑進了4小時,超過一般運動員水平。
一群程序員的助盲跑
何亞君不是一個人跑,2014年他創建了一個助盲團,幫助視障者跑馬拉松,奧森是他們的訓練場。
袁芳芳從未見過這麽多盲人,他們一身專業運動裝,由志願者牽著,轟隆隆地跑過去。全無印象中盲人拄著盲杖,摸索前行的樣子。
袁芳芳說明來意,也老實交了底,問能否加入跑團當志願者。一旁的盲友說,這太好了,現在盲友跑步熱情很高,志願者不少,但流動性也大。
後來袁芳芳才明白,志願者和盲人搭檔間建立跑步的默契,需要時間和裏程。
圖|袁芳芳(頭戴粉色帽子)和盲友們奔跑在奧森
就這樣,戰力只有2公裏的袁芳芳火線成爲志願者,成爲盲人跑友的“眼睛”。她第一次摸到“盲繩”,指頭粗細,一尺多長。分給她的那位盲友,跟著盲團跑了三年,一直在跑得最慢的五隊晃悠。
到了真正試跑時,這雙200斤的“眼睛”卻連最佛系的盲友都跟不上,剛燃起的心,一下又涼了。
袁芳芳是“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的一代。1991年,年僅10歲的她就寫出人生第一行代碼:Hello World。後來,她一路開挂,讀到博士,畢業後先去了甲骨文,2017年跳槽到阿裏巴巴。
也是那一年,她生了二胎,體重一發不可收拾,突破200斤。許多次安檢,刷臉系統掃不出來,滴滴尖叫。
圖|袁芳芳最胖的時候
有氧運動是甩脂的第一步。和盲人跑馬拉松是門技術活兒,不僅講究身高、擺臂、步頻、步幅、步速的配合,就連呼吸也相當講究,如果一個氣定神閑,一個喘得像拉風箱,節奏就會打架。
跑了大半年後,袁芳芳看到了效果,體重從216斤減了50多斤。
同事見她瘦了,都來問:“哪家私教這麽給力啊?”芳芳說給盲人助跑。大家聽了都覺得新鮮:那你是人肉語音導航嗎?你們牽繩還是牽手啊……
芳芳幹脆上阿裏內網發帖,一是回答同事們的疑惑,二是順帶發動一波志願者,解決助盲團長期“缺眼睛”的問題。
跑步時,志願者和盲友兩兩對齊,通過一根盲繩協同。志願者要拆解盲友的核心需求,及時提供信息,比如地面坑窪、路旁垂下的樹枝,保持一個細密的顆粒度,增強盲友的安全體感和奔跑體驗……
阿裏內部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員工每年必須完成最少3小時的公益,除了傳統的撿垃圾,大家也在打開腦洞想更新的公益項目。陪盲人跑步?這事還是讓不少人稀奇,再加上袁芳芳的“互聯網技術範”的講述風格,帖子很快在阿裏北京中心的幾個辦公室流傳開來。程序員們在評論區啧啧稱奇:“這是助盲跑,還是打磨互聯網産品?”
袁芳芳用行話打趣:“經過我們的合力打磨,助盲團已經有3000多活躍用戶了。”
帖子發出後,芳芳的釘釘開始響起來,開始是一天三四個,後來多至十多個。有些是咨詢細節,有些直接報名。
高德程序員趙思寒,是個佛系健身愛好者。看到芳芳的帖子後,也是不相信盲人還能跑馬拉松。
他用黑布蒙住雙眼,親自體驗一番。“心裏虛得很,方向感立馬就沒了,腳都不知道往哪踩。”
還有支付寶的錢添,甯夏銀川人,也是個程序員。當時,他正對支付寶的無障礙功能研發感興趣,但他卻沒有見過一個盲人。他需要深入這個群體,于是給袁芳芳發了消息:算我一個。
“阿裏助盲團”釘釘群很快接近百人,人數超出想象,那就不能放羊式管理了。袁芳芳效法互聯網公司架構,根據不同成員專業,把百位志願者分成SOP組、用研組和技術組。
SOP組負責搭建盲友和志願者數據庫,方便兩者快速配對;用研組負責搜集視障人士的互聯網産品需求,如讀屏、導航、網購等問題。
技術組相當于志願者教練,負責科普助跑技術,還要拍攝視頻,便于後期跑姿分析。
“不走出去,我永遠只是個按摩的”
這群程序員摩拳擦掌,在訓練時間來到奧森。他們用事先准備的SOP,按照身高、步速、耐力等“大數據”迅速匹配搭檔。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見到現實中的盲人。
圖|錢添(左)和盲友搭檔在做跑前准備
現場起碼有上百名盲人跑者。和芳芳的初次反應一樣,程序員們就像誤闖進一個平行世界——我們身邊竟有這麽多盲人?他們蹒跚而來,牽上盲繩盡情奔跑,然後蹒跚回去。
即便如此,能出門的已是盲人中的佼佼者。相處多了,程序員們覺得自己低估了生活的殘酷。他們覺得路邊有盲道,地鐵有電梯,扶手上有凸點,世界便通行無阻。
曾經轟轟烈烈的“文明城市”運動,讓中國的盲道鋪到縣一級,但真實的應用中卻有很多問題:不少盲道鋪成之字形,通往一堵牆或掉了蓋子的排水井,又或者停滿共享單車。“我甯願在馬路溜邊走。”一位盲友說,“盲杖能敲到馬路牙子就有路,但盲道真有可能導到坑裏。”
坐公交也惱火。有次訓練,一位盲友遲到了半小時,他一邊換衣服,一邊對趙思寒抱歉說:“等很久沒等到公交車,問人才知道,臨時改線了,通知就貼在站牌上,可我看不到啊!”
這樣的事多了,芳芳他們意識到,“盲人爲什麽不出門”的疑問真有點“何不食肉糜”。看得到的還只是現實中的“牆”,觀念裏的“牆”卻困住他們一輩子——他們幾乎一出生就被“隔離”,大多被關在家裏,運氣好點就去特殊學校。
很多盲人終其一生都沒摸過一本盲文書。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殘障人群文盲率高達43.29%。2020年,殘障人士就業率只有43.24%。缺乏教育和就業難,貧困將伴隨他們一生。
如果不是20年多前賭氣離開老家,助盲團團長何亞君估計仍困在四川巴中的小山村裏。10歲時,他得了腦膜炎,引發視網膜脫落。之後,他眼前的光亮像被蟲子蠶食,一點點消失。一度,他覺得自己這輩子就別想出門了。
後來,見過世面的表姐來家中提議:“爲什麽不學學按摩?”
圖|何亞君助盲團的盲友新潮在爲客人按摩
讓盲人學習按摩,幾乎是對盲人最大的善意。統計顯示,90%的盲友在從事按摩。健全人可以上大學,但面向盲人的學校少之又少,哪怕考上盲校裏的清華北大——長春理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出來後也大多只有兩個選擇:按摩和鋼琴調音。
何亞君先到成都學按摩,2002年來到北京,從此就和大多數盲人一樣,十年如一日,在幾十平米的按摩店裏工作與生活。
長期不活動,何亞君的體重從剛來北京時的100出頭,一路飙到2014年的190多斤,再加上脂肪肝和高血壓,一個鍾的按摩險些堅持不下來。
直到一位老顧客帶著他跑了一趟奧森,他開始逐漸愛上了跑步,後來陸續跑了全國70個馬拉松。
圖|何亞君在按摩店。他通過讀屏軟件和助盲團成員交流
何亞君說:“如果不走出去,我永遠不知道,除了按摩我還能做那麽多別的事。”
他希望通過跑步,可以讓更多盲人走出來。起初,他想有三五個盲友一起跑就行了,沒想到卻“炸”出一堆同病相憐者。很快,盲跑團登記在冊的盲友就有3000名。
3000個盲人跑者,各有難言的人生。盲友劉偉去招聘會找工作,衆目睽睽之下被罵出會場。28歲的盲友趙雷相親幾十次,都是見一面就沒有然後了。從上海跑到北京的劉哥,封控期間因爲無法通過APP搶菜,一天只能吃一包方便面,吃了十來天才被人發現……
他們大著膽子來到奧森跑道後發現,生活其實有著更多可能。
“抽到的牌再爛,也要拼命打好”
袁芳芳的跑搭子周玲,年近花甲,還跟個愛做夢的姑娘一樣,到處參加馬拉松。她是少數沒有從事按摩的盲友跑者。
2018年,周玲跑完無錫馬拉松後,她給搭檔袁芳芳透露了新想法:出國參賽。盲友們覺得這個好啊,長見識更長志氣。盲人出國,這種事過去想也不敢想。
志願者們幫周玲找國外賽事,最近的是日本名古屋女子馬拉松,跑完還能有一條Tiffany項鏈。周玲不知道是啥,芳芳說女孩子都喜歡。
圖|袁芳芳(右)和周玲(左)在奧森跑步中
次年春節還沒過完,周玲和芳芳就開始備戰訓練。春寒料峭,清晨的奧森還是黑漆漆的,但勝在沒什麽人。天亮了,就請旁人幫忙拍跑步視頻,再到北體大找田徑老師做技術分析。
名古屋濕冷,只在北京練不行。兩人還一起飛到杭州,繞西湖跑完10公裏,提前適應名古屋氣候。
2019年3月9日,芳芳和周玲提前一天到達名古屋。第二天一大早,天氣陰森,看樣子要下雨。這是她們最擔心的天氣,路面濕滑不說,防失溫也是一大挑戰。
果然,跑了六七公裏後,還真飄起了細雨,氣溫也驟降。袁芳芳感覺到,周玲呼吸節奏有些亂,甚至直接用嘴呼吸。她記起北體大老師的提醒,提醒周玲起步階段要盡量用鼻子呼吸,鼻子呼吸不夠,再口鼻一起呼吸,避免直接用嘴呼吸。
袁芳芳提議放慢步伐,調整呼吸節奏。周玲的呼吸這才穩定住。
兩人拉著繩子跑步的樣子,也引起了觀衆注意,個別懂行的發現是盲人,用日語爲她們加油。芳芳指指衣服上的中文,示意聽不懂,蹩腳的“加油”又稀稀拉拉在人群響起。
跑到30多公裏時,眼看勝利在望,周玲忽然臉色有些難看,往後拽了拽盲繩:“右腿有些抽筋。”
袁芳芳趕緊讓周玲停下,撸起她的褲管,看到小腿肚子青筋凸起,肌肉硬得像石塊,低溫運動最擔心的情況發生了。
袁芳芳一邊爲對方按摩放松肌肉,一邊做著心理按摩:“馬上到終點了,北京的盲友們等著我們的消息呢。”
周玲再次跑起來,她調整了呼吸和步頻,盡量讓身體放松。剩下的路程,兩人一直沉默,芳芳也不惜打亂節奏,配合周玲有些僵硬的步速。對她們來說,名次不重要了,跑完就是勝利。
沖過終點了!計時器報出5個半小時。隨之而來的是長槍短炮,現場的日本記者不知從哪裏知道有一位中國盲人選手,都跑過來采訪——對他們來說,這實在太罕見了。
袁芳芳已經癱倒一邊,但她還是盡好助跑的最後一份職責,提醒周玲:“三點鍾方向,有記者在拍照,沖他們微笑!”周玲此時也低頭喘著粗氣,聽到喊聲,她騰出一只手,擡起頭,比了個V字手勢。
袁芳芳當時覺得,她就像《老人與海》裏那個花了85天拖回大馬哈魚骨架的老漁夫,輸給了鲨魚,卻戰勝了自己。
圖|袁芳芳(右)和周玲(中)跑過終點線後合影
芳芳躺在地上,看著灰蒙蒙的天空和閃光燈中的周玲,感到前所未有的輕松。“生活不就是這樣嗎?抽到的牌再爛,也要拼命打好。”她說,“不管大到玲姐的眼睛,還是小到我的體重和日複一日的焦慮。”
施以援手者,也推開一個新世界
從名古屋歸來後,袁芳芳除了繼續助跑,還獨立征戰各種馬拉松,先後跑了杭州和無錫馬拉松,還跨國跑了新加坡馬拉松。當年的200斤女孩已甩掉六七十斤肉,還因爲助盲的事迹受邀成爲北京馬拉松協會理事。
她的志願者同事們也一直在跑,人均一個全馬。錢添如願打卡了家鄉銀川的馬拉松,趙思寒也成功完成北馬。袁芳芳還成了阿裏“跑步派”(阿裏內部的跑步社團)北京“派頭”。
他們陪伴過的盲友,也一個接一個拿到人生中第一塊馬拉松獎章。
阿裏每年會拿出營收的千分之三做公益,也很關注支持員工的公益嘗試和創新。這群程序員的助盲跑,得到了阿裏公益委員會的認可。除了陪跑,“跑步派”成員們在思考新的問題:除了手中的盲繩,還有什麽辦法能幫助更多的盲人呢?技術,能爲助盲再做些什麽?
近些年國家推行的無障礙環境建設啓發了他們,不僅是腳下的盲道,還有手機裏的“數字盲道”。“正好發揮我們所長。”芳芳說,“一條盲繩只能帶一個盲友跑,做好一款産品卻能幫助一群盲友跑。”
圖|工作中的趙思寒
高德的趙思寒,在助跑中感受到盲人對精准方位的敏感,到了陌生地方個身都要適應半天。
高德導航逐步上線看了轉彎震動提醒功能。趙思寒還了解到,丹麥有程序員開發出一個叫“Be my eyes”(你是我的眼)的應用,分爲視障人士和志願者兩種模式。當視障人士有導航等需求時,可以呼叫志願者,志願者通過手機視頻爲視障人士提供實時幫助。趙思寒說,未來,高德也可以加入類似功能,成爲視障人士和志願者連接的橋梁。
而錢添等程序員也想,未來可以開發出更精確的讀圖軟件。盲友們用手機拍攝周圍環境,軟件可以精准識別圖中物體和各物體間大致距離,便于盲友迅速熟悉陌生環境。
袁芳芳則更關注無障礙網購體驗。早在2018年,淘寶無障礙實驗室研發出“讀光OCR”技術,幫助視障人士實現“聽圖購物”。
袁芳芳還想借淘寶的無障礙經驗,優化Lazada的視障用戶體驗。她說,東南亞地區視障人士占人口的比例多達1.5%,全世界最高。東南亞的盲友們也應該享受到網購樂趣。如果不是助盲跑,她可能不會注意到這樣的小衆用戶需求。
程序員們慢慢發現,奧森的盲友們,從按摩師變成了矯健的跑者,而他們自己,也在施以援手中被這群堅韌的人啓發、感悟、激勵,推開一個新世界。
圖|當年200多斤的胖姑娘袁芳芳,已經是個馬拉松老手
2022年3月,由于堅持多年助盲跑,袁芳芳成爲了北京冬殘奧會火炬手。初春的張家口乍暖還寒,袁芳芳一身紅白相間的冬奧服,在兩名護跑員陪伴下跑過濕地,草木仍枯黃,但已見努力生長。
這份激動和榮耀的那頭,是奧森紅色跑道旁的盲人跑者們。周玲來了,何亞君也來了,他們用耳朵在手機裏等待袁芳芳的消息。
終于聽到這個熟悉無比的名字時,人們一陣歡呼。他們或許不知道天空和火焰的顔色,更不知道老朋友的樣子。但此時此刻,他們覺得手中盲繩仍握在芳芳的手中,旁邊映來熊熊火炬的溫度。
– END –
撰文 | 郭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