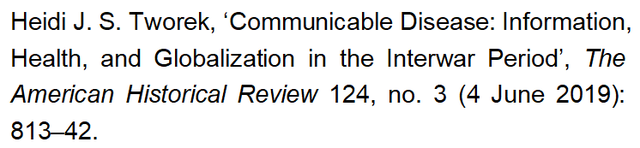可“傳播”的傳染病:兩次世界大戰間的信息、健康與全球化丨國政學人
作品簡介
【作者】Heidi J. S. Tworek(海迪·托萊克)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史系助理教授,哈佛大學曆史學與經濟學聯合中心訪問客座研究員。她的研究興趣主要是新聞與媒體、國際關系、公共政策、國際組織等的曆史。其代表作爲News from Germany: The Competition to Control World Communications, 1900-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編譯】周玫琳(國政學人編譯員,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曆史系博士研究生)
【校對】施 榕
【審核】陳 勇
【排版】吳 俣
【來源】
期刊介紹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國曆史評論》)是美國曆史學會(AHA)的官方出版物,創辦于1895年,宗旨爲“促進曆史研究、對曆史文件與遺物的收集與保存,傳播曆史研究成果”。
2018年該刊的影響力因子爲1.456,近五年平均影響因子爲1.639,在曆史學類期刊(95種)中位列第2 名。
可“傳播”的傳染病:兩次世界大戰間的信息、健康與全球化
Communicable Disease: Information, Health,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Heidi J. S. Tworek
內容提要
“全球化”通常被定義爲人員、貨物和信息在世界範圍內增加的移動,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方方面面並非同時發生。本文利用一個國際健康信息網絡的發展,探究爲什麽信息的全球化與移民和貿易的全球化步調不一。從各國意識到疾病是一個跨國問題,到國際聯盟衛生組織(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把國家、帝國和基金會聯結在一個健康信息的志願性交流體系中,經曆了將近70年 。該體系覆蓋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且生命力比國聯更持久。借助新無線電技術,基于殖民網絡、港口城市、海洋與天空,國際聯盟衛生組織構建了一套新基礎設施,其中新加坡與西貢的地位比日內瓦更重要。健康信息原本旨在預防流行病,但它也使國際聯盟衛生組織作爲標准化技術信息中轉方的身份正當化,幫助英法等殖民大國分攤帝國的財政負擔,爲日本等其他國家提供軍事優勢,讓德國參與國際事業以重獲國家聲望。追溯這些基礎設施的曆史,有助于曆史學家們克服“國家”、“國際”、“帝國”與“全球”之間的人爲界限。
本文所利用的詳實史料主要來自日內瓦國際聯盟檔案館,部分來自英國國家檔案館和大英圖書館等其他機構。
文章導讀
一、導言:信息、健康與不共時的全球化
本文始自一個生動的曆史片段:1929年,一艘從孟買途經馬賽最終駛向利物浦的客船上出現天花,關于天花爆發的信息迅速傳播,造成了歐洲範圍內的恐慌。法國禁止那些未及時注射天花疫苗的英國遊客入境。對此,英國《衛報》對法國人的“誇大”和“劇烈預防措施”表達了不滿,因爲實際上客船上只有一人感染了天花。當英國方面的抗議未能奏效時,國際聯盟衛生組織(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下文簡稱LNHO,“國際聯盟”簡稱“國聯”)適時出面平息了相關風波。
通過講述這段故事,本文引出其核心論點:LNHO的體系說明了信息流動爲何且如何能夠在人員與貨物流動減少的時期不減反增。西方國家自19世紀中葉已開始重視傳染病信息(例如霍亂)以實現有效地檢疫和流行病預防,但各國之間相互協調的信息交換遲遲未出現,直到LNHO的健康信息傳播體系出現。這一志願體系産生自經濟全球化與大規模人員流動退潮之時,它覆蓋了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並使信息在流行病管理中發揮關鍵作用。LNHO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存續下來,爲今天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奠定了基礎。
國際健康信息體系令人意外地形成于兩次世界大戰間時期(interwar period,下文簡稱“戰間期”),很少受到學界關注,但對該體系的考察能讓曆史學家不再僅僅關注信息如何促進了全球化。對“全球化”的經典定義是人員、貨物和信息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相應地,“逆全球化”則指更具限制性的移民和經濟政策,以及孤立主義。但是,正如全球化的方方面面並不是同時發生一樣,逆全球化也是如此。在既有的關于“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討論中,戰間期通常被表述爲“逆全球化”的典型代表,但是這一認知在信息上是不成立的。
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基礎設施,即“包括鐵路、高速公路、電話、電力和互聯網等在內的大型、耐久、運轉良好的系統和服務”。這些基礎設施使得信息的傳播更易實現。長期以來,曆史學家對基礎設施的研究都抱有興趣。關于信息基礎設施傳播,有三種主流的史學敘述:第一種聚焦政治與軍事控制,第二種重視媒體和技術公司之間的經濟合作,第三種走中間道路,強調政治經濟或“國家與市場關系”。但它們均忽略了國際組織的重要角色。在這些敘述中,國際組織的作用更多是建立技術標准,而不是信息的收集者或內容的創造者。
信息交流不一定與其他國際或帝國的互動同步發展。LNHO制作的地圖中呈現的基礎設施並非受民族國家號令,而是受制于港口城市、殖民網絡、海洋和天空等。國家和帝國的界限從來都不是溝通的邊界。20世紀初無線電技術的發展爲支配海洋與天空提供了新方法,也使得LNHO能夠將民族國家、帝國和基金會統合爲一個延續至今的新型國際健康信息體系。LNHO的流行病情報系統提醒我們,不應假定全球化與國際合作的方方面面是同時發生的。戰間期,人員流動更受限制,領土邊界得到加強,但信息交流在其他合作崩潰後依舊存續,盡管在各國政治對抗的高潮時期也未能完好無損。
二、如何開端?LNHO國際健康信息體系的演變
有關疾病監控的系統性國際交流發展較晚,這體現了信息的全球化如何且爲何與移民和貿易的全球化步調不一。從各國意識到疾病是一個跨國問題,到一個旨在交換流行病信息的全球性基礎設施網絡出現,經曆了將近70年。
類似交換信息的嘗試開始于19世紀中期。在19世紀30-40年代霍亂疫情爆發的背景下,歐洲各國政府于1851年召開首屆國際衛生會議(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但具體成效甚微。在殖民訴求的驅動下,西方國家繼續召開國際衛生會議,但在機制創設上動作緩慢。1902年,第一個國際健康組織泛美衛生局(Pan-American Sanitary Bureau)成立;1907年,旨在協調國際衛生會議的國際公共衛生署(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下文簡稱OIHP)在巴黎成立。與此同時,其他針對健康問題的組織開始出現。包括英國在內的帝國建立了醫學機構,如1899年成立的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校。他們的健康政策強化了殖民結構:醫學話語往往試圖令種族等級秩序合理化。流行病控制也協助處理了帝國擔憂的問題,包括“殖民疾病”與健康管理成本。
LNHO的出現使得疾病信息的非系統采集發展爲一個綜合全面的體系。最初促使LNHO誕生的直接動力並不是各國的殖民關切,而是 1918-1919年比一戰造成更多死亡人數的大流感(又稱“西班牙流感”)和1916-1920年肆虐東歐與俄羅斯的傷寒。1920年12月,國聯大會通過一項設立健康委員會(Health Committee)的決議。幾經易名改革,1928年該委員會自立門戶,正式成爲LNHO。LNHO聘用頂尖的公共衛生與醫療專家,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展開了各種健康項目。這一嶄新的國際健康協調機構將工作重心放在信息(尤其是標准化數據)上。成立于1921年的流行病情報部(Epidemiolog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是LNHO的核心業務之一。
LNHO信息戰略的根本在于爲流行病信息的采集和傳播搭建出一套新的基礎設施,其關鍵就是國聯第一次設在歐洲之外的部門:遠東健康局(Far Eastern Health Bureau),亦稱東方局(Eastern Bureau)。該部門于1925年設立于新加坡,其選址反映了三組利益的交彙:國聯自身的信息戰略,英帝國的傳播網絡,以及LNHO主要資助方——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偏好。洛克菲勒基金會長期堅持認爲信息和數據是公共衛生的支柱,因此收集流行病情報是東方局的“主要職能”。新加坡之所以能夠成爲健康信息樞紐,也是因爲東方局應用了無線電報這一新技術,跨越了帝國邊界,建立了可持續的信息基礎設施。無線電技術從在一戰期間得到顯著改進,還成爲一種“一對多”的通信手段。有了這些發展,即使帝國和民族國家在陸上存在競爭,它們仍可以在海空領域開展合作。
在領土邊界愈發森嚴的年代,無線電的興起讓LNHO(在技術上)可能成爲各國之間信息交流的中轉方。LNHO將國家(national)與帝國(imperial)的無線電信號塔相聯結,形成了一種運作方式迥異而持久的國際合作體系。各個國家和帝國首先默許了流行病情報的新“幹涉”,因爲他們了解這對各自經濟的好處,特別是帝國擔心疾病會影響海上貿易,信息的交流能爲它們提供解決的辦法。帝國主義的貿易動機有助于解釋爲什麽國際健康信息體系在非洲西部沿岸的存在感較低:信息的交流更聚焦在途經印度洋和大平洋到達歐洲的主要貿易線路上。東方局迅速采用了無線電技術來傳播流行病情報,然而相比技術的新穎,東方局選擇傳播的疾病信息也呈現出19世紀的殖民主義取向,旨在保護歐洲免受霍亂等“東方”疾病的侵害。
LNHO和東方局起初的任務與OIHP多有重疊沖突。1926年在巴黎簽署的《國際衛生公約》分離了OIHP和LNHO的任務,還給予了東方局獨立的運作空間,讓各政府先將信息傳給新加坡而非OIHP,再由新加坡向OIHP發送流行病信息與周報。
三、如何工作?東方局與流行病情報的産生
東方局的流行病情報經由采集、校勘和分發三個階段産生。每周一至周三,東方局接收各地關于天花、霍亂、鼠疫等最新數據的電報與郵件。英屬印度的信息僅在周四才送達,因爲德裏的官員們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從印度各省收集信息。電報提供數字,信件傳達有關死亡率、氣象條件和滅鼠措施等信息。
流行病情報的基礎設施加強了空域和海域的合作,也使曆史學家能通過追溯信息采集與分發網絡的産生與運作 ,來克服“國家”、“國際”、“帝國”與“全球”等人爲界限。東方局接收的大多信息來自太平洋和印度洋中的“海洋小鎮”,這些港口城市是公衛官員和醫生們與當地人口交流以及確定疾病類別的樞紐。到20世紀30年代早期,LNHO的網絡已覆蓋45個國家和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但是,全球化並不總是一個同步發生的過程,即使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重創了全球貿易網絡,關于流行病的情報網絡依然在擴展,這部分是因爲洛克菲勒基金會仍在繼續資助LNHO。
LNHO國際體系的繁榮也受益于它將各帝國與國家的信息標准化的努力,畢竟來自世界各國的信息對疾病的描述五花八門。隨著時間推移,LNHO將流行病情報的內容與形式都進行了標准化,令更多信息傳播得更遠。值得指出的是,數據的背後是重要的個體。不計其數的檔案和信息不僅經常掩蓋了國際組織中女性工作者艱苦卓絕的數據整理工作,也讓人忽略了在一線采集數據的醫生與當地人的功勞。不僅如此,數據也隱藏了不滿與困難。英德等國政府其實對東方局不夠精確的報告和數據統計方式頗有微詞,不過,對于統計方法的抱怨從未阻擋各國參與其中。
經過數據校勘,東方局和日內瓦會立即或定時分發信息。如果某港口或政府的衛生部門在其常規時間之外發送報告流行病的電報,東方局會立即聯絡OIHP和易感染地區。國聯官員們也會主動搜尋這類消息。在平時,東方局創設了兩種標准周報,通過郵件或無線電發送。無線電是LNHO的首選,因爲只有這種方式可以聯系海上的船只,經濟上更便宜,技術上能實現一對多,從而保證更廣更快的信息分發。東方局還發布年度報告,爲日內瓦總部提供其活動記錄,也向洛克菲勒基金會爭取繼續資助。每年的報告都宣揚無線電利用的進步和有線電利用的減少。
在東方局制作的地圖上,空間以無線電信號塔而非距離來標記,展現出國聯是如何通過共享健康信息來促進各國的合作,以及對基礎設施的重視。在地圖上,海洋與天空多于陸地,西貢和新加坡取代西歐成爲中心。在某種意義上,這描繪了一個以太平洋和印度洋爲中心的新世界,其中國聯是連結帝國與民族國家的必要機構。但在另一種意義上,這也通過將非洲與亞洲描繪成孕育疾病之地再現了殖民主義的假定。通過突出無線電信號塔之間跨越陸地邊界的交流,這些地圖強調了國際信息基礎設施發展中的帝國合作。帝國的等級制、偏好和資本塑造了這種合作的本質,但這些地圖暗示,只有一個(國聯這樣的)國際組織才能協調它們在空域共享的主權。與地圖相關的文字史料強調了這一體系參與度的增加,但與此同時,不應忘記這些地圖隱藏了某種等級制:只有精英公共衛生官員與船長能接收到信息,殖民地的人民被排除在了能接收信息的範圍之外。除此之外,東方局提供的信息從英屬新加坡發送到法屬西貢,再由荷屬印度尼西亞、法屬馬達加斯等地的基站轉播。這些信號塔之間的聯系是LNHO在英國、法國和荷蘭之間建立的一個新型帝國間合作模式的體現。通過共享這些基礎設施,公共衛生官員們建立了一個能交流的殖民地間主義體系(communicative intercolonialism)。
與之前各國圍繞有線電纜展開的激烈競爭相對比,國聯促成了帝國間通過無線電共享健康信息。帝國的參與清晰表明LNHO未能創建一個中立的信息網絡,而是依賴殖民秩序和技術來實現信息交流。國聯體系背後的這種帝國性的基礎令許多國家望而卻步,尤其是警惕美國的拉美國家,但是其他一些國家(尤其是德國)則通過參與LNHO來提高自己在信息傳播中的國際地位。德國從20世紀20年代初就開始參與LNHO會議,其間加入又退出國聯,直到1939年二戰在歐陸全面爆發才終止合作。
LNHO的信息交流體系爲何能有效運作到20世紀30年代?首先,LNHO希望能通過該體系接觸技術精英來增強(和平的)國際互動,爲此在發送編碼的無線電信息外還發送簡明易懂的解碼信息。其次,東方局與殖民地官員都努力確保該體系的可信度,加強監督,避免出錯。最後一點在于LNHO體系傳播內容的本質是信息而非解讀或建議。國聯官員認爲只有在當地政府不被迫遵從國際標准、能夠(自主)采取行動的條件下,傳播才能奏效。
四、誰受益?LNHO、東方局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國聯與政府官員看來,LNHO的流行病情報體系提供了三種益處,每一種都會促進和不同夥伴的合作。首先,信息能夠防止對貿易的幹擾;其次,國聯借此體系能成爲疾病知識的樞紐;最後,信息能確保軍隊在不必擔憂感染的情況下安全行進。這些意圖並非都是善意的,它們往往遮蔽了暴力動機或殖民野心。但在移民與貿易減少之時,這些彼此重疊的激勵促進了信息交流的增加。
首先,通過減少港口船只的周轉時間,無線電信息得以助力商業運作。例如,一旦港口官員獲知一艘疾病感染的船只即將抵達,他們可以迅速組織檢疫隔離。提前得知某艘船上疾病的具體爆發時間也能減少船只花費在隔離上的時間,使其更快續航,減少停留港口造成的貿易損失。
其次,流行病情報體系強化了LNHO存在的合理性。國聯官員們把LNHO打造成一處信息交換中心,借此爲其爭取支持。但是LNHO其實不能回應各國政府和流行病學家對更多疾病類型信息的訴求,這不僅是出于財政方面的原因,也是因爲接收信息的質量和頻率不一。
盡管國聯認爲其信息系統在保護軍事人員健康上扮演了有益的角色,國家的動機並非總是善意的。隨著二戰的推進,理想主義的國聯官員們爲流行病情報的軍事用途感到震驚。早在1920年代初,日本官員出于軍事目的想獲得中國的疾病信息,就率先提議國聯在亞洲設健康局。部隊進攻前夕,指揮官需要確保他們不會被疾病擊倒,而東方局是獲取這類信息的便宜又可靠的途徑。
隨著20世紀30年代國聯政治權力的式微,它爲了強化自身的存在意義而愈發重視LNHO這樣的所謂技術部門。盡管國聯沒有阻止戰爭爆發,至少它可以聲稱自己阻止了流行病的爆發、拓展了信息交流。但LNHO也對一些政府視流行病情報爲戰爭武器的事實心知肚明。1940年9月,美國中止向國聯發送信息。1940年11月,印度采取同樣舉措,因爲英國不希望疾病報告落入位于已淪陷的巴黎的OIHP或其他敵對國家手中。1941年9月,英國徹底停止向國聯發送任何有關其領土的信息。無線電的優勢在此時成爲劣勢。從1941年英國的視角來看,清晰易接收的周報意味著易攔截,而英國對德國優越的無線電能力一清二楚。日本對東南亞的入侵迫使東方局的員工于1942年2月逃往澳大利亞,東方局被徹底關閉,並在同年10月正式解體。
相比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二戰對流行病情報的幹擾是不太劇烈的,因爲國聯的流行病情報基礎設施通過其人員、出版物和理念延續到了戰後,這體現在了之後成立的WHO中。例如,東方局首任局長戈蒂耶(Raymond Gautier)繼續在WHO任職,直到1950年退休。在這些官員的領導下,WHO將新加坡、日內瓦和亞曆山大港保留爲流行病情報站,且延續了以有線電爲後備的無線電系統。東方局的周報《每周流行病記錄》(The Weekly Epidemiological Record)延續至今。“交流傳播能消滅傳染病”的疾病預防理念也被保留下來,其主要的目標受衆從公共衛生官員變爲了公衆,爲建立如今這個向公衆傳播的體系提供了基礎。
五、結 論
時至今日,在流行病管理中,國際健康信息傳播的有效性與重要性仍是熱議的話題,比如2014-16年西非地區爆發的埃博拉疫情中有關衛生實踐傳播缺失和人員跨境交流信息溝通不足的爭論。對疾病信息傳播的關注並不新鮮,但20世紀20年代國聯協調創立的國際健康傳播體系才是使其具體成形的一步。信息基礎設施變得無所不在,以至于它們在諸如資本主義或醫療衛生等重要曆史現象中的角色沒有在曆史學界得到足夠的關注。對健康信息傳播體系的研究多聚焦于當下時段,並幾乎完全從行爲主義科學汲取知識養分。
信息穿越邊界的方式未必與人員和貨物一樣。LNHO的世界流行病情報體系之所以能在一個明顯逆全球化的時刻出現,是因爲它在新的空間運作,並向不同的參與者提供不同的利益。健康信息旨在防範流行病,它強化了LNHO作爲標准化技術信息中轉方的地位,協助英法分擔了帝國的財政壓力,向日本等國提供了軍事優勢,又讓德國通過參與國際事務重獲國家聲望。信息通常被賦予與其內容不甚相關的工具性目的,但戰間期流行病情報的傳播絕非單純的技術發展,那些傳播健康信息的樞紐是自由國際主義在其他意識形態挑戰下的産物。戰後,這些樞紐及其實踐迅速重申了它們的重要性。
當前時刻和大部分的國際史讓人們傾向于將國際交流中的任何崩潰視作同質(事件),而關于健康信息和基礎設施的曆史爲我們展現了一個不同的故事。
本文由國政學人獨家編譯推薦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
爲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爲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