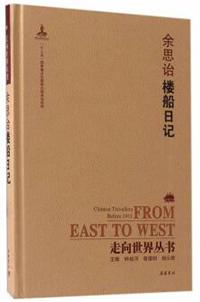鄧世昌于甲午一戰壯烈殉國,名垂宇內,然而除了壯烈犧牲的經過,有關鄧壯節公生平的可靠記載仍不夠詳瞻。本文將披露一些鮮爲人知的鄧世昌遺事:1891年率“致遠”“靖遠”艦爲訪華的俄國皇太子護航,1893年率領三艦訪問日本長崎,光緒禦賜鄧母匾額是“教忠資訓”而非“訓子有方”,1898年鄧氏宗祠原有門聯寫的是什麽。
鄧世昌與致遠艦同袍合影
兩次執行任務
光緒十三年(1887),鄧世昌奉命帶領海軍官兵400多人,乘坐招商局“圖南”輪船前往英國,接駕新下水的致遠、靖遠、來遠、經遠四艘軍艦回國,由北洋水師總教習英國人琅威理任總指揮,鄧世昌擔任致遠“管駕”(艦長),駐英使館隨員余思诒以文官身份負責“護送”,隨後寫成《樓船日記》一書。在一百多天的接艦航程中,余思诒與鄧世昌均駐紮在“致遠”艦,登岸時也時常一起活動,得以近距離觀察鄧世昌統率指揮致遠艦的各種演練過程,以及他的爲人處世之道。
鄧世昌熟悉海軍各種操作規程,有著豐富的航行經驗,多次鎮定自若地指揮“致遠”艦排險,處理機件損壞。在從新加坡出發的一段航程,由于沒有按海圖路線走,鄧世昌一夜沒有合眼,一直指揮、監控著整個過程。
鄧世昌高度的愛國心,不僅在體現在甲午年的薄敵陷陣,而是在平時的工作中時時處處表現出來。八月初四日,艦隊停靠在地中海入海口的直布羅陀(英國從西班牙手裏奪去的殖民地),有8個流落西班牙的廣東華工前來求援,敘述在西班牙被人欺騙的苦況,希望搭順風船回國。鄧世昌在查驗了他們的證件後,立即找到當地的英國警官,了解清楚情況,第二天把其中兩人接上船,並安排他們在船上做雜工。
世界海軍通例“凡水師登岸,行必成列,立必整齊。水勇遇各國水師官,皆摘帽傍立候過。”鄧世昌從英國、地中海各港到亞丁、錫蘭(斯裏蘭卡),都受到禮遇,只有埃及禮貌稍遜。當艦隊抵達新加坡時,鄧世昌與同僚登岸,沿途有數十個外國水勇列隊而行,見到四個中國艦長,竟然不按慣例避讓路脫帽致敬。鄧世昌立即大聲加以斥責,教育他們讓路行禮等候艦長們走過。(余思诒:《樓船日記》,第105頁)
《樓船日記》封面
光緒十七年(1891),俄國皇儲(即後來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訪問中國。3月24日,鄧世昌受命率領“致遠”、“靖遠”二艦提前抵達香港,爲迎接護送事宜作准備。4月4日,俄國皇太子乘坐“亞速號”抵港,第二天一早換乘招商局“江寬”號艦前往廣州訪問。4月10日,皇太子再次從香港出發,由鄧世昌率領兩艘中國軍艦護送,12日抵達馬祖,14日到花鳥島。15日,鄧世昌率“致遠”先行,在吳淞炮台迎接,“靖遠”則緊緊跟隨著皇儲座船。4月18日,俄皇儲在上海換乘淺水船上溯武漢,鄧世昌順利完成了“隨護”任務。(安徽版《李鴻章全集》第23冊第168-170頁)
隨行的俄國公爵、李鴻章老朋友烏赫托姆斯基寫道:“香港總督和英軍司令迪格比·巴克少將前來‘亞速號’拜訪。此外,還來了兩艘炮艇的船長(身著民族服裝),他們是從北方(李鴻章的艦隊)派來爲尊貴客人護航的。”“中國軍艦上的船員選拔自生長在島上或大陸海岸邊的水手,乃是上等人才。不幸的是,整個帝國沒有專門的海軍衙門,力量分散在四個彼此毫不相幹的總督手上,指揮官都不了解歐洲戰略和當代科技。”(《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第196頁)穿過台灣海峽的時候,船隊遇到大霧,“有一點讓人很吃驚,兩艘中國護航艦一分鍾也沒有落後于我們,它們設法不鳴笛航行,偶爾陷入灘上急浪中,然而仍然堅持執行李鴻章的命令。”(同書第241頁)在俄國船只受濃霧影響被迫打散隊形的情況下,鄧世昌能讓“致遠”“靖遠”緊緊跟隨皇太子座船,顯示出高超的指揮藝術。
俄國皇太子遊覽廣州華林寺
1893年再訪長崎
光緒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1893年3月11日),鄧世昌率“致遠”、“超勇”、“揚威”三艦訪問日本長崎,此事在各種清末海軍史著作中都沒有敘述,各種鄧世昌傳記也都失載。馮青在《中國近代海軍與日本》一書中,專門有一節是“北洋艦隊訪日與日本的應對”,寫了1886年第一次訪日與長崎事件、1891年第二次訪日、1892年第三次訪日,唯獨沒有談到1893年鄧世昌訪日。
1886年的北洋艦隊首次訪日時,發生了長崎事件。水師提督丁汝昌最初的打算只是單純的入塢修理與補充燃料,孰料發生中國水兵與長崎巡警之間的惡性沖突,1名中國海軍軍官、7名水兵死亡,約80人受傷,發展爲重大外交事件。日方實際認爲清廷此舉是一種“威懾”行動,由此加速了對華備戰的步伐。有論者認爲,北洋艦隊的幾次訪日,給了日方了解中國海軍實力以可乘之機,刺激了日本朝野對華的仇視心理,也讓日方得以詳細了解北洋水師的實力,是不明智的行爲。
丁汝昌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1893年初,他仍然派鄧世昌率3艦在海面巡邏時到長崎加煤。3月10日,《申報》提前得到消息,報道稱:“長崎理事署及采辦軍煤之榮昌號,接得北洋水師營來信,悉鄧正卿軍門將率致遠、超武(勇)、揚威三兵船東遊扶桑之國。”
3月22日,《申報》以“日東耀武”爲題,寫下了詳細的回顧報道:
3月11日下午4點,北洋水師致遠、超勇、揚威三艦自上海抵達長崎,只聽得炮聲如雷霆,中外人士都湧到港口眺望,但見致遠艦高懸“副統領”旗幟,進港時兼挂日本國徽,鳴炮21響致敬,日本軍艦“海門”艦升旗、燃炮作答禮。片刻,中國駐長崎領事(當時稱“理事”)張桐華登艦拜會鄧世昌,暢談一小時而別,鳴炮7響相送。5:30分,鄧世昌偕同超勇管帶黃建勳、揚威管帶林履中,穿戴官服,前往理事署回拜,張桐華以茶點招待,詢問行程,鄧世昌回答說,此次在長崎停留一禮拜,3月19日須動身前往高麗,沒有時間訪問神戶、橫濱。談話完畢,3人回船。第二天,經辦加煤的榮昌號東主,在“大鶴樓”宴請鄧世昌。午後,鄧世昌等偕同理事署翻譯王某,前往長崎縣署拜會代理知縣中村,賓主均用英語交談。13日上午,中村登船回拜,送客時鳴炮7響。14日晚,理事署宴請于三江會所。
此次訪日,距離甲午大戰一年半,致遠等三艦再次送上門來,給了日方又一次觀察中國戰力的一個機會。《申報》“日東耀武”標題,體現了當時社會妄自尊大的虛驕之氣,舉國上下對即將到來的危機毫無察覺。“致遠”爲何一定要從上海到長崎加煤,是否屬于當時北洋水師的慣常“動作”,這個專業問題,尚需留待海軍史專家解讀。
致遠艦(引自陳悅文章)
鄧世昌兩次前往歐洲接艦,多次往返日本,自身又勤于學習,善于觀察,他對世界各國包括日本海軍的實力、訓練情況有著深入的了解。他心裏非常明白北洋水師幾斤幾兩,一直顯得憂心忡忡。甲午年春,他短暫回到老家廣州,在與新會進士譚國恩敘談時,“戚然謂無事則已,海軍罔濟。”(譚國恩:《寫趣軒續稿》卷一)他知道一旦開戰,北洋水師打不過真正的強敵。可以想象,當中日戰爭爆發時,他早就抱定與敵拼命的決心。
譚國恩還寫到,公馀之暇,鄧世昌喜歡臨池作書,收藏圖書甚富,這跟他後人的回憶完全吻合。此次故鄉把晤,鄧世昌還請譚國恩爲規劃中的鄧氏宗祠內“繹思堂”題寫匾額。
當“致遠”艦即將沉沒時,譚國恩之子譚學衡也在北洋當差,駕輪向前救援,被敵艦所阻而未果。譚學衡1885年就讀于廣東水陸師學堂第一期駕駛班,畢業後留學英國,在北洋海軍服役。他是甲午戰爭中爲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這一批幸存者葉祖珪、薩鎮冰、譚學衡、程璧光、劉冠雄等人,日後都成了清末民初海軍的主要領導人。1896年,中國向英國訂購“海天”“海圻”兩艘巡洋艦,派程璧光、林國祥、譚學衡等前往監造。1897年,這個團隊負責駕駛兩艘軍艦回國。1905年,因管理安徽武備學堂成績突出,被提拔到海軍處副使,隨後出任海軍副大臣。辛亥年袁世凱複出時,命譚學衡代理海軍大臣,隨後在清帝退位诏書上以內閣閣員身份副署,見證了這一曆史時刻。
代理海軍大臣譚學衡
著名挽聯高邕撰書
鄧世昌于1984年9月17日殉國,清廷隆重賜恤,到乙未十二月十四日(1896年1月28日)在廣州光孝寺設靈開弔,“官吏紳士,無論平日識與不識,均具生刍一束,叩奠靈前。寺中房屋雖多,幾至無容足之地。挽聯祭軸琳琅滿目,美不勝收。”(1896年2月8日《申報》)其中最著名的挽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一直被誤傳是光緒帝禦賜。陳明福在《海疆英魂》依據鄧世昌曾孫女鄧立英保存的老照片,指出是高邕撰書,但並未能有效消除誤傳,至今仍有。陳明福在書中寫道:
鄧世昌的曾孫女鄧立英保存著一張世人未見過的鄧世昌照片。照片上的鄧世昌頭戴瓜皮小帽,身穿便服,坐在藤椅上,態度安詳。相片上端正中題有“鄧壯節公像”,左右題有對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下聯旁書小字“光緒乙未高邕”,下有兩個印記,已模糊難辨。(陳明福:《海疆英魂》第377頁)
由此可知,流傳于世的鄧世昌題聯遺像,最右邊“光緒乙未高邕”字樣及兩處钤印被剪掉了。筆者查到當年香港《華字日報》報道,爲陳明福的結論提供了有力佐證。
1896年1月30日《華字日報》爲紀念鄧世昌,特地將各方致祭的挽聯刊登出來,順序是“XXX雲”,跟著挽聯正文。這批挽聯當中,有一首是“水利局雲: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當時廣東尚未有水利局這樣的機構,該聯應該是上海南市水利局同人敬獻。1898年8月16日《申報》報道:“南市水利局幫辦高邕之司馬,現經江海關道劄饬幫辦會丈局務,所遺水利局幫辦一差,刻下尚未委人。”《申報》、《華字日報》與陳明福所親見照片,這三者構成完整的證據鏈,證明這副名聯確實是上海南市水利局幫辦高邕撰書。高邕(1850-1921),字邕之,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書法家。
後來,筆者從鄧輝粦老師轉發的某藏家藏品中見到這張未經修剪的照片,可見到“鄧壯節公像”左側有“高邕”署名並用印,對聯左側另有“光緒乙亥高邕”落款。至此,問題徹底解決,挽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可確定是高邕撰書,與光緒帝完全無關。
高邕題聯之鄧世昌像,鄧輝粦供圖
禦賜匾額“教忠資訓”
1897年9月,鄧世昌母親郭太夫人因病仙逝于上海,9月10日舉喪,靈柩暫厝廣肇山莊,儀式極爲隆重。《申報》記者不惜筆墨,詳加論列,爲免失真,將原文略加標點如下:
其前導除沖風、灣號、馬執事、馬吹打外,則有“肅靜回避”“提督銜廣東水師營副將賞戴花翎予谥壯節三代一品封典”等銜牌二十余對,又有“樂善好施”黃匾一方,繼之以制造總局所送之西樂一班,後隨炮隊營兵丁一隊,各負刀叉、洋槍等件,後又有督標奇兵營健兒一營,荷戈執戟,殊壯觀瞻,間以祭亭、豬羊亭、香亭、容亭等十余座,中雜清音,後隨僧道,每一人張以逍遙傘一頂,有八人各穿花衣,隨路吹彈絲竹,又有比丘尼八人執幡相送,後即銮架,又有“奉天诰命”等黃牌兩對,诰命亭一座,繼以西樂一班,頂馬一匹,對馬八匹,魂轎一乘,由子侄輩扶之而行,靈柩則用大紅縀全金蟒繡材罩,以十六人舁之而行,前有孝帏,後有護衛。至執绋相送者,親屬外,同鄉之人與壯節公之有誼者不下數十余人,沿途駐足而觀,人山人海,殊爲非常擁擠雲。(1897年9月11日《申報》報道“壽母殡儀”)
10月3日,《申報》又報道了光緒帝賞賜牌匾給鄧母的消息,巡行儀式十分隆重。10月2日,鄧世昌長子鄧浩洪恭備香案跪迎牌匾,10月2日“升入黃亭,遊行各處,前導除旗鑼傘扇外,有銜牌十余對,如‘予谥壯節’‘特旨旌獎’‘诰封一品夫人’‘晉封一品太夫人’之類,繼以銮駕全副、鼓樂兩部,及劊子軍、健香亭、诰命亭,材官八人持刀簇擁,由慎余裏公館過垃圾橋,繞道大馬路、四馬路然後折回。”由此可知,鄧世昌母親及長子因家族生意關系,定居于上海老垃圾橋邊、蘇州河北岸的慎余裏。
長期以來,人們都說光緒帝給鄧母所賜匾額是“教子有方”,這是又一個大誤會。《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二十三年八月辛巳條記載:“谕內閣。禮部奏,遵議禦史潘慶瀾奏請將已故總兵之母旌獎一折。已故總兵鄧世昌,恪遵母訓,移孝作忠,力戰捐軀,死事最烈。伊母郭氏訓子有方,深明大義,著賞禦書扁額一方。交譚锺麟等轉給祗領以示旌獎。尋頒扁額曰‘教忠資訓’。”光緒帝這個表彰行動,分成下令、實施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下達決定,第二個環節是由南書房翰林具體書寫,實際寫的是“教忠資訓”。皇帝表彰郭太夫人的上谕裏面有“訓子有方”四字,或者因此而引起誤會。
鄧世昌殉國後,光緒帝還下令在原籍廣州賜祭,由廣州知府主祭,1898年1月15日《香港華字日報》專門作了報道:“吾粵番禺鄧壯節公蒙恩予谥、宣付史館、賜祭一壇,褒忠盛典,至優極渥。月之二十一日,由廣州府州太尊排列儀仗,恭赍敕書,用‘德泰’輪船渡河前往龍珠裏公之專祠致祭,其公子浩洪門外跪迎。迨至禮成,太守駕返,公子亦叩送如儀。祠中高懸禦賜公母郭太夫人‘教忠資訓’匾額一方及京師大僚挽聯多軸。”該報並錄下鄧氏宗祠兩副對聯。
柱聯:
頒彜典而薦馨,谥以壯節嘉名,萬代不忘沾帝澤;
拜國恩于诰命,錫以教忠資訓,九泉深感頌皇恩。
門聯:
聖澤播于南陽,拜手庭階,穆穆皇皇,俨若天顔咫尺;
君恩承于北阙,對揚休命,雝雝肅肅,居然廊廟規模。
香港華字日報
鄧氏宗祠
今鄧世昌紀念館(鄧氏宗祠)原有匾額、對聯均在“文革”中失去,《香港華字日報》的記載有著很高的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