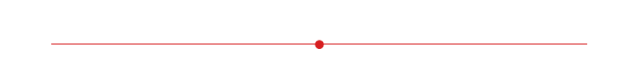確診于客工宿舍
在新加坡5月7日新增的741例新冠確診病例中,絕大多數是住在集體宿舍的外籍勞工,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僅占5名。新加坡政府疫情應對工作組組長黃循財5月6日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隨著對客工宿舍進行“廣泛的測試”,新加坡將在一段時間內繼續發現大量的新病例。在“廣泛的測試”中,中國勞工劉志康確診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哪裏感染上新冠病毒的。也許是在客工宿舍的一樓大廳,那裏在飯點時會聚集上百人;或者是在隔離區,沒有人知道那裏的室友們是否已經受到感染。劉志康今年48歲,在新加坡做建築工人,裝修、刷漆等是他的日常工作。疫情發生前,他住在新加坡克蘭芝客工宿舍。4月21日,新加坡政府宣布住在客工宿舍的所有客工不論所屬領域一律暫停工作。他的宿舍開始了隔離封鎖。“勞工們被限制了出行,如果有人不服從安排,想要離開,就會被扣下‘工作簽證’,徹底失去這份工作。”劉志康說。4月25日,劉志康感覺自己肌肉酸痛,有些頭暈,體溫38.3攝氏度。醫生帶他去做核酸檢測,“他把一個塑料的小條子,放進我鼻子裏,又拿出來,幾秒就結束了”。接著,劉志康被帶離宿舍,轉移到客工宿舍的“隔離區”。“隔離區”並不意味著“單獨隔離”,它的構造和宿舍相似,一層樓有26個房間,每個房間有12張床。4月26日,劉志康進入“隔離區”時,宿舍裏已經住了3個人,“最少時我們這間住過2個人,最多時住過8、9個人”。劉志康從醫生那裏了解到,住進隔離區的人都是因爲出現過類似新冠肺炎的症狀。他擔心自己住在這裏反而會被感染,連睡覺也不敢摘口罩,“我戴兩層口罩睡覺,但現在看來,好像用處不大”。醫護人員告訴他,只要隔離14天沒有問題,就可以回去了。但他沒有等到那一天的到來。5月2日下午,劉志康確診,他被帶離隔離區,入院接受治療。劉志康的病房裏有8張床位,在他住院時,病房裏已經有了5位中國人和2位孟加拉人,都是輕症患者。目前,其中三位已經康複出院。入院5天後,劉志康感覺自己咳嗽、發燒的症狀好轉。每天早上10點,護士會組織病人們做“廣播體操”,還會帶他們做小遊戲——在遠處放一個筐,向裏面投球,投中多的人會被獎勵一瓶汽水。除了有時感到夥食有點不夠吃之外,他很滿意醫院的生活,“比在勞工營裏好得多了”。截至5月7日,劉志康曾住的克蘭芝客工宿舍已累計確診410人。在醫院裏治療的劉志康每天都會和家人打電話報平安。5年前,他來到新加坡工作,今年1月初回安徽老家過完春節後,原本訂了2月11日去新加坡的機票,但臨行前幾天被取消,他改簽到2月6日提前回了新加坡。現在他唯一擔心的是,自己和雇主的勞動合同將在6月6日到期,“不知道到時候能否順利回國”?
“1個人感染,11個人都要遭殃”
5月2日,何昊從新聞中了解到,他所住的客工宿舍樓確診了17個新冠肺炎病例。但他無從得知確診客工具體住在哪個宿舍,“心裏特別沒底”。當天,他被安排了核酸檢測,目前暫未拿到結果,仍住在客工宿舍中。何昊所在的宿舍樓位于新加坡大士1道16號,名叫JTC Space,平日裏面住著大約400名客工,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國人。這家新建的宿舍有大面積的綠地,以及專供客工消遣的電視室、閱覽室、健身房、足球場等公共設施。何昊的宿舍有100多平米,由一個大臥室、一個客廳、一個廚房、兩個浴室、三個衛生間組成,住11個人。何昊覺得住的還算舒適,“和在學校裏差不多,當然我們的宿舍新,其他勞工宿舍就不像這樣了。”“現在宿舍樓裏人少了,很多人提前被雇主接出去了”。何昊說,4月中旬,疫情在客工宿舍爆發時,一些公司把員工接出去安排在賓館裏隔離。何昊的同事也曾向人事部反映過想搬出去住,但還未得到批准。何昊也有些擔心,“畢竟這裏人多,一不小心就可能會感染”。何昊無法和室友們保持社交距離,11張床挨得很近,他認爲,只要宿舍裏有1個人感染,11個人都要遭殃。“我們4月22日之前全部都還在上班,那時新加坡感染病例已經很多了”,4月21日晚,何昊接到人事處電話,讓他上完當天的晚班後,轉天開始“休息”。在宿舍隔離的時間裏,何昊不希望白白浪費,他報了一個線上英語培訓班,上午學習英語背單詞,下午鍛煉身體,晚上和家人視頻聊天。30歲的何昊在新加坡一家數控機床加工廠做技術工。2012年,他從技術專科學校畢業,通過勞務中介來到新加坡做工,經過8年的努力,底薪從4000元漲到8500元人民幣,算上加班費,每月能掙到約18000元人民幣。“中國工人都會選擇加班,每天工作11個小時,一周工作7天。”何昊說。如果不是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何昊原本打算在今年春節離開新加坡,回江蘇老家發展,與妻子和孩子團聚。1月底國內疫情開始爆發,回國航班減少,機票價格高,他想等一等再買,結果沒等幾天,航班就徹底取消了,他只好繼續在新加坡上班,沒想到又趕上了新加坡客工宿舍爆發的新疫情。眼下,何昊還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回國,他打算等到新加坡疫情完全結束再回去,“我不想給國內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希望可以早點開工掙錢
2018年,闫萬的女兒去了新加坡上大學,爲了能多看看孩子,也爲了多掙點錢給女兒交學費,闫萬和愛人通過勞務中介,先後到新加坡做客工。去年1月,49歲的闫萬開始在新加坡一家連鎖餐廳做廚師。爲了方便上班,闫萬住進了離餐廳很近的本茱魯徑的Cassia@Penjuru客工宿舍。他感到自己還是幸運的,因爲雇主的員工少,房間裏一共5個人住,包括他和其他4名孟加拉人。闫萬說,“像是船廠或者建築公司,他們有的宿舍有12到20人”。闫萬所住的客工宿舍區有十多棟樓,住著五六千人,大多是孟加拉和印度人。隔離時期,每天有新加坡政府的工作人員送一日三餐到宿舍大門口。午飯時間裏闫萬能到院子裏“透透氣”,但通常在樓下呆個十來分鍾就要上去了。隔離初期,公司給每個客工發了一個可以反複洗的布口罩,“有點像國內那種勞保口罩”。和母親在外租房住的女兒聽說後很擔心,專門來給他送了盒一次性醫用口罩。闫萬沒有詢問雇主關于停工期間薪水的問題,他從新聞中得知,“政府要求新加坡的雇主給客工正常發工資”。4月11日,新加坡人力部發表文告稱,在阻斷措施推行期間,住在宿舍的客工行動會受到限制,雇主仍要通過財路轉賬或銀行轉賬的方式來向客工支付薪水。但闫萬估計老板可能不會給全薪,“政府給公司的補助金應該還是會發的,可能每個人算起來也就是八九百塊錢新幣(約合人民幣4000元)。”除了補貼,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黃循財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爲客工進行大範圍的病毒檢測。4月28日,闫萬的一個孟加拉室友被叫去做新冠病毒檢測。一天後,室友的檢測結果出來,呈陽性。因爲語言不通,闫萬和4名孟加拉室友的交流不多,他不是很擔心自己受到感染。“是一個宿舍的,但是沒事的時候我們基本上不說話,床也不挨在一起,避免了飛沫傳播。”闫萬介紹,宿舍裏三面都有窗戶,全部打開,風扇也24小時不停地吹,他沒有感到身體不適,打算等幾天看老板有什麽指示再說。5月7日早上,闫萬和另外三名室友也被安排做了核酸檢測,目前還在等待結果。“我已經失去自由20天。”闫萬說,他希望可以早點開工掙錢。截至5月7日,闫萬所在的Cassia@Penjuru客工宿舍已累計確診123人。對于疫情在客工宿舍的爆發,闫萬有著自己的看法,“除了一個房間住12個甚至更多的客工無法保持安全距離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疫情爆發之初,忽視了客工宿舍的公共衛生管理。”據《聯合早報》4月18日報道,自2月初發現第一例客工感染病毒後,有不少其他客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相繼感染。有質疑聲音認爲,兩個月的時間內,由于針對客工宿舍的防疫和檢測措施不足,使其成爲新加坡疫情反彈的最大防控漏洞。5月4日,新加坡官委議員在國會提到客工宿舍裏的生活情況,特別是現在爲了確保新加坡人的安全,使客工們處在“全面封鎖“的狀態下,並問政府會否考慮向客工們道歉。當日的部長聲明稱,“我們將檢討如何提高標准,並留意那些可能尚未達標的舊宿舍。”
“還要被隔離多久?”
隔離在客工宿舍的日子裏,陳啓明時常想不起來“今天是幾月幾號”。半個多月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同另外11個舍友一起擠在30平米的宿舍裏吃飯、睡覺,躺在床上玩手機或看電影。他住在上鋪,下床後也沒有多少可以活動的空間,一天中大多數時間都在床上度過,“渾身疼”。陳啓明在新加坡一家制造廠做工,他住的客工宿舍樓位于新加坡西海岸,共有7層,其中有6層用作客工宿舍,每層分有6個宿舍,1個衛生間和1個公共澡堂,每個宿舍有12個床位。4月7日,新加坡政府開始實施關停工作場所和學校等一系列代號爲“斷路器”的措施。彼時的陳啓明還在工廠幹活,因怕被感染,他從客工宿舍搬去工廠裏住,一個房間只有他和另一個中國人,“雖然只能打地鋪,但活動空間大”。18日晚上11點,陳啓明接到了經理的電話,要求“馬上搬回宿舍”,但沒有告知原因。那時陳啓明所在的工廠還沒有確診病例,但他聽說宿舍隔壁的辦公室裏有人感染。淩晨十二點回去後陳啓明再也沒有離開過宿舍,登記在宿舍名下的其他勞工也被要求返回進行集中隔離,12名客工一起擠在30多平米的空間裏生活。他們被通知在宿舍裏“自主隔離”,“自己管自己”,公司每天會有管理人員來登記體溫,清點人數。陳啓明不敢離開宿舍,他一方面擔心私自離開可能會丟掉工作,另一方面覺得“就算現在出去也不知道該去哪兒”。宿舍裏除了4個中國人外,其余都是印度人,語言、作息、信仰等方面的差異,讓隔離在一起的客工們時常出現一些摩擦。有時,陳啓明甚至覺得宿舍“像監獄一樣”。陳啓明最害怕客工宿舍的密閉空間裏發生聚集性感染。新加坡常年溫度在30度上下,氣候潮濕,爲了保證室內在疫情期間的通風,他們不得不打開窗戶,逼仄悶熱的環境令他坐立難安。擔心被感染的日子裏,陳啓明能做的只是每天反複給自己測量體溫。除此之外,他和室友們還增加了清潔宿舍的頻率——從每周3次變爲每天3次。隔離期間,夥食費要自己出,爲了省錢,陳啓明每天會“故意晚起”,一天只吃中午和晚上兩頓飯。他只點一家飯店的飯菜,因爲“便宜,也會送過來”。送飯的人一般把盒飯放在宿舍樓下,下樓取餐是他一天中僅有的“放風”時刻,但不能逗留太久,否則會被舉報。飯菜多數時候是豆芽、土豆、茄子,也有些碎肉末,一天兩餐需要花40元人民幣。他有時候覺得自己“要吃吐了”,但又自嘲“都這時候了還要求啥”。陳啓明今年30歲,尚未成家。早年經商失敗後,負債十幾萬,2018年來到新加坡打工。疫情前,陳啓明每天做噴漆、補泥、打磨、抛光的工作,只要勤快些,願意加點班,一個月他可以拿到12000元人民幣。新加坡客工宿舍疫情爆發前,陳啓明覺得自己會一直在新加坡幹下去,直到把債還清。但現在他動了回國的念頭。想家時,陳啓明會和父母視頻——他走出宿舍,坐在樓道裏,視頻背景是空蕩蕩的樓梯,不想讓家人知道自己在宿舍裏的處境。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4月21日發表的電視講話中稱,把4月7日開始實施的代號爲“斷路器”的計劃延期至6月1日,這意味著他至少還要再隔離近一個月。陳啓明擔心,如果新加坡的疫情始終得不到緩解,客工們或許還要被隔離更久。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爲化名)(文:計巍 宋建華 文章原載于微信公衆號北青深一度,感謝授權新加坡眼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