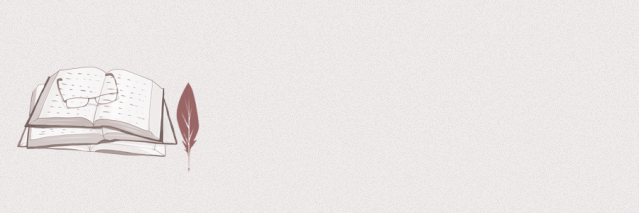2020年,最早一批“80”後已經40歲了。他們從青春期的懵懂少年轉型爲社會的中堅力量,並逐漸擁有穩定的形態和鮮明的特征,一路走來,猶疑與執著並舉,迷惘與堅定並在。值此節點,中國作家網特推出“‘80後’作家對話錄:個體·代際·經驗”專題,通過與八位知名“80後”作家、評論家、詩人的深入交流,力圖展現他們的新風貌,以及他們對生活、文學創作上的思考。此外,專題亦約請相關評論家關于“80後”文學的評論文章,多角度闡釋“80後”作家群體的創作。希望在本次專題中,我們能夠對“80後”文學群體有更多新的發現與思考。讓我們在回望中細致梳理,在展望中奮力前行。
本期作家
周子湘:漂泊的意義,不是回到故鄉
文 | 周茉
新加坡著名景區,廣場上矗立著潔白的萊佛士雕像,一個將新加坡建爲世界重要國際港口的英國人,一百多年前從這裏登陸。他的身後,流淌著新加坡的母親河,兩岸高大的芭蕉樹搖動綠葉,把一個姑娘裹進懷抱。
“429,去把機台上的晶片送到蝕刻區!”
“429,Super來了,快下貨!”
“429,給工程師打電話,五號機台出問題了,快!”
坐落于新加坡的世界著名半導體晶圓電子工廠,那台Super一路呼嘯,被429用推車推著穿過人群。像大片白桦林,連體的白色防塵服裹著一個個人,阻隔了灰塵和細菌,也阻擋了呼吸。
Super是帶著南洋音的英語:超級晶圓。所有機台都要爲它讓道,耽誤它一分鍾進機台,整月工資都不夠賠它一小塊。
429,一個代號,是隱姓埋名的女工,是站在新加坡河岸的姑娘,是十年前的周子湘,和像她一樣的萬千海外打工者。
如今再想起,周子湘只覺得,時過境遷,漫長光陰沒讓那些東西彌散掉,“他們就在我身邊,我的腦子裏,我的心裏,從未消失。”他們,散落在《慢船去香港》的紙頁上,在周子湘的這本中短篇小說集裏呼吸生長。生活的根紮進故事,虛構的不虛了,五年海外打工經曆的所有記憶與情感,在周子湘筆下淌成了三十萬沉靜的文字。
“中國在海外務工的兄弟姐妹生存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他們不被人發覺,我想將他們的心靈故事寫出來。”
截止2017年12月,中國累計出境務工人員已超過850萬人,僅是合法渠道出境人員,通過蛇頭、黑中介等方式出境謀生的“黑勞工”並不算在其中。一個龐大群體,沉默的,隱形的。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散落著遠離故土的打工者,周子湘也在其中。
“二十出頭吧,打工妹,我是其中一員。”
01 船上船下
4萬噸重量,12層甲板,600余間客房,麗星郵輪雙魚星號從香港出發,在公海繞上幾圈,周子湘的一天過去了。每日要接待郵輪上大量觀光客就餐,餐廳裏強壯的印尼小夥子,一手叉腰,一手扶著肩上的托盤,兩條長腿矯健如飛。邊走路邊和香港客人聊天,印尼味的英語裏夾雜幾句粵語。
離開中國去海外打工前,香港郵輪上的餐廳是周子湘的工作地之一。來自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的各國打工者,填滿了行政管理、酒店前台、俱樂部發牌員等等不同崗位。
餐廳裏內地來的其他打工女孩,有人很快學會了粵語,周子湘很佩服,自己的語言能力實在有限,同餐廳的上海女孩用粵語爲遊客推銷紅酒,她只能站在一旁幹看。這段經曆,後來被她寫進中篇小說《天涯廚王》,發表于《人民文學》。
“每天早晚夜三班倒,沒有休息,除非你生病。九、十月份台風季休船時候,能放上幾天假,就是這樣子。”
待過幾艘郵輪,航線遠至越南、泰國,海水顔色不同,浪花翻湧的形狀不同,透過船艙玻璃,周子湘看到的一小塊被切割成四四方方的海卻沒什麽新鮮,她每天面對最久,也是唯一的風景。在陝西西安出生成長的姑娘,第一次那麽想念家鄉古舊的城牆。
船上很多來自內地的打工妹,帶著夢想,也帶著現實生活中的遭際與碰撞,在異地他鄉生存。周子湘代表作之一、短篇小說《慢船去香港》中的主人公茉莉,原型是郵輪上的姐妹,在餐廳端盤子的姑娘想方設法要坐在行政秘書的辦公室裏,重溫以前在家鄉的舒適與體面。輿論對一個女人爲了達成目的的無端想象總帶有幾分不堪,然而當一個掙紮在社會底層的女性被欲望裹挾前行,也許終究逃不過隕落的悲劇命運。
“我想回家,我最怕這裏的夜晚和大海了,永遠望不到頭,不知道前面是什麽,不知道我自己是什麽。”
——《慢船去香港》
這篇小說最早刊發在《民族文學》,2018年被《小說選刊》轉載並獲得第九屆“茅台杯”《小說選刊》短篇小說獎,同年被翻譯成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朝鮮文五種文字,發表于《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
“我一直在堅持投稿,邊學習邊修改,才慢慢走出來。” 結束海外打工生活後,周子湘決定成爲一個真正的作家——從打工故事寫起。第一本小說集出版,名字就叫《慢船去香港》。
2016年,陝西省實施“陝西百名優秀中青年作家藝術家資助計劃”,作爲導師之一,作家賈平凹選擇了周子湘——
“敘事是容易的,但在敘述中要把故事人物的靈魂寫出來,這是一件非常難的事。周子湘走的是寫實的路子,她有很強的寫實功力。無論在人物塑造、性格刻畫、故事架構、立意拓展等方面,她都敢于硬碰硬,而不繞著走。”
怎麽能不寫實呢?他鄉,是刺進打工者內心深處的一根芒刺。那些痛感和質感,像藤蔓,和周子湘的生命緊緊糾纏在一起。寫作,是安撫這根刺的療愈之途。
很多人說,從這個“80後”作家的小說裏讀出了生于六七十年代人的味道,純正,堅韌。“和年齡關系不大,畢業後十幾年我在很多地方,從事了很多工作,接觸過各式人群。”周子湘說,生活經驗和社會經曆讓自己不同于書齋式作家,“我沒辦法單靠想象或某種精神性的東西寫作,必須要有真實做底子,哪怕它很堅硬,會紮疼你。”
面對生活,周子湘不是幻想主義者,也不是浪漫主義者。她的文字和她的人一樣,腳踏實地,幹脆利落。人物塑造和內心世界的刻畫,讓人讀出穩准狠。
“小說到底寫的是人性,人性是什麽?是一個人不願展示給外界的痛與欲望,是隱匿于內心的幽微情感和精神活動。寫人,有血有肉,豐滿立體,讀起來才能活。”
小說《女人花》中,花店老板綠月和客戶沈子健最終沒有在一起。讀時我猜想,二人的前期鋪墊會不會引出後續的一段感情?整篇小說是不是以綠月的感情線爲主?
做過花卉生意的周子湘笑,“他倆一個是欠錢的,一個是要錢的,怎麽可能在一起?那是浪漫愛情故事裏才有的橋段。”
家具廠老板沈子健,表面風光,實際公司已經虧損,不想還錢,因爲拿去還賬就沒法維持公司運營。他還得維護面子,不顯得掉價,不能直接說自己沒錢了,只有拖著。綠月,一個單身女人,靠賣花爲生,先得活下去,再考慮談戀愛,考慮跟誰喝紅酒喝咖啡。這並非虛構,很多現實的例子遠比這個殘酷。“按你說的,照著開頭倆人互有好感惺惺相惜發展,曆經磨難最後走到一起,生活規律來說根本不可能。”
“什麽是生活規律?”
“處在實際情況下,人物的想法、選擇、行動,他會怎麽做。好比這篇小說,它的規律就是商業競爭,在商言商,利益永遠是第一位。你讓他倆談戀愛,就不符合生活規律。”
當我們在衣食無憂的環境中思考人生哲學時,現實讓更多人體驗著生存的鋒利。對他們來說,活下去,比怎麽活更迫切。
《慢船去香港》獻給曾經與周子湘一起同甘共苦的打工姐妹。底層打工者的渴望與理想,有掙紮,亦有執守。故鄉回不去,遠方亦是無法到達的彼岸,“我想記錄和挖掘她們靈魂深處的訴求,觸摸她們的脈搏跳動。”
“你的打工姐妹看到這本書了嗎?”
“看到了,只要回國的就都看到了,還讓我寄書。”
“她們看完什麽感覺?”
“她們不懂文學上的事兒,但是她們說很真實。對我來說這是最高的贊譽。”
上下鋪的四人宿舍,周子湘在郵輪上兩年的棲息地。“你想不到,女工的宿舍布置得精致而美麗”,周子湘回憶,“房間整潔幹淨,她們愛美,清貧也能安排好生活。很多從農村來的女孩子,你以爲可能邋遢,但恰恰不是,特別心靈手巧。”
包容和無視只在一線之間,很多生命得已展開的前提,是他們足夠微小,不被看見。“不是說我們是作家(情感)就豐富,別人不是作家就不豐富。無非是她們不會寫,沒有形式和渠道表達出來。”
小說裏很多人物原型,是周子湘異地異國打工時的朋友,寫下來,成了《天涯廚王》《惘然記》《新加坡河的女兒》《愛哭的珍妮》《她的世界正下雪》《別了,蘇菲》…… 人們看到的零星報道中只有這個群體的簡單面目,他們鮮活的世界,比新聞凜冽而真實。艱辛打拼,頑強生活,精神和肉體的沉痛與撕裂,同事、朋友、伴侶、老鄉,相互傾軋又相互砥砺;出走的打工者歸來,面對生疏的家鄉故土,在漂泊的身份中重新觀照自我。這是周子湘,和一代青年面向世界的探索意識。
現實中主人公茉莉的原型,沒有像小說中魂歸大海,最後選擇回國。彼時的打工姐妹大多留在了異地異國,或一人奮鬥,或遠嫁他鄉,回國的只有零星幾個。有的家裏給訂了婚,有的聯系好了國內新工作,有的實在受不了,覺著太苦太累。
“沒想過也在外面闖一番嗎?”我問。
“沒有,”周子湘回答得很果斷。“出去就是幫家裏,爲掙錢。”
“那個時候你在做什麽?”
“剛大學畢業,學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我以爲終于能開始好好寫作了。”
02 驚心動魄的“80”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人文精神重燃,各種思潮湧入。周子湘回憶,那才真的是全民閱讀。“窗戶和門都敞開,開放和熱烈的年代,中西碰撞,火花四濺。”
小時候家裏書架上放著朦胧詩選和《浮士德》,是周子湘當工人的親戚買的。“當時的標配,大家都買,工廠裏很多人帶著書,看懂看不懂都看。”搶著買書、讀書成爲潮流的八十年代,空氣裏都能嗅出知識的味道。生于1980年,10歲的周子湘和顧城、舒婷、北島、歌德相伴。
上初中後,周子湘自己攢錢買了《中國現代小說辭典》,讀到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海派,現代派,先鋒派……,厚厚一本,到現在還留著。大量文學專業名詞她分不大清楚,但能通過文字描述感受到區別。
《芙蓉鎮》《風筝飄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遊園驚夢》《金鎖記》《十八歲出門遠行》——周子湘邊讀邊模仿著寫,看不太懂,但是覺得有意思,還想看。“就是喜歡讀書,喜歡寫作,常把身邊發生的事模仿書裏寫成故事。”語文老師整天拿周子湘的作文當範文讀,推薦她參加全國作文大賽,獲了優秀獎。“我記得特清楚,全校就三個人獲獎,我寫的是北戴河。”
老師說周子湘有天賦,以後可以創作,搞文學。她不懂天賦是什麽意思,卻記住了後半句。
“80後”是幸運的,這代人年輕時趕上了改革開放後文學的蓬勃生長,在觀念形成和語言習得上都正當其時。1998年,上海《萌芽》雜志聯合多所高校舉辦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以“新思維、新表達、真體驗”爲宗旨,號召作者用真情實感,寫出具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文章,由此成爲一代“80後”寫作者的敲門磚。
韓寒,是談到“80後”無法略過的作家之一。周子湘讀他的小說,語言表面戲谑、諷刺,但內部有對社會的思考和批判。“他常常關注一些細節,引人發笑的背後透出思辨性。”
在周子湘的青春時期,慶山(安妮寶貝)留下的影子比韓寒更深。海外打工期間,周子湘常帶在身邊的書裏,總有一本慶山的小說。直到現在,周子湘都在關注慶山的創作,“她的小說具有極致的探索性、獨具一格的語言和對人性黑洞的深刻洞察力。她對現代都市人群的敏銳觀察、不斷探索自身精神成長的特點,在小說《蓮花》中展現最全面。”
再後來,衛慧的《上海寶貝》出來了。周子湘的朋友從地攤上買來了這本書,扔在一邊,她看見拿回了家。生理欲望、同性感情、迷惘與沉淪……對于當時成長中的文學青年來說,算是徹底“炸”了一次。“沖擊,真是沖擊……它跟之前的文學作品都不一樣,之前都是比較正統的路子。”周子湘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同文學觀念相互沖撞、驚心動魄的文學時代。
在這樣的文學沃野上奔跑的“80後”作家,自由叛逆的精神,無畏無懼的青春姿態,讓大衆視野聚焦于他們極具個人氣質和自我經驗的文字,校園文學、青春文學一度成爲“80後”寫作的標簽,以至個性化敘事發生了過度泛濫的危機——“格局狹小、自我封閉、精神單薄”,久而久之,這波初登文學舞台的青年作家受到诟病。
周子湘沒有時間像大多“80後”作家那樣,在那個年紀沉溺于自我的精神世界,她真正的文學理想和寫作啓蒙,在海外打工的日子裏生根發芽。
03 我的疼痛,不是異國他鄉
香港郵輪工作期滿後,周子湘到新加坡電子廠當女工,更累,收入卻高一些,當時彙率大概1:5,1元新幣相當于5元人民幣。芯片檢測員,從晚上七點到早上七點,十二個小時的夜班,周子湘幹了近三年。每天早上別人醒過來,她剛下班,倒床上沾枕頭就睡著。
周子湘經常看著宿舍門外被晨光拉長的自己的影子,對著它歎氣:只有你與我相伴了。異國漂泊,文學成了唯一的慰藉。新加坡圖書館的圖書證上,紅色印記蓋滿了每一頁,周子湘是借閱率最高的讀者,圖書館管理員認爲她信譽良好,寬限了借閱期限。
“說起來,我真正開始動筆,是在新加坡,在更苦更累的這個電子廠。”
車間裏,穿著厚厚的防塵服,戴著防塵手套、防塵口罩。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只留兩只眼睛,在電腦上邊看屏幕邊偷偷敲鍵盤。不是寫工作報表,是寫小說,所以只能膽戰心驚。一旦暴露,就有被開除的風險。
一邊構思人物情節,一邊防著組長進車間巡查,周子湘小心翼翼,還是被抓住了,組長說她上班不務正業,再有下次就嚴肅處理。後來有一天,組長在《聯合早報》上發現了周子湘發表的小說,對她說,你寫的小說我看了,不錯。沒想到你還真會寫。只要不耽誤工作,你寫吧,我不抓你。在這之前,同爲女工的姐妹因爲被查到電腦有遊戲記錄而被遣返回國。
“可是我很失望”,周子湘說,“因爲不是正經的文學刊物。”
1997年,原創文學網站“榕樹下”橫空出世,風靡于抱有寫作理想的文學青年群體。通過網絡,許多人圓了一次寫作夢。甯財神、蔡駿、郭敬明、饒雪漫……這些人都曾經在榕樹下發文,有些人因此成名,徹底改寫了自己的命運。有網友說:這裏有比文學更重要的東西,我不再僅僅爲文字寫作,我爲生活寫作,寫出自己心裏的感受。
除了工作車間,“榕樹下”是周子湘待得最多的地方。省吃儉用攢錢,花兩千新幣(約合一萬元人民幣)買了台電腦,“那時的作品還很稚嫩,都是練筆,談不上好。反正一有時間就寫。”
周子湘不是驕矜的人,80年代在工人家庭成長起來,有小十多歲的弟弟要照顧,家裏大小事她都參與拿主意,是個扛擔子的主心骨。我一直不明白,既然體力上的苦累都不是問題,爲什麽她反複說海外打工最難忍受異鄉的孤獨。
“你不知道,我太想寫作了,但是沒人支持,海外打工(寫作與發表)太難了,” 周子湘說,“母親強烈反對,覺得搞文學沒用,沒前途,能當飯吃嗎?” 寫作這條路上,周子湘孤軍奮戰。
家庭不理解,做出的努力與成績都是否定。身邊沒有朋友對文學有興趣,能同她分享。在新加坡電子廠,上班不能遲到,周子湘每次早去車間1個小時,休息室人少,能多些安靜看書的時間。其他打工姐妹帶著零食瓜子,邊聊天邊看她,覺著她像個傻子。沒人關心周子湘發表了什麽,多一張報紙包東西比上面登出的信息更能吸引她們。
“喜歡寫作的人更注重精神層面的交流。海外打工,大家都孤獨,但不是我這種孤獨。她們的孤獨是沒有男朋友、不能出去玩的孤獨。”
唯一能交流文學的對象,是網上的一個老師。回國後,周子湘報名參加“新教育網絡師範學院”的線上授課,其中一門教授哲學和古典詩詞,她常把自己寫的小說發給那門課的講師看。“他告訴我自己的閱讀感受和寫作建議,給了我很大幫助。”
周子湘在小說中寫了很多女性,她筆下的女性總是疼痛的。像一篇評論所寫:她們的疼痛不是青春的小打小鬧,不是物欲餍足之後的敏感空虛,而是來自生活磨砺與重擊的切膚之痛。她們投入一段段感情,這些感情棲身于陰影中,投射到現實生活,大抵會被演繹成以女人爲原罪的狗血八卦。作爲女作家,周子湘貢獻了與男性主導的社會所不同的視角,她將女性置于中心,細細描摹她們的心路,使她們的感受傳遞出溫度。
提筆之前,周子湘並不確切清楚自己的角色。“直到打算寫她們,我才發現,我就是女工,身在其中,和她們一樣。我不悲憫著俯瞰,也不仰視,爲她們歌功頌德,我是這個群體的一員,她們是我,我也是她們。”
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寄回家裏,家裏人從銀行取出的,是厚厚一沓人民幣。紅色的紙,像女工們的血液,河流一樣流回自己的家鄉。
——《新加坡河的女兒》
這篇《新加坡河的女兒》,寫了一個女孩在異國的打工生活,還有注定無疾而終的愛情。周子湘告訴我,這篇小說爲自己而寫。她讀過打工文學,讀過鄭小瓊的詩歌,“她的詩寫得很好,打工那種痛,我能深切地感悟到。”
“打工群體的關鍵詞是痛嗎?”
“不一定,我不敢妄議。有的人不一定覺得痛,他可能覺得是別的東西。就我個人來說,是有一種痛感的。”
痛感是什麽?周子湘最遺憾的是,如果有比較好的環境能接觸到文學的話,會對自己的寫作更有幫助。
“你對文學非常熱愛,也非常想寫作,但是你沒有渠道。沒有渠道是什麽意思?信息是封閉的,想學你都不知道跟誰學,沒地方弄明白文學是怎麽回事,怎麽能寫好。正式發表渠道也沒有,除了網上隨便寫一寫,就是看個郵箱瞎投。”
04 從淺灘到江河
如果“80後”的群體個性被定義爲自我與張揚,在周子湘身上,這份特質變成了內斂式的隱忍和堅持。
二十出頭的年紀,只身去海外打工,哪個女孩會真心願意呢?“挺委屈的,犧牲了我的青春和理想,從學校畢業,我想好好寫作。但是沒辦法,家裏那個情況,你張不開嘴。”
妥協和退讓,在生活裏有,在文學裏沒有。“委屈化成了動力吧,我更要追逐文學理想”,周子湘說,“現在我家裏都不知道我在寫什麽,他們也不看。”
豐富的生活經驗塑造了周子湘紮實厚重的文學風格,寫小說,她不困難。“一氣呵成,我寫小說很順。不是嘩嘩寫出來不停筆的順,是思路順,清晰,不卡殼。好像這個寫完了,下個就在那等著我。”
周子湘覺得,寫小說很快樂。
“沒有過痛苦的時候嗎?”
“有啊,生活當中有痛苦,寫小說沒有。”
“提筆回望海外打工的日子,不會有痛苦嗎?”
“那還是生活本身的經曆。我寫小說是享受的狀態,真的,很快樂。我生活快樂的來源,很大一部分都是寫小說在支撐。”
周子湘將寫作比喻爲談戀愛,你欣賞對方,對方也喜歡你,兩人在一起志趣相投,鬧別扭也能很快和好。“你們彼此有渴望,不就是在談戀愛嗎?”
海外打工是周子湘的一段經曆,有一天寫盡了,她的寫作該往何處去?對此周子湘並不擔心。“很多人會問脫離打工生活你寫什麽呢?對我來說不成問題,因爲我有捕捉生活的能力。”
寫《納棺人》,周子湘走近爲去世親戚進行殡葬美容的化妝師,描繪了一個邊緣群體的內心世界;寫《女友夏蘭蘭》,周子湘自己到即將拆遷的城中村,和村民們唠嗑聊天,有了在男友安排下與老光棍假結婚的進城女孩的故事;寫《駱玉珠傳奇》,周子湘采訪了到雲南執行任務的緝毒警察……
寫小說一定要有設身處地的現場感嗎?我有些疑惑。當某個人物或事件足夠吸引你,占有素材的基礎上進行虛構似乎是慣常手法。
“不,我絕對不這樣寫,”周子湘很肯定,“人物是靈魂,人物不能造。很多人物爲什麽扁平化,虛構太多了,都靠猜。要麽失真,要麽單薄。對我來講小說第一點不是抓故事,不是抓情節,是抓人。”
以前,周子湘看到什麽就寫什麽,寫別人,寫自己。現在她更深入地關注和思考整個社會。
新作中篇科幻小說《月球異鄉人》,發表在《小說月報·原創版》。還是打工青年的故事——周子湘想象了60年之後的地球與月球,主人公傑克爲了移民月球,要完成秦始皇兵馬俑DNA複制的任務,小說在科幻想象力的外殼下探索人物內心世界。
最初她對科幻並不感興趣,機器怎麽能和人相提並論?直到看了一部紀錄片《宇宙大爆炸》,“吸引我的是,它裏面也有人文性的東西。並不只是冷冰冰的科技。”
周子湘常說起張承志的小說《北方的河》,現代知識青年探索人生的精神曆程。一邊是黃河、湟水、永定河、額爾齊斯河和黑龍江,一邊是主人公追隨它們的青春足迹。她很喜歡這篇小說,爲自己整個青年時期帶來深遠影響。“和他的許多小說一樣,這篇小說呈現出象征意蘊濃厚的詩化風格。是小說,也是一首生命長詩。”
一晃,“80後”年近不惑。人到中年,周子湘的腦海中無數次出現那條“北方的河”——像生命進入河流的壯闊與深流之處。
“以前我是淺灘裏的小魚蝦,蹦呀蹦。現在回看,自己有很多無知的行爲,包括對寫作的無知,都會有。你獲得越多的時候,越會感到自己的無知。”
“現在呢?”
“我不是那種對生活要求很高的人。我唯一的要求,有個安靜的地方寫小說就行。”
後來,周子湘特地寫了一段話,囑我一定要呈現在文中——“這是我最真實真誠的想法”:
假如你站在陝西奔騰厚重的黃河岸邊,就會明白,個人在整個時代中的渺小。年齡讓你經曆了事情,已經有自己的判斷力,知道輕浮的生命應該過濾掉,留下沉甸甸的生命質量。漢江讓我思考,個體的生命,如何最終獲得生活的真正意義。渭河使我懂得,無論怎樣奔騰的河水,最終都會變得平靜而深流。
本期記者
1
2
3
微信編輯 | 鄧潔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