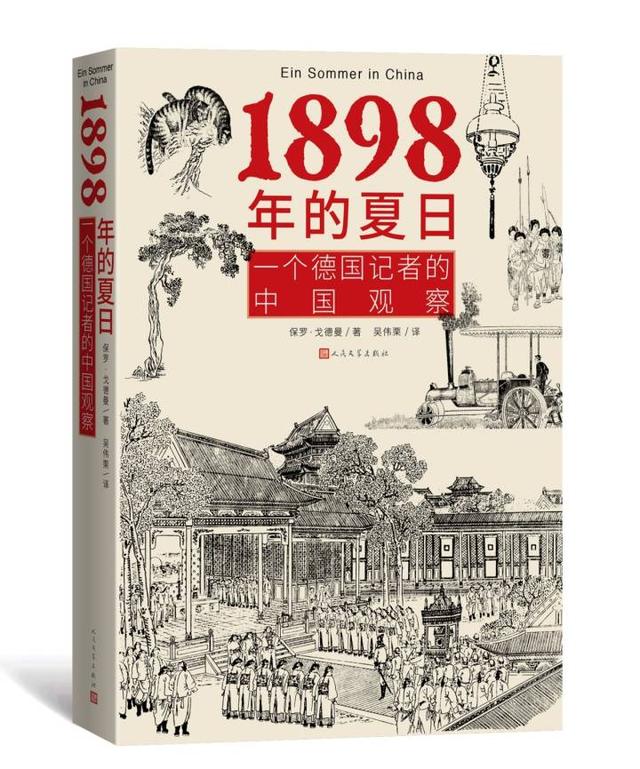189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年份。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與德國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4月10日,德國記者保羅·戈德曼受《法蘭克福報》指派,從意大利熱亞那港出發,對中國進行采訪。
戈德曼乘坐的德國“普魯士號”遠航機械船出發後,穿越地中海,經由埃及、蘇伊士運河、亞丁灣,遠航至歐洲式東方新城——新加坡。
而後,他從香港登陸,經廣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國腹地,進行詳盡考察。途中,他先後采訪了時任廣東總督秘書兼厘金局長王存善、上海道台蔡鈞。從上海又沿長江乘船而下,在鎮江、漢口、武昌等地停留。
戈德曼此行所見到的中國近代史人物頗多。在煙台,他與原清政府駐歐洲外交官陳季同相遇。這是一位曾在歐洲大力推廣中國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在天津,他采訪了清政府的陸軍總領、直隸總督榮祿。在北京,他拜訪了剛剛下野的李鴻章。
因爲這趟中國之行,戈德曼寫下了《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
《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
[德]保羅·戈德曼 著 吳偉栗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1年1月版
戈德曼,1865年1月31日生于德國布雷斯勞市(現爲波蘭弗羅茨瓦夫市),1935年9月25日在維也納去世,奧地利及德國新聞工作者、公關人員、旅行作家、戲劇評論家、翻譯。1892年至1902年,他擔任《法蘭克福報》記者,于1898年期間在中國進行遊曆和采訪。
他記下的目睹所見,對于我們了解19世紀末沿途城市的風光風貌以及中國社會的面貌,有一定的幫助。尤爲可貴的是,在書中,戈德曼對他所接觸到的中國人民的勤勞、勇敢、智慧給予了高度肯定。他當時曾預言:上海會以數十年的努力,成爲東方一座偉大的城市。這個預言後來成爲了現實。
在書中,他也以記者的客觀,披露了最初中國鐵路規劃過程中,歐洲列強資本競爭的內幕,以及中國經濟與歐洲經濟相融相斥的情況和列強之間的利益紛爭。通過與清政府不同級別官員的互動,他記錄下清末官員對改革和與西方合作的不同主張,以及民間對這種主張的不同反應。
保羅·戈德曼在中國的這段采訪記錄,觀察細微,文筆優美,對中國民間和中國老百姓的認可度也很高。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很難能可貴。時隔百年,這本書能夠被發現、翻譯、出版,也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保羅·戈德曼作爲德國記者,對中國是持友好態度的,在反對納粹等重大曆史問題上,他的立場和氣節也是令人贊賞的,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這本書中,他是站在德國的視角看中國的,有時候表達就難免會沾染一些殖民的色彩,某些時刻甚至會流露出殖民者的口吻。這顯然是一種曆史局限,也是他的偏見,所以我們中國讀者在肯定這本書的曆史史料價值的同時,還需要對殖民化表達提高警惕,需要持批判的立場去閱讀與理解相關內容。
讀史以明志。放眼今天,我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多災多難的古老中國終于擺脫了受制于人的厄運,迎來了嶄新而令人振奮的局面。
很多大家已是這本書最早的讀者。在著名作家唐浩明的眼中,中國與世界,處在一個命運共同體中,我們需要曆史的溝通、文化的溝通,需要消除偏見,需要相互尊重。這也是這樣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種價值和意義所在。
這既是一本曆史書,也是一本文學書,有清晰的社會風貌,也有鮮活的曆史場景。通過外國記者的眼睛,普通讀者可以看到1898年的風情與故事,專業讀者則可以驗證某些史料和細節的真實。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忠文則這樣認爲:一個德國記者對清末官場和社會的觀察,總不免帶有一些西方人的偏見,但換個角度看,他的觀察和分析也多有獨到之處,常常是中國人自己容易忽略和熟視無睹的地方。應該承認,保羅·戈德曼的遊曆和采訪,展示了國人未曾想到的1898年前後中國社會的一些原始樣態。
【後記】
一部奇書的旅程
2011年的初秋,我第一次前往亞得裏亞海岸。在地圖上看,從維也納出發,穿過斯洛文尼亞,是到達亞得裏亞海邊城市的裏雅斯特的最近路線。在夜幕低垂的傍晚時分,我進入斯洛文尼亞邊境,斯國海關警察把我攔了下來。盡管斯洛文尼亞是申根協定國,按協約應當撤消邊境檢查站,但他們依然要求檢查我的證件。我遞交了我的全部合法證件,斯國海關警察看後說,證件沒有任何問題,但我沒有買高速公路票,要繳納罰款160歐元。事實上,在進入斯洛文尼亞之前,我一直都在留意公路兩邊的商店、加油站。我已經預想到進入這個國家是要購買高速公路票的,但是,一路上並沒有看到任何營業場所。按理這個時候再買也是可以的,可是兩個警察不由分說就要罰款,而且,態度十分蠻橫,直接扣下我的護照與駕照。看來不交罰款人走不了了,這個從前南斯拉夫分離出來的國家,經濟上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警察也是見錢眼紅了。對我來說,時間可比金錢更重要,只好交了160歐元的買路錢,繼續這趟亞得裏亞海的旅程。
我原打算在這個國家的首都停留一兩天,了解一下他們的曆史、文化與城市風貌,但經曆了與斯國海關警察不愉快的糾葛,我對這個小國家興趣全無。驅車穿過斯洛文尼亞進入意大利,大約有兩百多公裏的路,汽車疾馳不到三個小時,我就來到了亞得裏亞海邊的意大利城市——的裏亞斯特市。
已經是午夜,汽車駛出高速路沿著盤山公路向下,遠處是一片燈光,看來這座城市的規模很大,遠遠超出我之前的想象。駛入市區,馬路開始由寬變窄,柏油路變成了石頭路面。古老的街道、老舊的房屋,一切都是一座有曆史的城市應該有的樣子。
我在歐洲學習、生活多年,每到一座城市我都喜歡去看古董店和郵票店。徒步古老的街道尋覓曆史痕迹,是我在外旅行的最大愛好。這座城市依山而建,環抱亞得裏亞海岸。我住的威斯汀酒店位于城市的山頂,從高處沿著狹窄的石頭街道走下來,山腳下就是這個城市的中心。這一天是星期六,恰逢城市的周末跳蚤市場,我逛了一圈並沒有什麽收獲。于是,我沿著古老的街道漫步前行,來到一家古董店前,這麽偏遠的地方,應該會有什麽寶貝吧?舊貨琳琅滿目,然而我在裏面足足轉了近半個小時,也沒找到什麽特別的東西。
當我打算離開的時候,禮貌性地問了一下店老板:“您這裏有來自亞洲的東西嗎?”老板看了看我,想了一下,然後,用德語回答道:“我們店裏有本一百多年前的書,裏面寫的是中國的故事,您有興趣嗎?”說著他從身後書架上找出兩本書,小心翼翼地遞給我。我看了一眼書的封皮:Ein Sommer in China,意思是:一個夏天在中國。這是一套上下兩冊的舊書,泛黃的封面與僵硬的紙張略有破損。我小心翼翼地打開來看,竟然全是古典字體的德文。我沒有學過古典字體德文,一時間看起來有些吃力,也看不出什麽門道和價值來,但我想,既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出版物,就當是古董買了也不錯。
只經過一個回合的討價就成交了!這店鋪裏陳列的舊書不計其數,我估計店老板自己都沒有讀過這本書。他或許也不會想到,這本書對我們中國人而言意義重大,它給了我們一幅塵封百年的中國曆史畫卷。
一周以後,我回到了法蘭克福的辦公室,立即把書拿給我的朋友烏利先生,請他認真看看,然後把裏面的內容大致整理一下,告訴我。烏利先生是德國的經濟律師,父親曾經是德國政府的高級官員。他接受過德國和瑞士兩國的大學教育,如今年近七十歲,知識淵博,他是看得懂古典體的。烏利先生用幾天時間把書讀了一遍,然後,興致勃勃地來到公司,坐下來給我詳細介紹這本書的內容。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時任《法蘭克福時報》的記者保羅·戈德曼先生,受報社指派,于1898年前往中國,專程對大清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司法、出版、宗教等進行考察。他四月從意大利北部熱亞那港口出發,乘坐德國普魯士號遠航機械船,由地中海經埃及薩德港、蘇伊士運河、紅海-亞丁灣,遠航至東方歐洲城新加坡。他從香港登陸中國,經廣州、上海深入中國腹地。1898年是中國的戊戌年,整個夏天,他先後拜會了廣東總督秘書兼厘金局局長、上海市市長、兩個通商城市的地方要員。他沿長江乘船而下,在漢口、武昌、鎮江等城市都有所停留,對中國鐵路建設中列強資本競爭的內幕有所了解。他在武昌考察了德國軍官訓練營,結識了湖廣總督張之洞,記錄了德國工程師與軍事教官在中國工作的全過程。然後,他又前往膠州灣青島、威海、芝罘(煙台),探訪剛剛納入德國租界的膠州。接著,他從煙台繼續北上到達天津,訪問、參觀了天津武備學堂,拜訪了陸軍總領、直隸總督榮祿。此時,北京發生了戊戌變法,他被困在天津多日。待北京戒嚴解除,他進入北京城采訪,拜訪了剛剛下野的李鴻章……
聽了烏利先生的介紹,我頓感這本書的重要性。外國人寫中國的書有兩本,一本是馬可·波羅的《中國遊記》,一本是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而這本《一個夏天在中國》時間正好介于這兩本書之間。如果我沒有判斷錯的話,這應當是第三本曆史價值重大的、外國人探訪中國的書。德國記者對1898年中國社會的描述,無論是什麽樣,應該都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尤其是他曾在那個特殊的年份,與清政府高級官員對話,一定能夠爲已有的曆史敘述提供一些參照,說不定能提供我們更多關于戊戌變法,關于中華帝國在艱難危局中轉型的重要曆史細節。我預感,這一定是一本記錄中國曆史的好書!
我馬上請烏利先生著手調查這本書的作者。首先,我們從記者任職的《法蘭克福時報》入手,由烏利先生代表公司發了問詢函,遺憾的是,今天的《法蘭克福彙報》與之前的《法蘭克福時報》之間,並沒有任何法律上的繼承關系。曆經兩次世界大戰,他們亦無法找到關于這本書的更多信息。但是,他們告訴我,因爲作者反對納粹,這本書曾經被列爲禁書,納粹時期要求全部銷毀。我們在報社的建議下,馬上與德國版權管理機構聯系,他們很快給了我們書面答複:該書已經過了七十年解禁期,我們可以申請獲得再版的權利。由于原書是古典字體德語,普通人閱讀困難,于是,我委托烏利先生用了一年時間,將古典德文逐字轉換成現代德文,2014年在德語國家出版。爲完成這套書的整理工作,我的朋友烏利先生用眼過度,患上了嚴重眼疾,待完成文字轉換的時候,他的左眼幾近失明。2017年12月21日,烏利先生因骨癌在法蘭克福去世。他是我親密的朋友,也是很多中國人的好朋友,在德國法蘭克福、巴登洪堡,有許許多多的中國人都曾獲得過他的法律援助。他愛中國,樂于幫助中國人,遺憾的是,他沒有來過中國。我答應要帶他一起來中國看看,我們說好了,晚年他在我身邊養老……這成了我一輩子的疼。
自2015年開始,我就著手這本書的中文翻譯工作。由于作者的宗主國橫跨普魯士、奧匈帝國以及魏瑪共和國向第三帝國的演變進程中,他的語言南北混雜,我幾乎找遍了中國的德語翻譯大家,都無人肯接受這本書的翻譯工作。我也深知這套書的翻譯難度很大,但是,我也深知,對研究中國曆史的價值而言,這樣富有現場感的記錄有多麽難得!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外國記者的采訪與描述,從“他者”的視角,換一個眼光看到清末中國社會的真實風貌。就算是“片面”的真實,也萬分寶貴。
我下決心要完成這本書的翻譯工作,沒有人願意幹,我就組織人自己幹。我和烏利先生,還有他能找到的,能夠識別古典德文的朋友和專家一起工作,2017年,中文直譯工作基本結束——深切懷念我的朋友烏利先生!
原著于1899年在德國出版發行後,1900年很快發行了第二版。作者爲了確保曆史記錄的准確,在再版時根據後來的事態發展做了一些注解。我買到的恰恰是第二版,所以,讀者能更好地了解這本書的全貌。翻譯過程中,查閱曆史資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爲了便于今天的讀者理解,我也對一些人物與事件做了注釋,這些注釋在這本書中都以腳注的方式呈現出來了。(節選自“後記”,標題爲編者加)
【搶先讀】
拜訪李鴻章(節選)
步行走過大門,穿過用大片長方形石板鋪成的幹淨園子,踏上石板階梯,李鴻章老先生已經站在門口迎接我們了。門幾乎跟他的身高一樣高,讓他看起來比實際上要高大一些。一個高高在上的老人樣貌,令人肅生敬意。
他穿著簡單的居家服飾,一件紅棕色錦緞長袍,一件藍色絲質外衣,外衣上的紐扣沒有扣上,脖子領口附近還有些磨損。曬得黝黑的臉孔沒有什麽變化,就像他在歐洲時人們所認識的那樣。他鼻子上挂著一副眼鏡,不是一般中國文人用的那類怪異樣式的(誇張、奇異、不尋常的),而是金色細框的歐式眼鏡。鏡片後面是一對精明的、細小而靈活的眼睛,有時也會目露凶光。他說話的聲量很小,聽起來並不會讓人感到不舒服,倒像是因爲上了年紀聲音有點兒糊在一起(法國人稱此爲口齒不清)。可能的話他盡量寡言少語,起碼一開始是這樣。
之後他的話變得稍微多了起來,但依舊掌控著話語的內容,並帶著狡黠的目光。有時候他會在說話時突然冒出短暫的笑聲,此時,他嘴巴裏的黃牙便清晰可見,那是牢固、修長的犬齒。當他這麽笑的時候,臉上便會閃過一絲嘲諷的神情,但隨即又恢複嚴肅與呆板。這位老先生的頭上已經毛發不剩,頭皮下是骨骼強健的圓形頭骨。
李鴻章手上拿著一根有著象牙握把的黑色木質拐杖。由于他喜歡把自己當成是中國的俾斯麥(這是某些歐洲馬屁精一直對他說的奉承話,說久了他自己也就相信了),所以弄來一支鐵血宰相晚年攜帶的拐杖複制品也不無可能李鴻章的遺物中,有一根鑲滿鑽石的手杖,據說是世界上最貴的手杖,原是美國總統格蘭特的。一八七七年格蘭特卸任,偕妻子朱莉娅作環球旅行。一八七九年四月抵達中國,成爲美國總統中第一位到達中國的人。李鴻章在天津直隸總督行館設盛宴款待格蘭特夫婦,對格蘭特的精美手杖愛不釋手。格蘭特于是說:中堂既愛此杖,我本當奉贈。只是此杖是我卸任時,國會代表全國紳商所贈,我不便私下贈人。待我回國後將此事公布,如果衆人同意,我即當寄贈給您,以全中堂欣賞雅意。一八九六年李鴻章訪問美國,格蘭特遺孀不忘當年承諾,將該手杖贈予李鴻章。自此李鴻章與此手杖形影不離,直至去世當作遺物陪葬。。
我們現在所在的房間是一間有著石頭地板的前廳,屋裏幾乎沒有什麽家具,只在角落旁放著一張歐洲皮椅,皮椅前方另有幾把中式椅子,後面是房子的內部,被一面漆著綠色的木板隔著。當沒有訪客時,板子似乎會被擺回去。李鴻章同我們握手,讓我介紹自己的名字,並看我們給他的拜訪函。他嘗試著讀我的名字。之後他便坐到皮椅上,並請我們在椅子上入座。他伸著兩只腳,穿的是柔軟的中國布鞋,腿上是白色麻布制成的裹腿。之後他向我們介紹他的孫子,年僅十三歲、想法十分開明的中國青年。德國的反猶主義者大概會把他隆起的鼻子視爲他亞洲純正血統的一種反證。這位年輕先生穿著深紫羅蘭色華麗長袍,禮貌但有點害羞地向我們伸出手握過之後,就在一張稍遠的椅子上直挺坐下,專心聽他的祖父說話。
皮椅的不遠處已經有一位賴姓仆人隨侍在側。雙方在談話時,李鴻章一會兒要他拿東一會兒要他拿西。首先他要香煙。他用一個小巧的鍍金濾嘴抽著,之後又要金屬制的水煙煙鬥,忠實的賴姓仆人得把煙管放進他嘴裏。然後是一杯茶。除了水煙之外,他也給我們提供了所有服務。李鴻章在他的皮椅上放了一只壺,像是一個被開啓的容器。他不時會把它拿到嘴前,往裏頭吐上一口,然後再放回原處。由于所有的門都是開著的,風吹得有些誇張,我們身上都穿著外衣,但還是感覺冷。“賴”在沒有被呼叫的情況下,主動拿來了一頂中國家居帽,戴到老先生光禿禿的頭上。
從試圖了解我開始,李鴻章開始和我對談。他用拐杖指著我,提出了一堆問題:爲何從德國過來?在中國多久了?拜訪過哪些地方?在膠州停留了多久?何時會回歐洲?
之後出現了空當,我便利用這個機會趕緊提問,並把談話內容帶到重點上。我說道:因爲《法蘭克福日報》正確地預料到眼前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才派我來到北京。目前我只是個異鄉客,不懂得如何去理解這場危機,如果能夠從您那裏得到對以下這個問題的答複我將感到十分幸運:“到底發生了什麽?”
李鴻章遲疑了一會兒,然後慢慢說道:“錯在年輕官員。”
“爲什麽?”
“資深、有經驗的官員,被不曾處理過國家事務的年輕一代排擠出去了。他們想從中獲得利益,直到最終不能再走下去爲止。經過這次危機,這些比較年輕的官員已經被鏟除了。”
“這次的巨變,若是能讓資深官員重新回到職位上,應該會是好事。但這樣的事情似乎沒有發生。而人們已經從中看到,目前處于艱困時期的中國還沒有給像您這樣的人職位。”
老先生興奮地點了點頭,確認這也是他的看法。但他仍舊遲疑,沒把話說得更清楚。因此我必須稍微試著催促他一下。
“就我所知,”我說道,“如果沒有一個適當人選能夠代表中國政府的話,是無法掌握目前狀況的要害的。外國使節們眼下要跟誰進行協商呢?我可以想象,他們現在正處于極大的混亂之中。”
之所以如此想象,是因爲我有我的理由。馮·達高茲先生(Herr Von Goltz)確認了我的想法,他表示,德國使團如今已不再進出總理衙門。總理衙門已經被棄置了,李鴻章也被趕出衙門了,那誰還會留在那裏呢?
“是呀,但是政府一直都在。”李鴻章回答。
“政府光在那裏是不夠的。”我回應說。
“政府必須發揮點職能。現在事情已經過頭了,中國會面對後果的。最起碼,中國的信用會遭受損害。”
李鴻章解釋說:“只要中國還能支付貸款利息,便不需要爲金融信用一事擔驚受怕。目前利息都是按時支付著。”
“與這些貸款與利息有所關聯的是過去。關鍵是未來,中國更需要信用。歐洲企業的時代現在正要開始,這需要動用歐洲資本。如果歐洲不給你們錢,中國連鐵路也不能修了。”
“那就不要修。”李鴻章沉著地說著。
在歐洲,這位先生被當作是追求現代化的先鋒,但從他口中聽到這番話,讓我感到訝異。馮·達高茲先生則提出實例加以說明,中國是如何在最近的事件中喪失信用的:比利時人不想再爲北京至漢口這條由他們負責的路線提供更多資金。德國商業聯盟也對新疆到天津的鐵路計劃感到茫然,表示想要撤回。
我再次表示:“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爲沒有一個歐洲能信任的人在中國官府裏頭坐鎮。對中國的信用來說,李鴻章先生是最好的代言人。實在無法理解,竟然不讓您繼續服務。在領導中國的官員之中,您幾乎等同于中國信用的名號,如今竟毫無作用。”
李鴻章眼睛眨也不眨地聽著這些贊揚的話,似乎可以察覺到,這些話打動了他。他深思了一會兒,然後說道:“外國人是依照過去的成就來理解我並推崇我,但如果中國人並不這麽想,我又有何可供效力的呢?”
“我不這麽認爲!”我說。
“這毫不虛假。俾斯麥首相就曾經曆過這樣的事:他贏得所有文明國家的信任,唯獨沒辦法讓他的皇帝信任他!”李鴻章說。
“那麽您又爲何失去了貴國皇帝對您的信任?”
“人們抨擊我,認爲我對外國人太過偏袒。他們稱我是賣國賊。”
當李鴻章這麽說時,臉部因怨恨而出現了一絲抖動。當他說到“賣國賊”這三個字時,爆出了一陣大笑。
……
文圖 | 人民文學出版社提供
本文爲錢江晚報原創作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複制、摘編、改寫及進行網絡傳播等一切作品版權使用行爲,否則本報將循司法途徑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
來源:錢江晚報·小時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