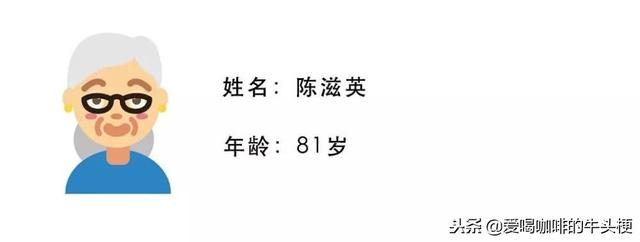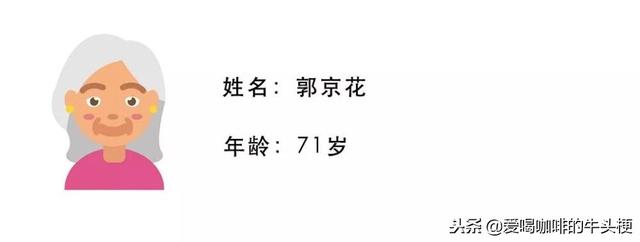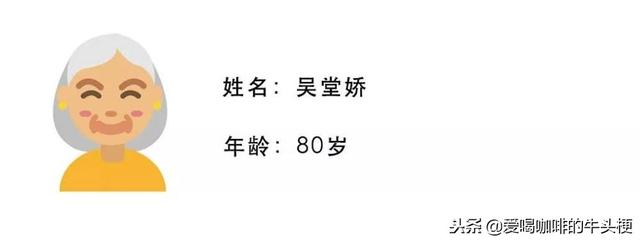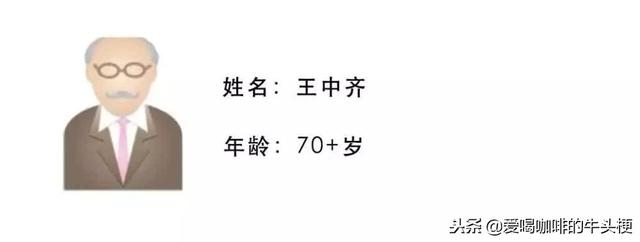81歲的陳滋英住在金融街90平米的房子裏,小區平均房價超過12萬元/平米,但空蕩蕩的房子常讓她覺得孤獨、慌張。她決定,不能自己一個人住下去了,搬進了到處都是人的養老院;
郭京花活到71歲都匆匆忙忙,終于在養老院的理發室剪了個年輕、時尚的發型,爲了讓臉上的斑淡一點,她每周做一次臉上針灸;
90年代,兩個孩子都出國發展,吳堂嬌兩夫婦決定和更多的老年人“抱團”。吳堂嬌在養老院把自己出生、上大學、工作,做成三個視頻:人生的開始、行醫的道路、家庭幸福生活。最後一段關于老年生活的,還在剪輯之中。
70多歲的王中齊每天堅持在電腦上寫文章,他的自傳已經有一本《紅樓夢》那麽厚,他講述了自己化解孤獨和寂寞的辦法,“每天的時間安排得比較緊,一直到晚上吃完晚飯才沒事,這一天我就過得很充實。”
衰老對所有人一律平等。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全國人口中60周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7.3%,意味著我們身邊每6個人中就有一位60歲以上的老人。這些老人們有的在家中安享晚年、有的選擇了養老機構。
我們找到其中四位老人,他們講述了選擇養老機構抱團養老的經曆。
“住進養老院,心裏踏實了”
1992年退休的時候,陳滋英擁有了第一架鋼琴,現在擺在養老院她的房間裏,蓋著白色碎花的布防灰。這架木質結構的鋼琴已經陪伴陳滋英26年,剛買鋼琴的時候,她跟著4歲多的外孫女一起學,到現在,外孫女已經取得碩士學位、在美國工作,只有鋼琴還陪著她。
女兒和女婿在意大利定居,2005年,女兒把她接過去住了一年半,逛遍了意大利100多個教堂。在那裏,“我自己又不會開車,我沒法生活,所以我還是很孤獨。”2006年5月回到北京以後,陳滋英的老房子拆遷、回遷房安置在金融街附近,那是全北京最富裕的地方之一,現在每平米房價超過12萬元。
白天,數以萬計的白領隨著車流湧入這一地段,金融街區域金融機構管理的金融資産總額達到16.2萬億元,占全國金融資産總額的60%,控制著全國90%以上的信貸資金、65%的保費資金,每天的資金流量超過100億元人民幣。
對陳滋英來說,這棟價值不菲的房子也僅僅是一個“家”而已。2010年老伴去世,90平米的兩居室只留下她一個人。陳滋英覺得無聊的時候,把老朋友叫來家裏聊天。因爲工作的關系,過去的朋友們大都住在北京的西北邊,弟弟更遠在回龍觀,地圖距離超過20公裏,搭公交往返得兩個小時。
長期一個人待在空蕩蕩的房間裏,陳滋英覺得害怕,每到晚上六點,做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琴也不想練了、總覺得有人藏在房子裏、外面敲門也不敢答應,她睡不著覺,只能靠安眠藥助眠,躺在床上,血壓會突然升高到200,心率也超過了100,心髒“嘭嘭嘭”的跳動。女兒聯系朋友、親戚把她帶到醫院,心電圖、核磁共振都做了,什麽生理病症都沒查出來。
到2017年,每個月都要鬧上這麽幾次,前前後後僅呼叫的120救護車就不下5次,在一家以精神科爲長的醫院,醫生判斷,80多歲的陳滋英患了“焦慮症”。
她決定,不能自己一個人住下去了。2017年5月,陳滋英搬進了養老院。進了養老院,陳滋英心裏踏實了,養老院到處都是人,“吃飯也吃得很好,睡覺也睡得很好”,馬上胖了六斤。
養老院平均年齡86歲,陳滋英81歲,算是個小妹妹,同住的老人們有文學家、雕塑家、醫生和演員。她的朋友“有當過新四軍的,有當過志願軍的,有當過野戰軍的,還有參加過板門店談判的英文翻譯。”
養老院內,很多老人的孩子都不在國內,住在她隔壁的是一位92歲的書法家,兒子女兒都在新西蘭。平常,陳滋英想和女兒通個電話都要算時差,隔著6小時的時差,北京的夜裏十二點,意大利的天剛亮。
81歲生日那天,女兒給她定了一盆蘭花,快遞到了房間裏,擺在沙發旁邊的桌子上,每一朵花都開得燦爛。那天,女兒的兩個朋友來養老院接走陳滋英,帶她在外面吃了頓西餐,算是代替女兒盡孝心了。
“所以我就覺得她雖然說那麽遠,但是我們還是很近的”,科技多少拉近了和女兒之間的距離,每天,女兒通過微信消息能知道她的動向。陳滋英的桌子上常年放著一個放大鏡,她眼睛不好,要通過放大鏡看手機上的消息。
陳滋英和女兒開玩笑說,“小的時候我們把她送到托兒所,因爲我們要上班,兩歲就全托,我老了以後她把我送到老人院,送到這兒全托。”
陳滋英說,“我現在狀態就是,身體無病、心中無事。”
“我這頭是不是有點時尚”
剛搬進養老院的時候,郭京花推著坐輪椅的老伴下樓遛彎,老人們都主動和她打招呼,勸她多帶著老伴出來走走。
年輕的時候,老伴得了血栓,腿腳不利索。身體上的不適影響著心情,今年4月,老伴突然不想吃飯、整天叨叨“怎麽還不死”。
78歲的養老院鄰居于大姐專門寫了三篇文章,討論《對待疾病我的親身體會》,送過來,讓郭京花念給老伴聽。
郭京花的房間門口,有人給送來新鮮蔬菜,要她給老伴做飯;有人送來酸奶和小吃;有人邀請她推著先生一起去晚上7點的音樂健步走,即使不能下輪椅走走,來一起熱鬧也能對心情好。
養老院裏,老人們有一種說法是,“這應該是最後一站了,就是咱們家吧。”
郭京花住在一層,把房間外面的一塊空地布置了一下,鋪上木地板、建了圍欄、擺上茶幾,能利用這塊地方平常讓老伴曬曬太陽。
曬太陽,在過去也是奢侈的事。老伴出門得推著輪椅,老兩口原來在家的時候,輪椅把小區裏普通人行走難以察覺的不便放大了:路面不平的顛簸、石子多、路窄不方便輪椅轉方向、車停的到處都是走不了輪椅……因此,老兩口大多數時候待在家裏,只能對著電視消磨時間。
對健康的人來說,坐沙發是個再簡單不過的動作,但老伴可能就會一屁股坐在地上,以郭京花的力氣,她一個人沒法把他扶起來。“要是在家裏,除非去找要好的街坊,人還有不在的時候,是不是?”
養老院組織了各種活動,有練書法的、唱歌的、教畫畫的,品嘗餐廳的小點心、喝咖啡、量血壓、按摩、中醫問診、洗眼鏡和剪頭發。即便已經到了“七張”的年紀,老人們愛美,郭京花一只手指卷著自己的頭發問,“我這頭是不是有點時尚?”
過去,她出去剪頭發,“一看你這麽大歲數就隨便剪剪”,拿給男士剪頭發的推子,在她腦袋上忙活十來分鍾就好了。這次剪頭發,老人們領了號碼牌,坐成一排等著,挨個剪。剪頭發的小夥子也細致,一邊剪頭發,一邊“爺爺奶奶的叫著”,剪完了走出理發間,郭京花的朋友說,“哎呦,年輕了。”
每周三,有組織來做針灸,郭京花會找她們紮臉,“我試試,你這能斑淺點。”女孩說。郭京花指著臉上問我,“有點效果吧?”
兒女都出國了,老兩口決定“自力更生”
醫學院畢業以後,吳堂嬌被分配到了一家綜合醫院的內科科室。退休前15年,她是醫院的業務院長,形容自己“賣給醫院了”,只要有重病患者就不能離開。老伴說她從來沒放過假,“不管哪個科有搶救的,跟她都有關系”,即使有節假日,心裏也得憂著病人。
今年,吳堂嬌80歲,還沒徹底退下來。前些年她被醫院返聘,每周上三個半天班,給新醫生講課、爲重病患者把關。醫院來了重病患者,吳堂嬌過去一瞧,情況准有好轉,醫生們都叫她“福奶奶”。
兩個孩子長大後都學了醫,兒子學的是運動醫學,女兒學了口腔科。畢業以後,兒子在北京一所大學的運動醫學專業留校當助教,他教書教得好,“做的那標本,腦子神經都做得准”,女兒進了一所醫院的口腔科。在她看來,都是體面、穩定的工作。
上世紀90年代的留洋潮,兩個孩子都嚷嚷著要出國,“不是我給他送出去,他自己非要走,”吳堂嬌說起來,多少還帶著點遺憾,兒子去了日本,女兒去了新加坡,兩個人都不再從醫。
因爲出國的事,老伴不同意,和兒子“打了一架”。打架的結果是,“誰出去我們都不管了,半年我都沒理他,”老伴說,直到有去了日本的朋友做了說客,找兒子見了一面,他“感動了,跟我做個檢討”,父子倆的關系才緩和。現在,每年兒子回家一趟,女兒把外孫女一起帶到了新加坡。
他們決定“自力更生”——住進養老院,與更多年齡相仿的老人待在一起。
以前上班的時候,吳堂嬌把所有時間投入在工作上,直到退休以後才在老年大學學書法、在養老院學唱歌。第一次上音樂課,她緊張得不知道怎麽出聲。
唱歌小組唱俄文歌、英文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雪絨花》和《想你的365天》,有住戶一句句教他們回憶俄文的讀音,大家跟著唱下來,逢年逢年過節上台表演。
除此以外,吳堂嬌還在老年大學上電腦課,學Photoshop和視頻剪輯,給自己做視頻。她把自己出生、上大學、工作,做成三個視頻:人生的開始、行醫的道路、家庭幸福生活。最後一段關于老年生活的,還在剪輯之中。
“人忙起來,也就沒空去想別的了”
2014年1月8日,王中齊搬進了養老院。他精確地記得這個日期,將此視爲人生中的重大轉折。他的大女兒在美國定居、小女兒在北京成家,入住養老院以後,房子挂在網上租出去了。
在養老院住了一年後,老伴去世,生前,老兩口商量好,去世後不火葬,把遺體捐獻給協和醫學院。老伴離開的當晚,一輛車子把她帶走,從此,只剩下王中齊一個人了。他把房子徹底賣掉,“我一個人絕對不可能再回去”。
王中齊聊起“晚上的寂寞感”,他給自己設定了規律的作息:每晚坐著看電視、洗澡,一定在十點前睡覺,“再好的晚會我也不看”。規定了睡眠時間後,每天六點起床,鍛煉、七點半吃早飯、九點鍾做眼保健操、然後看書讀報紙、寫文章、十一點打台球、幫前台分發報紙、十二點准時吃飯、飯後散步、一點午休、兩點起床後繼續看書讀報紙、寫文章、下午四點下樓散步、五點半吃晚飯。
每天,王中齊在電腦上寫文章,寫《我的養老觀》、《我住養老院的原因》,他寫的《我的人生》打印出來有半本字典的厚度。
“怎麽化解孤獨和寂寞,就是我把每天的時間安排得比較緊,幾點到幾點幹什麽?幾點到幾點幹什麽?一直到晚上吃完晚飯才沒事,這一天我就過得很充實。”他說,人忙起來,也就沒空去想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