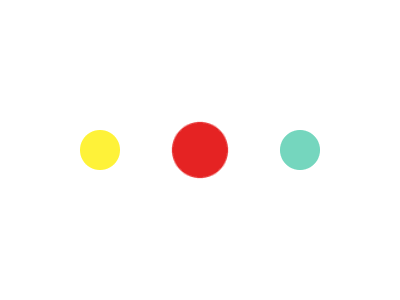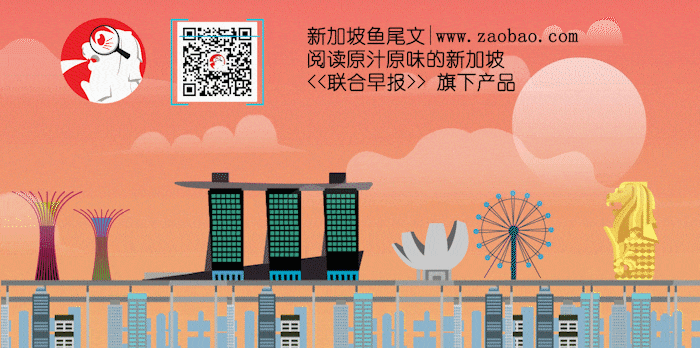蘇海米收藏馬來短劍“克裏斯” 受中文武俠片啓蒙
蘇海米(左)在家打造了一面玻璃櫥,展示他珍藏的“克裏斯”。(龍國雄攝)
上馬來短劍收藏家蘇海米(Suhaimi bin Nasrain,50歲)的家采訪,敞開著的門傳出懷舊武俠電視劇《天蠶變》主題曲。蘇海米開門熱情迎接,才確認並無走錯地方。蘇海米說這是他最愛的武俠劇,但他不完全聽得懂歌詞,最近友人轉發了有馬來文翻譯的視頻讓他百聽不厭。這說明了各文化的轉譯對我們這個多語文社會何其重要。
蘇海米收藏了六七十把馬來短劍“克裏斯”(Keris),每把短劍平均有百年曆史,最古老的有200年。有趣的是,他對屬于自身文化的“克裏斯”的興趣則是受到華人功夫武俠片所啓發。小時候,他常去祖母荷蘭通道的家,叔叔會帶他去附近露天戲院看戲:“一張票才三毛錢,坐木凳。我在那裏看了很多邵氏武俠片、少林功夫片、李小龍的電影。在學校,我的華人同學常把武俠小說、《水浒傳》等文化經典改編的公仔書借給我。後來,港劇在本地熱播,我迷上了《天蠶變》《小李飛刀》《倚天屠龍記》《陸小鳳》等。我們會吵著媽媽買玩具刀劍,市面上的設計不是西洋劍就是武俠劍,我開始好奇,爲什麽買不到我們馬來人的‘克裏斯’,只好用紙皮在家自制。我對‘克裏斯’的興趣從那時萌芽。”
與武吉士人遷移史有關
蘇海米笑言,到了30歲,得到太座“恩准”後,才買了他人生的第一把“克裏斯”。他收藏的大部分“克裏斯”跟新加坡和武吉士人(Bugis)有關,都是透過互聯網從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尼購買,有的遠至菲律賓。他說,透過“克裏斯”散布的地區可追尋武吉士人在本區域遷移的曆史。20年來,他的收藏已多到客廳特制的展示櫃不夠地方擺示。
大衆娛樂和流行文化裏的中華武術對他收藏“克裏斯”不只有重要的啓蒙,耳濡目染的跨文化興趣也滋養及豐富了他對收藏品的求知與探索。爲了深入了解“克裏斯”,他除了翻閱各種東南亞學術書籍,連有關其他宗教如佛教、道教、印度教的著作也虛心參考。他說,馬來群島的族群不是一開始就信奉回教,之前就有泛靈信仰,笃信萬物有靈,也有印度教和佛教信仰。他說,古時候佛教僧人到印度取經之前會到印度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學習,在本區域,僧人西遊之前則到印尼蘇門答臘的巨港(Palembang),在當時的佛學、梵文大學學習。
長形的“克裏斯”是最高權威的象征,唯有統治者能擁有和使用。(龍國雄攝)
這些信仰的曆史演變即使在馬來族群普遍回教化後也被流傳下來,透過隱晦、抽象的形式表現在“克裏斯”的設計和鑄造上。他說,泛靈信仰相信刀劍有靈氣,對攜帶者有護身作用。“克裏斯”劍身的造型源自印度教和佛教的“娜迦”蛇神,“娜迦”在漢傳佛教則變爲神龍。直劍象征靜態的龍;彎曲的“克裏斯”則象征動態的龍。他說,回教徒用“克裏斯”的曲線來比喻和象征大自然,因爲自然界沒有筆直的線條。
有些“克裏斯”的劍柄設計稱爲“含羞的公主”(Putri Malu)。這詞在馬來文也指含羞草之花,不過體現在“克裏斯”劍柄上的則是一個頭戴面紗,將花容遮掩的半蹲抽象人形。蘇海米說,有學者相信這跟印度教主神之一濕婆的配偶、嗜殺的複仇女神杜爾伽(Durga,難近母)有關。女神化身爲杜爾伽時面容可怖,叫人視之喪膽,須蒙上面紗,回教將戴面紗的杜爾迦女神的形象抽象化,設計成方便手握的劍柄。
這刀柄設計稱爲“含羞的公主”,學者相信是抽象化的複仇女神杜爾迦的造型。(龍國雄攝)
劍鞘上的藤編手藝極爲精致,今日懂得這技藝的工匠少之又少。(龍國雄攝)
這把劍使用馬來西亞生長在岩石間的貴重黃金木制成,其美麗的木紋是在岩石壓力下形成的。(龍國雄攝)
鑄劍師在靠近劍柄的肩部雕了一張人的側臉,經蘇海米提起,才發現這隱藏的細節。(龍國雄攝)
在古時候的馬來社會,“克裏斯”有著許多重要的社會象征與功能。在馬來西亞和文萊,“克裏斯”長劍是統治者權威的象征。它在封建制度社會裏也代表著至高的地位,只有精英權貴才有資格佩戴。正因如此,到了現代社會,“克裏斯”也成爲最高級別的符號,譬如國泰五六十年代的馬來制片公司便稱爲“國泰克裏斯”(Cathay-Keris),也以一雙交叉的“克裏斯”作爲商標。
見證馬來人的造物智慧
當然,“克裏斯”最主要的用途是武器。馬來半島族群擁有數千年的文明,蘇海米認爲,“克裏斯”的設計見證了馬來人的造物智慧與創造力。很多人因“克裏斯”婀娜多姿的彎曲形狀而低估了它的殺傷力。他拿起一張白紙,用“克裏斯”彎曲的劍刃稍微刺破白紙幾公分,把劍拔出來時,再稍微左右切動,原本小小的切口,忽然擴大了好幾倍,很是驚人。蘇海米說:“使用者只需刺入三到五公分,就能大大破壞內髒和血管,抽出劍後,傷者甚至還會穿腸破肚。你看它的造型是這麽的美麗,但它卻能讓人一劍斃命。我將‘克裏斯’形容爲殘酷的雅美。”
也是這個“殘酷的雅美”導致許多現代馬來人不願在家收藏“克裏斯”,急于轉讓或抛售,有的甚至用布將它包裹起來抛到海裏。蘇海米說,大部分虔誠的回教徒會因爲“克裏斯”象征好鬥、具侵略性的能量,以及它融入其他宗教的元素而抗拒它。他自己則沒有這個包袱。
他說:“我因爲收藏‘克裏斯’而研究其他宗教,我懂印度教不表示我就成了印度教徒呀。”他強調自己是以學術爲出發點,透過研究了解“克裏斯”看到自己族群的文化演變。他把“克裏斯”當成文物收藏:“從選材、設計到鑄造和雕刻,當中各個階段的巧思和匠心,都讓每把‘克裏斯’成爲一件獨立的藝術品,而不單是一把武器。”蘇海米還特地挑選了三把最珍貴的“克裏斯”送給妻子和兩個兒子,作爲傳家寶。
當了28年的監獄官,提早退休的蘇海米閑來在家把玩、保養收藏品。因爲本地氣候潮濕,他會自制香氛油,時不時把短劍拿出來拭擦、上油防鏽。他還經常穿上傳統服飾,帶著收藏的“克裏斯”去演講,跟不同族群分享文化典故、收藏心得。
蘇海米的父親祖籍印尼爪哇,母親有一半爪哇和一半南亞旁遮普血統,對自身的多元文化的認識,讓他堅信,深入研究一個文化的微曆史,更能看出天下大同。他說:“我越研究就越能看出不同文化核心的相似度,而非迥異度。我雖以馬來人的角度研究和收藏,但我最終發現‘克裏斯’其實是東南亞共享的文化遺産。我身邊就有很多華人‘克裏斯’收藏者,收藏的數量比我還多。
文:林方偉圖:龍國雄
一只愛生活、文藝範的小魚尾獅帶你了解新加坡原汁原味的風土人情領略小島深處那些鮮爲人知的文化魅力~ 新加坡《聯合早報》旗下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