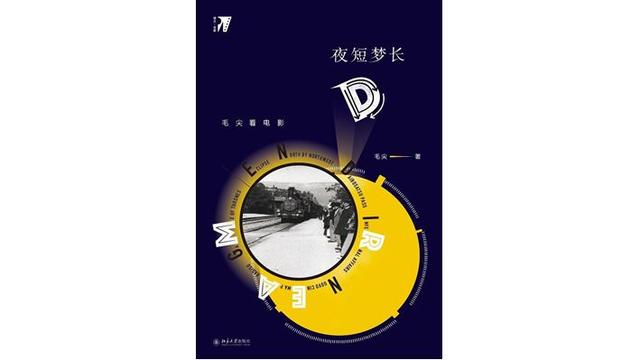“而回頭想想,半輩子過去,電影不僅成了我生活的度量衡,一節課是半場電影,一個暑假是一千場,四年大學是兩萬場,活一百歲,就是活過四十萬部電影。電影,似乎也只有電影,讓我完整地走過了《戀人絮語》描述的所有階段,包括沉醉、屈從、相思、執著、焦灼、等待、災難、挫折、慵倦以及輕生、溫和、節制等,面對電影,就像羅蘭·巴特說的,我控制不住被它席卷而去,而這一去,就像‘二進宮’的賭徒,回頭無岸。”
在毛尖的最新電影隨筆集《夜短夢長》裏,她依然用很“毛尖式”的筆觸,總結了她與電影糾纏半生的關系。轉眼間,毛尖已寫了將近二十年的影評,當年跟著毛尖一起看電影的文藝青年也慢慢步入中年。不管信息革命使得影評的形態和業態發生了多少變化,中國電影市場繁榮還是蕭條,她也一如既往鋒利地審視著當下中國電影的動態。
過去一年來,令她失望的電影一如既往地多。即使她曾經贊過的印度電影,在這幾年被各方點贊後,她如今也覺得“近兩年印度電影有一點點被我們高估”。畢竟,作爲一名影評人,能堅持獨立的批評, “能把持批評者的良心,就是最大勝利,如同裏爾克說的,挺住,就是一切”。
毛尖,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影評人,在新加坡、上海、香港和台北等地報刊開設專欄,主要代表作有《非常罪,非常美:毛尖電影筆記》、《當世界向右的時候》、《慢慢微笑》、《亂來》、《意外》、《一寸灰》和《有一只老虎在浴室》等,最新文集《夜短夢長》的中國大陸版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19年2月出版。
Q1:你新書的書名《夜短夢長》該如何理解?
答:2016年,應程永新老師的邀請,我在《收獲》寫電影專欄,程老師讓我給專欄取個名字,當時定了“夜短夢長”,大意就是“夜太短電影太多”。專欄寫了兩年,出文集延用了專欄名,本來電影就關乎“夜”關乎“夢”,也還算准確吧。
Q2:李歐梵在《夜短夢長》序裏說,最令他吃驚的是你的觀影速度。你是如何在二十多年的“影齡”中把一個世紀的電影經典觀賞殆盡的?
答:我二十幾歲時認識歐梵老師,他就沒給我加過歲數。我的影齡其實跟我年齡差不多,四十多了。我們七十年代出生的,從小最大的娛樂就是看電影,那時沒有那麽多電影看,一個《保密局的槍聲》可以看四五遍,回頭想想,那時算是提前修了電影精讀課,我後來看電影再沒有那麽聚精會神過。
一個多世紀的電影經典無論如何看不完,再給我三生三世,也還是會看了嘉寶漏了鮑嘉,但我之所以還敢寫影評,一方面確實是我自覺看的電影達到了專業要求的數量,另外一方面,現在寫影評門檻很低。不過,無論是出于驕傲還是出于公益,我的觀影心路一直很健康,那就是“我喜歡看電影”。當然,寫了那麽多年影評,也多少有點責任感,甚至職業感,不過哪天我不喜歡了,我就會離開。
《夜短夢長》
Q3:你最近在看的是哪部電影/影視劇?
答:最近在重溫《權力的遊戲》。四月要出新季了,幾百個人物,得複習一下。《權力的遊戲》經得起看,虛擬世界如此血腥又如此燦爛,所有的人,都比現在的人大一號。另外,春天要在三聯出一本新書《凜冬將至》,想再寫一篇關于《權力的遊戲》的文章。
Q4:你去年看過的最好的一部電影是哪部?
答:最怕回答有關“最高級”的問題。非要說一個的話,《我不是藥神》吧,因爲這部電影具有一種國家議題性,嚴肅緊張又商業活潑。影片塑造了一類人的命運,裏面有我們久違又熟悉的共同體形式。此外特別喜歡徐峥的表演,刷新了過往電影史所塑造的低度汽泡酒似的上海男人形象。
Q5:去年有哪些電影令你失望?
答:那太多了。去電影院看電影經常遭遇“滑鐵盧”,兩小時出來,能夠不卑不亢,就是人生贏家了。2018年讓人失望的電影,一如既往地多,沒法點名。印象裏,續集的、翻拍的,都失敗,比如《英雄本色2018》,看完以後,“英雄”這個詞都要重新去查詞典。
Q6:你覺得去年被高估的電影有哪些?
答:很難說高估低估,因爲並沒有一個真正的“琅琊榜”。籠統地說,我覺得最近兩年印度電影有一點點被我們高估了。2016年,《摔跤吧!爸爸》燃爆全球,我自己也寫過文章贊美印度電影的方法論,但隨後呢,印度電影各路引進、各種點贊,這讓我有些擔心,我們會不會學不了印度電影的精氣神,但把他們最沒創意的套路給學了過來?此外,還有像《廁所英雄》這樣的印度電影,我們的掌聲圍繞著政治正確轉,但政治正確不是一部好電影的充要條件啊。
《我不是藥神》
Q7:今年你期待將出新作品的導演有哪些?
答:最期待《第一爐香》。張愛玲原著,王安憶編劇,許鞍華導演,三個“最高級”,是不是想想就有些激動,不過不知道明年能不能出來。另外期待《荞麥瘋長》,因爲從制片藤井樹到導演徐展雄,都是我們華師大的人。
Q8: 哪些電影或者導演對你影響最大?
答:看過的電影都會影響我,有時候一部爛片的影響還會超過一部好電影,尤其當曾經喜歡過的導演和演員,突然拍出一部匪夷所思的電影。像《擺渡人》就很令人詫異,爲什麽梁朝偉會在五十五歲的年紀去演一個連郭敬明都看不上的小情種,想不明白啊,大概是王家衛和他的往日情誼太動人,士爲知己者演吧。
現在正面來回答你的問題。希區柯克對我影響非常大,他太厲害,完美地實現電影的最高功能,改造我們的意識形態。看希區柯克的電影,從來不希望黑色人物被繩之以法,這是他的邪惡,也是他的牛逼之處。
Q9:你重看過次數最多的一部電影是哪部?
答:一般情況下我會回答,小津的《東京物語》或者希區柯克的《驚魂記》,因爲上課經常用到或提到這兩部電影,但回頭想想……好像也不一定。小時候看過很多次《少林寺》,看到每句台詞都會背,以後再也沒有這樣過了。
至于爲什麽會喜歡《少林寺》,可能因爲我們之前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影,突然發現,我們在教室裏追追打打的荷爾蒙,原來還可以有這樣的形式。藉此,我們髒亂差的少年時代在武俠電影裏獲得了合法性。
Q10:還記得有什麽電影在第一次看時曾讓你震驚/震撼/記憶深刻?
答:剛剛說了,第一次看《少林寺》被震驚過。第一次看《小花》和第一次看《保密局的槍聲》也都記憶深刻。有個小學同學,小時候大概沒怎麽看過電影,有次和我們一起看八一電影制片廠的電影,八一的廠標五角星在銀幕上發著光逼近我們,他就激動哭了,這些震驚體驗以後都不可能再現了。
長大以後,看到新的類型片,或者大師之作,雖然還是會身心恍惚,但神魂顛倒的經驗不太有了。印象深的有一次,大家集體看錄像帶《感官王國》,開頭以爲是藝術片,沒想到這麽重口,人人故作鎮靜,一句話都不敢說。那次口幹舌燥、人人裝逼的場景,還近在眼前。
Q11:在小衆的導演裏,有哪些導演特別值得推薦給大家?
答:這幾年看過的年輕導演,特別有印象的電影有兩部,一個是楊瑾的《有人贊美聰慧,有人則不》,一個是郝傑的《光棍兒》,很中國、很有元氣。
《有人贊美聰慧,有人則不》
Q12:假如讓你來拍電影,您會拍些什麽?
答:如果你十年前問我,我心一橫,大概會說,我要拍個武俠。但我現在死心了,拍武俠電影要求的體力和智力,我都沒有。
Q13:你一般選擇在什麽樣的環境下看電影?
答:能在大銀幕看的,會首選大銀幕。看不了的,網絡解決。不過這麽多年,用電腦看美劇看英劇,似乎也成了一種觀影方式。
Q14:近年來,有影評人說中國的新獨立電影時代到了,比如《心迷宮》《米花之味》《路邊野餐》《八月》和《塔洛》等新生電影力量在各大影展拿獎,你怎麽看待這一現象?
答:當然是好事情,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到達“新獨立電影時代”了。而且,“新獨立電影時代”,這個名稱本身也不完全是新力量展示,所謂的“新”還包括電影行業的新境遇、新轉向,甚至新危機。在電影、電視劇和網劇爭奪山河的大時代,新獨立電影到底意味著什麽,絕不是以往“獨立”一詞可以涵括的。這裏的“新獨立”,更新的不僅是電影人對電影的理解、電影語法的代際,還有電影的制播方式、電影的行業份額等等,後者可能更關鍵。
《八月》
Q15:你最想邀請哪些人去你家做客?
答:去年夏天答三聯問卷的時候,嘴閑說了句,想認識潘金蓮和西門慶,想和他們一起吃個飯,到現在,朋友還會調侃我,和西門慶吃上飯沒有。所以你看,如果我要維持我人設的連貫性,我得說,我還在等潘金蓮和西門慶。
Q16:在你自己的作品裏,最滿意的是什麽?最遺憾的是什麽?
答:我寫的不是長篇,都是短文章,所以不太需要考慮“滿意”或“遺憾”這樣的問題。小文章嘛,不滿意,另寫一篇就是。或者你也可以說,我一直還在寫文章,是因爲我至今沒有寫出滿意的作品。
Q17:如果讓你做文化媒體的執行主編,你想做什麽類型的刊物,會設置哪些欄目?
答:嚴肅地說,眼下中國更需要汪晖黃平時代的《讀書》,但我自己沒有能力編。另外也想編一本《核心期刊》,因爲實在受夠了大學這些年的核心期刊考核制度,尤其對年輕學者越來越嚴苛。當然,這是玩笑,想編《核心期刊》的人,估計每個學校都有一大把。
讓我當執行主編,我想編一本《大怪路子》,我是撲克迷,四五歲就跟著外公上牌桌了。小書《夜短夢長》第二輯,就是用賭徒視野串起來的影視小史,我本來的願望是寫出一副牌,包括大王小王,老A老K,但沒有全部完成。我的雜志欄目,也想按撲克序列分欄目,王事黑事,二貨八婆,各自歸位。
Q18:所有對你進行采訪的人裏,你最喜歡/最記憶深刻/最惱火的是哪次采訪?
答:像我這種跟誰都能相處的,要把我弄惱火,不容易。不過,活了半輩子,接受過的采訪確實也五花八門、二三百次了。印象裏最痛苦的一次,是一個很厲害的時尚雜志來采訪,化妝發型服裝折騰我整整一下午,當時真的有點惡向膽邊生,很屌地說了句,我等會兒只接受白襯衫牛仔褲。然後他們就放棄了花樣年華的我,直接拍攝了。
最難忘的一次是,我在香港完成博士大考後回上海,躲在天鑰橋路寫論文,居委會以爲我是無業遊民,要幫我介紹樓下華聯超市的收銀工作。我很尴尬地告訴居委會阿姨,我是有工作的,只是在寫論文。阿姨倒是很爽氣,說,那你是知識分子喽,我也只好認了。然後過了一段時間,她帶了一個講英文的記者來,說,你回答他一下,問題很簡單,“在上海生活幸福嗎?”我用英文回答了。居委會阿姨很滿意。不過我到現在沒搞清楚,是阿姨在考驗我,還是我配合了阿姨。
Q19:你現在經常閱讀的媒體是哪些?爲什麽讀它們?
答:文學雜志,經常讀的是《收獲》《思南文學選刊》《上海文學》《小說界》這些;學術刊物也看,不過很多文章經常在各大公號上看,像“保馬”“三聯學術通訊”“雅理讀書”“海螺社區” “文藝批評”“活字文化”“新青年電影夜航船”等。
我讀它們,往硬裏說,因爲我在大學教書,必須保持自己對當代文藝的閱讀和閱讀量;往軟裏說,我總得讀些有營養的吧,像我師兄羅崗和陳越老師主持的“保馬”,每天推一本書一篇文章,我有時候看完爛片覺得虛度一天,看看保馬文章,似乎挽回一局。
Q20:隨著媒介的變化,影評的形態和業態也隨之變化,您覺得對于影評寫作來說,不變的東西是什麽?
答:寫評論,總是怕政情、人情幹擾,所以,說得樸素點,能把持批評者的良心,就是最大的勝利,如同裏爾克說的,挺住,就是一切。
Q21:您對未來有什麽新的規劃嗎?
答:教書二十年,專欄二十年,一直想休息一下,一直沒成功。有時候會覺得,好像一直是被動著被未來規劃。不過也許,我們這一代人,從小沒有被培養獨立之精神,從小喜歡側身在溫暖的集體懷抱裏,和大家穿一樣吃一樣做一樣,隨大流讀書上學,隨大流結婚生子,連表達一點異議也是隨大流的,所以,我們大概生來是隨波逐流的,生來就是活在被動語態裏的。不過,眼看著現在越來越多貌似個性十足的“詩與遠方”,反倒覺得,我們雖然不曾霸氣地設計未來,但至少從不自私的。我好像離題了。不過,對于未來,確實沒有規劃,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吧。
作者:毛尖;采訪:徐悅東
編輯:榕小崧;校對: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