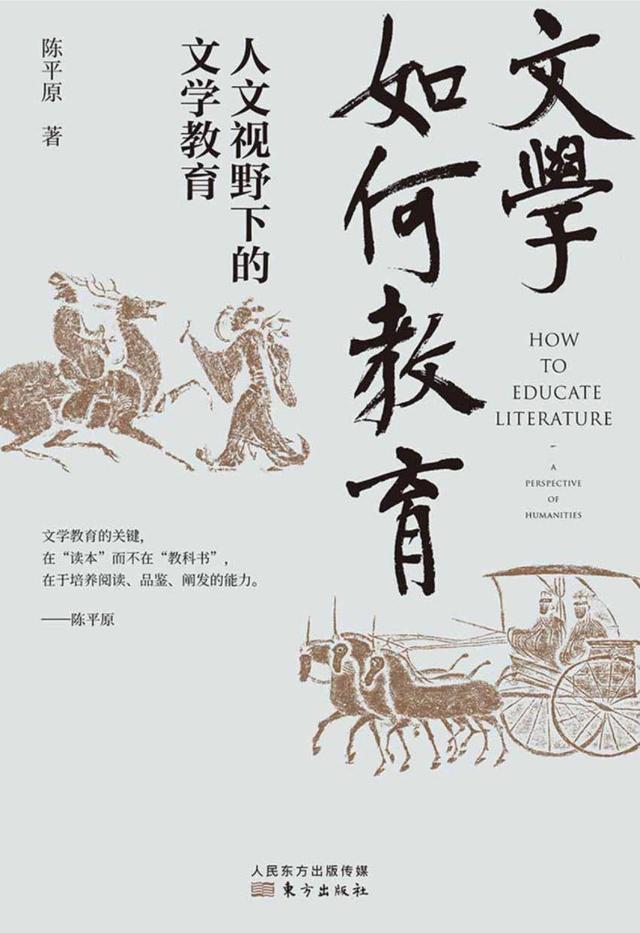陳平原
關于學術評價與人才養育,我寫過好多文章,在學界有不小的影響,最常聽到的反饋是:你說得很好,也很對,但沒用,因大勢已成,格局早定,誰也扭轉不了。這我承認,但只要有機會,還是要說。就好像曆史文化名城建設、文化遺産保護,以及學科評估指標設計等,只要認准了方向,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多少還是起作用的。越是弱勢群體,越需要奮起抗爭,只是必須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理准備。
這回不太一樣,是體制內的思考與獻策——具體說就是複旦大學國家智能評價與治理實驗基地主持的會議,名曰“反思與探索”,但我希望主要不是發牢騷,也不僅僅是做文章,最好有些微的實際效果。因此,我傾向于“老調重彈”——不是說重要的話要說三遍嗎?下面的發言,夾雜自我引述,有的反省,有的堅持,有的則進一步發揮,最後落實爲若幹建設性意見。
七年前,我在北大校園接受複旦大學“人文社科評估標准項目”課題組專訪,那次答問的內容,以《人文學科的評價標准》爲題,初刊2016年4月6日《中華讀書報》,收入我的《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東方出版社,2021)等。其中涉及今天我想著重討論的項目化管理,主要是以下三句話:第一,“項目經費對于社會科學和理工科特別重要,但對于人文學科的意義不是很大——除非你做大規模的社會調查、資料搜集等”;第二,“我反對用得到多少經費來看待一個學者。評判學者,既要看他的學術成果,也看他的教學情況,唯獨拿多少錢不重要”;第三,“有些擅長編列預算做大項目的,把很多年輕學者拖進去,把一屆屆博士生、碩士生也拖進去,弄不好,真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呀!”因人各有志,且才華有大小,什麽是人文學的最高境界,這裏不想爭辯,只談談以項目管理爲標的的“計劃學術”之利弊。
《文學如何教育》,東方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同樣讀書做學問,老一輩文史專家大都主張沉潛把玩、博學深思,這與今天課題優先、出活第一的學術風氣,明顯不是一條路。所謂“草鞋沒樣,邊打邊像”,或者“出水才看兩腿泥”,這種學術風格,在推崇項目化管理的今天,顯得十分不合時宜。這個時代,需要的是明確立場、事先規劃、大膽吆喝、提前報喜的能力與膽量。項目(最好是重大項目)到手後,穩坐了釣魚台,那時再自我調整。否則,再好的才華、再大的雄心,若手中沒有項目,在今天的評價體系中,極有可能早早就出局了。
多年前,我曾強調:“‘項目’是爲‘科研’服務的,允許有‘科研’而沒‘項目’,反對有‘項目’而沒‘科研’。人文學者以及偏于思辨的數學家或理論物理學家,完全可能在沒有項目經費支持的情況下,做出大學問來。”(《要“項目”還是要“成果”》,《雲夢學刊》2014年第4期,人大報刊複印資料《社會科學總論》2014年4期轉載)這話今天大概沒有人(或很少人)願意相信了。記得十年前,北大全球招聘講席教授(全職),那時我是中文系主任,推薦了倫敦大學某名教授,人事部長看了材料,問我:你不是說他很強嗎,爲何沒有研究項目?我當時的答複是——歐美大學的人文學教授,主要自己做研究,著書立說,沒必要申請項目。校方接受了我的解釋,可惜人家最後選擇了美國的大學。爲了今天的演講,我專門請教哈佛大學某講座教授,不出意外,他也“對這類獎助金項目一向十分疏懶,竟然從來沒有申請過”。以有無項目來評判人文學者,這是亞洲華語地區(包括新加坡)的特色,在全世界範圍內,並不具有普遍性:“歐美的確沒有這套制度。但有ACLS、NEH等有公信力的民間或半官方基金會設立的研究獎助金可供申請(CCK算是國際漢學獎助基金會),但沒有任何規定學者必須申請,以此作爲晉升標准。最後的判准,如你所說,是學問(出版的文章、書籍)的品質,不是項目、金額的有無。”
那麽,爲什麽在中國的人文學界,會有如此獨尊項目的風氣?依我推測,第一,最近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及文化迅速崛起,基于時不我待的良好願望,政府希望通過合理調配人力物力,采用類似計劃經濟的運作方式,彎道超車,體現制度的優越性。第二,這套制度的核心是規劃與管理,而管理要想上軌道,必定追求數字化,在確保時間、技術、經費的條件下,盡可能提高生産效率,完成預定目標。第三,項目化運作在工程技術領域確實很有效,用在社會科學也還說得過去,唯獨人文學很不適應;而目前中國著名大學的校長多爲理工科出身(因需要院士頭銜),他們對這套管理體制比較熟悉,且容易親近與接受。
二十年前,項目化管理剛剛進入人文學領域,國家科學技術部辦公廳曾就那時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原始創新”話題,舉辦了一次跨學科座談會。第一個發言的是中科院資深院士鄒承魯,第二位發言的陳述彭,也是中科院資深院士;我排在第三位,後面還有好些科學家及人文學者踴躍發言。這次座談會的紀要,以《自然、人文、社科三大領域聚焦原始創新》爲題,初刊《中國軟科學》2002年第8期。我在發言中談及那時剛冒頭的“人文研究的工程化”,強調人文學的特殊性:“工程管理需要計劃,人文研究則有很大的隨意性。學者靠的是長期的修養,靠的是不懈的追求,最後靈光一閃,照亮了平生的積累,抓住機遇,再加上自家努力,就這麽出的大成果。根本不可能是原先計劃好的,要是結論早先就有,而且可以按部就班地推進,我很懷疑這種研究的價值。”發完言後,一位院士跑來跟我解釋,說我誤解理工科了,他們真正的學術突破,也大都像我說的那樣,“最後靈光一閃,照亮了平生的積累”。
我的批評與質疑之所以不起任何作用,一方面是人微言輕,且所論集中在“原始創新”,沒有考慮均衡發展與社會服務,明顯有所偏頗;另一方面則是1986年經國務院批准設立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不斷積累經驗與資金,如今戰績輝煌:投入二十六億五千萬元,資助各類項目兩萬四千二百八十三個,推出研究成果四萬五千多項,有效地促進了中國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發展。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範圍越來越廣,不僅有重大項目,還有專項工程、後期資助項目、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年度項目、青年項目和西部項目,以及單列學科(教育學、藝術學)等,幾乎無遠弗屆。考慮到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收益實在太大,不免有蠅營狗苟之士鑽漏洞,因而出現若幹偏差,比如過分揣摩趨勢與潮流、分析中獎幾率、培訓填表技能等,好在基金委不斷調整策略。如今年初網站發布《2021年12月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青年項目和西部項目結項情況》,通告總共驗收了四百五十七個年度項目、青年項目和西部項目結項申請,其中三百二十六個項目予以結項,一百一十個項目暫緩結項,二十一個項目被終止。也就是說,有關部門已經意識到,除了嚴格評審制度,還得加強後期驗收,否則很容易功虧一篑。
今天生活在中國的人文學者,可供申請的,不僅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還有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文社會科學項目、所在市或校的人文社會科學項目。因此,在大學教書的,不管老中青,大都有這樣那樣的科研項目,甚至有一部著作或一篇論文挂好幾個項目的。以至當有人拿出沒有任何項目支持的研究成果時,其學術水平及含金量會被雜志社、出版社、大學科研處以及評獎機構廣泛質疑,起碼低看一眼——當然,如果是名家,早就表明態度不參與這套遊戲的,那又另當別論。可以這麽說,以項目爲中心的學術生態,乃當今中國大學的一大特色。
這套管理體制,有其利,也有其弊。既然大勢已經形成,自然有其合理性;作爲個體的學者,我們只能自己選擇,盡可能地趨利避害。
十四年前,在北大一套大書的出版座談會上,我談及如今這套管理及評估體系,剝奪了人文學者本該有的從容、淡定與自信:“以我的觀察,最近二十年,好的人文學著作,大體上有三個特點,第一,個人撰寫;第二,長期經營;第三,沒有或很少資助。”具體的闡述就不說了,文章最後提出一個設想:“建議政府改變獎勵學術的機制,除了現行的課題申請,應增加事後的獎勵。沒拿國家資助的學者,可以憑已出版的著作,申請下一步的科研經費。經過專家鑒定,確實優秀的,不妨按質論價。”(《學界中誰還能“二十年磨一劍”》,2008年2月18日《人民日報》)文章發表後,不少人叫好,但也有領導表示不以爲然,擔心沒有計劃書和時間表,教授拿了錢不幹活。我的回答是:凡真正的好學者,做學問猶如穿上紅舞鞋,只要生命不息,閱讀、思考與表達就不會停止。若這個獎勵能幫他/她解除一些後顧之憂(包括各種考核),更加自由自在地探索,那何樂而不爲?
八年前,我應邀撰寫了上面提及的那篇流傳頗廣的《要“項目”還是要“成果”》,除了對獨尊項目的風氣做了若幹剖析,文章最後,重提我的設想,希望政府特別表彰那些沒拿國家經費而做出好成績的學者:“今天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資助18萬,你自力更生,沒拿國家經費而獲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獎的,給五十萬獎勵行不行?到目前爲止,教育部總共頒了六次獎,我得了五次,其中兩次還是著作一等獎。可我所有獎金加起來,還不夠一個一般項目的資助。這你就明白,爲何大家都把心思放在爭取項目,而不是做好科研。爲了扭轉學風,不妨考慮我的建議,獎勵那些誠笃認真、行事低調、不喜歡開空頭支票的學者。”
這裏的基本思路是:中國的人文研究,産量已經足夠了,基本水平也還不錯,缺的其實是原創性成果。原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書記郭傳傑接受網易科技《科學大師》欄目專訪,稱:“從數量上看,我們人才隊伍是很大的,據科技部2020年的官方統計,RD(研發)人員已經達到710多萬,規模世界第一。但是我認爲,其中大量都是普通人才,以二流、三流的人才居多,一流的人才,就是錢學森錢老所期待的那種人才,我們還是很缺少的。”(2022年5月17日《科學大師》)其實,這個問題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領域更爲突出。科技水平高低有相對客觀的標准,成敗得失比較好檢驗,聰明的管理者大都心裏有數。至于人文及社科的成果是否具有“原創性”,短時間內,基本上“全憑嘴一張”。不能說沒有標准,但相對模糊,很難一目了然,需要時間來淘洗。
因此,我們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應鼓勵天馬行空、不拘一格的創新思維與表達。而在我看來,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基本上都是無數次艱難探索乃至失敗後的“靈光一閃”,而不是靠人海戰術拼湊出來的。在進一步完善現有的這一套行之有效的項目管理制度的同時,尊重那些不太聽話、喜歡質疑、特立獨行的人文學者的選擇,具體策略可簡化爲三句話:第一,評價大學或具體學者時,大幅減少課題(項目)的權重(起碼不該有一票否決那樣的提法),轉而注重代表性成果;第二,若經費都在同一個盤子,建議相對削減科研經費,轉而提高優秀成果的獎勵額度;第三,凡事先沒有(或不願)申請項目的優秀成果,獲獎後,不用填表申請,直接加倍獎勵科研經費,允許其自主決定研究方向、題目、完成時間與成果形式。這麽做的目的,是在穩定大局的前提下,保留一塊相對寬松、可供自由馳騁的天地,進行另一種研究方法、思路、境界的探試。
這裏我必須做一個小小的修正。多年來,我在好幾篇文章中提及自己不喜歡“領軍人物”這個詞,而更欣賞“獨行俠”。那是因爲,工程技術或某些社會科學,需要大兵團作戰,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確實是本事,可文史哲及宗教、藝術等領域,情況不是這樣的。“以我淺見,人文領域的創新與突破,大都屬于這些壁立千仞、特立獨行的學者。領著幾百上千人做學問,那只能是整理或彙編,滿足領導‘盛世修大典’的虛榮心。‘學術組織者’的能力,與‘千裏走單騎’的膽識,同樣值得尊重。可眼下整個社會的價值判斷,越來越向‘組織者’傾斜,見面先問行政級別、手下人馬以及經費數目,這可不是好現象。”(《關于“人才養育”的十句話》,2015年12月22日《光明日報》)後來想想,假如放長視線,且不拘泥于組織形式與課題經費,那些意志堅定、思維深邃、勇于挑戰成規與常識的“獨行俠”,萬一曆盡千辛萬苦,最終闖出一片新天地,給學界提供可以追摹的新領域、新課題、新方法、新思路,不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領軍”嗎?
目前的制度設計,主要著眼點在建立各種關卡,防止營私舞弊,可不知不覺中,演變成爲鼓勵穩妥的選題、均衡的思考、平庸的表達。太個性化的探索,很難被接納。所謂慧眼識英雄(尤其是在其沒有盔甲與標旗的時候),不是那麽容易的;更何況,一個人說了不算,還必須有好幾個伯樂湊在一起。而真正的一流人才,很可能不屑于或沒能力填好如此複雜的表格。不能埋怨評審者有眼無珠,而是你走得太前了,且仍在探索中,論證不夠嚴密。審讀每份申請表格的時間那麽短,評審者當然只能根據自己的立場與思路來做判斷。了解這一點,你就很容易明白,再好的制度設計,也都不能保證“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基于這一判斷,我才會再三申述,希望有關部門在嚴格管理,杜絕各種弊端,保證撒下的每顆種子都開花結果的同時,預留一定的自由探索空間,選擇/允許一小部分人不計前程,全憑個人直覺與興趣,放手一搏,說不定哪天會有意想不到的大創獲。
(本文爲作者2022年5月31日在複旦大學智能評價與治理實驗基地主辦的“反思與探索——人文學者談學術評價”會上的發言)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