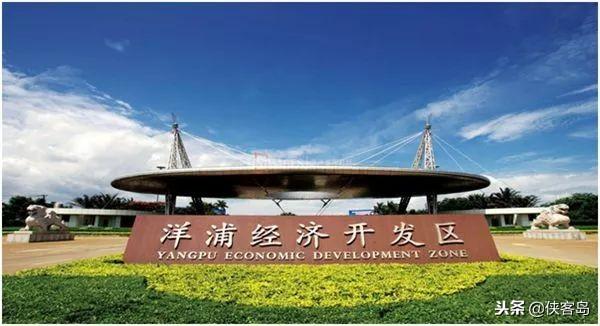【俠客島按】
改革開放的40年,是人類曆史上波瀾壯闊的畫卷。
橫亘在中國老百姓腳下的堅冰,慢慢融解;而那些新生力量,從初生、草莽,到成爲主流、蓬勃發展,也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40年長途,有的人,在曆史進程的驚濤駭浪中翻船泯滅;也有的人,舉著改革先鋒的火把破浪前進,爲後人照亮方向。
今天,俠客島推薦一篇來自“智谷趨勢”的文章,《改革開放40年的三個隱秘故事》。每一段過去,都是我們的探索曆程,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繼續前行的寶貴財富。
海南
80年代末,深圳經濟特區搞了七八年後,鄧小平認爲,中國是時候搞一個比深圳更大的特區了。
天大的機遇來到海南面前。這顆南海明珠,其地理、面積、資源等條件與亞洲四小龍中的台灣差不多,如果能把海南搞上去,不就可以向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嗎?
然而,彼時的海南卻還只是一個光禿禿的“破島”。工農業總産值50多億元,財政收入不過4億元,空空如也的錢袋子,壓根沒法支撐起它的野心。那時中央財政也沒錢,只能向外找法子。
恰好,海南建省籌備組有兩個重要的主力。一個是從廣東調任過來的許士傑,一個是深圳經濟特區的元老梁湘,兩人誓要讓海南成爲另一個神話。他們不是複制深圳模式,而是准備向新加坡學習,“引進外資,成片承包”。
1988年5月的一天,許士傑來到資本滿天飛的香港,找到最大的建築商熊谷組,雙方達成一致協議——海南以每畝地2000元的價格,把洋浦交給熊谷組成片開發,租期70年。洋浦戰略位置優渥,靠近東南亞,又有深水港和豐富石油資源,只要把這個棋子搞好,海南整個盤子可能就活了。
洋浦戰略位置
當年6月,海南省政府出台扶持政策,框定了即使現在看來仍很大膽的三個“自由”——資金進出自由;境外人員進出自由;貨物進出基本自由。這個獨一無二的大紅包,讓這片30平方公裏的土地“比特區還特”。
藍圖畫好了,資金來源也基本解決了,然而,事情的後續發展遠遠超出了許士傑的想象。他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土地租借方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其股權構成部分爲:于元平17%、李嘉誠17%、日本熊谷組37%。
37%的“日本血統”成爲了衆矢之的!
1989年3月,一位北京來的高級官員,在海南實地考察整整12天後,連夜撰寫了一份發言報告,痛批海南的“割地行爲”,在他眼裏,中國本土又將出現相當于舊北京內、外城三分之一面積的外國租界地,洋浦有引狼入室,開門揖盜之嫌;隨後,兩百多位政協委員也聯名遞交提案反對,似乎一旦租借,洋浦就會成爲“資本主義世界”;一些學生還上街抗議,大聲呼喊“聲討海南賣國”、“還我海南”的口號。
盡管鄧小平批示認同這一模式,但是以土地換資金的舉措觸發了大衆痛點,洋浦的開發不可避免地被拖延。直至三年後,中國結束左右之爭,洋浦經濟開發區才真正落地。
這一拖,就讓洋浦模式徹底失去了先發優勢。原本准備在洋浦投資的各種大公司、大財團、大項目,幾乎全部轉到比海南晚起步的浦東新區。浦東一躍而起,而海南卻錯失了曆史機遇。
在大國重新崛起的道路上,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始終是我們處理與外界關系的底色。這種隱秘心理,有時候會像一個楔子般打入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中韓關系、中朝關系,影響著中國與世界的走向。
中國與外部的關系,是改革開放40年來第一個核心命題。正如當下中美之間發生的故事,也依然在延續這一命題。
而今天,中國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做使命,這也決定了下一個四十年中國與外部世界承轉啓合的方向。
天津
天津大邱莊,曾經是一片鹽堿地。
70年代,這裏靠天吃飯,窮得連附近的女娃都不敢嫁進來。短短十數年後,這裏就成了老百姓頂禮膜拜的“首富村”,三千多個村民,每個人的年收入均超過高級幹部。
大邱莊神話的締造者,叫禹作敏,一個身材瘦削的農民。他本人的座駕是國內罕見的奔馳600,當時全國只有兩台。而這個4400人的村落,有16輛奔馳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整個村子“富得流油”,每家都建起了別墅洋房。
1977年,禹作敏當選爲大隊書記。望著當時那片不毛之地,他明白即使分産到戶,每個人也只能分到一畝鹽澤地,依然窮得響叮當。只有搞工廠,才會有出路。
此時距離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有一年。中國還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禹作敏就突破禁锢,大膽奉行“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的理念,把一個農業社會的村子,硬生生撺成了工業社會。十年間,大邱莊辦起了二百五十六個小工廠,每年千萬的利潤,滾滾而來。
禹作敏很會鑽空子,也“敢于”蔑視規則。他給一些國家幹部塞“信息費”,以獲取市場信息;他給駐地大邱莊的工商部門、公安人員、法院人員開工資,換取免稅優惠和保護傘……
在八、九十年代,“指標即一切”的體制才剛剛塌了一個角,“出路”未明,很多法律建設尚未完善,膽子大的狂人反而更容易闖出一片天地。他們在灰色地帶遊走,攫取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從而獲取“能人”光環。而那些還沒弄明白時代是怎麽回事兒、急于脫貧致富的農民,一看有了帶頭人,紛紛歸順,一呼百應。
兩者相互交織,在後來的大邱莊迸發出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強人政治。
禹作敏在村口蓋起一座牌坊,命令所有訪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車,換乘大邱莊的迎賓車,俨然是古代皇宮門前的“下馬碑”;他還在村裏修築了九龍壁和九龍飯店,追隨古代帝王九五之尊的蹤影;有人說,大邱莊沒有法律,禹作敏就是王法,一條條辦公室內發出的指示好像是禦令聖旨。
大邱莊村口的牌坊
不過,生也權力死也權力。這個作風專橫的鄉村能人,最終還是栽在他自己身上。1992年12月,當全國各地都在被“南方講話”所鼓動起來的時候,地處北方的大邱莊一片蕭蕭寒意。
一位外來人被懷疑貪汙公款,禹作敏私設“公堂”,命令下屬將其關起來審訊,毒打7小時致死。事後老爺子還包庇罪犯,把前來辦案的警方關了起來。後來,400名武警開赴大邱村,禹作敏一聲令下,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集體大罷工,上萬名農民拿起棍棒鋼管鎮守村莊……
1993年4月,禹作敏被逮捕,而後服安眠藥自殺。自此,大邱莊陷入了沉寂。
人雖然走了,但禹作敏現象並未消失。對能人的迷信,對規則的漠視,今天仍給我們的社會運作造成一絲龃龉。敢于闖雷區的能人,或許能夠凝聚力量、打破發展枷鎖,創造出一個個亮眼的奇迹。但建立在蔑視規則上的成績,終究只是“眼見他起高樓”的一時興衰。
淩志軍在《變化》一書中曾說過,“改革之路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一些無法無天的人開辟出來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無法無天才能真正地成熟”。
人治與法治的關系,是改革開放40年第二個核心命題。而下一個四十年,該是制度代替枭雄的時代了。
從道路的命名“百億道”就可看出大邱莊的野心
深圳
當代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複興,從蛇口開始。
1979年,蛇口工業區批准成立。這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重要實踐,由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完成。他叫袁庚,一位土生土長的深圳人。
1973年,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被無端關押在秦城監獄5年半的袁庚終于出獄。隨後,他擔任交通部外事局局長,多次陪同領導出國考察,走過歐美那麽多發達國家,他深感中國其時之落後。
在深圳,袁庚站在一江之隔的灘塗上,遙望對岸燈火通明的香港,被兩地的落差震驚得久久不能平息。這邊,是頻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大逃港的浪潮一波又一波;那邊,是東方明珠,亞洲的驕傲。
搞情報出身的袁庚,嗅覺靈敏,消息靈通。自他從國家領導人手中“接過”這片36平方公裏的土地起,“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會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便始終萦于腦際。
袁庚擔任蛇口工業區總指揮期間,蛇口推出了多項在當時看來極爲大膽的改革舉措,比如超産獎勵、工程招標、人才招聘、住房改革、按勞分配、社保制度等。如今看來平常的動作,那時在全國卻有破冰意義。蛇口真正成爲了中國改革的風向標。
1979年,蛇口工業區在碼頭工程中率先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實行超産獎勵制度;1980年,蛇口工業區中瑞機械工程公司在全國率先實行工程招標,打破了以往“以領導意志爲轉移”的分配傳統;1982年7月,袁庚率先引入外資,成立中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南山開發……
有些老幹部們參觀完深圳特區後,回去放聲痛哭,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邪路”。改革,是一個隨時可能掉腦袋的事情。但袁庚說“大不了再回秦城”,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創造了24個全國第一。
除了經濟方面,蛇口改革最爲人稱道的是在配套制度改革上極具前瞻性——第一個進行民主選舉、第一個實行人才公開招聘、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第一個實現住房商品化……
在蛇口這個“實驗室”中,袁庚沖破了當時的兩大禁區:市場經濟和行政體制,成爲中國改革開放實操第一人。
他要求《蛇口通訊報》刊登批評領導人甚至批評自己的文章,讓權力受到監督制約;他廢除傳統的幹部任用方式,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蛇口管委會——這是中國第一個經過“直選”産生的地區領導機構。每一舉措,都是冰天雪地裏的一聲春雷,石破天驚。
40年過去了,如今的蛇口早已不是灘塗,但袁庚創造的“蛇口模式”中所蘊含的改革先鋒精神,仍在改變著中國。而他也成爲了改革開放40年表彰的傑出貢獻人物。
改革與舊利益格局的關系,是改革開放40年第三個核心命題。改革的勇氣,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貴而稀缺的,即使是今天。
袁庚
洋浦風波背後反映的中國與外部的關系,大邱莊現象反映的人治與法治的關系,蛇口改革反映的改革與舊利益格局的關系,在未來的改革開放路上依然是關鍵問題。
正如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所言,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
偉大進程“不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幹出來的”。
來源/智谷趨勢(微信ID:zgtrend)
編輯/點蒼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