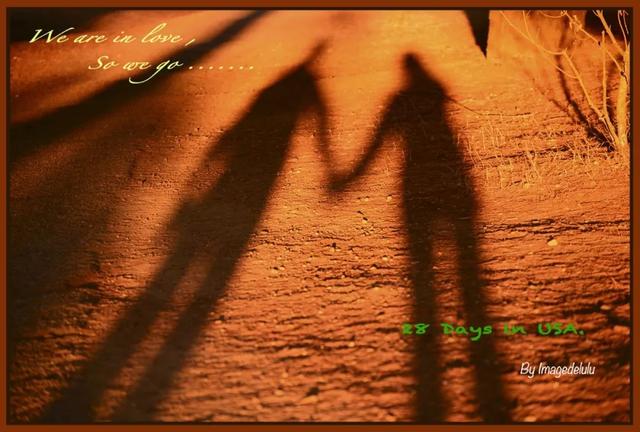中學的時候,我一直暗戀高我兩級的校草,看著他從高三,升到複讀班,沒讀完,就突然消失掉。
我本來可以只做一個安安靜靜的看客,把暗戀變成一種追憶,消散在開著栀子花的晚風裏,可沒有意外的話,生活將多麽缺少情調?
有天放學,我忘記帶東西,又折回教室去取,我正一個人在座位上找,突然有人來敲門說:“同學……”
我擡頭,魂都飛了,門口站著的,正是消失了很久的校草,他愣了一下說:“盧璐,你知道美術教研室搬到哪裏去了嗎?”
天啊,他居然,居然知道我的名字,幸福比原子彈的沖擊還要猛烈,讓我心跳到窒息。
兩個月之後,校草過生日,我買了一本很精致的日記本,寫了一篇文章:《十六歲,雨季不再來》。
轉天,他打電話給我,一副要通知繳費的口氣說:“明天,我去接你下晚自習。”
從那開始,整個秋天,他常常會來接我下晚自習,有時,是約好的,有時,是個驚喜。
我們的學校在一個小山上,我總是一溜煙兒地穿過正在放學的人群,就能看到,他穿著深藍色的風衣,站在桔色的路燈下面,180的身高,玉樹臨風。
總覺得心頭一動的甜,“燈下看情哥哥,眉清目秀”。
那年我16歲,他也才剛剛18歲,這也許就叫愛情。其實,我們什麽也沒有說過,但是我能想到但是沒有說出來話,都是類似于天荒地老,一生一世。
從秋到冬,法國梧桐很快就沒有了葉子。
深冬,我們爲了一件小事吵起來,不歡而散。轉天,他還如常地來接我放學。臨走把日記本給我說,“你回家再看。”
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家,心中有點末世的惶惶然。
我打開本子,反反複複地看了三遍,才看明白他龍飛鳳舞的兩行字:
“故事的開始,只不過是我在寫著玩和不玩紙團裏,抽到了那個玩。”
九十年代的青島,那麽小,在後面的幾年裏,我都還跟他有聯系。每次離他兩米開外,我就如一只霜打的茄子,慫到不能呼吸。
我甚至沒敢問過他,我們究竟算不算交往過。因爲前女友也是一個身份,我不知道我有沒有這個殊榮。
原來,愛情是一種軟弱的青澀,一碰就破了。
原來,在愛情中,並不是每一次付出,都會有美好的結局。
我在上了大學之後,有了第一個正式的男朋友。
他是我高中的同學。高中的時候,是個其貌不揚的土豆,高三的一個暑假,竹筍一樣,躥到182,朗眉劍目,看著他好像在看偶像劇。
我們並不在同一個大學,但是他總來幫我打水,打飯,搬東西,不止一個女生給我說:如果你們分手,第一手時間通知我,我領號。
他是個非常完美的男朋友,很高很帥很溫柔,鞍前馬後,很會寵我,把我捧在掌心裏。
我們在一起三年,很開心,很快樂,很幸福,但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不敢想將來。
他是從高二,就開始憧憬著吃完晚飯,哄著女兒玩的植物男人,而我是命裏寫著“驿馬”的動物女生。
我知道,我不會永遠地停留在這個海濱小城裏,或早或晚,我終將遠離,開辟自己的天地。
有的時候,人生和愛情,並沒有太大的關系,分手並不是因爲不再相愛,而是我們不再有共同的軌迹。
再後來,我誤打誤撞地認識了一個居然長到181的上海男孩子,憑空飄出來一段莫名其妙的愛情。
他給我申請了一個只有七位的QQ號,現在每次告訴別人我的QQ號,我說完了,別人還在拿著筆,等著聽。
那時候,他常常打電話給我,無論我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直到現在,我也很喜歡聽上海男孩子講普通話,有一點糯的兒音,不像是京片子的油滑。
有天深夜,他在電話說:“你明白我爲什給你打電話,我並不知道開始,但是我卻知道結局,可是我還不能說服自己……”
我從北京坐東航的飛機回法國讀書,到了機場之後,才發現居然是北京出關,去上海轉機。
我在浦東機場,買了電話卡,用機場的電話打給他,他驚訝又驚喜,“你在上海嗎?我來看你?”
其實,我不是在上海,我在已經離境的國際區域。
當巨大的空客,再次緩緩升起來的時候,我依著窗口,看著整個城市的萬家燈火,一遍一遍地說著再見,從此後會無期。
人生是一段長長的旅程,路上,我們總會遇到各種各樣,迷惑人心的妖精。
那些意亂情迷,有過就是有過,愛過也就可以走過。背起行囊,邁步再行。
我四歲第一次坐火車,18歲第一次坐飛機,22歲第一次出國,迄今,我去過近四十個國家,停留過,三百多個城市。
我人生最初的三十年,總是一個人在收東西,一個人上路,一個人拖著箱子,一個人到達目的地,然後再一個人慢慢地回去。
1999年的跨年夜,我擠在巴黎凱旋門旁邊,十秒倒計時,旁邊全是一對對法式深吻的情侶,只有我一個人看到,天上有燈火劃過。
2000年的跨年夜,我在羅馬的西班牙廣場,有人穿著紀梵希的黑裙子,裝扮成赫本的樣子,從台階上走下去,下面,卻沒有派克等在那裏。
2001年的跨年夜,我在四周垂立的布魯塞爾中心廣場,零點的時候,有人抛灑歐元硬幣。到處都是拿著煙花瘋狂的人們,我被擠到不能呼吸,只想隨著人群流出去。
我曾坐著只有三個車廂的小火車從塞維利亞去直布羅陀,整個車廂裏,只有我一個人,穿過空無一人的群山和河谷,仿佛是一場永遠也不會結束的旅行,一直開到世界的盡頭。
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票實在太貴,我站在雨裏執著地等,開場45分鍾後,有黃牛賣給我一張5歐元的票,三樓包廂的角樓裏,女仆坐的板凳。
讓我遺憾的是,走了這些路,我從來沒有過豔遇,但是我遇到過很多有趣或者沒趣的故事,吃過很多好吃或者不好吃的東西,看過很多壯麗或者不壯麗的風景,都慢慢地凝結成了一些淺淺淡淡的回憶。
可是時間太久了,有時候,我已經不知道,這究竟是我在風裏的臆想還是真正的回憶。
三十歲,是現代女人心力交瘁,強弩之末的一扇鐵門,我從29歲零8個月開始,就已經陷入不能掌握的歇斯底裏中。
在我三十歲生日之後的第四天,收到了一封郵件,朋友的哥們兒,爲了證明他真的很喜歡攝影,郵件裏附加了一張比硬幣還小,用電腦攝像頭截出來的頭像,像素低劣,畫面模糊,無框眼鏡後面,有一雙ET一樣,迎著光的藍眼睛。
好吧,知道的人都已經猜出來了,他就是我的先生,盧中瀚。
他其實不姓盧,只是爲了討丈母娘歡心,他跪地,請丈母娘給他賜的名。
原來有一種愛情模式,叫做自我膨脹,盧中瀚先生,唯恐自己不夠膨脹,唯恐占據不了我的人生,思前想後,還做出來眼睛大大的盧思迪,和卷卷毛的盧子覓。
從此我的人生終日不得清淨,從此我去哪裏,做什麽,都會至少一個人證。
迄今爲止,我們已經帶著兩個孩子,去過法國,西班牙,捷克,奧地利,希臘,匈牙利,芬蘭,葡萄牙,埃及,比利時,荷蘭,中國,斯裏蘭卡,美國,馬來西亞,越南,泰國,菲律賓,柬埔寨,印度尼西亞,斐濟,新西蘭,新加坡,韓國,馬爾代夫……,也許還有吧,一下子記不起清,而且很多地方去,不僅僅一次。
我把我們在一起的點點滴滴,都寫進了一本書裏,這本書的名字叫做《和誰走過萬水千山》。
不過請注意,這本書可並不是遊記,這本書,是用我的世界觀,來闡述婚姻與人生中的關系。
每一年,結婚率越來越低,離婚率越來越高,生孩子的人越來越少,婚姻越來越跟社會背離,可是我們結了就是結了,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緊不慢,不徐不疾。
再相愛的戀人,再熟悉的夫妻,我們總是有兩個大腦,兩個靈魂,總要在一起慢慢走,我們才能懂!
人生不過是一場旅程,根本是你旁邊的人,來決定你能到的風景。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我這本《和誰走過萬水千山》,和那個人一起,慢慢地,並肩走過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