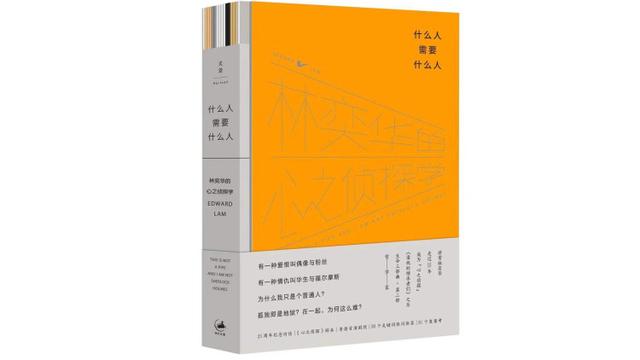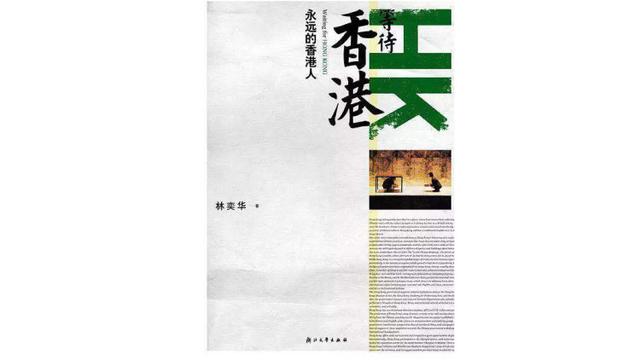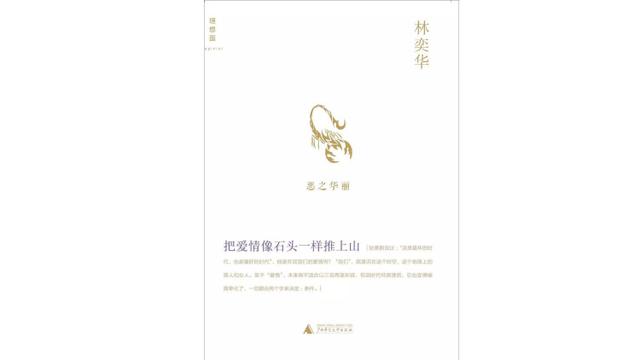如今,“斜杠青年”是個時髦稱呼,人們習慣用它來統稱跨界人士。以此來觀察,林奕華一定是個斜杠青年了。導演、作家、編劇、批評家……這些名號都是他的身份,但都不足以概括他。
最近,他創作的領域轉向了音樂劇。他的音樂劇《梁祝的繼承者們》,正在進行第二輪巡演,3月份林奕華來北京做了一場以音樂劇爲主題的分享,我們借此契機和林奕華聊了聊天:聊成長與家庭,暧昧與流行,滋養他的香港、台灣文化,以及我們當下的種種“時代病”——不追求穩定就是不成熟嗎?爲什麽成功學會成爲我們的新式宗教?爲什麽我們還如此年輕,就學會了後悔?
林奕華,1959年生于香港,是跨越劇場、舞蹈、電影等領域的創作人、批評家。1994年憑電影《紅玫瑰與白玫瑰》獲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1999年獲香港藝術家年獎。舞台代表作有《半生緣》、《包法利夫人們》、《水浒傳》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等,出版有《等待香港》《什麽人需要什麽人》等作品。近期改編自“梁祝”的音樂劇《梁祝的繼承者們》將于4月19日-21日在北京上演。
話劇導演林奕華,做了一部音樂劇——改編自“梁祝”的《梁祝的繼承者們》,主角依然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只不過兩個人的身份變成了藝術學院的學生。
18位演員,分別飾演著不同版本的梁山伯和祝英台,18首由林奕華填詞的歌曲,講述著成長、愛情、性別、藝術等多個主題:爲什麽我們不能和父母談生命的意義,只能談生活的意義;爲什麽書本能接受一盞燈的追求,而領帶只能和襯衫做同事;爲什麽一罐“屎”可以成爲藝術;而藝術,可不可以來治我們的“病”……
無論哪個主題,林奕華一直在強調“經驗”,人來這個世界走一遭,留下的最寶貴的東西就是獨立思考,父母不能替你生活,雞湯金句不能替你生活,卡拉ok不能替你生活。林奕華說有些流行歌字那麽多,就是爲了幫你完成思考,讓你在情感上對號入座,可是唱卡拉ok就像進“宜家”,雖然能嘗到“家”的滿足感,但那畢竟不是“家”。而只要你親身經曆過的,哪怕最後的結局是憑吊,那也不是“失敗”,而是“風景”。可是現在的人們,都把後悔的腳步提前了,以前的人們經曆過才後悔,現在連中學生都不想面對未來的痛苦了。
1
成功學,
大概是現在人們最信服的宗教
新京報:在《梁祝的繼承者們》中有一句歌詞,“長大長大,就是保護脆弱的羽翼”,你對“脆弱”怎麽看呢?
林奕華:把我放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下,或者環境我很熟悉但是我控制不了的狀態,對我來講就是脆弱。現在的人很喜歡去控制事情,如果不能90%-100%成功,那我就不去談戀愛了;如果我不一定會成功,那我就不去創作了。這種不打無把握之仗的想法,就是一種“脆弱”。你其實有兩個選擇,用盔甲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風,或者從盔甲中明白自己的脆弱。
就好比暈車,你爲了防止暈車准備各種藥,或者爲了不暈車就不坐公車,封閉了通向某種體驗的可能,你覺得克服脆弱讓自己強大了嗎?其實不是。你只是“把自己的腳指頭都切了,那沙蟲就咬不了你了”。這是消極的。
對于我來講,脆弱就是讓你意識到,你還有一些珍貴的、沒有長繭的那些感受的能力,這些能力其實是可以幫助你認識自己的。所以誰最不願意表現脆弱,男性。
《梁祝的繼承者們》劇照。
新京報:那你認可創作就是要表現脆弱的嗎?
林奕華:我自己的創作是這樣的。但不見得所有作品都要表現脆弱。不然現在漫威英雄怎麽會變成最大的票房來源?一定程度上我們需要這些英雄給我們鼓舞,給我們一種投射。他們這些英雄本身也有脆弱的地方,但是最終“結果大過過程”,最後這些英雄都出頭了,我們更希望看到結尾,而不是代入過程。
所以成功學大概是人們現在最願意信奉的宗教。成功學的框架下,最終被放大的就是我的業績、我的流量。我們現在的創作裏,爲什麽宮鬥戲那麽受歡迎,因爲它讓我們看到瘦小的女子有強大的力量。我們生活在一個鋼筋森林裏,生存是首要的,這樣一來就會放大“強悍”的重要性,所以我不認爲所有的創作都要表現脆弱,因爲有些創作最後還是要業績,要名譽。
創作是爲了讓自己更了解自己、讓別人更了解自己,這種想法並不是主流。但對我來說,表現“強悍”有時是“逞強”,人如果在還沒有接受自己的時候,就讓別人接受他,到最後會容易受到更大的傷害。因爲他制造了一個虛構的自己,到最後連自己都相信這個是“真實”的。這個虛構的自己,會用“背面”來面對自我,而不是“正面”。
2
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張國榮之前的張國榮
新京報:你的成長中,什麽是滋養你創作的養料?
林奕華:普及文化(流行文化——編者注),還是最俗爛的。這裏需要講我爸爸的家庭,我小時候到姑姑家,全部都是電影雜志、瓊瑤小說。所以我的童年裏全部都是電影,詹姆斯·邦德、歌舞片,還有《老夫子》……六十年代是全世界普及文化最興旺的時候,剛剛冒頭,而且香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大家也都有錢了,可以通過消費來滿足自己的文化需要。
普及文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模糊社會不同階層的界限。比如那個時候,我們有“邵氏”那種海派的(風格),雖然邵逸夫是新加坡人,可是他吸納了很多南來香港的大陸電影工作者,然後又把日本文化當作工具,所以我們有上海來的大明星,同時也有日本來的導演來重拍一些已經在日本很成功的諜戰片、家庭倫理片。我還會看一些很窮的粵語片,去複制其他電影。像蕭芳芳啊,陳寶珠啊,她們會學奧黛麗·赫本,把好萊塢的那些當作模板。這些複雜的東西共同彙合成爲我成長的脈絡,有中有西,有窮有富,有時尚,也有傳統。
這種氛圍一直維持到我從兒童成長爲少年。13歲,我去台灣念書了,“嘭”,開了另外一個窗口。哇,林青霞、秦漢、瓊瑤,另外一種風氣——校園、戀愛、純情。回到香港後,“嘭”,粵語文化又起來了,許冠傑、譚詠麟、張國榮、梅豔芳,一個接一個,全部都是流行文化的炮彈。這些流行文化跟美國英國不一樣,我們更雜糅,在張國榮他們身上全部都“有中有西”,還有“日”,現在更有“韓”了,這些會讓你的文化觸覺變成散發型的。
《什麽人需要什麽人》,作者: 林奕華,版本: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
新京報:我們現在都在懷念你們那個時代。
林奕華:在我們那個年代,並不會有所謂的“懷舊”,因爲全世界都還是新的。沒有梅豔芳之前的梅豔芳,沒有張國榮之前的張國榮。但現在大家都在找下一個“張國榮”是誰。現在的這些(偶像明星),大家都是“刷一刷”,就過去了,沒有辦法成爲“經典”。因爲現在不像我們當初那樣有時間,現在都太快了。以前是人們追明星,現在是明星來追你。
我們所謂的“粉絲”其實是“偶像”。你知道這些偶像和他們的經紀人會花多大的精力來“勾”粉絲嗎,不是你自然而然去追他們的,而是他們“撒狗糧”、做很多事情讓你去追他。以前張國榮不用做這些事情。現在時代完全不一樣了。以前是個性,現在是“符號”。
在對文化的學習和思考過程中,我慢慢知道了消費文化是什麽,Create(創造)和Produce(制造)有什麽不一樣,原來人格也是分創造和制造的。然後我就分出什麽是平凡什麽是平庸,最後區分出什麽是依賴什麽是獨立。而獨立思考,獨立人格,才是你來這個世界跑一趟幾十年,最有意思的結果。
《等待香港》,作者: 林奕華,版本: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9年5月
新京報:制造的人格,就是人設,最近幾年很火的話題。你怎麽看待人設這個問題?
林奕華:就是因爲電動遊戲玩太多啊。把電動遊戲的概念搬到你的人生裏來了,所以才會有那麽多人覺得狼狽,我們太習慣用formula(公式)來formulate(公式化)我們的生活。我們以爲“打通關”,就是人設的終極目的,可是這種人在鏡頭中,就是一個偏執狂。偏執其實是用來轉移你在真實生活中的手足無措,生活中的事情,不是你窮按一個“按鈕”就能解決的。
我最近還在跟小夥伴討論“Analog”(模擬)和“Digital”(數字化)的區別到底是什麽。用唱歌來比喻的話,以前科技不發達的時候,你唱的不好需要從頭來過,但現在在錄音室,你哪裏唱的不好哪裏重新唱一遍就好了。所以現在錄《我是歌手》很多人去不了,因爲他們是科技歌手。我說的“Analog”,就是要從頭到尾去完成一件事情,乃至人生。“Digital”就好比現在人們愛引用雞湯金句,可這些有你自己的思考嗎?別人的想法是會打架的,這時候你作爲戰場,要判誰贏呢。
人不能斷章取義地對人格進行設定,你需要有自己人生的完整邏輯,那才是主動的人生,而不是被動的“人設”。
3
“不穩定”就是“不成熟”嗎?
新京報:我想聽你對一個詞的“初印象”和“現印象”——“彼得潘”。
林奕華:“彼得潘”會讓我想起我的房間,睡衣,我成長的地方。現在“彼得潘”代表的是一種普遍的不願長大的現象。
新京報:你對這種“幼態持續”的現象怎麽看呢?持正面還是負面的態度?
林奕華:所有的現象都包含積極和消極的一面,我不會說“正面”或者“負面”。“積極”是因爲,它會給你提供了解它的契機。“消極”是因爲——“你能做什麽呢?”這些現象不是三朝兩夕的事情,它突然蹦出來,你就要成爲它的一部分嗎?
(回到)我們現在講到的“彼得潘”現象,你其實沒有辦法從一個外觀上去判斷他在思維上、人生態度上有多成熟。“成熟”是相對的,如果從社會化的角度來說,我是不成熟的。“社會化”就是你要去擔當角色,做符合角色規範的事情。而現在人們對“成熟”的定義是擔負起經濟上的責任:要把多少錢給家裏,要爲自己的生活做規劃,要爲老年生活做一些保險的事情。這些我通通都沒有。讓一個跟我一樣的年齡的人來談,我就像個中學生。我賺的錢遠遠低于像我這個年齡、有這樣工作經驗和人生經曆的人該有的水平。不過這是我願意的,我沒有那麽多家庭負擔。
但你說我跟一個中學生在思維上沒有差距嗎?有,差距就是我們走過的路。比如昨天劇場有個觀衆問我,我很喜歡一個人,但我不確定他喜不喜歡我,我還應該付出嗎?這種問題我現在不會問了。我只能告訴她,“付出”其實不是按照你喜歡不喜歡一個人來定義的,“付出”是你人生的態度。你平常如何看待事物決定了你會對什麽付出,而不是看見一個特定的對象再來思考要不要付出。
林奕華
新京報:所以未來的不確定性不會影響到你?跟你的家庭環境有關系嗎?
林奕華:我家庭有部分原因。我爸爸沒有父母,沒有受到父母期待的束縛。他是被6個姐姐帶大的,被寵的不得了。他想到什麽就說什麽,我猜我是蠻向往的,就像我們現在身處的房間,它給人最初的印象就是“光”。
新京報:你媽媽那邊呢?
林奕華:我媽媽是一間“有窗簾”的房間。我爸爸的家庭接受的是西化教育,他念完中學就去當海員周遊世界了。而我媽媽來自一個家道中落的家庭。我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長大,兩種我都看過。我的姑姑們又很疼我爸爸,我是我爸爸第一個兒子,所以我在我姑姑這邊想要什麽就有什麽。但我也很喜歡另一邊,因爲我的阿姨都很年輕。我爸爸的姐姐們住半山(香港豪華住宅區——編者注),我的阿姨住九龍西洋菜街,就是中下階層的街區,所以我到我的阿姨家去玩的時候,就會變得“街頭”,跟附近的小朋友在街上玩。
長大後我離開家,自己租房子,出國,我爸爸又搬到了內地,所以我在香港沒有家了。這裏住一住,那裏住一住。所以我只有皮箱,買了書全部堆在地上,因爲沒有書架。我到現在都是一個這樣的狀態,家裏永遠都是開不完的箱子,打包的箱子,隨時都有可能搬走。
新京報:這樣漂浮的生活你過了多久?
林奕華:應該從我離開香港去英國開始的,1990年到現在。
新京報:不想給自己買個房子?
林奕華:哪裏來的錢。
4
你會想和誰一起看鯨魚?
新京報:你說你向往爸爸自由的生活,是不是說明了你並不是你爸爸那個狀態?
林奕華:可以這麽說,我小時候身上兩種都有,我爸爸的狂放,我媽媽的內斂。我跟我媽媽比較親,她很內向害羞,我爸爸比我媽媽大十歲,他們兩個反差很大,我覺得這恰恰是我爸喜歡我媽媽的原因。我爸爸認識我媽媽的時候,她得了白血病,醫了一整年。我小時候經常聽到說本來不會有我,因爲醫生說我媽媽沒救了。所以我爸爸就跟我媽媽說,你能康複的話,我們第一件事就是結婚。
新京報:你說過男孩子都有少女心,喜歡一個人是因爲看到了和自己相同的地方。你的爸媽差距那麽大,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林奕華:“反向吸引”是年輕的時候特別容易發生的事情,就像冬天會愛上夏天。我覺得反向吸引是來自一種不安全感,比如我們看到一個人非常有條理、非常克制、跟自己完全不一樣的時候,我們眼睛會睜得大大的,以爲那就是我們想擁有的。不過人有很多類型,像我就比較願意跟不一樣的東西産生聯系,而有的人則不會對相反的事物産生幻想。
反向吸引到後來發生矛盾的時候,你會抱著一個什麽樣的態度去面對它,決定了你們能不能在一起。我爸爸媽媽後來離婚了,他們的婚姻維持了12年。他們很年輕的時候婚姻就出了問題。其實到了一個階段,你就會想,我的余生都要用這種方式去度過嗎?
《把愛情像石頭一樣推上山》,作者: 林奕華,版本: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年10月
新京報:說到感情,我想聽你再解讀一個詞,“暧昧”。
林奕華:暧昧,是必然會發生的,因爲總有說不出口的原因。王爾德曾經說過,我們這種愛是一種說不出口的愛。暧昧好玩的地方在于,你不知道對方喜不喜歡你,或者你不知道對方是把你當作一個男孩子來喜歡,還是女孩子來喜歡。
性別上的暧昧,會帶來情感上的暧昧。我們其實是很幸福的,因爲我們不會用一個固定的性別,來和對方發生情感上的聯系。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愛上另外一個男生,或另外一個女生。當情感的吸引力,超過了一般人對于性別的認知的時候,它就會把你帶進一個一般人從來沒有去過的空間。這種暧昧去掉了既定事實給你帶來的角色扮演的束縛。讓你回歸到中性的狀態,感受中性的自己。
我猜每一個人,無論以後和什麽人結婚生小孩,她或他生命中都曾有過這樣一個給予其暧昧情感的對象。暧昧的對象不像婚姻中的人是有角色的,我沒有辦法形容他是我的誰,但他確實曾經跟我非常親密,不可替代。
新京報:你認爲所有人都是中性的。
林奕華:你要相信人是中性的,這件事情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的。就好像你從來沒有到過芬蘭沒有見過北極光,就不相信北極光的存在了。但北極光可以發生在任何人之間,而且它不一定是綠色的。
新京報:在你的《梁祝》故事裏,祝英台爲什麽會愛上梁山伯?
林奕華:這就是問我爲什麽會愛上某些人。我覺得所有的愛,都有一個字——“憐”。你看見對方,就想要去給予。這個“憐”爲什麽會來呢?從某個角度講,你覺得你有,TA沒有,而有意思的是,你爲什麽會願意看見TA,也是因爲TA有的,你沒有。我覺得祝英台會愛上梁山伯,是希望他能再快樂一點,或者說她覺得他應該再快樂一點,這是一種情感的投射。
《梁祝的繼承者們》劇照。
新京報:《梁祝的繼承者們》有句很有名的歌詞,“我們會一起遇見鯨魚嗎?”這裏“鯨魚”是有什麽故事嗎?
林奕華:沒有。我那天只是覺得鯨魚……最簡單好了,我問你,你最希望和誰一起看見鯨魚?
新京報:……
林奕華:唉,你笑了吧。有些東西就是這樣,你希望它出現的時候,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看到。你可以把它解釋成一種少女心。80年代我看了一部法國電影叫《綠光》,女主角非常偏執,有很強的自我,談戀愛總是被甩。有一次她在火車站遇到一個男生,兩個人之間有了火花。傳說如果兩個人一起看著地平線,當太陽剛好在地平線上消失的時候,如果能夠看見綠光,兩個人就能快快樂樂地生活在一起。她就抓著男生去看落日。記得當綠光出現的時刻,整個電影院的人都“啊——”我會寫這樣一句歌詞,可能是因爲我看過這個電影。
《綠光》劇照(侯麥,1986)。
5
你在美術館哭過嗎?
新京報:在《梁祝》這部戲最後,你把“哭墳”的情節搬到了美術館。這裏的“哭”,哭的是什麽?
林奕華:啊這個問題是今天最好的問題。“哭”是哭自己錯過的事情。
現在的人後悔的腳步提前了很多,以前是你有經曆才後悔,現在是還沒開始經曆就已經在後悔了。連中學生都想回到過去,不想面對前面等待他的痛苦。這就回到最開始你問的彼得潘。彼得潘受到一次傷害,就認爲所有的媽媽都是壞的,這跟現代人爲什麽會拒絕情感關系比較類似,他只要當王,不要分享;只要權力,不要公平。但有意思的是彼得潘被溫蒂吸引了,當溫蒂把lost boys帶回家,彼得潘只是飛到窗外,他是想成爲其中一員的,但是他打死都不會承認。
小孩哭是爲了他得不到的東西,而大人哭,是爲了那些我本來可以有的、但是我拒絕了(的東西)。我覺得現在大家好像重疊了這兩種哭。你還很年輕,內心的矛盾卻已經大到口是心非,我們情願擁抱遺憾,也不願意在事情還有轉機的時候放下面子,去接受自己脆弱的一面。簡單說就是,永遠不要再提這句話,“認真就是輸了”。
《你有在美術館哭過嗎》這首歌講的,是經驗的重要性。美術館裏的藝術品是有故事的,每個人都在創造故事,制造經驗,哪怕你最後是在憑吊,那都不叫“失敗”,而是“風景”。
新京報:很多人覺得這種遺憾是一種美。
林奕華:因爲它被商品化了。我希望《你有在美術館哭過嗎》這首歌和卡拉ok歌不一樣。我有分享過,我之所以要做音樂劇,是因爲我極度痛恨卡拉ok歌。我覺得它是一種商業制度下的交換。它針對的是一種市場需要,很多人不能夠好好去理解自己的問題,所以填卡拉ok詞的人,會把人們各種心理活動合理化,告訴大家人生就是這樣的。
卡拉ok就像告訴你該同情自己,你是受害者,所以人們在唱卡拉ok的時候會得到釋放。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歌,每個人也許能多想一點。但現在卡拉ok歌基本都是——哇,它講得好“中”我——變成了一種對號入座。對那些沒有經曆過的人來說,這些歌曲已經建構了他們對于情感的態度。這樣的人生,會越走越狹隘。
我覺得這些問題是填詞者應該思考的問題,但是商業制度下他們沒有這個義務。但我覺得創作應該是主動的。這就是藝術和商業的區別。商業是服從市場的需求,而藝術是我們要帶著一些人走出狹隘。
新京報:你說藝術品都是有故事的?你看重藝術的曆史感?
林奕華:我看重人的曆史感。
新京報:可你覺不覺得現在的藝術已經跟曆史脫離了關系?
林奕華:這就是《梁祝的繼承者們》裏面的一首歌《我是一顆藝術屎》,講爲什麽大便會跟藝術史發生關系。
藝術家的糞便 | 皮耶羅·曼佐尼
意大利藝術家皮耶羅·曼佐尼1961年聲稱將自己的糞便分裝在90個罐頭裏,用當時黃金的價格爲自己的罐頭定價。這一系列作品在拍賣中賣出高價,還被英國泰特美術館、法國蓬皮杜美術館以及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收藏。如今《藝術家的糞便》系列作品價格,已經比黃金高出了數十倍。
藝術評論家約翰·湯普森評價:曼佐尼是對藝術家的身體和藝術産品進行批判,這種行爲和觀念直指了一個認知——即藝術家的角色和藝術家的身體,都能成爲一個産品,一個能夠被消費的物件。糞便在暴力性地反對它成爲商品的可能,但它還是成爲了消費循環的一部分。
我很想爲安迪·沃霍爾做一部戲,他掌握了現代人的心理,把自己當成了藝術品在創作。他把現代心理變成一個物件,這個物件本身就能打動很多人。現代概念藝術有很多爭議,但是它反射了人們的欲望。“藝術屎”把最沒有價值的東西變成最有價值的東西,其實就是在反射人們的心理。你說它表現了“愚昧”,那這也是它傳遞的信息。
“愚昧”體現在人們的跟風心理中。越多人買它,它就越貴。就像班克西(英國塗鴉藝術家)說他的作品也沒有多少價值,可就是因爲你們如此追捧他,他才要在拍賣會上銷毀自己的作品,他創作了一幅人們不能永遠擁有的作品。他的行動成爲了一種評論,這種評論才具有藝術價值。回到藝術和曆史的關系,他們(班克西、曼佐尼)就在創造曆史啊。
班克西自毀作品,拍出104.2萬英鎊(約合人民幣939萬元)高價。
換一個角度講,我們不會因爲擁有一張凡·高的畫,而感受到凡·高創作的心境。藝術的曆史,更重要的是藝術品的前文後理,在我們認知這個作品的時候,能夠因爲觀看而打開思考的深度、廣度和寬度。
所以我現在還在學習。我現在處在一個有更大學習意願的階段,它會讓我意識到我這個人還在“長。而我的存在對于別人來說是一種“陪伴”,剩下來的時間我會把我學到的、想到的拿來和大家分享,這種分享並沒有幫助到別人,我是在幫助我自己。
作者 呂婉婷
編輯 張婷 張進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