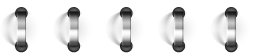前 記
2017年8月,商務印書館爲慶祝創業120年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一是13日舉行的商務印書館創業120年——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文化的興起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是21日舉行的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出版專家座談會。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前總裁陳萬雄和李祖澤分別參加了會議,我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對陳先生進行訪談,在“專家座談會”上對李先生進行訪談,主題都與陳原先生有關。
8月21日,在北京飯店召開的專家座談會上,我有幸拜見前來與會的李祖澤先生。
會前,我的心情非常忐忑,畢竟素昧平生,貿然打擾顯得過于唐突,簡直不知道如何開場,也擔心他因事情多、時間緊而婉拒我。但會議結束後見到他,心中竟升起一種溫暖的感覺——李先生給人的印象是儒雅、親切、隨和。他匆匆地浏覽了訪談提綱,同意安排訪談,並問了一下旁邊隨行的工作人員,然後對我說,不如坐我的車,中午一起吃飯,這樣節省時間。午餐是在華僑飯店,在座的有香港商務和台灣商務的出版界朋友。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我趕忙拿出會議發的商務印書館120周年紀念封,請他們一一簽名留念。李先生特意安排我坐在他左手邊。飯中氣氛非常輕松,話題當然是以李先生爲中心,一衆人稱他爲香港出版界的“彌勒佛”。飯後,他放棄了寶貴的休息時間,解答我關于陳老的幾個問題,還興致盎然地談了一些出版往事,以及記憶中的陳原印象。
李先生精神矍铄,記憶力驚人,幾十年的舊事記得非常清楚,普通話也講得特別好,他看我在做筆記,特意貼心地放慢語速。其間,因爲有一位老先生的名字想不起來了,他馬上打電話到香港詢問,可見其認真細致的風格。
此前我與李先生曾見過一面。2006年11月4日,陳原老去世兩周年之際,由商務的總經理楊德炎先生主持,在涵芬樓舉辦陳老的追思會,李祖澤先生和陳萬雄先生特意從香港趕到北京,滿懷深情地追思陳老。當時我沒有趨前請教,一直引以爲憾,沒想到十多年後又一次在北京見到李先生,而且圓了之前的心願,還與他合影留念。我在心中默念:真是托陳老的福!
會後,我匆匆將對兩位先生的訪談整理出來,想留作以後寫作陳原專題的資料,也就沒想找刊物發表。
2018年12月21日,商務印書館舉辦“爲書而生的智者——陳原誕辰100年紀念座談會”,李祖澤先生和陳萬雄先生都從香港趕來參會。我再次拜訪了兩位先生,先請陳先生在他著作扉頁簽名,然後把陳原家屬保存的李先生早年致陳原的信函複印件送給李先生,同時請示他能否授權使用。會議茶歇時,李先生走到我座位前告訴我,他的信函可以使用,並問複印件他是否能保留。他的慷慨和信任于我而言可以說是意外的驚喜,我連忙向他表達謝意。
《聽陳萬雄談陳原》經陳先生審訂後在《新聞出版博物館》2019年第2期刊發後,我才想起對李祖澤先生的訪談稿也應請他本人審閱。我沒有李先生的微信,不像與陳先生能在微信中溝通交流,只好通過電子郵件聯系。但郵件往來卻有一點曲折。我按李先生名片上的地址發出後,可能是某個環節出了問題,一直沒有收到回複,在不安之際,我又冒昧地按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葉佩珠女士的名片地址發了一封郵件,請她轉給李先生,沒想到當天就收到回複。她說,李先生最近身體欠佳,她會把文件送他家修訂。待李先生修訂後覆我,請耐心靜候。
2019年7月24日,我收到李先生發來的郵件,他信中說:“可能以前郵箱地址有誤,我沒有收到。香港商務葉總轉交給我才看到。這篇稿寫得很好,我修訂個別錯字後,再交葉總轉給你。謝謝!”7月26日,又一次收到李先生的郵件,附件是他審閱過的文稿,已轉爲PDF文件。他糾正了我誤記的個別內容,還仔細改正了簡體字轉繁體字時出現的幾個錯誤,如幹校的“幹”字,範用的“範”字等。我十分汗顔,簡轉繁後沒有認真審讀,以致出現這些低級錯誤。我回複李先生,“將謹記李老無言的批評,在以後的編輯工作中細致認真,如履薄冰”。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打斷了所有的計劃,愧對李先生的是,關于陳原與李祖澤深度交往的專題文章至今沒有完稿。現在重讀這份訪談稿,不禁回憶起那個場景,李先生親切慈祥的面容,娓娓動聽的談話和話語中的真情流露,都恍如昨日。
初冬微寒,遙望南天,恭祝李先生健康快樂!
2017年8月與李祖澤先生合影
訪 談
于淑敏(下簡稱于):李先生您好!從您與陳老的書信得知,您與陳老從1977年甚至更早的1975年就開始交往,當時您在商務印書館香港辦事處。陳原老1978年因病住院,您寫信問候致意,並說,“請多保重,我們還要你多帶二十年”。請您回憶與陳老幾十年的交往中,陳老給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麽?這二十年您收獲最大的是什麽?
李祖澤(下簡稱李):我與陳老,很早就認識了。因爲他的夫人余荻是我的一個同事余萍的姐姐,而余萍是我的助手。其實我們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就認識。那時,陳原是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陳原代表文化部出版局宴請我。所以我知道陳原是出版界的一位老前輩,語言學家,懂得六門外語。陳原是廣東新會人,你想,在北京,有一位長輩,會講廣東話,你會感到特別親切。
陳原老最大的特點是很謙虛。我其實更多是把他當作一位老長輩,要說跟他交往這二十多年的收獲,那就是,他是我知心的老師,我有問題都請教他,他都能給我很好的建議。我們互相之間能理解。我們交談,不只談出版物,也談人。比如,當時,怎樣把陳萬雄培養成一個出版家,每次到北京來,他都給我很好的建議。陳老認爲,一個學者,並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編輯,所以,他建議我重視培養陳萬雄的市場感覺,如何把知識變成市場,這是一個循環。當圖書變成資金回籠,這個出版圈才算完成,如果只完成一半,只是圖書出版了,沒賣掉,出版圈就沒有完成,書則變成廢紙。
陳原老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到五七幹校。他在幹校做什麽呢,他很聰明。那時,工農兵的領導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他做聯絡員,送信,到城裏取,來回跑,有點悠遊自在,那時,龍文善、楊德炎,他們都在一起,當時楊德炎是他的領導,派他到城裏取信,這也是鍛煉身體的機會,他也能借此了解社會動態。直到1972年他才從幹校回來。
陳老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作爲一個知心的顧問,我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他總用他的經驗來指導我,他有國際視野。
李祖澤先生審閱稿
于:您和陳原都曾主持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香港商務和內地商務是不同的發展路徑,您如何理解陳原個人對商務的意義?
李:70年代,我們出版界有“五君子”之說,是陳翰伯、陳原、丁樹奇、範用,還有我。每次我來北京,我們就聚在一起聊天,開始都是在範用家,有一次,我們感覺到不好,怕有人打小報告,我們就開車去盧溝橋,幾個人一起,無所不談,非常暢快。
1977年,我來北京住在華僑飯店,我請了陳翰伯、陳原,商量怎樣紀念商務80周年。當時上面對商務還沒有定論,三聯被批是黑店,商務是黑上加黑,既然這樣,我們就在香港搞商務的80周年活動,我決定出版一個大型的畫冊,請一些專家給我們題字。當時請翰伯、陳老幫忙請了茅盾、冰心、胡愈之、葉聖陶,他們對商務的評價,那時是冒著風險的。商務與中華書局在文革後期是合署辦公的,至1979年才開始分開。館慶活動非常成功。我寄來了一些畫冊到北京,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
商務80年代中期成立董事會,陳老是董事長,我是副董事長,林爾蔚也是副董事長。董事會最重要的工作,當時我給陳翰伯講,商務應該實行總經理負責制。但當時在內地不可能實現。董事會是虛設,商務的資産,需要董事會的授權,才可以處理,比如印刷廠等。
香港商務有一位張子宏,是陳雲原來在上海商務領導工運時的師父,我和他一起在商務工作。張公是香港商務辦事處的主任,他每次回北京,陳雲都派一輛紅旗牌轎車去車站接他。陳雲是很感念他的老師父的。張公管理印刷廠、店面,管編輯部。
香港商務中華,爲什麽能夠恢複?商務就是因爲張公在那裏,張是很愛國的,中華是吳叔同,“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因爲貪汙900萬,逃到台灣去了。“文革”時,商務只印一本毛澤東語錄,出版很難維持下去,後來,大約是1971年,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來北京,向周總理彙報工作。周總理突然問起,香港有一個中華商務,現在怎麽樣?
爲此,我們連夜寫好報告,寄到北京,報告香港商務中華的情況。總理在報告上批示了八個字:“加強領導,積極經營”。
因爲周總理的這八個字,香港成立工作小組,把我派到這個組當組長。這樣,我才與商務扯上關系。這個工作小組做什麽呢,就是恢複它的經營,重新審查圖書,准備重印。我與張公一起工作,老人家非常好,他用放大鏡看書。我們花了三個月,審查了1000多種書,分三種情況,一種是有問題的,停售;一種是一半有問題的,售完不再重印;一種是沒有問題的,可以接著賣。這樣,商務才有書賣。後來,張公退休回內地,我擔任香港商務的總編輯。
1980年,我第一次到法蘭克福參加書展,那時,世界不知道有香港,不知道香港有出版,主辦方甚至不同意給我們一個展位,我們到那裏很開眼界,幾十萬冊圖書,畫冊最多。我感觸最深的是,各國不論大國小國,都有介紹自己國家曆史的畫冊,只有我們中國是空白,作爲出版者,這是很慚愧的事。所以我們一定要彌補缺陷。那時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內地出版百廢待興,內地的印刷條件也不具備,所以我們決定在香港開始。
我們策劃出版的第一本畫冊,是出版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畫冊,這是周總理看過、批准的書,當時不能在內地出版,我們看後想對內容的編排進行一些調整,但沈老不同意,他說這是周總理看過的,應該原封不動。但這書稿總理是十多年前看的,最後沈老終于同意調整,以年代來排列。
(于注:陳原主持編纂的《商務印書館大事記》1987年版,在1981年的大事中記錄有,“港館出版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1997年出版的《商務印書館百年大事記》中,相關內容刪去了)
陳原老鼓勵我們這樣做,他那時主持北京商務,出版管理工作特別忙。
概括來說,“文化的理想,經營的頭腦”,是商務作爲文化企業不斷發展的最重要的經驗。
2018年12月李先生參加陳原誕辰百年紀念座談會間隙
于:1997年,陳原爲商務印書館百年紀念作《百年頌歌——千丈之松》,這是根據您的提議而作。請問,您提議創作“館歌”,爲什麽想到由陳老來創作?
李:1997年,商務館慶100周年的時候,我想到商務要有館歌,就想到陳原老,當時給他寫了幾封信,開始他不同意,我說他是希臘神話中的音樂神阿波羅,非他不可。我還說,最了解商務的其他人都去世了,就只有你最合適,你不寫誰寫?
我又是壓,又是贊,“逼迫”他寫館歌。後來他同意了,就是現在的館歌《千丈之松——百年頌歌》。歌詞寫得非常好,他引用張元濟、葉聖陶、茅盾等人的名言,其中只有張元濟的詞是較早的,其他的都是爲商務八十周年新作的。這些題詞都保留在商務印書館八十周年的紀念畫冊裏。
陳萬雄先生有一篇文章,談到館歌的創作經過,可以參見。(于注:陳先生的文章是《企業文化與精神的現代意義——由商務印書館館歌的創作及內涵說起》,是2017年8月提交商務印書館創業120年——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文化的興起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並在會議上作主題演講)
商務印書館館歌《千丈之松》
于:陳老在1997年說過,商務傳承在香港是陳萬雄,在北京是楊德炎,對他們寄寓厚望。您了解的情況是怎麽樣的?
李:按陳萬雄的條件,他隨時可以到大學做學者,做教授,不必像做出版這麽辛苦。很開心的一次是,1980年初,陳原、陳翰伯到香港考察,陳萬雄是1980年來商務的,二陳考察結束後,我給陳萬雄講,你還沒有度蜜月,你的任務一是護送陳老回北京,二是補度蜜月。當時他們是坐火車,兩夜三天,幾十個小時,我說,你一定要把這個人盯住。陳萬雄有很多想法,很多都是陳老的想法。陳老提出香港商務是從張元濟到陳萬雄,他把自己給淹沒了,這是陳原老在鼓勵他。陳萬雄每次到北京,像任務一樣,都去看望陳老。
我與陳原老是很好的朋友,只是相隔兩地,聚會不易。我們曾一起到過新加坡,考察商務的海外公司。我們很有默契,特別在陳萬雄身上,陳老花了不少腦筋。當然,這些我都沒有告訴過陳萬雄,這是陳老我們之間的秘密。
陳原老認爲,一個學者,只有懂得市場,才成爲一個好的總編輯、總經理。如果沒有這個轉變,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陳萬雄,陳老在堅定陳萬雄的信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下了很大的功夫。
1988年陳原(中)與李祖澤(左一)在一起
于:您在商務百年時提出“知商務者”,六人也。這六人(蔡元培、張元濟、王雲五、胡愈之、茅盾和陳原)中,您把陳原與商務的前輩先行者相提並論。請問,您是基于怎樣的考量?您的這一說法,得到陳老的認可嗎?
李:茅盾對商務的影響很大,他在商務很久,改革《小說月報》,今天的大會上提到茅盾;商務80周年時,陳翰伯特意找茅盾題詞《桂枝香》,其中有“順潮流左右應對”說得非常好。所以我說,茅盾是知商務的六人之一。
另外,陳翰伯對商務影響很深,1958年他主持商務。陳翰伯很幫我們,雖然他是局長。我對1979年版的《辭海》意見很大,認爲整篇都是“四人幫”的影響,儒家的語言都被廢掉,這是極“左”的《辭海》,我非常想重印出版1965年的《辭海》試用本,那本編得很紮實,于是我請示陳翰伯,問,你覺得怎麽樣?他說,我沒有聽見。我說,行,我明白了。《辭海》1965年版在香港重印出版後,影響非常大。後來《辭海》的修訂版,否定了1979年的版本,我們也在香港出版了。包括《現代漢語詞典》1977年在香港印行,1978年出版修訂版後,香港又出版了《現代漢語詞典》的修訂版。
于:陳老在80年代就想複刊《東方雜志》,但沒有成功,後來又想在香港複刊。請您談談陳老想在香港複刊《東方雜志》的情況吧?
李:複刊《東方雜志》,我也與陳原老提過,但條件不成熟,在內地出版,時間不能快,要做計劃,要審批,同時,總編輯不好找,我想讓他當總編輯,但他事情很多。與其這樣,若恢複《東方雜志》,沒有這個班底,就搞不好。後來一再考慮,就沒有出版這個雜志。而且當時台灣商務已經複刊了《東方》月刊,主編是金耀基。
我想,不能隨便搞一個雜志,沒有一個可靠的班底之前,還是不要出版。《東方雜志》原來的班子影響很大,不是隨便找一個學者,就能夠把雜志搞起來的。
陳原(右二)在香港,右三爲李祖澤,右一爲陳萬雄
于:出版界都認爲,陳老主持商務印書館時,是80年代最早實行改革開放的,而與藍燈書屋的合作,是通過您進行的。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李:當時藍燈的總裁,是韓國人,對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很熱愛,他很想與中國的出版社合作,我們是在法蘭克福書展認識的。藍燈有一個大的詞典,美語詞典,商務與牛津最早有合作,也是我們介紹的,商務與牛津合作出版英語詞典,美語詞典也應該出版,我們是介紹最好的出版社與商務合作。
陳原組織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當時也有不同意見,但它利于東西方文化交流,利于我們吸收西方先進文化思想。漢譯名著叢書能做到今天,這是陳原對商務的重要貢獻。
商務的對外合作,後來還因爲楊德炎發揮了重要作用。楊德炎的德語說得非常好,這有很多故事。有一年,我與許力以、楊德炎,還有龍文善,在法蘭克福書展,楊德炎走在後面,後來我們發現楊德炎怎麽不見了,失蹤了?原來他被德國俱樂部的人拉進去了,以爲他是日本人,後來他講一口純正的德語,把那些人嚇著了,把他給放出來了。
于:陳老晚年在香港商務想成立漢語語詞庫,是請王濤先生在做嗎?請您具體介紹一下。
李:王濤編過《漢語大詞典》,是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的社長,他夫人是鋼琴家,他到香港後,因爲有做過“漢大”的經驗,有漢語數據庫的經驗,所以主要工作就是在商務做數據庫。他與陳原老聯系的多,因爲陳原是語言學家,“漢大”也是陳原的工作之一。爲一本書,成立一個出版社,可見國家多麽重視。王濤後來做漢語資料庫,是陳萬雄負責的。
于淑敏2017年8月30日整理
李祖澤先生2019年7月25日審訂
(感謝陳原先生的兒媳何敏提供部分照片)
責任編輯:郭豔紅
秦穎攝
作者簡介
于淑敏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審。1990年研究生畢業于河南大學中文系,先後在鄭州航院、河南日報社從事報刊編輯工作。業余研究中國出版史及出版人物,編注《陳原序跋文錄》(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近年在《中華讀書報》《文彙讀書周報》《出版科學》《中國出版史研究》《出版史料》等報刊發表十多篇文章,間或發表散文作品。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出版六家公衆號的所有內容,均爲原創。
未經許可,請勿使用。
歡迎合作、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