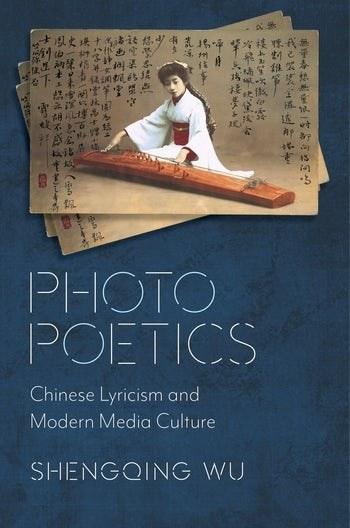吳盛青
【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曆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爲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曆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並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吳盛青與三位分別身在東京、新加坡、紐倫堡的青年學者共同討論其新著《光影詩學:中國抒情傳統與現代媒介文化》(Photo Poetics: Chinese Lyricism and Modern Media Culture)。本文爲吳盛青對三篇書評的回應文章。
吳盛青(李佩桦攝)
西諺有雲,書自有它的命運。感謝段書曉、趙振興、王瑞分享他們閱讀拙著 Photo Poetics: Chinese Lyricism and Modern Media Culture(《光影詩學:中國抒情傳統與現代媒介文化》,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後的意見,三篇書評分別題爲《詩心題鏡影,銀鹽現丹青》(段書曉)、《跨越媒介的有情的光影》(趙振興)、《媒介間性中的抒情傳統》(王瑞)。三位書評人對拙著付以真摯心意的閱讀,深入闡發本書未完成的學術抱負、意義框架以及未來指向。Photo Poetics(暫譯《光影詩學》)的緣起是當年我在撰寫關于晚清詩詞的博士論文時,經常在晚清人的集子裏讀到“自題小照”這類小詩,出于好奇,開始關注相關的話題。一個沒有藝術史訓練的人,就這樣以一種無知無畏的姿態闖入了一片文字與圖像、詩與照交涉互滲的地帶,一本書的輪廓也在沉酣故紙堆的過程中日漸明晰。
這本書主要想回答的問題是,當毛筆遭遇快門,傳統的詩、書、畫的組合,在何種意義上能擴展到新興媒介環境中?這種新的圖文關系如何相互作用或彼此抵觸?技術化的攝影如何成爲抒情的媒介?作爲一個文學史研究者,跨越傳統學科受訓範疇,涉足攝影史的研究,我一直有種步步驚心的感受。所幸得到三位學人的肯定,他們集中指出本書命題立意的關鍵在于“突破常規視角限制的全方位考察”,強調媒介“之間” (in-between)或者間性的討論(段書曉);“在20世紀初那延續千年的中國抒情傳統,如今又借由攝影媒介,在新時代找到了靈光一現的陣地”(趙振興);“質疑科學啓蒙的主流集體敘事,將中國抒情傳統的審美主體、個人表達與情感結構置于現代攝影技術、大衆印刷媒介、世俗化的道釋思想與宗教實踐的本土社會生活中動態地研究當時人們關于現代性的想象與現代化的實踐”(王瑞)。在多有認同肯定的同時,三位學者亦指出了本書的諸種不足與遺憾,皆中肯綮。遂綴此篇,簡約回複如下。
首先,我多年來一直孜孜矻矻糾結于所謂的抒情傳統的現代轉化問題,我的前一本書《現代之古風:中國抒情傳統的現代轉折》Modern Archaics: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1900-1937(哈佛大學東亞出版中心2013年版)討論的就是晚清民初的古典詩詞寫作,試圖超越五四啓蒙話語展示這一舊文類融入現代文化的強悍生命力。而《光影詩學》旨在探討一種廣義上的抒情特性(lyricism),姑且稱爲抒情風,以耐人尋味的方式形塑了現代視覺媒介文化,以及民國文化人調動傳統美學資源在處理新的圖文關系中所煥發的創造力。以“意”爲脈,本書勾勒在新媒介環境中一條或明或暗的“詩意”流動的版圖,詩歌作爲文類、詩意作爲共享的抒情特性的再媒介、再經驗的過程。因而,“真實性”、“真”、 “幻”、“變”、影像虛構性背後的文化母題與認知模式,是我在書中反複探討的話題。“真”之義,在近代攝影文化語境中歧義紛出。笠原仲二等學者早已指出,傳統美學與哲學話語中的“真”的概念不同于科學客觀性概念、或康德意義上的客觀有效的普遍性,而與“神”、“氣”、“禮”等概念意同。本書第一章關于肖像照的討論、第六張關于美術攝影中“風景”的論述,都涉及對“真”的把握與理解。三位書評人顯然都對第六章有偏愛,趙振興如是概述,“民國畫報攝影家們對待場景的態度不再是再現真實的生活形態,而更多的是將攝影術視爲徹底改造現實、回應心智、捕捉理想主義終極 ‘真理 ’的新契機”。傳統美學中的觀看之道,不是僅僅仰仗感官經驗的看,而是集視點遊動、目識心記、遷想妙得爲一體的綜合性的審美體驗。無論是肖像照,風景照,還是靈魂攝影,拍的不僅僅是眼前所見之實景,而是對語言與文本中先驗存在的經驗的呈現,是抒情之“心眼”、“心象”對視覺現實主義的反動與改造。最近,哈佛東亞中心出版的顧伊老師Chinese Ways of Seeing and Open-Air Painting(哈佛大學亞洲中心, 2020),梳理了寫實主義、室外寫生、焦點透視等概念及民國時期相關藝術實踐,頗有新意。但我這本書取徑相反,意在探討西方視覺現實主義的概念與實踐進入晚清中國後,是如何被僭越、吸納以及偷梁換柱的。段書曉敏銳地指出了真實觀念的複雜多層性,認爲只有在兩種“真實”觀念的針鋒相對、彼此佐證下,才會“有更深入和激動人心的推進”。這是相當精彩的提醒。趙振興援引錢鍾書先生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對詩與畫的兩種不同評判:“論畫時重視王世貞所謂‘虛’以及相聯系的風格,而論詩時卻重視所謂‘實’以及相聯系的風格。”此處所謂“詩中之實”,是與“詩言志”的傳統理念有關。山水詩中當然可能有虛構誇飾成分,但其寫作與閱讀的基本期待即是,詩中表達的是自我親曆山水的真實體驗的片段。而“畫中之虛”則是指畫家通過想見、臥遊等審美機制去描繪想象中的山川景致。“詩中之實”與“畫中之虛”的邊界有時也很模糊。趙振興問道,“作爲一種兼具‘虛’與‘實’、詩與畫多重成分的‘混合性媒介’的中國山水攝影,它是否同時亦包括了攝影家們親曆山水的‘自傳性’成分和某種程度的‘非虛構性’特征?”該問題對我們理解民國美術風景攝影頗爲關鍵,而我在英文版中未能詳細展開。簡單來說,民國美術攝影的興盛與便攜照相機的流行有很大關系,攝影人要親曆山水,置身于山水間,這其中“自傳性”、“非虛構”成分占主導;同時,山水風景不是信手拈來,可以隨便入鏡的,此處的“風景”必須是有人文曆史積澱的地景名勝,有詩情畫意的美術風景。民國攝影人開始強調“取景”與構圖的概念,張藝影解釋說,“審美觀念通過鏡箱的媒介而表達于作品所經過之途名爲‘取景’”(《審美觀念與取景》)。攝影,是詩之影,亦是心與物交錯下的光之影,是親眼所見之景與審美觀念的協商交涉的結果。本書對觀念中的圖景與“再現”了的真實之間的相協相阨,闡發未晰,還需要在一個更爲廣闊的視域融合的前提下去剖辨其間的玄奧與複雜。
套用麥克盧漢的著名說法,媒介是人的感官經驗的延伸與擴展。技術媒介作爲現實一種,已深刻改造了現代人的感官世界、情感結構與生命體驗,成就“有情的光影”(趙振興)。但當我過于迷戀傳統的抒情姿勢,大張旗鼓地頻頻強調傳統文化在現代語境裏的中介催化之功用,三位心思缜密的書評人都注意到了這些圖文實踐中脆弱、幽暗、虛張聲勢的一面。段書曉認爲,“在作者提到的圖—文間張力的例子中,可以看到隨著現代性的一步步展開,攝影自身的語法和表現力一步步掏空了其周圍的詩歌,使其變得僵硬、陳腐和不倫不類。”趙振興指出,“從情感上講,書寫題詞是一種有意識的、但又脆弱的嘗試,以填補被擦除所撕裂的空隙,防止記憶形式逐漸消失。”段書曉認爲本書對諸如圖5.14(王敦慶的《諸濤山靈魂攝影》)、圖6.6(李世芳的《似水流年》)闡釋開拓力度不夠。這些飽含“詩意”的時刻已經在使用一套全新的視覺語彙,而不是傳統的“詩情畫意”所能囊括的。王瑞亦指出,第七章中關于上海寶記照相館歐陽慧锵的《攝影指南》的案例研究中,筆者只關注到康有爲的畫意點評是將攝影作品置于傳統繪畫的範疇裏,套用陳規俗語來褒揚老友之子的攝影作品。受制于“問題意識”,本書聚焦在傳統抒情文類與攝影的這場邂逅,與白話相關的內容我均很少涉及。王瑞問道,康有爲公式化的點評與歐陽慧锵精確的技術參數的記錄之間有無緊張之關系,當時代的讀者會如何理解此類寫實風景照與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字之間的並置關系?這些問題都值得繼續探討。對傳統“詩意”的預設,或者被召喚回來的古典詩意,既有可能變成陷阱,也有可能在新的媒介“裝置”裏被重新賦形。段書曉打了個生動的比喻,說手裏有兩張牌,因爲配置不同而決定了不同的牌面及其結局。傳統在現代的延續或者延異,更多地呈現詭異的分裂、錯置,乃至翻轉。現代性中的褶皺、“刺點”、“即逝”及其間的錯綜複雜,還有待于更爲小心的厘析辨證。
段書曉指出本書在處理材料的問題,“材料充實可能帶來的一個小小弊端就是好材料太多,難以取舍,論述過程易生枝蔓,有時候一個主題下的材料太過豐富,每一個材料都指向不同的問題,就會使得大主題的統合力度不夠,而衍生出去的小主題又沒有篇幅深入展開。”王瑞指出本書的第三部分,“有些案例分析似乎比較匆忙,未能形成步步深入的論證,給人略有材料羅列之感。”兩位學人都委婉指出,本書在涵蓋大量原始材料的同時,有時逸枝衍蔓,有的個案則需要更爲深入的探討。用定點橫斷,還是曆史縱貫方式來裁剪一手材料確實是個涉及方法論的大議題,在今天這個數據庫時代更是如此。作爲一個文學文本的研究者,這部書的寫作給我帶來的一個巨大快樂是我因而得以走訪了許多圖書館、大博物館。進入“一個掩埋在時間廢墟之下更爲幽微的人的情感與想象的世界”,趙振興將之稱爲“抒情的考古”、“影像的考古”,而我在此也就欣然領受了。猶記得當年在上海圖書館的近代文獻資料室、複旦文科圖書館的近代資料閱覽書庫裏被有才的民國人逗得樂不可支的情形。面對不同語境中讀者的閱讀期待,英文寫作必須刪去大量原始材料,爲不熟悉文化語境的讀者講述一個相對明白曉暢的故事。而日後出中文版,我可能還會不懼其雜,添加更多的細節例子,但段書曉、王瑞都提醒了我這種缺乏脈絡化的處理、浮光掠影的論述的負面效果。由小知大,見微知著,亦是我對自己的問學期待。但與此同時,我一直非常關注意象、修辭方式在不同文本間的輾轉流離。希望通過對這些意象旅行、概念變遷的描述,來揭示晚清與民國文人觀看與理解世界的思維定勢,抒情表意背後一整套制約規範的象征體系。在大量浏覽了各種畫報期刊、詩集影集之後,諸如化身、喚真真、真幻、寫意、紅粉骷髅、靈魂等關鍵概念亦隨之呼之欲出。這種思考與書寫方式的弊端就是往往不能兼顧兩端,或許有了曆史譜系的勾勒,但少了些對局部紋理的深度描繪。
段書曉同時提出了幾個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意象,例如舊詩中“藥”、“仙藥”與感光劑、顯影水的混搭。王瑞亦指出,把顯影水當仙藥,把照相機當魔鏡,晚清有其他文本也可佐證這類在暗處湧動的“幽傳統”的隱形力量,“現代科學技術是被理解爲具有魔幻性質的”。段書曉進一步認爲,晚清“像”“影”“鏡”等指稱,在將新的視覺形式納入向舊的概念框架時,本身亦是翻譯問題,“在考察以語詞爲載體的概念框架對接問題時,翻譯所帶來的語義嫁接問題可能是不可忽視的一環”。此說極是,觀念與術語的厘清辨析的確是近代文化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陳寅恪先生在1936年說過的一句話廣爲征引,“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循此思路,細繹一個詞語在新舊語境中的接受與意義的擺蕩就是一部微型近代文化史,而日本在其間扮演了至爲重要的中介角色,很多想法、實踐都可以在近代日本得到參照佐證。如前所述,我一直十分關注“寫真”一詞,並爲“真”的概念困擾很久。北美學者對早期日本照相史中“寫真”一詞的釋義,均聚焦在明治之後,強調技術之眼對視覺現實主義觀念成型中的關鍵作用。這與我所理解的晚清影像文化中的“真”意涵相去甚遠。後來我在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讀到這本東京都寫真美術館編的小冊子《寫真渡來のころ》,頗爲興奮,與我所想遙契相合。策展人橫江文憲明確指出“寫真”中“真”之義,指試圖超越外在形式來把握主體的內在性,“只有整合對攝影對象的外表與內在的把握,肖像攝影方顯爲真”。在此,我們借他鄉之鏡照見了自己。筆者也希望日後能對“藥”“像”“鏡”等攝影文化中的關鍵概念在近代的縱橫流變,作更爲深入的梳理。
三位書評人都指出了未來可以繼續拓展的範疇、材料與議題。近年因爲受羅蘭·巴特《明室》等經典作品的深刻影響,諸如張愛玲《對照記》中死亡、愛欲與影像的話題備受關注。其實廿世紀的圖文、詩照關系中,女作家中除了張愛玲,吳芝瑛、周煉霞、陸小曼的詩、書、畫、照都值得從媒介的角度切入討論。至于有關民國時期的白話文學與攝影互動的議題,英文學界中William Schaefer的Shadow Modernism: Photography, Writing, and Space in Shanghai, 1925-1937(杜克大學出版社, 2017),對摩登上海現代主義小說中諸如蒙太奇手法的運用多有討論。在當代媒介理論研究中,無論是對ekphrasis 的討論,照片的文本化、敘事性,各種文學文體寫作中的視覺化,均是學術研究增長的興奮點,相關內容可參考弗朗索瓦·布魯納的《攝影與文學》(中國攝影出版社2016年版)。近一二十年,中國早期攝影史研究也開始爲海內外藝術史家所重視,英文的研究中巫鴻老師、伍美華、Claire Roberts等都有深入透辟的論述,仝冰雪、顧铮老師等都對本書的寫作提供過許多幫助。總之,面對大量還未被涉獵的曆史事迹,無論是從攝影與印刷媒介史的角度,還是抒情風中的審美感經驗與修辭格式等方面,都可以成爲我們打開民國媒介文化的諸種方式。
最後,感謝金雯、康淩兩位老師組織此番對話,謝謝三位學人同好段書曉、趙振興、王瑞的惬心貴當之言。吾道不孤,感謝在2021年的春天有這樣一場奇妙緣遇,促我反思,也與學海同道者共勉。
Photo Poetics: Chinese Lyricism and Modern Media Culture(《光影詩學:中國抒情傳統與現代媒介文化》),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