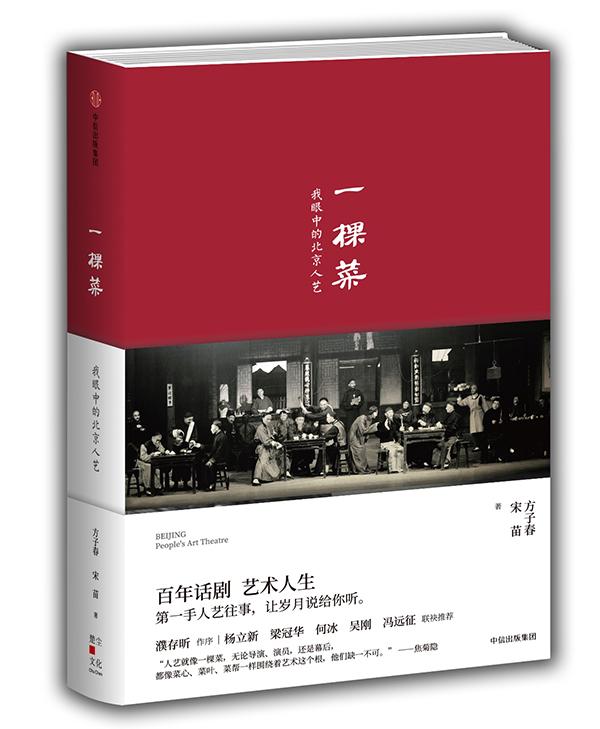【編者按】
顔值時代,演員能否將提升自身修養當作職業信仰,關乎中國影視業發展的未來。
2018年4月,楚塵文化策劃出版了演員方子春和丈夫宋苗合寫的《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藝》(中信出版集團發行),書中展現了焦菊隱、歐陽山尊、藍天野、呂中、朱旭等41位“人藝人”對藝術的不懈追求,更有吳剛、濮存昕、馮遠征、楊立新、何冰等人的口述實錄。
作者方子春是北京人藝著名表演藝術家方琯德的女兒,從小成長在人藝的大院中,親眼目睹和見證了北京人藝的人和戲。她在書中爲讀者展示了這些演員熒屏之外不爲人知的另一面。
看完41位人藝人的經曆,你會對“戲比天大”、“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和“一棵菜精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授權摘錄書中部分內容逐篇刊發,以飨讀者。今天我們刊發的是演員楊立新的口述。
楊立新和我很熟,熟到去他們家不用提前打招呼,可以隨便著裝,不施粉黛。我們住得不遠,我和他夫人關系甚好,平日裏有來有往。立新很忙,他在家時我反倒少去,怕打擾他。
自從我有了出書的想法後,我又像平日那樣去他們家討主意,兩口子也像往常那樣爲我出謀劃策,使我本無目標的寫作有了明確的方向。只是我有一點沒說,就是也想好好寫寫他,寫寫這個聊起戲來充滿激情的人。
我常說自己是演藝圈一農民,平時很少應酬,基本不參與什麽大吃大喝的事兒,晚9點就上床睡覺了。楊立新卻是個夜貓子,越晩越精神,加上他最近要拍電視劇還要排戲,當我爲組稿走進他家時已是晚上9點,正是我平時睡覺的時間。本以爲我會犯困,沒想到我們一口氣聊了四個半小時卻全無睡意。言歸正傳,聽聽是什麽把我的瞌睡蟲趕走且夜半時分還讓我意猶未盡的吧。
寫人藝首先要談人藝在楊立新心裏的定位。立新說:“一個劇院要有自己的風格。北京人藝的土腥味兒絕不能丟,人藝如果丟了土腥味兒,就沒有北京人藝了。人藝絕不是斯坦尼,也不是歐美電影,不是實驗話劇院,也不是青藝,人藝就是自己。
“人藝如果全都從理論出發,到理論的結果,再到理論的演出,人藝就沒了。所以人藝的演員特別注重體驗生活,生活在人物之中,要做到‘像不像,三分樣’。例如黃宗洛老師排《龍須溝》時,他在排練廳門口弄堆泥,要進排練廳排戲了,先在泥上踩吧踩吧,帶著人物的感覺再走進排練場。”
他又談到了首都劇場:“北京人藝建立于1952年,首都劇場建成于1956年,劇場的風格和劇院的風格是統一的。如果你坐在首都劇場的22排(最後一排),你會發現首都劇場的台口像是鑲著個寬寬的金邊,像一個相框的邊,如果相框中放入列賓的《伏爾加河上的纖夫》,就是一幅漂亮的油畫。由此不難看出從劇場的設計上就奠定了人藝的現實主義基礎。演員出現在舞台上定住格,應該是一幅幅畫。每一個插畫應該是有動作性的、有欲望的、有人物行爲的、沖動的、有可看畫面的,所以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劇院。”
我理解楊立新在這裏所說的“可看的畫面”就是戲劇。他說:“演戲歸根到底就是劇作者內心有的那點沖動,原汁原味地將其寫成了文字,當讀者讀到這些文字又能感受到這點沖動時,就是一個好的文學創作。同樣的道理,演員讀出了編劇的寫作沖動,演員在舞台上把這份沖動傳遞給了觀衆,觀衆接受的同時,根據自己的生活閱曆有著不同感受,把感受升華擴大,形成整個劇場的沖動,這就是戲劇。你把內心要寫、想寫的東西記錄下來,讀者一定會有沖動。魯迅有部作品叫作《呐喊》,你連‘呐喊’的欲望都沒有,只是寫‘你滾,痛苦死了’,這沒用,讀者感受不到。一定要呐喊,你拿文字記錄下來,喊出來,這就是激情。
“不論什麽故事,拿‘二爲’尺子一量,是爲人民服務嗎?是爲社會主義服務嗎?那就無法寫了,沒有按照方針寫東西這樣的規矩。當然,也別把話劇說得那麽神,說多了就複雜了,理論多了就繞了。北京人藝就是這麽土,排《雷雨》時,朱琳就經常問曹禺,您這段戲什麽意思啊。曹禺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把自己內心那麽多的憤懑、痛苦全都寫了進去,絕不是梳理成章後才落筆。這是激情,不是理論的作品。”
談到對戲劇的理解,我想楊立新年輕時並不是個文藝青年,他也沒有拿著考生號牌考中央戲劇學院那樣的經曆。在去人藝之前,他甚至沒看過話劇,只是被人拉著上過台,僅僅在台上不害怕而已。他說自己是在北京南城珠市口長大的,那裏的劇場、戲園子、電影院比較多,光劇場就有前門肉市的廣和劇場、鮮魚口的大衆劇場、糧食店的中和劇場、天橋的萬盛劇場、陶然亭的中國戲校排演場、虎坊橋的北京市工人俱樂部等等。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劇場環繞的特色依然很明顯。
楊立新跟隨家長看的第一出戲是河北梆子《八大錘》。當時的他只有四五歲,小孩最純真的時候看戲,很容易當真,他把台口的框給忘了,被台上的大花臉嚇得直往後躲。“文化大革命”時,他經常踮腳趴在台沿上看《紅燈記》,後來還有電影《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這些戲都非常經典考究。他就這樣不停地看,從電影看到舞台,逐漸得到了熏陶。其中,戲曲的節奏、韻律,以及劇情,無形中爲他後來的話劇生涯做好了前期准備。
“我看的第一出國內話劇是20世紀70年代在青藝演的,內容好像是當時林彪的一號通令剛剛下來,全國人民都在爲執行黨中央的緊急命令像打了雞血一樣地努力工作著。那個戲就是表現一個印刷廠爲了趕印中央文件而連夜工作的故事。戲中具體的情節內容都已經記不住了,只記得當初的印象非常強烈:話劇怎麽這麽難看啊!
“所以當1970年代中期,我調到北京話劇團後,也就是有了一份糊口的工作,沒有激情,沒有新意。不來話劇團,沒有這份工作,那就得去插隊。到劇團總比插隊強吧?于是1975年,我與叢林、張萬昆、張華、劉章春等人就這樣懵懂地撞進了人藝。抱著這樣的心態,沒有太多的欲望,內心當然不會浮躁,反而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北京人藝有句話:畢業就演大主角是一大災難。你沒那能耐,站在台上會哆嗦,私心雜念太多,肩膀扛不起這大梁。”他看我不解地看著他,便不慌不忙娓娓道來,闡述他的觀點。
他提到了一部那個時代人都很熟悉的戲《萬水千山》。這是一部以總政話劇團的演員爲基礎,又借調了好幾個部隊文工團的力量,排練的一部反映紅軍長征的史詩級話劇。正是通過這個戲,楊立新扭轉了對話劇的看法,他第一次覺得話劇怎麽這麽好看。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楊立新與劇院的同志們打著腰鼓從劇場一路出發,穿過王府井,走到天安門。年底,劇院無戲可演,就移植了總政話劇團的話劇《萬水千山》。童弟演李有國,朱旭演國民黨劉軍長,楊立新演敵副官。當時有老同志講,這個戲不是人藝的風格,地方劇團演軍人的戲不如部隊文工團,有位老師在草地上有段歌唱得直跑調。而楊立新卻通過這個戲得到了很好的鍛煉,他身兼數職跟衆人扛著槍跑場、站場,這是一個特好的實踐過程。有了演小角色的經驗在台上就不緊張了。他覺得別把演戲說得多神秘,說得神秘了就把所有的人都嚇死了。
“剛上台的人,一定得給他一個簡單的東西,讓他去完成。告訴他不要考慮得太複雜,待到完成了,再加一點兒,千萬別把他嚇著。告訴他有這麽多的思想內容,這麽大的主題,這麽大的任務,誰都接受不了,做不到。進門就是進門,一步步地邁步。上來就給個大主角沒好處,弄不好把好坯子給毀了。
“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定時長的。在講台上當老師,被學生盯的時間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不慌了,會笃定了。在台上也是一樣,站的時間也有長短,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在《異類》一書中指出:‘人們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並非天資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只要經過一萬小時的錘煉,任何人都能從平凡變成超凡。’他將此稱爲‘一萬小時定律’。要成爲某個領域的專家,需要一萬小時。計算一下就是:如果每天工作八個小時,一周工作五天,那麽成爲一個領域的專家至少需要五年。這就是所謂的一萬小時定律。用到話劇領域,排戲和演戲的時間要大打折扣,沒有三十年的磨煉,怎能成大器。時間夠了,實踐夠了,你站在舞台上不害怕了,就有時間品別人的戲,就可以琢磨別人的戲了,就能看出來戲的好壞了。
“我在三十歲前沒演過重要角色,在劇院就是踏實地學戲、演戲。跑龍套,看別人分析劇本、排練,聽別人談角色,帶著疑問到排練場看人家怎麽試戲,比較看有什麽不同,實際排練時他們扔掉了什麽加強了什麽,最後看人家上台表演時的效果如何。整個過程都是特別利于學習的。我在《蔡文姬》裏飾衛兵,拄著大杆在台上一站就是一場戲。排《王昭君》時,主要角色談人物,談劇本,通知群衆演員可以不來,我照樣去了。這一禮拜的旁聽讓我興趣盎然,因爲我們這代人缺課!我深知缺什麽就要補什麽。
“1976年前後,當得知解禁了一些圖書時,我起大早,頂著星星到大柵欄新華書店排隊買《唐詩三百首》和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求學若渴。那時,每周騎自行車回家,把詩詞抄在卡片上,等紅燈時掏出來念上一兩句,騎上車再默誦,如同在腦子裏拿一小刀刻道兒。當時想把《唐詩三百首》都背下來。甚至在去山東演出的火車上給《紅樓夢》拉家譜,現在回想這些瞎功夫沒白費。
“從1975年到1977年排《蔡文姬》,到1979年排《王昭君》,1983年排《小井胡同》,到1980年代初拍電視,我始終都是這樣做的。通過不懈努力,就會看出些門道。當看到同時有兩三個人演同一個角色,而有人演得好有人演得不行時,就思考一下爲什麽?從觀看到看明白,從吃到品,再到咂摸咂摸,這方法論就出來了—哦,原來老一輩演員並不人人都是藝術家,我得跟著演得好的大師去學。”
有了收獲,有了踏踏實實的積累,功夫不負有心人,三十歲以後楊立新就開始了他一步一個腳印的實踐。
《日出》劇照(攝于1981年),嚴敏求飾陳白露,楊立新飾方達生。
1981年楊立新有過一次失敗的經曆。刁光覃排《日出》,讓二十四歲的他演方達生,比他大十七歲的嚴敏求飾陳白露。這個對手戲比較難演,楊立新很不自信,那時他不論從演技上還是能力上都實在是太弱了。在這出戲裏,共産黨進城後,把官僚資本家徹底打倒,還有一部分人叫“民族資本家”“産業資本家”,像榮毅仁、樂松生。現在知道股票是怎麽一回事兒,可當時楊立新這代人根本不了解股票是怎麽回事,潘月亭是怎麽回事,銀行是怎麽回事。他們概念中的銀行是中國人民銀行,哪懂什麽私人銀行、股票。中年演員不懂,年輕的楊立新就更完蛋,其他演員還有一些舞台經驗,而楊立新什麽都沒有。所以那個戲他自認演得極其失敗。
然而,此時的楊立新早已深深地愛上了話劇。1977年至1978年《茶館》《蔡文姬》的演出和《王昭君》的排練,都讓他覺得舞台是那麽的好看,那樣的有魅力。
“當時有這麽個小細節,《茶館》演出時,我在台下看得十分興奮,在演出中從台下看台上《茶館》的景,簡直就是西安門大街上的某一處,周圍的環境都是如此的逼真。第二天上午我就自己溜到後台,此時空無一人,我走到沒有燈光的舞台上,站在搭著的布景內,發現那曾五彩斑斓的一切原來什麽都不是,跟在台下看的完全是兩回事。在台下看時,當大幕拉開,舞台上呈現的這個大茶館,每一個人物,甚至舞台這第四堵牆,這無形的一面你都想象得出來,你的信念、信仰,對戲的激動是真實的。但此時我站在台上,景片子後面都是布,是木頭框架。站在台上除了自己是真實的,其他什麽都沒有,全是紙、布,一切全是假的。再回頭看觀衆席,黑漆漆的全是一排排的空座椅。我心中頓悟,演戲太難了。要想幹好這事,要想旁人不笑話,能夠在台上站住,二十幾歲的我還早著呢。從那時開始,我要在藝術道路上一步步地、穩穩地向前走,我還年輕,要想成功,路還很長。”
我也是一名演員,我也曾在演出前或散場後站在無燈光的舞台上靜思過,因而我特別理解他說的這種感受。我不想打斷他的思緒,立新小有停頓接著說:“剛進入演員這行,別給他們太大壓力。戲劇學院三年級就排《哈姆雷特》,我覺得是件特別可怕的事。應該從最容易理解的戲演起,從最容易模仿的角色演起,從最容易想象的事演起。打好基本功,不要給他太遠、太大、太深、太重的東西。”
楊立新人生中真正的藝術開端是從1985年的《小井胡同》開始的,他演小力笨。這個人物是真實的,是生活中能見到的。戲的排練和演出都很順利,從而逐步建立了他的自信心。演員的自信心很重要,台下的一千多雙眼睛,除了贊揚你、欣賞你、崇拜你的以外,還有另外一面,批判你、唾棄你、仇恨你。當你演的什麽都不是的時候,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眼光了,那是不得了的。
這又回到了北京人藝的老話—畢業就演大主角真是一大災難。就算還沒演大主角,演個配角或幾個人撐起這一台戲,都能給你莫大的壓力。要從小角色一點一點演,就像年輕人的成長,稚嫩的肩膀還沒有擔一百斤的能力時,那就從二十斤開始,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肌肉的發育,逐步加重擔子。不讓你沒追求,又不能壓垮你。
“1988年的《天下第一樓》,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戲,當時何冀平拿出劇本給大家讀後,我就覺得大少爺唐茂昌這個角色就是給我寫的。于是我給導演夏淳寫了個條:‘我申請演戲中的大少爺,我可以演好。’”
演員的自信來自對人物的理解。因楊立新是在北京南城煤市街長大的,自幼聽河北梆子、評戲、京東大鼓、京韻大鼓、京戲,他對戲劇和曲藝有一種天生的駕馭能力。夏淳導演終于給了他展示的機會,分配楊立新飾演大少爺的B角。由此可見,角色不是等來的,而是爭取來的。
楊立新對爭取來的大少爺這個角色很是上心。他是個好琢磨的人,且不去想什麽A角B角,機會有了就要把心全用在戲上。他飾演的大少爺,一上場要唱兩句西皮慢板—“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歎,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大少爺心中很複雜:今天我要把這幾位名角都請來,他們來不來?楊立新想到這兒就和導演說:“這兩句的下句是‘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如果延上這半句,正好對應大少爺的這種心態:我是藝術家呀!這麽個飯館牽墜得我無奈啊。”夏淳導演欣然同意了立新的方案。
“從戲的主題上說,該戲是從飯館的興亡盛衰寫起的,不是從大少爺是不是一個藝術家寫起的,如果換個角度,寫的是梨園行的故事,開飯館耽誤了大少爺學戲就是俗事了。但這是寫飯館,大少爺只是這飯館中的一個配角,但是不管戲從哪個角度寫,角色都不分大小,演
員都要從人物的角度去演。觀衆眼裏的配角卻是一個演員身心的全部,演員要捋著脈絡找人物,要想把人物的喜怒哀樂表現得淋漓盡致就要尋找人物的根,人物一言一行的出處。
“大少爺這個人物是有一定藝術氣質和才能的人,但大少爺終究成不了大家,如最後是譚鑫培、譚富英那另當別論,大少爺終究只是個有水平的票友。所以我就要求自己,要把這個人物演得像模像樣,唱戲要具有一定的水平。尤其到第二幕時,在拜師的過程中,我必須自己唱。
“原來劇本寫的:順手拿過夥計送菜的盤子,唱了段《紅娘》裏的‘叫張生隱藏在棋盤之下,我步步行來你步步爬,放大膽忍氣吞聲休害怕,這件事例叫我心亂如麻,可算得是一段風流佳話,聽號令且莫要驚動了她’。這段戲都弄下來了,有人指出這《紅娘》可是新中國成立後重新寫的。仔細一想,這還真是,新中國成立前只有《西廂記》,于是爲了保險起見就改成了《蘇三起解》。如果要是能用那段棋盤舞,會很有彩,特別俏。
《天下第一樓》劇照(攝于2001年),嶽秀清飾玉雛,楊立新飾盧孟實。
《嘩變》劇照(攝于1988年),(左起)任寶賢飾格林渥,楊立新飾伯德。
“《天下第一樓》的演出是一周六場,A角、B角一人三場,常貴也安排了B制,請林連昆演四場。結果有些人請人看戲專買第四場,也就是我和林連昆同場戲的場次。演到第四十場以後,院裏就決定取消AB制了,到上海演出也是我出演了。”
這真是,機會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只有你負機會,沒有機會負你。當機會來到面前,是否能駕馭不光要用功,也要有天賦。楊立新天生有副好嗓子,開口就有幾處彩兒,這大少爺一唱,觀衆先是一靜,疑惑下是演員本人唱的嗎?確定之後接著是“哄”的一陣掌聲。每天只要這裏有掌聲,林連昆老師後面的喜歌就格外地賣勁,他得拿下來。
舞台上就是這樣叫場。叫上場了,戲才好看。
沒戲演不見得永遠沒戲演,有戲演不見得永遠有戲演。如果把演戲當成一輩子的事去做,你就會幹下去,不見得當時就得成功,而且成功與不成功是客觀的評價,與己無關。成功就幹,不成功就改行,作爲愛戲之人是說改就改得了的嗎?楊立新回想自己的演藝之路,他說:“我的每個角色都可以這樣捋。可以說,有的人是劇院培養的,我是自己幹出來的。演員就是四個字—個人奮鬥。《天下第一樓》的角色是我爭取來的,上面壓著一個巨大的A角,自己是像竹筍拱石板一樣拱出來的;《嘩變》別人不演了,才輪到我;1989年排《田野》,初期安排我是群衆,到六月份時卻暫停了,年底複排時任寶賢去新加坡講學,七老爺子這個八十歲老頭的角色讓我來演……我的角色就是這麽一路替過來的。
“20世紀90年代院長讓我出去拍電視劇,使我有了更多實踐的機會。之後讓我回來排《茶館》,開始派演的是龐太監,記者就問我:‘您演龐太監怎麽演呢?’我說:‘我不知道,往前摸著走,相信結果不會讓你失望。’”
是啊,每個演員因爲自身條件不同,不會套用前輩的演法。
“排練開始後才排了第一幕就停了,說是要開會討論。那天我正好去打水,碰到李導,我對李導說:‘時間這麽緊,不排練,瞎研究什麽呀?’李導說:‘你不知道呀?常四爺的戲得換人呀。’我應聲道:‘要是必須換,是誰就是誰,換就是了。’李導接著說:‘你不知道呀,小濮想演常四爺。’”
“一聽此話我這個氣呀,心想,我可以演常四爺,也可以演秦二爺,你們卻讓我演龐太監,現在你們反而在考慮小濮能不能演常四爺。這就是我在劇院的狀態嗎?此時母親的諄諄教導在我耳邊響起:‘人啊,兩肩膀扛個腦袋,人與人之間沒有區別,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告訴你,小子哎,自己努力去,沒有人寵著你把你當寶貝兒。’
《茶館》劇照(攝于1999年),(左起)楊立新飾秦仲義,梁冠華飾王利發,濮存昕飾常四爺。
“母親的話沒錯!人,要有個人奮鬥的精神,要靠自己混出人樣兒來,別人才會把你當回事。吃演員這碗飯更是這樣!我又想到一次次給我機會的刁光覃老師。這一輩子,我感謝刁光覃,他能把我當回事兒,給我那麽重一個角色(《日出》中的方達生),我沒演好,後面照樣锲而不舍地用我。這倆角色(方達生和小力笨)就奠定了我繼續做演員的信心,以後全都是憑個人奮鬥。”憑個人奮鬥的楊立新最終飾演了《茶館》中的秦二爺。他扮相英俊、形體挺拔,一亮相便滿堂彩。
我看著楊立新,認真地聽著他對其他人物這麽具體的分析。我們都知道,演戲,演戲,就是演人物關系。不吃透對手,不了解台上的每一個人物,就把握不准分寸,演不好人物關系。楊立新就《茶館》這部戲,沒有因一瞬間的不愉快而影響對人物的創作。其實這種情況,演員常會遇到,正是他的戲路子寬,領導才會對他放心。他還因此寫過三個角色(龐太監、常四爺、秦二爺)的人物小傳,這對把握人物大有好處。
我們話鋒轉到楊立新在《雷雨》中飾演的周樸園。他第一句就是:“太難演了。”
仔細想想確實是很難演,前邊有鄭榕老爺子、顧威前輩,底下有180人,就有179雙眼睛在盯著你,這個戲不好接呀。但是,楊立新也有這麽多年的實踐了,已經有些經驗了,他是個非常虛心的人,會聽取所有意見,全都擱在肚子裏,但他絕不會照搬,否則永遠是在模仿,要把人物真正演到位就要找准自己的切入點。
在排練《雷雨》時,楊立新就提出了異議:“五十年來大講這個戲是反映階級鬥爭,但對于周家,階級鬥爭是胡說八道、牽強附會。曹禺二十三歲寫的《雷雨》,之前沒有讀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沒有學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以必須按照作者的創作思路去捋。這個家庭裏面,不可回避的就是一個亂倫的問題,沒有過去那場以性爲基礎的故事,就沒有後來這麽複雜的關系。如果後來這個複雜的關系中沒有亂倫的發生,這個戲就不成立。
“《中國百年戲劇精華》中對《雷雨》的介紹有這麽句話:‘三十年前周樸園對魯侍萍的始亂終棄,造成了三十年之後的悲劇。’所以我就尋找這個點,周樸園當時是否對魯侍萍始亂終棄?所謂始亂終棄就是在無錫的大宅中,一個少爺玩弄使喚丫頭,如果手下有五個丫頭,其中有兩個漂亮的,他就玩弄倆,玩弄一個抛棄一個。如果發現懷孕了怎麽辦?絕對不會讓她生下來。要是生下來也罷,將孩子留下,把大人轟出大宅。這是舊社會大宅門裏一貫的做法。
《雷雨》劇照(攝于2004年),龔麗君飾繁漪,楊立新飾周樸園。
“魯侍萍生了第二個孩子,這個過程是一年多。魯媽說過,周樸園爲了娶門當戶對的小姐,讓她抱著剛滿三天的孩子離開了周家。據此可以推測周家上下是同意魯侍萍和周樸園的關系的,而且兩人之間是有真正感情的。”
分析人物時,楊立新就是死心眼,其實這樣費功費力,不是爲了給別人帶來多大的說服力,而是要讓自己自信。
“北京人藝《雷雨》的演出本裏故事的開始時間是1925年周樸園五十五歲時,然後進行倒敘,推算周樸園出生在1870年,去德國留學的時間應在二十歲左右。
“當年無錫經濟交通很不發達,一個財主家的孩子能去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先驅德國留學,理應非常的優秀且有志向。學成歸來後大約是1894年,在家中待了兩年。爲什麽沒有馬上出去做事?必須找個理由,這就是甲午海戰。甲午海戰用的是德國的軍艦,這對一心想技術報國的周樸園是一個打擊。對這樣的青年打擊太大了,不巧他在家這兩年與魯侍萍經曆了一場愛情,有了大少爺周萍,又有了第二個孩子魯大海。
“戲裏有句台詞:‘你在哈爾濱包修江橋,故意讓江堤出險,淹死了300多個小工,一個小工你克扣30塊現大洋。’又有:‘你們家讓我抱著剛生下三天的孩子,把我趕出了周家的門。’曹禺寫的是‘你們家’,沒有說‘你’。劇本透露給我們的信息是:周樸園當時沒在家,他在哈爾濱包修江橋呢。但按中國的習俗,周樸園過年必定要回家,從哈爾濱趕到無錫,年三十晚上才到家,這個推理說得過去。所以周家在周樸園到家前把剛生完孩子三天的魯侍萍趕出家門就很自然了。這絕不是周樸園幹的,他回來一看魯侍萍不在了,馬上追出去,到河邊見到了衣服,裏面有封絕命書,但人已跳河,沒辦法了。所以,這場愛情悲劇其實是周家其他人造成的,而周樸園和魯侍萍之間是有著真感情的。
“後來周家又安排給周樸園娶了媳婦,劇本定論此人不知所終。按照繁漪的台詞:‘你那惡魔般的父親把我騙進你家,只讓我生了沖兒,再也不理我了。’我又一次找到了周樸園對魯侍萍的愛情依據。周沖十六歲,他和二十七歲的周萍、二十六歲的魯大海之間年紀相差八九歲,這段時間裏繁漪這個媳婦在周家杳無痕迹。戲一開始,屋內的陳設還是魯侍萍走時的樣子,滿腔抱怨、惡魔般的周樸園逼著繁漪喝藥。通過繁漪對魯侍萍的嫉妒,可以看出周樸園對魯侍萍的愛,三十年來對魯侍萍的紀念呀。”
從下面的分析更進一步看到楊立新對人物剖析的深刻程度:“周樸園回來幹什麽來了?因爲礦上出事了。故事發生在北方一城市,四鳳有句話:‘老爺從前天回來,就不停地在省政府開會。’當時的省政府在保定。第四幕有個說法:‘從礦上回來,2點半有趟火車,天亮4點可以到。’這個距離應該是開灤。“第一幕,周樸園回來的三天後,曹禺通過繁漪的台詞告訴觀衆:周樸園在客廳會客,會見了包括警察局長在內的三撥人。曹禺是暗示這件事的背後跟公檢法有關系。周樸園回來是平息礦上開槍打死工人的事情,礦上已經罷工了。頭天晚上,他把追到省政府的三個工人代表打發走了,只剩魯大海一個了。第二天便輕松了,問問孩子們的情況,關心繁漪的病情。”
時鍾已指向半夜一點半。我邊聽邊站起來舒展久坐的身體往門口走,准備告辭。立新話卻沒停:“周樸園是實業家,是從德國留學回來的鄉紳,他見事做事,見招拆招……”
我知道,楊立新一聊起戲來就兩眼發亮,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一個演員能如此這般地分析人物,能對角色充滿激情,他能不成功嗎?我不知道在現如今這個浮躁的社會裏,在我們下幾代的演員中,是否還有這般認真的人。對戲能如此較真的好演員,是稱得上藝術家的人。
《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藝》書封
(本文標題爲編者所加,原題:楊立新——自強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