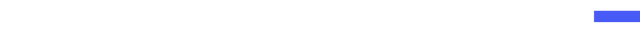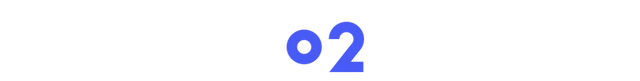在2022年的新加坡,用中文聊web3.0,喝黃釉瓶茅台,以及讀一本名爲《大衰退》書,都是正經事。
文|袁斯來
編輯 | 楊軒
來源 | 36氪Pro(ID:krkrpro)
封面來源|視覺中國
要在新加坡尋找中國創投圈大佬,最好從餐桌開始。
即便坐在烏節路餐廳,中國人仍然固執地捍衛著自己的口味——比如對茅台的執念。
在每天不重複的酒局,通過酒的種類,大概能看出組局者的分野。新加坡當地人喝威士忌、紅酒,中國創業小年輕喝啤酒,小有成就的新富豪飯桌上清一色茅台,有時白瓶中還夾雜更稀少的黃釉瓶茅台。參加的酒局夠多後,有人已經能一口分出中國茅台和新加坡茅台的區別——“國內賣的醬香會更濃點。”
一位餐廳老板在朋友圈曬出賣茅台的彙款單:200萬人民幣,還是預付款。他寫下感激的話:“關鍵時刻大佬都在背後默默支持著我。”他停掉了清酒、大閘蟹業務,專心分銷茅台。
一場酒局上,茅台成列。黃瓶茅台不是稀罕物品。采訪對象供圖
除了喝酒,大佬們日常也有平淡些的小聚。有人就在街邊大排檔,看到字節跳動張楠和小米王川湊一起吃海鮮。如果喜歡踢足球,可以加入某個球局,前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最近幾周都會出現。
一個國內億級用戶APP的老板在工作間隙,會在家裏組局吃榴蓮。七八個人光腳圍坐,客廳裏彌漫開甜膩的水果香氣。其中有個人總是出現在同一個富豪身後,一問,不是家裏人,賣保險的。
這是新加坡華人圈的另一種生態:不少富豪身邊都會跟個保險經紀人。各種組局上,經紀人必須善于活躍氣氛,比如德撲打到興起,大家要玩真心話大冒險,保險經紀人會毫不猶豫跳上牌桌,跳一段性感的table dance。
一些新來者很走運,仍能遠程操縱國內業務。而一些前輩企業家們,已經開始習慣遺忘往日的榮光。幾個前些年退休的大佬有個微信群,叫做“二把手俱樂部”。其中一個曾經將公司做到行業前二後賣掉。退隱新加坡多年,他似乎很無聊,因爲除了在家做飯、帶孩子,時常能在各種飯局看到他。另一個人是上市公司前高管,據說喜歡和web3.0圈子打德撲,還“玩兒得很大”。
有些更有名的人物過于難以接近,只出現在閑談碎語中。比如雇傭私人飛機跨洲接送自己的某頂級未上市公司創始人,據說在新加坡調養。有人聽說Top大廠的創始人在新加坡避了一段時間風頭。在AI圈子裏則瘋傳,行業頭部公司的高管們組團待在新加坡。
“新加坡就像在開大展會。類似于國內一個酒店擴大無數倍,裏面全是大佬”,一個老創業者對36氪總結。
在這場“大展會”裏,人來人往,整個城市沉浸于金錢的潮汐之中。
但對想盡快做點成績的人,酒杯碰撞的聲音清脆而空洞,到最後甚至讓人厭倦。
一個來到新加坡的創業者說,原以爲新加坡創業氛圍很濃郁,呆了一段時間才發現,怎麽天天都是大佬遊艇party,酒局,大家喝酒、抽雪茄,在甲板上友好地聊完一圈,然後呢?“啥都沒有,ROI(投資回報率)太低”。
遊艇party常見項目:海上看落日。采訪對象供圖
呆了幾年的過來人,早就對這種落差習以爲常。他們多少會帶點看戲的心態。一個FA告訴我:“你最好明年1月再來看看,說不定很多人就回去了。”
高檔中餐廳和豪宅外,隱秘的不安在一場場聚會和一杯杯咖啡之中蔓延。水滴籌CEO沈鵬在一場線下分享中說,自己在新加坡待了一段時間,發現人人都在讀辜朝明的那本《大衰退》。
但無論如何,2022年,源源不斷的新人持續湧入新加坡。他們的興奮撐起了新加坡的喧嘩和騷動。
一切到9月迎來高潮。
新加坡,“看上去”很美
新加坡絕對不缺錢。但想從富豪手裏拿到錢,絕不比在中國更容易。
最開始,說起去新加坡,投資人John有些不情願。
一旦確診,可能會困在國外一個月,這還不算回國隔離的時間。
但沒有哪一個中國投資人會對9月在新加坡舉行的Super Return熟視無睹。
疫情開始的三年來,這是第一個全球知名LP(出資方)會同時出現在線下的大會。9月那一周,新加坡可能是整個亞洲財富最集中的城市。500多個衣飾得體的歐洲、亞洲人穿梭在金沙灣會展中心,他們背後是手握重金的資方——南洋理工大學、阿布達比主權基金、大保險公司或者面目不詳的高淨值個人。
今年John所在的基金還沒到募資期。大會開始前一周,John的老板還在猶豫要不要到跑這一趟。但翻看同行的朋友圈和各自的聊天記錄,老板無法再保持淡定:新加坡無處不在。
“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錯失)的情緒終究還是占了上風。在Super Return開始前一周的例會上,老板終于拍板,“咱們還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可他自己是不願意冒風險的,結果是John這個新合夥人辛苦一次。
三年時間,足以改變很多事。同行之間聊天,壓力大是逃不掉的話題。連Top20基金創始人都會感歎:“今年壓力大,主要在搞錢。” 即便還沒有到募資期,John必須出現在老出資人們跟前。安撫之余,試探他們未來幾年的投資意向。
他這一次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去挖掘新的家辦和中東LP。“畢竟,現在宇宙的盡頭是新加坡。“他有些嘲弄地告訴我。
John落地已經是Super Return 開始的第二天,比起那些一周前就出發的同行,他們基金可以說很不積極了。
從樟宜機場一路開向城市CCR(Core Central Region),John忽然進入了久違的洶湧人群。紅色、金黃和藍色霓虹燈閃耀在濱海灣的夜空,挂滿彩燈的遊船駛過漆黑的海面,泛起光斑。
等待他的是初秋氣候已經溫吞的新加坡,還有到處熱氣騰騰的流動盛宴。
從早上9點到深夜12點,烏節路輻射的,街角的咖啡廳、樓頂的餐吧,只要John願意,他就能找到一場聚會。除了無處不在的web3.0創業者,又多出2000多個從世界各地趕來的金融圈人。
Super Return舉辦地在新加坡標志性的濱海灣金沙酒店,據說是全球造價最高的單體建築。三棟塔樓與其說是酒店和購物中心的集合體,不如說是一座小型城市。整個酒店有2561個房間,45個餐廳, 22家酒吧,1間博物館,1條運河,1家賭場,170個品牌的購物中心,其中包括LV在巴黎以外最大的旗艦店。
到9月中旬,金沙酒店房價已經炒到上萬。John只能到喜來登定了房間,普通大床房花了5000多元人民幣。雖然也在市中區,但附近甚至找不到一家便利店。那幾天,金沙酒店門口永遠排著幾十個人打車,他只能走回酒店。
陽光透過落地窗照進挑高到9米的展廳,人的聲音也變得稀疏。John站在4、5米寬的走廊,眼前是平靜的海面,新加坡海峽吹來的海風彌漫濕氣,真正的現代氣息、硬件簇新明亮。
2018年06月21日,新加坡金沙大酒店,空中花園。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開會第一天,John在展廳來來回回走了不下2萬步。
早在出發前,他就在大會APP上給各種類別LP發了幾百條私信約見面。除了私聊,他想過在現場臨時找出不認識的LP。浪費了很多時間和同行寒暄後,他學會裝作不經意地搜尋對面人的胸牌,找出LP名字下才有的小黑色五角星。從早上9點到下午4點,他見了二十多個LP。
只是,中東大亨的錢沒那麽容易收入囊中。中東LP們的口味是過去中國美元基金陌生的。來自迪拜、阿聯酋的大金主們對短期內十倍、二十倍的回報似乎沒多大興趣,他們會問John陌生的問題:你們如何幫我們提升社會發展水平?這讓John驚訝之余,絞盡腦汁改變自己的慣常話術。
中東LP的錢可能只在此短暫停留,好在新加坡本土也並不缺錢。根據聯合早報的報道,今年新加坡會新增500多個中國富豪,他們將爲這個國家帶來至少24億美元。
不止一個投資人都會提到同樣的數據:今年新加坡家族辦公室從2020年的400個漲到700個,而“家辦”最低的基金管理規模也提到了5000萬新幣(約合人民幣2.6億元)。
實際上,“5000萬是不好意思開家辦的。” John告訴我。他這次見到了管理3、4億美元的家辦負責人,背後金主身家在20-30億美元之間,也有國內前五互聯網公司的SVP(高級副總裁)。
他們同樣不好捕獲。很多家辦剛落地新加坡,還有些摸不到門路,盡管他們的投資軌迹已經在世界地圖上四處跳動。
“今天投個歐洲房地産項目,明天投個亞洲基金,後天投個北美互聯網項目。”連John都覺得奇怪:“你爲什麽這個時候去投歐洲的房地産。”對方回答:“因爲老板和其他有錢人攢了個局,地産也是老板朋友的。”
在一個陌生的市場,如果家辦管理人還沒有完全獲得老板們的信任,能做的是老板對什麽感興趣,他們就看什麽項目。
以至于這些家辦管理人自己都不敢保證對中國的美元基金多麽了解,即便能叫出一個個基金的名字,卻弄不清它們彼此間的區別。當John追問對方能投多少錢,他們只能含糊地說“300-3000萬美元都是我們的範圍。”至于能不能給錢,“回去得和老板商量,不確定老板喜不喜歡。”
新加坡看似遍地黃金,但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新加坡走馬觀花的半個月,真正調動起John情緒的事卻和融資無關。
結束後,隨之是web3.0圈裏衆人皆知的大會——Token2049。這場大會真正點燃了新加坡。
那幾天,在新加坡的投資人,很多朋友圈都被Token2049刷屏,誇張點的分享和圈裏名人的合照,普通的分享則是人滿爲患的咖啡廳,反正都是些搞大事的畫面。
有些活動直接辦在夜店,台上兼職當DJ的web3.0創業者打碟,鮮豔的燈光閃爍不停。在各種web3.0群裏,他們曬陳柏霖、林俊傑、伊能靜的照片。
場面實在太過盛大,以至于有個提前離開的投資人很快開始後悔:開始以爲Token2049只是個規格比較高的會,有些活動而已,沒想到是個“大party”。
“你在國內真體會不到這種氛圍,還是很酷的,千禧一代以後的感覺。”這個投資人告訴36氪。
John原本只是帶著些看熱鬧的心態加入,但到那一周結束時,他已經參加了40多場活動。如果和活動上的web3.0創業者聊得對味,他可以在淩晨2點約海底撈,一直吃到天色將明。“web3.0沒有夜晚,”他說。
Token2049活動現場。圖片來自官網
前一周在金沙會展中心,John擦身而過的很多白發蒼蒼的投資人,被中老年人包圍太久了後,John懷疑是到了另一個世界,放眼Token2049,幾乎都是年輕鮮嫩的臉孔。“這對比真的是太強烈了。”
在Token2049間隙,John去了次創投圈聚會。聚會在當地算得上高檔的中餐廳舉辦,或許是爲了凸顯中國元素,進包間就能聽到傳統民樂,銅鑼唢呐一派喜慶,還以爲春節提前了幾個月。
包間裏近百號人,基本都是互聯網投資人或者新加坡銀行、政府的官員。最近很活躍的金沙江合夥人朱嘯虎,自然沒有缺席,還能看到軟銀、淡馬錫和中東基金的人。
或許是爲了照顧本地人,桌上沒有茅台,只有紅酒。大家有禮貌地聊天、敬酒。要有人問起“你最近關注什麽?”通常只會收到平淡的回答:“沒什麽投的,也沒什麽關注的。”John受不了沉悶的氛圍,呆了一個小時就退席,跑去參加web3.0活動直到半夜。
但狂熱的party之後,John無法忽視矛盾之處。就算手裏沒有數據支持,他也憑直覺知道,眼下的新加坡,投資人比靠譜的web3.0項目多。“這場會,對我這種不太了解的黑子是破圈的機會,但好的項目比例很小。”
這也是很多投資人的普遍感受。2022年新加坡創投圈,最多的是投資人,但錢和好項目卻都難找。看上去滿地機會,但很少有人真正願意爲“夢想”和隨之而來的風險買單。
浮華背後
一個創業者奔赴新加坡時,如果想重新看到中國2015年時“萬衆創業”期的盛況,必然會失望。全球經濟衰退時,新加坡只不過比亞洲鄰居表現好一點,並不會幸免。
新加坡的水溫已經開始下降。Token2049 人潮湧動,新加坡互聯網圈子聊的卻是大裁員。
當John到達新加坡時,和他有過一面之緣的創業者Paul,已經決定關掉公司。
如果看履曆,Paul算是在東南亞有經驗的中國創業者。他在本土頭部公司當過高層,說很流利的泰語、英語、印尼語。自己做的電商項目,之前還拿了點知名機構的融資。
8月末的早上,Paul剛醒來,發現平靜很久的蝦皮離職員工群,忽然“噼裏啪啦”進來一連串剛被裁掉的人,群裏一片喧鬧。那些人告訴他,有十多年曆史的實驗産品孵化部門沒了,一個人不剩。
Paul當時正爲自己項目找下一輪融資,找到頭發花白。看到消息時,他知道大勢已去。連頭部公司都降低預期不再投入新項目時,自己沒有必要繼續掙紮。
Paul有很多找錢的渠道。他交遊很廣,認識很多有錢人,也和本土基金關系不錯。
老板們很樂于在宴會上看到他。新加坡呆了很多年的老江湖曾帶他去私人會所。Paul曾聽說美團的前幾號人物和朋友來過這裏聚會。會所落在別墅和私人公寓林立的丘陵地帶,門外看不到任何招牌,也不會對外營業。
剛一進門,他就看到的是橫七豎八停放的豪車,最顯眼的是輛黑色勞斯萊斯,方形車頭上的歡樂女神像銀光閃耀。車輛停放隨意,見縫插針塞滿並不寬敞的院落,“看著像香港電影裏黑幫的聚會。”
忙的時候,Paul一個月在家吃飯的次數五個指頭數得過來。但和他忙于奔命不同,大佬們似乎不太著急于追逐事業第二春。他聽到營收千億的上市公司前總裁在私人聚會上表示,我們在歐洲投了一個億,東南亞也該布局了,現在也有牌照,就是不知道做啥,“既然大家都來了,我們也來看看。”
“看看”是很多富豪的心態。“我不投錢我也不做什麽,就在那裏花曾經賺的錢。”Paul這樣總結。
畢竟新加坡至少在眼下能給大佬們足夠舒適和安全的生活。
新加坡聖淘沙海港,遊艇擁擠。采訪對象供圖
Paul有時會被朋友邀請,去中國互聯網圈子老板們很熱衷的住宅區參加聚會。幾個相近的小區中,戶主包括曾經某行業排名前三公司的創始人、頭部基金合夥人。最近,戶主還多了個社交獨角獸公司創始人,她剛到新加坡不久。
小區門外就是繁華的CBD。房子大多只有十多層高,大樓配色和外觀看似簡單,但正好完美搭配院落裏的棕榈樹。院中50米長、8條水道的泳池永遠蔚藍,池邊藍色遮陽傘下,黑色躺椅空無一人。
看慣一線城市高層住宅的人,都知道如此疏落的布局,在寸金寸土的新加坡是一種真正的奢侈。
新加坡四處飄散著這種隱形的、豐裕得被人視爲草芥的金錢氣息。但它們解不了Paul的困局。比起給創業公司投錢,老板們甯可去投資些本土房産金融産品。投資人總是禮貌地說:“你去找領投吧,有領投,我們也跟一些。” 有投資人更直接:“你項目就算不錯,也很難撐過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天。”
真正的好時候已經過去。即便在亞洲此刻最熱門的城市新加坡,景氣度也已經不複從前。
在中國投資人們蜂擁而至前,以美國放水爲節點,軟銀、Tiger global、DST就在新加坡大肆掃項目。一個當地投資人總結:“之前他們都沒什麽存在感,這兩年出手大,出手快。”出乎意料的是,這些被投資人們戲稱爲“接盤俠”的國際大基金,在2021年經曆被投公司IPO血虧後,開始“躺平”了。
這樣一來,似乎突然之間,在新加坡做到B輪C輪的創業者,發現自己找不到錢了。
一個已經盈利的AI公司,做了七八年,到今年,願意再投下一輪的投資人消失了。創始人找到一家基金的老大,對方甚至不願意開個價格,“開不了”。
基金們看項目時熱情有多高漲,轉瞬之間掏錢時就有多謹慎。
John就在新加坡拒掉了一個中國高管的創業項目,他認爲市場太小,對方要價又太高。而此人在圈子裏還有些名氣,曾經在國內經手過類似的生鮮頭部項目,一路做到了高管。當他爲融資四處奔走時,圈子裏傳開五味雜陳的流言:“你看,連他都找不到錢。”
新加坡marina海灣和商業中心的清晨。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似乎只有web3.0圈子的熱情從未消退。
在市區,甚至當地房地産商也搞起 “元宇宙+web3.0”活動。售樓處的沙盤描摹出價格3000多萬人民幣高端公寓的樣子,LED屏幕打出web 3.0的活動海報,沙盤旁擺放百來把座椅。場地有些簡陋,但擠滿了人。
如果到新加坡麥裏芝水庫附近的綠道,最常見的是web3.0圈子的徒步。誇張的徒步活動,可達浩浩蕩蕩一百多人。他們會冒雨在步道走幾個小時。三五個人一排,隊伍黑壓壓一片,整齊出發後如同行軍,彼此還要提防雨傘的碰撞。
有些活動則走華麗路線。賽馬場普通看台旁,穿拖鞋短褲的中年男人攥著馬票,睜大眼睛拼命想看清遠處屏幕上的小字。但在vip包廂的web3.0聚會,頭頂屏幕就滾動著實況字幕和直播畫面,落地窗外可以清晰看到終點線。房間內紅色地毯柔軟厚重,沙發是絲絨套。女人們妝容細致,短裙配高跟鞋,男人們則西裝革履。安靜的房間上空,幣圈黑話飄來飄去。
但這場浮誇背後,注入太多水分。
或許是出于同行相輕,美國web3.0圈會嘲笑新加坡的圈子:“新加坡十個項目九個騙,還有一個在路上。”
那些拿了融資的公司,往往有著神秘的面孔。一個web3.0創業者告訴我,他們前後融了1000萬美元,但前兩輪都是代幣。具體架構如何,他“不方便透露”。
同樣神秘的,還有這群創業者的生活。他們會告訴我,自己生活很簡單,不愛到處聚會,生活很健康,最多就是去徒步、打網球。但其實飯桌酒局間,少不了會看到他們的身影。
但是,抛開這些真假摻半的談話,如果只討論業界話題,一切都讓人興奮。飯局上,大家聊起誰又成了獨角獸,誰又募了100億(token,意思是代幣),“真是獨角獸都不夠用了。” 一個在新加坡看web3.0項目的投資人調侃道。
可圈中一些行爲讓他很不喜歡。做加密貨幣貸款機構乍富的聯合創始人,新買了輛勞斯萊斯,在新加坡街頭無比搶眼,而且他的豪車不止一輛。這樣以豪宅、遊艇爲標配的造富速度差不多要以天或者小時來計算。
他算是個老投資人,這種場景和對話似曾相識。“怎麽和當年P2P騙局的時候一樣?還沒成功就開始高消費了?”至于交易所,他斷言:大部分“就是賭場”。
找到稍微靠譜的項目真如同大海撈針。好不容易聊到下一步,沒想到項目方很快又開始發幣、ICO。“太容易割韭菜,A輪就發幣,上市,套現,然後買個豪車就玩吧,誘惑實在太多了。” 他告訴我。
6月中旬,加密貨幣貸款公司貝寶告訴合作夥伴“我們已經資不抵債”。接下來,不少豪車從新加坡街道消失。
創始人亡命天涯的故事也開始流傳。飯局上,朋友有些遺憾地宣布:“本來今天要介紹某人給你認識,但昨天他出事兒,來不了了。”
這個投資人一直沒能見上那些年輕高調的web3.0傳奇人物,說實話他也沒興趣再見。他看起了傳統的互聯網項目,再提起web3.0,他會搖搖頭:“太早了,市場太小了。”
敗興而歸
度過了幾個不眠夜後,John已經考慮離開新加坡,盡管他在市中心的咖啡廳,還時常碰到熟面孔,都是些中國的美元基金投資人。
金沙江的朱嘯虎有時還出現在web3.0大合照裏,有時被人看到在機場等待。Paul戲稱:你在新加坡飛中國的飛機上問一嗓子有沒有投資人,一定會有人搭腔。他座位背後,就坐了個頭部基金投資人,兩個人後來的話題之一就是比慘。
美元基金們紛紛張羅著開設新加坡辦公室,哪怕現在根本招不到當地負責人。因爲當地的管理人才“都在本土和國際大基金”。
中國投資人們偶爾的大動作,會讓其他投資人感到匪夷所思。有個投資人看到中國同行投了某大佬的創業項目,給了上千萬美元天使輪,而他們看過的類似項目,估值更加便宜。這樣一來,對方出手的邏輯就顯得奇怪了,“就覺得挺離譜,投資不能只看報表。”
如果穿透過這場盛會的外殼,會發現那些爲利忙碌的熙熙攘攘,實際上很少會有什麽實質性的結果,更多人似乎是被環境“逼”到新加坡。
“新去的(投資人)都和沒頭蒼蠅一樣到處亂竄。從這個公司看到那個公司,所有的地方如數家珍,誰都認識,誰都知道,工作就完成了,報告也能寫了。”Paul說。
沒人知道新加坡的喧鬧能持續多長時間。一個FA就告誡自己的朋友:“你過來看可以,但是國內的業務不能丟,不然你在東南亞投不出項目,回去團隊就沒有你位置了。”
這位FA告訴我,他接觸過一個基金高層,開會時高層直接扔來兩個問題:“你說下東南亞哪些投資人比較活躍?每年案子有多少個?”FA覺得奇怪:“你怎麽不查查報告?都是公開的數據,怎麽問我這個問題?”對方很不客氣地回答:“我都知道了還來問你幹嘛。”
最近流入新加坡的錢還是太年輕。說到底,新加坡進到金融中心前三也就是今年剛發生的事。
新加坡最高建築Gucco大廈三層頂層公寓由華人廖凱原買下,他也是特斯拉最大個人股東之一。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2019年,John在香港跟著老板募資時,新加坡在資本圈還是個不入流的城市,資本流動性差、沒什麽創業生態,誰要說起去新加坡上市,圈裏人第一反應是“爲啥去新加坡?能有什麽好處?”一位投資人2018年跳槽到新加坡基金,他記得中國來的VC“五根指頭數得過來”,投一個東南亞本土項目,他們可能是唯一一家有中國背景的資方。
事實上,當時除了騰訊、字節的戰投部,很少有機構看得上東南亞。
相比之下,合夥人們在香港會停留更長時間,機構可能只派個associate(助理)級別的中層在東南亞粗略掃一圈,回國在會上推薦一下,整件事通常以“推不動”告終。如果有份東南亞的創業項目書到了投資人面前,投資人會一臉質疑:你真的熟悉這個市場嗎?潛台詞是:“我覺得不靠譜”。
蜂擁入新加坡的很多人更多是追逐熱點和寬松政策而來,比如web3.0。但到底怎麽在這裏做生意?大家沒有答案,沒有底氣,也沒有定力。
未來該往何處去?暫時也無清晰答案。John和同行一樣,沒人會把那本《大衰退》擺在桌上,但他欺騙不了自己:“有些行業就是到了末路,比如中國在線教育,比如歐洲的房地産。”
9月末,John的新加坡之行已經興味闌珊。他離開新加坡回國,坐在隔離酒店,顯得更加冷靜:“目前的挫折是階段性的。香港很快就能恢複,它對中國的戰略意義很重要。新加坡畢竟體量太小,那裏不是我的重點。”
他還記得2019年參加香港萬豪酒店的Super Return。走廊燈光昏黃陳舊,三十年曆史的歐式雕花扶手、色澤濃郁的地毯,又增加了沉重感。人群擠在狹窄大廳,蒸發出的汗氣讓空氣瀕于凝滯。這和新加坡金沙酒店的開闊全然不同。可John還是懷念香港,起碼在那個老牌金融中心,“你想象不出來,只是多了幾千個人,酒店價格就崩潰了。”
(根據采訪對象要求,Paul、John爲化名。感謝36氪作者劉旌、任倩、于麗麗做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