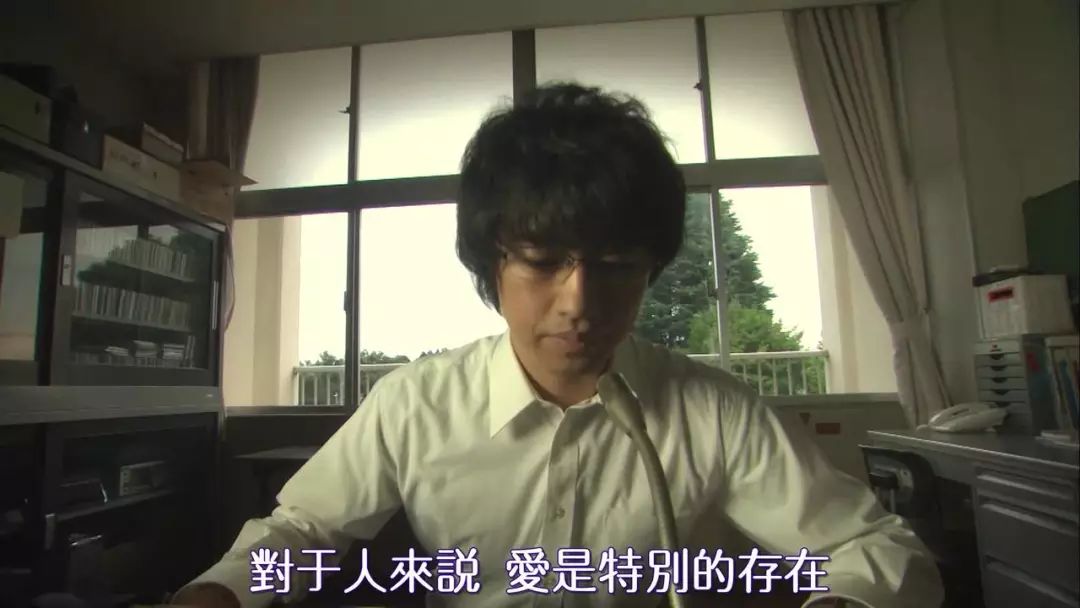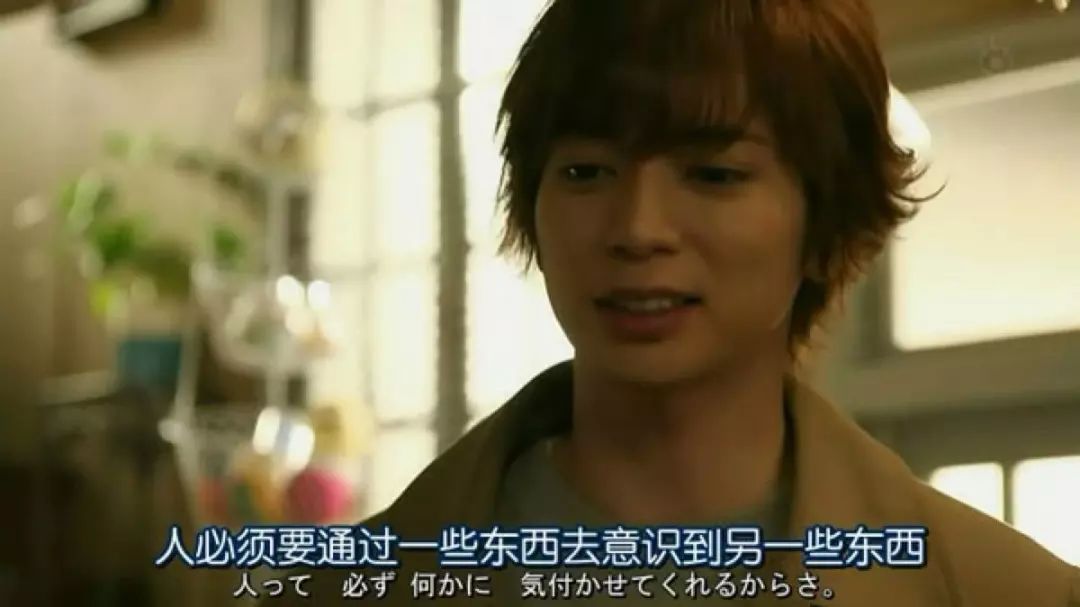異鄉異客,逃不過的悲歡離合。
北漂這個詞一直很火,似乎已經和夢想、奮鬥、苦難,艱辛聯系在一起。
在新加坡呢?
不想用新漂這個詞,因爲漂泊是一種無所依靠的狀態。即便是蒲草,再細的根也是接觸到土壤上才會生長。
在新加坡紮根、成長,只是偶爾回望,會有想要不顧一切的沖動……
一.就那樣啊
石毅,25歲,異國戀第7年。
上學時就知道他在中國有女朋友,一直無緣得見。他話不多,偶爾問他保持愛情的秘訣,總是笑笑說:“就那樣啊。”
上學時,他們尚且還有假期能夠相聚。而工作以後,機會愈發的少了。
他爲女友做過很多,寄禮物,拍視頻,所有能想象到的他都做了,只是無法陪伴。看到網上曬異地戀的車票,他很羨慕地說:“他們能見這麽多次啊。”
雖然主管對他並不友善,他依然努力工作,因爲他想申請PR,把女朋友接過來一起打拼。
聊到這些的時候,他說的特別認真,認真地像在做著保證。
某天喝酒,大家起哄要見他女朋友。他笑著推脫,可拗不過大家,還是打開視頻。
起初有說有笑,他給女朋友依次介紹每個人。但漸漸,表情變得有些嚴肅,默默走到門外。回來時,表情有些莫測,沒人敢再提起這事。
那天,他喝的很醉,卻格外清醒。
送他回去的路上,他盯著車窗外沉思。
“我剛才差點買了機票回國”他冷不丁的一句。
“她哭著看著我,說很久沒和我一起吃過飯了。我們9個月沒有見面了,而我知道,這還要持續很久很久。”他冷靜得讓人驚訝。
“爲什麽不回去呢?”有人問。他沒接話。
過了幾天再見他,他還是笑著回答:“就那樣啊。”
淺淺淡淡的一句,藏著許多無奈和情深。我們在一方小小的土地上灌注夢想,也許爲的是某個地方等待著的人。
二.感謝這心不安處
第一次見曾傑很驚訝,電話裏聲音粗犷,真人卻很秀氣。坐在他家樓下的酒吧,就開始聊起天。
問他來新加坡的原因,他說:“當初趁著留學熱潮就來了,年紀也不大,懵懵懂懂的,純粹爸媽指哪打哪。”他挺幽默,有時還很可愛。
聊著聊著話題轉到在新加坡的生活,他說:“我16歲來到這裏,交了兩個最好的朋友,可惜他們都回中國了。”
“原先三人一起吃飯打遊戲,喝酒喝到一起哭起來,也許莫名其妙,但那種感覺真好啊!現在我也和別人吃飯喝酒,就像現在,我只能笑著。”
他頓了頓,喝光了面前的啤酒。酒吧的大叔利落的收走了空酒瓶……
笑著忍住眼淚比痛快大哭看上去更堅強勇敢,可背後的無處與人說,才是最折磨的。
再聯系他,他已在國內,他媽媽住院了,癌症。
問他:“你不打算回新加坡了吧?”
他不說話,顯然在思考,半晌才說:“不會,還是要回去的,這次只回來一周,公司請不了太久的假,我也扣不起獎金,我媽這還需要錢。”
“這樣你安心嗎?”
“不安心,但我得把這個家穩住。”
“有沒有回國發展的打算?”
“暫時沒有,我挺喜歡這的,很感謝這方土地。而且我等不起啊。”他笑得很坦蕩。
都說小時候我們詞不達意,長大了卻學會言不由衷。他的話很真誠,感謝自己在新加坡的成長,感謝新加坡對他的認可,只是心向故鄉與親人。
三.我可能很不孝吧
東陽從小是爺爺奶奶帶大的。初二時,奶奶中風住院,左腦梗塞,失去了說話的能力。
20歲時,他說起這件事,平淡而從容。想來時間已經讓他接受這件事。
南洋這裏經常下雨,每次下雨他都有點惆怅,問他原因,他說:“初中時學校離家近。下雨天,奶奶給我送傘。傘上有個洞,我當時特別嫌棄,拿著傘也不肯打,兩個人淋著雨走完回家的路。”
他停頓了一會,又說:“那次之後沒幾天奶奶就生病了,你說會不會是因爲陪我淋了那場雨?”
後來,因爲各種原因,和他有5年沒有見面。再見時,問他奶奶的狀況,他悠悠地開口:“已經去世了。”
他自顧自地打開了話匣子:“我記得忌日是9月26日,可是我已經很久沒有回去掃墓了,今年清明還是我媽媽替我磕的頭。”
“小時候奶奶對我那麽好,我連每年一次的祭拜都做不到,奶奶一定會怪我吧,好幾次都想回去,可是……”
突然間他擡起頭:“完了,我有點想不起奶奶的樣子了。”他無措地像是等待懲罰的孩子。
最後他用無比肯定的語氣說:“我好像很不孝。”
多少人曾想過“我要不顧一切地回去”,但最終卻“顧了一切”。
只是因爲這片土地還有值得我們追求的東西,物質的也罷,精神的也罷,我們就在這裏,慢慢紮根,也許有怨,但是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