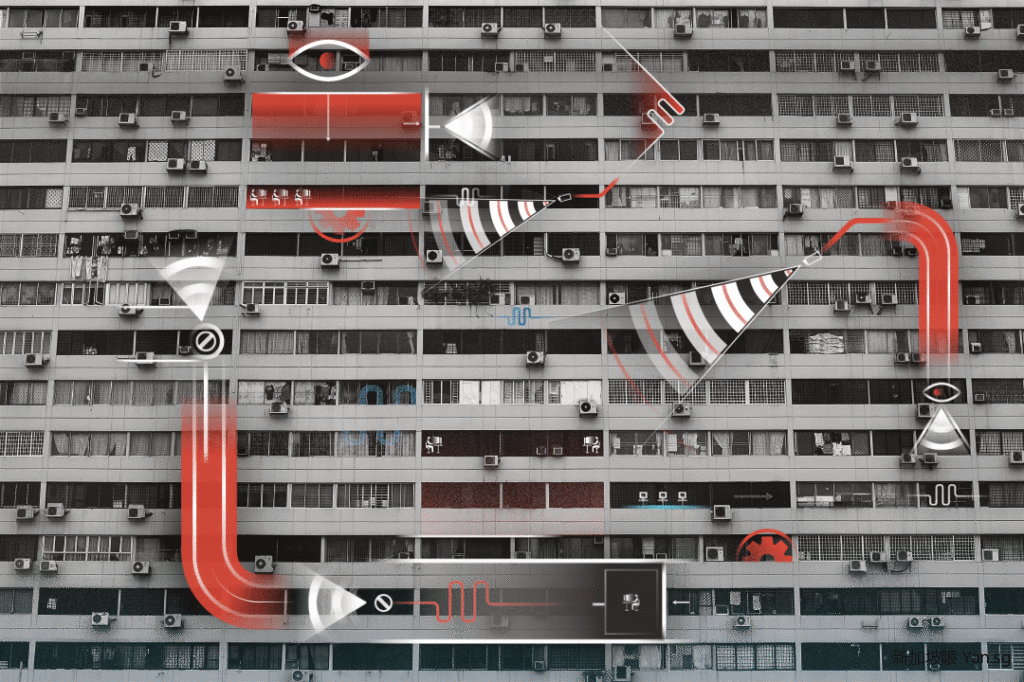The Social Laboratory
對以維持秩序爲目標的中央控制式複雜技術系統而言,新加坡是最佳實施場所。
如果社會穩定意味著要接受更多的監控和大數據掃描,新加坡人似乎很樂意做交換。
在新加坡,人們普遍覺得如果你不是犯罪分子或者反政府者,就不用擔心什麽。
從拍下警察在警車內睡覺並上傳推特的憤怒市民到挑戰執政黨理念的反對派博客,新加坡的領導人也無法逃脫民衆的監控。
美國的網絡監控引起全世界對“大數據”的警惕,而新加坡卻另辟蹊徑,展開一場實驗,希望在保護國家安全之外,還能借助“大數據”打造更加和諧的社會。
2012年10月,新加坡國防部長PeterHo參觀了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該局以“出品”M16步槍、隱形飛機技術和互聯網聞名。不過,Ho此行不是爲了軍備,而是爲了會見已退役的海軍上將約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此人曾任裏根的安全顧問,當時是DARPA一位高級項目主管。Ho聽說他正主持著一個新奇的實驗:搜集大量電子信息,從中鑒別可疑活動— 主要是恐襲。
從TIA到RAHS
在維吉尼亞辦公室的白板上,波因德克斯特一番描畫,向Ho介紹了自己構思的TIA系統(Total Inform ationAw areness,意爲“全面信息認知”)。該系統融合各類電子信息—包括電郵、電話、網絡搜索記錄、航空和酒店信息、信用卡交易信息、醫療記錄,再根據預設的檢測模式,尋找恐襲的蛛絲馬迹。其理念是未雨綢缪,發現恐襲于策劃階段,及時通知司法及情報機構介入。
這個系統讓Ho折服,“它可以將大量數據聯系起來,實現大海撈針的目標。”他想知道這個尚未在美國部署的系統能否用于新加坡—就在10天前,恐怖分子在印尼巴厘島襲擊了酒吧、夜總會和美領館,導致202人喪生,東南亞各國都惶然如驚弓之鳥。
帶著靈感,Ho回到了新加坡。四個月後,機會到來:非典疫情暴發,新加坡有33人死亡,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新加坡政府利用波因德克斯特的設計,迅速建立了風險評估與環向掃描系統(RAHS),防止恐襲和“非常規打擊”。新加坡官員紛紛就“大數據服務國防”一事發表演講,接受訪談。
與此同時,在美國,TIA成爲爭議話題。波因德克斯特與Ho會面後僅幾周,記者就報道說,五角大樓出錢資助挖掘公衆隱私的研究。一些國會議員和民權活動者呼籲關閉TIA,並獲得成功。但TIA的關閉僅僅是名義上的—2003年末,一些贊同波因德克斯特理念的議員暗地運作,把TIA分成幾個小的秘密項目,頂著新的代號,在國家安全局(NSA)主持下繼續進行,瞞著美國民衆,搜集他們的信息,進行恐襲分析,2013年,NSA前雇員斯諾登披露了該計劃的詳細內容,在美國引發了40多年來最激烈的關于安全和隱私問題的討論。
這一番吵鬧讓美國許多現任和前任官員將新加坡視爲樣板:即如果沒有隱私法和自由傳統的幹擾,他們將鑄就怎樣的情報機器。2003年波因德克斯特離開DARPA後成爲新加坡RAHS系統顧問,很多美國情報人員也跑到新加坡對該項目進行第一手研究。令他們著迷的不僅是新加坡式的監控,還有這裏民主與家長式混合的制度:政府通過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住房、教育、安全),換得民衆的順從。這是一個充滿法律與秩序的社會。
非典暴發成爲引子
成立兩年後,RAHS的發展超出波因德克斯特的想像。新加坡不只將它用于竊聽和找炸彈,搞采購、做預算、經濟預測、移民政策發布、房地産市場研究、教育方案設計—各部門都用上了大數據分析。他們還留意分析臉書、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的帖子,評估“國民情緒”—他們對政府社會計劃的反應、可能出現的騷動。換句話說,新加坡已成爲一個實驗室,它不僅想看看大規模監控和數據分析能否阻止恐襲,還想知道是否能用技術打造更和諧的社會。
對以維持秩序爲目標的中央控制式複雜技術系統而言,新加坡是最佳實施場所。在這個由工程師和技術官僚管理的國家,有一個堅定的信念:新加坡數百萬公民、居留者(包括華裔、印度裔、馬來裔)以及100多萬外來勞工一直生活在和諧與動蕩的邊緣,隨時可能出問題。“新加坡是個小國”—幾乎每個新加坡人都會對來訪者說起這句話。自1965年從馬來西亞獨立,它就充滿了緊張感,怕被強大的鄰國欺負,擔憂本土資源短缺,害怕淡水供應過于依賴馬來西亞。“新加坡本來不應存在,它是個創造出來的國家。”一名新加坡高級官員最近對我說。
但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裏,新加坡取得了巨大成功。2012年一份報告以人均GDP排位,將它列爲世界最富裕國家;新加坡港口吞吐著全球20%的海運集裝箱和一半原油運輸船,它的機場是東南亞空運中樞,數千家公司將其亞部總部設在新加坡。這樣的崛起速度堪稱空前,但新加坡發展得越快,新加坡人就越是害怕失去,源自中文的“kiasu”(怕輸)一詞傳神地體現了這種心理。
非典的暴發之所以能爲RAHS打開大門,原因正在于此。2003年2月末到7月,病毒在新加坡肆虐。官方調查後發現,是5位“超級傳播者”造就了該國238個病例,如果政府早點發現這些人,就可以阻遏病毒的傳播。
病毒發現兩周後,新加坡衛生部門成立一個工作組,采取了非常應對措施。但他們對病毒的傳播方式所知甚少,到四月中,到訪遊客進一步減少,酒店入住率直線下降,商店、餐館、出租車司機收入銳減,失業率不斷攀升。官方將2003年經濟預測從2.5%調到0.5%,最終研究表明,與之前一年同期相比,經濟收縮了4.2%。這讓新加坡人意識到,小小的病毒僅用幾個月時間就能危及他們國家的繁榮。
病毒退場後幾個月,Ho及同事利用TIA理念進行了一次演練,看能否預測出疫情,結果相當鼓舞人心:如果之前部署了大數據分析系統,新加坡可能會在病毒抵岸前兩個月便捕捉到疫情暴發迹象。比如非典來臨前,已經有報告說中國出現了難以解釋的肺部感染患者。類似的線索集中到一起,便會引起警覺。
一年之後,RAHS投入運行。它搜集並篩查大量數據,加以分析,創建模型,預測可能出現的事件,並在新加坡政府機構內分享。任何部門只要覺得信息有用就可以保存下來,以便進行針對性的關注或決定何時深挖。
廣爲接受的監控
主管RAHS的官員對該系統到底監控哪些數據守口如瓶,他們承認其中相當一部分信息來自公開渠道,如新聞報道、博客、臉書和推特。但RAHS不必只依賴公開信息和大部分政府搜集的那些情報,在新加坡,對居民和訪客進行電子監控普遍存在,而且被廣泛接受。
監控始于每個家庭。國防部一名高級官員告訴我,除了商業和企業通訊,新加坡所有網絡流都經過濾。主要有兩類內容受到控制:色情網頁和種族主義言論。大約有100個以性內容爲招徕的網站公開被禁,名單是國家秘密,但普遍認爲其中包括《花花公子》和《好色客》的網站以及標題裏含有性詞彙的網站(一個新加坡人告訴我,想找色情內容其實挺容易,只要網址裏沒有明顯的性詞彙就行了)。其他網站—包括外國媒體、社交網站和博客—都對新加坡人開放。但如果你發布法律認爲違規或有煽動性的帖子和文章,警察可能就要來敲門了。曾有新加坡人因爲在網上發表種族主義言論被控觸犯《煽動法》,但官員並不認爲這是審查。他們說,仇恨言論可能破壞該國多種族文化組成,因此威脅到國家安全。新加坡官員強調,公民可以自由批評政府。事實上,本年度新加坡暢銷書之一《艱難抉擇:挑戰新加坡式審查》就是抨擊政府的,書中指出1959年起一直掌權的人民行動黨故意制造“新加坡距毀滅只有一步之遙”這樣的危言,以便把大衆變成順民,鞏固該黨的權力。
但是,對個體的性格或動機進行指摘是不行的,官方認爲這就像種族主義言論一樣,會威脅到新加坡微妙的平衡。記者——包括外國新聞機構——常被指控觸犯該國嚴格的誹謗法。2010年,紐約時報集團因爲發表在《國際先驅論壇報》的一篇專欄談及李光耀家族的“王朝政治”而被告上法庭,最後支付11.4萬美元達成和解,《國際先驅論壇報》刊登了道歉啓事。
政府不僅關注民衆在公開層面的言論,也可依據反恐法、反毒品法和反不良出版物法合法監控各種電子通信,包括電話。“國際隱私組織”表示,“(新加坡)政府權限極大……如果認爲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秩序和公共利益受到影響,無須搜查證便可進行搜查。”
監控也延伸到訪客身上。遊客每到一地,通常要買當地手機SIM卡。犯罪分子喜歡一次性的SIM卡,因爲難以追蹤。但要在新加坡買卡,你得提供護照號碼,跟電話號碼聯系起來,這意味著電話公司(及政府)有你每次通話的記錄。
“國際隱私組織”表示新加坡人想擁有網絡賬號也要出示身份證明—主要是身份證—然後網絡服務提供商“據說會定期將用戶信息提供給政府官員”。一名國防官員告訴我,新加坡內政部也有權強制在新加坡的企業提交威脅電腦網絡的信息,以防惡意軟件和黑客侵害新加坡電腦系統。美國國會多年來一直聲稱,類似的規定可以強行要求一些對美國經濟和安全至關重要的行業交出威脅性信息,但遭到商會和企業的阻攔,認爲這是政府對私有安全事務的粗暴幹預,且成本高昂。
在新加坡,可能沒有哪種監控形式比攝像頭網絡更普遍了,警方在全國150多個區域布下這一網絡。建築物角落、電梯頂、酒店牆上、商店、公寓大堂都是攝像頭,但我遇到的新加坡人大多不太在意生活在一個“監控泡泡”裏,而且他們知道並不只有新加坡才這麽幹:“倫敦和紐約不也到處是攝像頭嗎?”新加坡人認爲攝像頭是用來震懾犯罪分子的,“在新加坡,人們普遍覺得如果你不是犯罪分子或者反政府者,就不用擔心什麽。”一名政府高級官員對我說。
今年,研究法治的“世界正義工程”組織將新加坡列爲世界第二安全國家,因爲這一榮譽,新加坡被認爲是“亞洲最適宜經商的地方”。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也在新加坡建立一個宏大的新中心,監控網絡犯罪,它是Interpol在法國裏昂和阿根廷之外設立的第三大中心,既反映出該組織打擊網絡犯罪的決心,也顯示出它對新加坡的信心。
大數據的社會化應用
但是,你很難知道新加坡的低犯罪率和遵從法治是普遍監控的結果還是新加坡人彼此之間有不成文的約定:千萬不能互相作對,以免這個島國從小處開始分崩離析。若是因爲後者,那政府即使在每個街區都裝上攝像頭,將每條網絡信息都搜集起來,還是不足以有效抑制犯罪、阻止恐怖主義或傳染病蔓延。必須在國民心中灌輸團結一致、要麽一塊沉下去要麽共同向前遊的意識,因此新加坡也在利用技術做這件事。
2009年,新加坡領導人決定將RAHS系統和情景規劃的應用擴展到國家安全之外。他們建立了“戰略未來網絡”,成員包括每個部的副部長,將RAHS方法輸出到整個政府系統。這個網絡利用未來規劃法應對各種國內社會和經濟問題,包括確認“戰略突發”和所謂的“黑天鵝”事件,即可能突然影響到國家穩定的情況。
RAHS就公衆對于住房體系的態度及願望做了一個調查。向民衆提供價格合理、公正的住房是新加坡政府的一個基本承諾,讓民衆在社區中幸福生活對國家和諧極爲重要。新加坡80%的公民住在組屋裏—高樓大廈中的時尚公寓,有些在公開市場可以賣到100萬美元。擁有新加坡80%土地的政府以低于3%的貸款利率出售房屋,允許買家通過強制性退休儲蓄賬戶來還按揭,雇主也要往這個賬戶裏付錢。結果就是幾乎所有新加坡公民都擁有房産,而且並不需要耗用太多收入。
未來規劃法也應用于許多政策問題,比如研究人們育兒態度的變遷,是否應該弱化新加坡曆來推崇的唯分數論,旅遊局用它預測下一個十年的遊客趨勢,政府則用它調查實驗室研發出的替代食品能否減少新加坡對于食物進口的依賴。
新加坡開始研究民衆中間流行的“懷舊”心態,即渴望更簡單、節奏更慢的生活,新加坡經濟騰飛之前、從第三世界沖入第一世界之前的那種生活。“懷舊也有負面影響,”政府警告道,“它可能反對現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反對新加坡成長爲多元化、全球化城市,培育出孤芳自賞的民族主義。我們在研究怎樣做可以把這種懷舊情緒引導到前進的方向。”
但未來正是讓新加坡人擔心的事情之一。2013年,政府發布了一份“人口白皮書”,描述了發展計劃,預計新加坡人口到2030年會增加30%,屆時已很擁擠的新加坡常住人口將達690萬。結果爆發了一場反對該人口計劃的遊行,有4000人參加,成爲新加坡史上最大的公衆抗議活動之一。這表明新加坡人不僅反對政府將國家建設得太大、太快,還開始反對移民鄰居們,認爲他們是房價上漲、工資下降的元凶。
這場抗議影響了“國家情緒”,政府立即反應,決定采取措施平息風潮,減少外來勞工。新加坡國家人口和人才署—類似于移民和人力資源部門—打算在接下來十年內,每年將外來勞工增長速度降低1到2個百分點,相對于過去30年每年超過3%的增長,這是極大改變。與之相伴的是,新加坡G D P增長可能回縮到年均3%到4%。不知道富裕的新加坡人和外國投資者能否容忍新加坡經濟放緩,也不知道這個總和生育率只有1.2的國家在外來勞工不足的情況下能否維持增長。但政府認爲,這是保持和諧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大數據就是這麽說的。
被監控者變成監控者
總之,如果社會穩定意味著要接受更多的監控和大數據掃描,新加坡人似乎很樂意做交換。RAHS一項研究表示,大部分民衆已經接受“監控”是阻遏恐怖主義和“自我極端化”的必須手段。新加坡人常虔誠地談到民衆和政府之間的“社會契約”。他們自覺選擇交出部分公民權和個人自由,換取最基本的保證:安全、教育、供得起的房子、醫療。
但是社會契約是可以談判的。“不應視之爲理所當然”,RAHS團隊警告,“也不應視之爲永恒。今天人們可以接受的監控措施也許新加坡未來幾代就無法容忍。”一項旨在調查“自下而上監控”的研究認爲,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盛行正將被監控者變成監控者。這些新科技“賦予民衆權力,使他們可以密切審視政府精英、企業和司法官員……使他們的名譽更易受損。”從拍下警察在警車內睡覺並上傳推特的憤怒市民到挑戰執政黨理念的反對派博客,新加坡的領導人也無法逃脫民衆的監控。
在新加坡2011年選舉中,人民行動黨“僅僅”獲得了議會87席中的81席。在多數政治觀察家看來,這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反對派獲得了史上最佳戰績,第一次對執政黨形成威脅,新加坡人開始反對政府管理國家的方式。甚至總理李顯龍也將這次勝利視爲值得警示的失敗。“這標志著我們政治景觀中一個顯著變化。”投票結束後他對記者說,“很多(新加坡人)希望政府采取不同的風格和方法。”
這個選舉結果跟監控本身關系不大,但監控及其表面上的好處正是政府塑造新加坡模式的一個切實部分。2002年Ho與波因德克斯特見面時,波因德克斯特表示在新加坡建立大數據分析系統比在美國容易多了,因爲新加坡的隱私法寬松得多。但是Ho回答說,法律不是唯一需要考慮的方面,公衆對于政府計劃和政策並非全盤接受,特別是涉及到侵犯人們權利和利益的時候。
看來這是一個精准的預測。在這個小小的大數據實驗室,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結果:新加坡人在網上待的時間越長,讀到的東西越多,跟他人及政府分享想法的時候就越多,就越會意識到新加坡的做法在發達民主國家中並不完全正常,政府也並非絕對可靠。新加坡是其他國家仿效的模範,在這個方面,新加坡更能提醒人們的,或許正是大數據的局限性,不是所有問題都能預測得到。
(文章來源于《外交政策》,文/Shane Har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