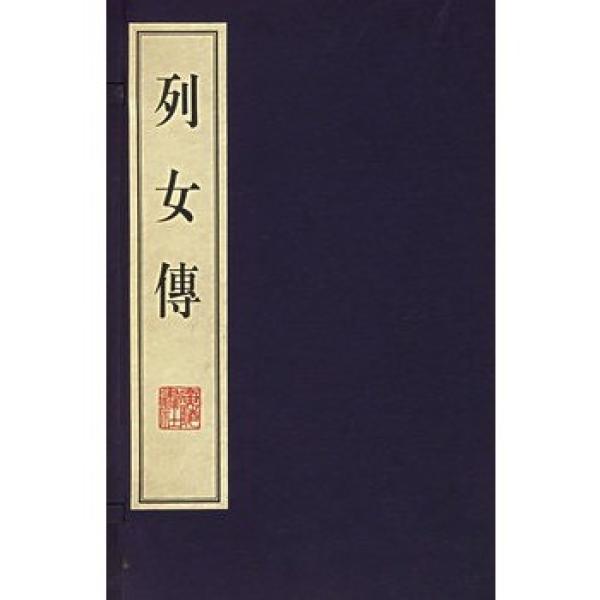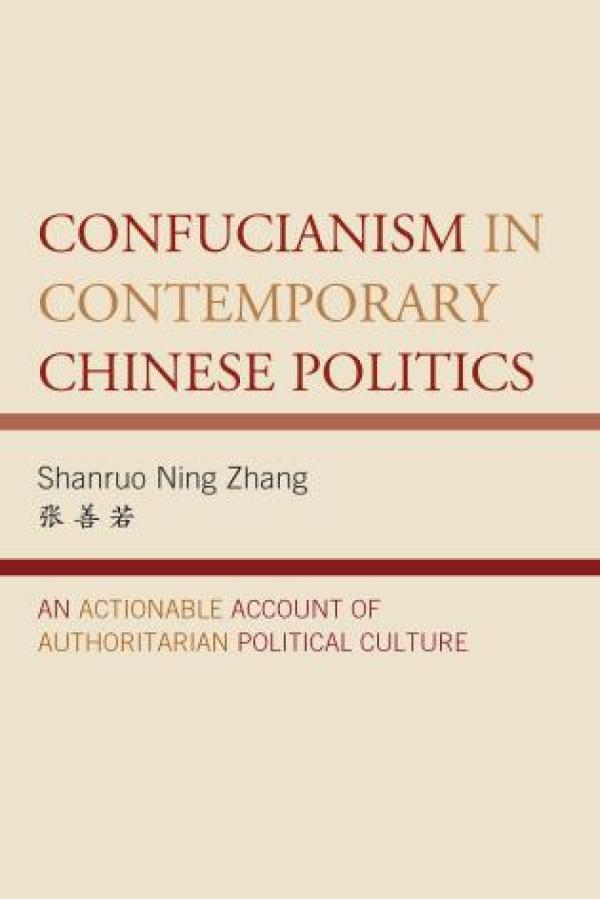近日,歌手孫楠一家爲送孩子學國學從北京搬到江蘇徐州的消息引發熱議。原來,孫楠爲孩子選擇的是一家主打國學教育和傳統文化的學校“華夏學宮”。視頻資料顯示,孫楠的幾個孩子能熟練背誦《弟子規》,潘蔚還會在家教女兒們女紅,爲的是讓她們“用針線傳遞愛”。潘蔚在視頻中強調自己是爲了追求內心的平靜而傾心于國學的,她個人也在這所學校擔任女紅、茶文化老師。
國學教育往往以弘揚傳統文化爲宗旨,但這些教育也往往由于與現代精神的違背而飽受爭議,而往往與國學教育綁定的“女德班”則更是常常爆出聳人聽聞的課程,以東莞蒙正“女德班”爲例,他們將“德行”解釋爲三道:姑娘道、媳婦道、老太太道。“每道都有女人要守的本分”,然後才能擁有健康和財富。
“女德班”頻遭诟病卻又屢禁不止的深層原因已多見諸報端。例如,性別研究專家宋少鵬認爲女德班是市場需求的産物,女德班滿足了部分中國女性想要緩解作爲“個體人”與作爲“家庭人”的結構性沖突的需求。她認爲,面對赤裸裸的性別不平等,女德班用傳統女德來正當化“男女不一樣”的運作原則。女德班教導女人與其在兩種互相沖突的原則中受煎熬,不如接受一種原則來化解內心的痛苦,並能更好地接受現狀。
而我們關心的問題是,爲什麽近年來的公共討論裏,女德班總是和國學“綁定”在一起?女德班和 “國學熱”存在自然而然的聯系嗎?澎湃新聞也就此問題采訪了旅美政治文化學者張善若。
張張善若博士于2007年在美國加州⼤學聖巴巴拉分校獲得政治學博⼠學位, 師從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M. Kent Jennings 教授,現爲美國加州理⼯州⽴⼤學政治學系教授。她的英文著作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 Actionable Account of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ulture已于2015年出版。
張教授是中國出生、成長的學者,同時因爲在美國生活近20年,她對美國社會有長期的觀察和個人經驗,她的女性身份,也使她在探討相關議題時可以提供女性視角。從此次大衆文化事件切入,我們和張教授聊了聊她對女性主義以及女德的看法,儒家思想的複雜性,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産生的對儒家的誤解。
張教授認爲,首先,女德和儒家以及國學是不應該放在一起討論的,因爲儒家塑造的文本裏面的女性形象其實多種多樣的,並不是流行印象裏的“女德”那一種;第二,那種認爲儒家思想裏找不到性別平等的思想資源繼而等于文化糟粕的觀點毫無道理,我們也談到了外國學者爲什麽研究儒學,以及從中尋找到了什麽樣的思想資源;第三,國學班這種反潮流的文化現象在美國也出現過,張教授認爲,文化的發展裏面總會參雜一些反潮流的東西,不必過分驚恐,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
張善若教授
【對話】
“儒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多種多樣,並非流行觀點中‘女德’那一種”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看待女德這個概念的?又如何看待女德班往往和國學或者儒學的綁定?
張善若:我認爲“女德”這個概念其實它掩蓋了很多現實,道德當然是好的,學習道德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爲什麽要把某一些道德專門標榜成女德?爲什麽只有女性才應該具有這樣的道德?所以女德這個概念,看上去是以德作爲閃光點,但本身它就有一定的不平等的內涵。爲什麽沒有男德的概念呢?當然這個社會對男性也有某些具有刻板成見性的要求,但是從實踐上講,爲什麽只有女孩子被送到這些學校,去學女德,爲什麽男孩子不被送到學校去學溫良恭儉讓呢?
而且女孩子到這些學校,除了所謂的國學傳統經典之外,其它實踐完全又脫離了這些美德教育。比如我搜索了女德班的相關新聞,馬上照片就出來了,可是他們那些具體細碎的行爲規範,也和所謂的儒家美德譬如三從四德沒有必然聯系。我在新聞裏面看到一些女孩子要跪在地板上擦地,中午吃飯要等到男孩吃完了以後才去吃,這些和道德都沒有什麽關系啊!它的實質是從價值觀到行爲,一系列的這種點點滴滴的滲透灌輸,強行壓制進去男女不平等的一個觀念啊!
國學或者儒學其實是很豐富的,爲什麽非得挑出女德這一塊來教或者來營銷?當然,如果硬要討論,我們也可以討論女德和國學之間的關系,但實際上這個關系是非常疏離的,女德和國學不存在一個自然而然,理所應當的一個聯系。女德也並不是國學的一部分。如果講女德的時候打著國學的旗號,是很值得商榷和懷疑的。女德這個概念和儒家沒什麽關系,據我了解,很多是用國學或儒學來包裝女德班吸引學生而已。
澎湃新聞:爲什麽他們的聯系並非自然而然?
張善若:國學這個詞是清朝中末以後,西學越來越盛行的大背景下被提出的。國學就是中國的學問,屬于中國的學問,中國的學問就是文史哲,那麽儒家框架下的文史者,如果說因爲孔子說了“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這樣一句話,那麽現在這種“女德”就是儒家文史哲的一部分,我不認同。如果我們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敘事和話語都看做是龐大的“儒家文本”的體現,那麽梁山伯與祝英台、穆桂英、花木蘭、《孝女傳》、《烈女傳》都是這一個文化體系的一部分。這些女性形象,倡導的究竟是什麽呢?不是女德班教的那些具體的細瑣家務和照料責任,這些與“國學”和“儒家對女性的定義”都沒有必然聯系。
如果我們一定要說這個女德是儒家思想體系龐雜的思想體系中的一個小支流的話,我可以想到的文本是三從四德這些東西,那麽三從四德又和讓女孩子們跪在地上擦地板有必然聯系嗎?和讓女孩子們等男孩子吃完了飯以後再去吃有必然聯系嗎?女德和國學是不應該放在一起討論的。
澎湃新聞:在《列女傳》或者《孝女傳》裏面,其實並沒有如今這些女德班教的東西是吧?之前看過一個視頻是溫州的女德班,也是記者暗訪的,很多家長送孩子去。記者拍到的視頻裏面,小孩上完課得出的結論是:“我媽媽生病都是因爲我不孝順,”家裏面發生任何不好的事情,都是因爲孩子不孝順。
張善若:儒家有《孝女傳》,《孝女傳》裏面這些孝女究竟是什麽樣?那是大孝大勇大智啊,而不是趴在地上擦地板。不是現在的女德班裏的那些如何做家務的內容。
另外,在儒學經典裏面,其實是有一些女性是很有力量的。 儒學是一個非常浩大的一個文本體系。如果只是基于所謂的儒家經典,比如四書五經,甚至現在在孩子教育中流行的《三字經》、《弟子規》之類的文本,就給儒家蓋棺定論的話,我覺得儒家就冤死了。當我們提到儒家的時候,它不是一個像活化石一樣的,就那幾本書,它是一個活生生的話語體系,一個話語體系,一種思想體系。比如說孟母三遷,孟子的母親,這些有見識有能力,有魄力的女性,小說中女性的將領(如穆桂英),這些難道不都是儒家思想體系中的女性形象嗎?
這些具體的課程內容是打著儒家或者國學的名義在造假,特別是在我們現代的視角下,一種對女性的故意打壓,如果這些學習班通過這樣的做法去向女孩子們灌輸一些觀點,還堂而皇之地挂上國學的旗號,這就是糟粕了。
澎湃新聞:我好像確實會帶有偏見,可能我會把儒學思想當成活化石,然後那些強大的女性,就覺得好像跟儒家沒關系,沒有想過她們其實也是該體系裏的産物。
張善若:她們當然是這個體系中的産物,我們現在過于看重孔子說了“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以及新文化運動打到孔家店,所以儒家是被簡單化了。儒家是什麽?儒家是孔子的學說,還是董仲舒後來發展的東西,還是朱熹王陽明後來的發展出來的宋明理學呢?儒家是一個非常龐大浩瀚複雜的一個思想體系。
儒家思想裏關于性別平等的思想資源少不等于儒家就是文化糟粕
澎湃新聞:我覺得現在很多人認爲儒家的整套理念思想裏是沒有任何可以去學習的了,特別在性別這一塊,因爲現在輿論爭論的最厲害的一個就是到底如何做女性的問題,有人可能就覺得沒有必要再看這些東西了,它完完全全已經是跟不上時代的事,是完全的糟粕,你又怎麽樣看待這樣的觀點呢?
張善若:剛才講過儒家經典本來就是非常的紛繁複雜,它內部也存在很多的多樣性,也是分階段的,它也並非一致性非常高的東西。當然,儒家所謂的經典以及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對女性的關注低,這個也是沒有什麽可爭議的。
在其他的國家,曆史也是差不多的,可能全球範圍都會有這樣一個趨勢。那就是,女性地位經曆了從低到高的過程,這和生産方式的變化息息相關的。農業社會的時候,生産就是靠體力,男性是更主要的一個生産力的來源,那麽逐漸進入工業社會以後,對體力的要求就越來越少了。那麽女性的智力,女性的情商,女性的溝通能力,語言能力協調能力就逐漸的慢慢都凸顯出來了,包括一些創造力也都體現出來了。
但是我們現在認爲在儒家傳統裏面的女性社會地位很低,一方面它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現實,當時社會的現實又是在秦漢大一統以後的一個封建家長制,也就是說現實和思想是互動的關系。當時的這種生産方式使得男性有一個更加顯赫的地位,這樣的“男權”式的知識體系又制造了很多思想和學說來合理化以及鞏固這樣的狀況,有意無意的鞏固這樣的一個地位,所以在這一套思想體系中,我覺得現代女性所需要的那些資源和思潮在儒學裏面可能真的是很少的。
也就是說,儒家沒有像我們現代女性希望的那樣給女性一個平等,但是那個時候就不是這麽一個時代,沒有平等的現實的條件。但是,這一套思想體系裏面沒有特別現代的關于女性的意識的話,是不是就直接可以把它定位成糟粕呢?
再說,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現代和後現代社會,在這樣的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爲什麽一定要到儒家裏面去找到資源呢?難道我們要說,2000年前他們沒想到我們2000年後需要這麽一個東西,沒寫到這個《大學》裏頭,所以它就是糟粕嗎?!這毫無道理。
澎湃新聞:一直很好奇,外國人研究儒家,他們是基本上有什麽樣的共識,或者是他們認爲這個研究的重要性是在哪裏?
張善若:這個問題很好,研究這些的一般是曆史學家或者是學政治思想的,他們是從美國的角度或者西方角度出發,想解決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針對西方的問題,東方智慧給我們提供什麽資源,他們發現了哪些資源?他們發現比較多的,就是我們的團體精神,集體主義精神,英語叫做“communitarianism”,因爲對他們來講,針對西方的極端個人主義,東方的團體精神是一個解藥。
舉個例子,前兩天,我們學校的殘疾學生援助中心派了一個人來到我教室裏說,班上有一個同學沒法自己做筆記,需要一個同學自願幫助他,只要把他的筆記拍成照片然後放到網上就可以了,這個人問有誰願意,全班靜默了好幾秒,沒有人願意,這些東西在中國可能都不太成問題。但是在美國就成了非常顯著的問題,因爲他個人主義特別的嚴重。我上博士的時候,全班有十幾個同學,我那時候有一個好朋友,她是一個韓國人,全系當時就只有我們兩個是亞洲人。然後每一次班上需要同學把這篇文章複印一下,然後放到網上大家都能看的,或者班上要吃一些東西,有沒有同學願意到哪去取一下,這些事情永遠都是我和她在做。其實我一直都沒有什麽感覺,我覺得爲集體做點事情是應該的,但是她就很生氣,她說,你有沒有發現每次都是我們兩個亞裔的女孩兒爲大家服務?
儒家使得外國學者有興趣的另一原因是東亞經濟崛起對歐美人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意外。他們沒有想到在二戰結束以後二三十年的時間,日本韓國這些他們以前認爲非常窮的地方,新加坡以前都是殖民地,突然經濟可以發展成這樣。所以像哈佛的杜維明寫的東西,就是講儒家的這種團體精神以及刻苦精神,勤奮精神等相當于歐洲的新教,歐洲是因爲新教發展出資本主義,那麽東亞就是因爲儒教發展出了資本主義。
第三種情況,包括我自己的作品,是說“冷戰”以後,如何去研究如何去看待中國的發展?大家就逐漸看到除了社會主義視角以外,還有一個曆史和傳統文化的視角,所以又有一些書,包括我自己的就是在探討這些東西,就是說現在中國的發展有哪一些是需要從1949年以前曆史爲基礎來解釋的。一方面是想說中國政治有中國政治的特點:一個是這種精英主義,一個是善治,中國的體制能夠很有效地把精英把最聰明最能幹最刻苦最投入的人放到治理系統裏面去,于是中國的治理才如此的有效。那麽這一種治理方式從哪裏來的?從文化傳統來說,就是從儒家來的。
澎湃新聞:所以你的研究是理解儒家思想對當代的中國政治實踐的影響,你認爲儒家思想已經是我們的一部分了,如果一定要否定這種影響的存在也是不尊重現實,並沒有要去推廣它或者是複興它,是這樣嗎?
張善若:對,這麽說吧,如果把儒家剔除出去,我們是無法完美地理解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的。文化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不是斷裂性的,中國文化發展的路徑到底是什麽?很多儒家的思想確實在影響我們現在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從此出發,中國需要尋找自己的道路,中國也正是在自己的道路上的,我們需要很踏實地很安心地去發展出屬于自己的文化。
但是雖然我研究儒家對當下政治文化的影響,但我個人的立場也不是要把孔子當年寫的文本或者董仲舒的那些文本,這種幾千年以前的思想在當下複活。我們要走自己的道路也不等于要去複興儒家,要去穿漢服,要把幾百年以前的東西拿回來,也並不是這樣。難道大家都穿了漢服了,中國就複興了嗎?我覺得這兩個事情之間沒有什麽聯系。
我們現在生活在2019年的這樣一個世界裏面,世界有那麽多精彩的思想,在中國能接收到世界各地的學者給我們帶來如此多的思想和文化資源,我們爲什麽要把精力單一地花在推廣儒家上?這樣的做法和我們現代的進步的思想以及日新月異變化飛快的中國實踐都是不相吻合的。我不贊同這樣的做法,我不會送我的孩子,男孩女孩我也都不會送他們去學這些東西。
從曆史诠釋學的視角來看,一個國家、社會、文化對自己傳統的認識,永遠是不可能真正地回到那個時代文本被制造出來的時代那樣去認識和實踐的。我們對傳統的認識,應該考慮的是如何激活儒學,怎麽樣去讓它爲我們的現代來服務,而並非把2000年3000年以前的社會風俗,家庭、習慣人際關系等在現代社會重演!這樣做一是背離時代精神,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澎湃新聞:儒家的哪些資源你覺得是特別積極的?
張善若:其實在中國文化裏面,關于話語和討論有我們自己的傳統。比如說中國人一直就講同情心、憐憫之心,其實放到現在話語裏面,不就是共情的意思嗎?就是你能夠把自己放在別人的角度上去思考和看待問題。我們中國人講和就是以和爲貴,這句話裏面富含長年累月積累的曆史經驗。這個和諧如何形成,在一個紛繁複雜的社會和文化現象裏,通過共同的討論和真正的深層交流,能夠讓社會形成一定的認識。這個認識當然也不是不變的,它根據現實能夠形成一些引導的作用。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一些問題。
儒家裏面積極的資源很多,比如說學行合一。這是多麽大的智慧,知識論和實踐論結合在一起,是儒家文化中對現實非常實用理性的一個概念。當鄧小平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時候,爲什麽中國人馬上就接受了?爲什麽這個概念如此容易被接受?因爲這就是我們思想深處的東西。
儒家這個概念作爲一個符號,對不同的人來講,意味著不同的東西,我其實也都不太說儒家,我覺得這一套東西其實就是中國政治文化。從夏舜禹的時候開始,我們的政治曆史開始發展,然後曆史學家們政治家們通過對這樣的曆史發展進行歸納總結,然後發展出我們自己的政治理論,然後用這樣的政治理論去指導我們的政治實踐,對于政治的理解和政治的操作是我們很獨特的一份寶藏。
這樣的政治的經驗,我覺得都是非常值得我們現在去研究和學習的,而不是說一些什麽帶了儒家標簽的價值觀,或者說觀念,或者說女孩子要去做手工。做了手工你就變成好女人了嗎?你會刺繡你就變成好女人了?現代社會對女性的要求真的是這樣的嗎?
我們對女性的定義、期待不應該是脫離社會現實的,作爲有思考能力的人,她在學的過程中,也會去想知和行到底是什麽關系?在女德班中學到的東西對我現在2019年面對的我這個現實究竟是一個什麽意義,我想學生們也會去思考這些問題。
澎湃新聞:具體來說,那些學習儒學的人,或者那些上女德班的人,最終學到的東西是不是也是不一樣? 在此次熱點事件裏,當事人女孩就堅稱她上的那些課,她不認爲是女德,她也不希望網友評論她的所學。
張善若:當然,學習永遠是很個人的過程。我給學生上課,上課雖然教一樣的東西,每個學生都從自身的角度去學習,他們去攝取和反思知識,最後變成自己的理解。每個人的理解也都是不同的,他把這個理解重新融入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當中,然後再把這一套東西投射到他的實踐裏面,實踐又跟外部世界相互動,所以每個人學習的經曆以及其效果都是不一樣的。
我們談儒學也是一樣的,其實每個人讀《論語》讀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我們是把孔子當時說的文本,通過我們的現代的視角去攝取進來的。我們也只是攝取部分,沒有人能夠真正的攝取到論語的全部。我們只是去抓取對我們這一刻來講最有意義的那一部分,然後把它拿到我們的世界裏來進行理解和诠釋,其實是把孔子當時的視域和我們現在的視域融合在一起,變成了我們對論語的理解以及現在的應用。
張善若所著《當代中國政治中的儒家思想》
“文化運動中必然有反潮流的部分存在”
澎湃新聞:女德班爲什麽會出現?對于這種現象,你是如何理解的? 如何看待這種卷土重來的“男人是天女人是地”類似這樣的說法和寫作?
張善若:文化的進步就是亦步亦趨的,不可能是線性一元性發展,一定是一個多元性的發展,有人要往左走,有人要往右走,有人要飛速的近現代化進步,有人想要留住傳統文化的發展,一定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也必然是有反潮流的部分的。這種情況在美國也是如此,比如說美國女權運動從女性爭取選舉權開始就開始了,就是100年以前1920年左右,那個時候已經如火如荼了。但是最近幾年在美國南部比較保守的一些地方,卻開始重新討論女孩子的貞操。有一些當地女孩18歲生日的時候,就會在左手無名指上帶一個象征貞操的戒指,並且會發一個誓言,說我在結婚之前不會有性行爲。這些人基本上是比較虔誠的教徒,受地方文化氛圍的影響很大。
我記得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美國的各大媒體也都做了很多報道。我和同事因爲在加州,文化就比較開放,就覺得特別無法理解。
女孩長大的過程中,她的價值觀就是被培養的被社會塑造的,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學者們認爲人就是十七到二十五歲這個階段思想最爲開放,二十五歲以後人的價值觀就不會有大的改變了。這個階段在學術上叫政治社會化。人剛出生的時候,還是一個小baby的時候,並沒有任何價值取向,然後我們是如何一步一步從一個腦子一片空白的個體,變成一個社會和文化的一份子的過程就叫做政治社會化:通過給你灌輸一系列的價值觀思想知識等,讓你變成了社會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這個反潮流算是一個貶義詞嗎?
張善若:看從哪個方向講。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講,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其實挺正常的一個現象。但是這個正常不代表我贊許,不代表我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更多。只是說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我覺得是可以預見到這樣的事情是會發生的。
我不贊同現在流行的這種國學課或者女德班,但是我也不覺得應該把它一棒子打死,因爲你把這個聲音壓下去,他們也不會被消滅掉。因爲這確實也是一部分女性的聲音。我們可能沒有這種觀念,不能不允許別人也沒有。人們的經曆不同,思考問題的方式也不同。如果這是他人真實的想法,也應該給予他們一定的空間去實現。
澎湃新聞:說到“女性形象”的潮流與反潮流的問題,現在表現出特別顧家反倒成爲一個不合潮流的事情。前段時間女星伊能靜一個微博發言,大概意思就是說現在想把重心放在孩子和家庭上,她下面的評論中點贊最多的是:你給現代女性做了非常不好的榜樣。意思就是說她作爲一個女明星,她應該給女性的榜樣是如何去追求自己的事業的。這些評論人的眼裏面就是你回歸家庭,等于你不再是一個獨立女性了。這樣的觀點我是不太認同的,成爲獨立女性的這種聲音在城市裏面是非常強的。大家看到只要女明星不再是這種所謂大女人的人設,她表現出特別顧家反倒成爲一個不合潮流的事。
張善若:現在家庭主婦的做法可能確實是反潮流,因爲現在的潮流是女性主義嘛,潮流是獨立女性,但是所謂的女性獨立追求的最後追求的是什麽?追求的是一個選擇的自由。
我們之所以現在講女性獨立,是因爲女性一直不獨立,她沒有選擇的自由,她想上學沒學上,她想上班沒班上。因爲她在經濟上它依賴于男性,所以她受到各種各樣的束縛,現在做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爲了給女性一個選擇。但是以前只能向左走,現在只能向右走,那不是又沒有選擇了嗎?
同樣,這個現象也不光是中國有,美國十年以前就有很大的討論,一些家庭主婦就覺得這個社會是不支持她們的,她們從社會和文化裏得不到資源得不到支持,因爲大家都在討論職業女性,就是越職業越好,越不顧家越好。
我認爲只有當女性獲得這樣自由以後,男性也獲得了這樣的自由,這才是真正的平等。就是說一個男性他如果說我想呆在家裏面做一個好丈夫,只要他們兩個人能夠商量好,社會不應該對他有任何的歧視,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兩性自由。所以在解放女性的同時也在解放男性。這個結果就是兩個性別都獲得了更多的選擇的自由,這個才是我們的進步的目的。
澎湃新聞:談到美國的話,我也了解到一些私校有男女分校。在男女校裏面是不是他們學的東西確實是不一樣?比如說女生就有一些手工課,而男生沒有?你對這種男女性別分開接受教育是不是也不太認同?你認爲應該是一視同仁地接受教育,接受社會化?
張善若:因爲以前女孩子就不受教育,只有男孩受教育,後來一些比較開明的家庭願意送女孩去上學,也許已有的學校不知道該怎麽聚焦于女孩子,或者可能認爲男女孩子一起上學會有一些麻煩,他們沒有這種管理的經驗,所以可能就專門給女孩子們開一個學校。
回到你這個問題,我覺得做手工當然沒問題。我想強調的是,隨著機械化以及電腦化的這種發展,其實很多手工的男女界限開始消失了。我最近發現一個現象,我的好幾個女性朋友都開始學做木工了。我9月份去開會的時候,碰到一個教授朋友,她快退休了,她退休的計劃就是准備搬到緬因州的一個地方去學做木工,包括木雕等。我回到學校以後,發現我的一個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同事最近也開始做木工。
然後同時又有一些男性他會去做一些可能我們認爲比較偏女性化的東西。比如說我有一個男同事,我經常在菜市場、超市碰到他,他經常下了班去買菜。我在街上看到爸爸推著嬰兒車的情況也越來越多了。現在美國25%的家庭裏面,女性的收入已經超過男性了。電視電影裏面看到女的CEO越來越多了。
澎湃新聞:有些人倒也不是不承認家庭主婦的貢獻,但是他們會強調在職場的女性,她得到的那種滿足感是更高級的滿足感,照顧孩子獲得的滿足相對是低級的滿足。這些人認爲家庭主婦也在爲社會做貢獻,但是家庭主婦沉浸在一種低級的勞動裏面,會忘記了女人還可以做更高級的事情。
張善若:我覺得這個關于低級還是高級的決定還是讓當事人自己去做吧!我覺得當一個好媽媽要對個人素質要求是非常高的,因爲當媽媽要做各種各樣的判斷,采取各種行動,不是一件不如工作的事情。這個真的就是個人的選擇,有的人當媽媽都很快樂很開心,甚至要比你工作起來可能滿足度要更高。
從個人角度來講,我們沒有必要去爲別人做一種判斷。而從社會來講,一個好的社會,它的功能就是給各種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提供支持。那麽當一個職業女性她想生孩子的時候,你就給她産假,你讓她能夠有足夠的時間去把孩子的最初降臨到世界裏的一段時間的這種急需的要求給它處理好,給她一些靈活的空間,讓她能夠兼顧孩子和工作。然後如果說一個女性她很想回家當媽媽,然後也放棄一段時間工作,這個社會也不要歧視她,讓她很開心很安心的去當媽媽,因爲一個快樂的媽媽才能教育出快樂的孩子。
快樂的孩子對這個社會也是很重要的。當一個媽媽把孩子養得差不多了,在孩子上學後她又有空閑的時間,她又想回到工作崗位。社會也不要歧視她,要給她機會去找到合適的工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理想化的社會應該給女性提供的保障。同時我也認爲也應該給男性提供産假,比如說在美國我的男同事,他們妻子生孩子他們也有産假。男性的産假肯定會減輕女性的負擔,能讓女性更快地回到工作崗位。
一個女性如果說我生了孩子,但是我特別熱愛我的工作,我就是想回去工作,然後夫妻兩人都同意,說男性可以呆在家裏面管孩子一段時間,社會也不應該歧視這個男性。我覺得好社會就應該是這樣的,而不是總是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對別人下判斷。
澎湃新聞:還有一種看法是,那些選擇去做家庭婦女的女性,她根本就沒有反思過,譬如那些偏遠城市的人,從來沒有考慮過女人還有把事業放在第一位的這種可能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人會覺得要矯枉過正,要旗幟鮮明地鼓勵女性,不要去學女德那套教女人順從的東西,而是鼓勵她們像男人一樣去工作,他們會認爲在現在的社會是應該強有力的去鼓勵大女人的。
張善若:我周圍的很多女性都是女博士,但是最後這些人做的選擇也又有不同。有的人就是會更顧家一些,有的人就是會在事業上走得遠一些。我的經驗是,我的每一個女朋友的情況都那麽錯綜複雜,每個人的現實都那麽的真實,每個人都是那麽一步一步的攀登,然後每一個人面臨的這種機會結構又非常的不一樣,所以往往我們認爲可以輕易做到的,別人可能真的就是做不到,可能就是沒有空間。反過來也一樣,在別人的生活軌迹中似乎非常自然而然、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們卻也覺得困難或者有阻力。
所以我覺得精英從自己的這種制高點,不管是什麽樣的制高點出發去評價別人都不好。我能夠理解矯枉必須過正的想法,這樣一種策略,也相信用意是好的,但是在我的人生實踐中沒有成功過,所以我覺得我就是一個溫和的支持者的態度,才能夠讓每個人按照自己的速度一點一點地去進步。
澎湃新聞:你希望社會對國學班或者女德班形成一種什麽樣的態度?不只是女德班,現在也有太太班,出現這樣現象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麽樣去看待她們?
張善若:我覺得應該加強理性的討論,不應該有那種自動性的“膝跳反應”。不能因爲這種做法跟我不一樣,我不會這樣做,那我就自動認爲它是錯的。我覺得如果能從這樣的一個狀態中暫時的脫離出來,大家能夠作爲一個社會成員,在動態的發展狀態中去討論一個現象,文化發展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每個人的經曆和需求是不一樣的,社會給每個人的角色也是不一樣的,人們想要學什麽,需要獲得一些什麽樣的知識,這些都不同,我們很難從一個外部的角度去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