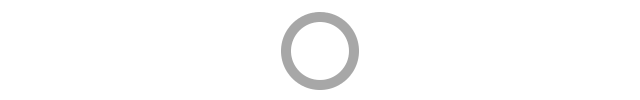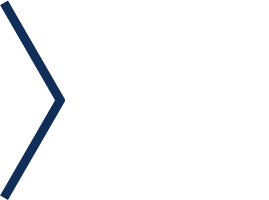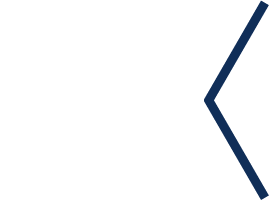提要
《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産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又稱《新加坡調解公約》)于今日(2019年8月7日),在新加坡開放簽署。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聯合國秘書長法律事務助理Stephen MATHIAS出席公約簽署儀式並發表演講,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過視頻發表講話。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李成鋼代表中國政府簽署該公約,目前公約簽署國已達46個。
《新加坡調解公約》于2018年12月20日在第73屆聯合國大會上通過,適用于調解産生的國際和解協議。《新加坡調解公約》確立了關于援用和解協議的權利以及執行和解協議的統一法律框架,是一部便利國際貿易並促進將調解作爲一種解決貿易爭端的有效替代方法的文書。本文擬對有關《公約》的八大問題進行梳理與分析。
《公約》帶來的深層次影響
加入《公約》帶來的深層影響有如下幾個方面:首當其沖的是可以讓締約國公權力提供和解協議的“保險櫃”。《公約》的實質是讓締約國對協議執行給予更高水平的保障,即通過對“不認賬”的一方強制執行來救濟另一方,以保障協議的確定性。換句話說,是締約國對于通過調解來解決爭議的鼓勵。
此類爭議如果通過訴訟或仲裁解決,耗時長、程序多、花費大且容易導致雙方更加對立。調解則簡便高效、不傷和氣,但執行容易存在問題。如果對方事後不配合執行,還要重走一遍其他爭議解決程序。
調解實踐中,雙方采用諸如“第三方賬戶”等自行執行的辦法,可以提高協議的確定性。由此,是否可以建立一個有公權力保障的機制,將這類協議放到一個更牢靠的“保險櫃”裏確保執行?《公約》可以說是應運而生,讓締約國提供了這個“保險櫃”。
加入《公約》爲可執行財産與部分營業地在中國的企業提供便利。根據《公約》第一條,具有國際性的協議只需要爭議雙方營業地及執行地中任意一項具有國際性。就中國而言,可以有以下排列組合:中-外-中(執)、外-外-中(執)、中-中-外(執)、中-外-外(執),其他情形不予討論。加入公約,可以保障可執行財産在中國的中-外-中(執)、外-外-中(執)型和解協議的確定性,爲商事主體提供便利,讓當事人多一種途徑解決爭議。只要公約生效,執行地加入,那麽中-中-外(執)、中-外-外(執)型也能得到保障,與我國是否加入無關。
加入《公約》可節省締約國司法資源,改善營商環境。如果爭議雙方能夠通過調解達成協議,締約國不必再興師動衆對此進行處理,可以節省締約國司法資源。同時,多元、高效解決爭議對于商事活動而言肯定是利好。協議內容由爭議解決雙方商量確定,較訴訟省時省力,較仲裁節省費用,能夠在《公約》的締約國保障執行,由此可以激發企業活力,改善締約國營商環境。
加入《公約》還爲營業地在中國或可執行財産在中國的企業帶來更多優先合作機會。對于國際經貿合作而言,通過此種方式解決未來潛在爭議,可能也會獲得更多的合作機會。
對“明示適用公約”是否保留
是否保留“和解協議當事人已同意適用本公約”,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似乎都有道理。
認爲應作此保留的主要考慮是:首先,和解協議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産物,如果當事雙方想給和解協議一個更加嚴格的履行義務,但沒有在和解協議中明示適用《公約》,就不容易判斷當事人對協議的法律後果是否明確。
其次,也會導致協議雙方權利義務不平衡。如果當事人未明示適用《公約》,而申請救濟的一方即便不知道,也可以在事後申請強制執行,則另一方只能被動接受《公約》制約,難免有“厚此薄彼”之嫌。
此外,對于締約國由《公約》産生的強制執行義務而言,只有明示適用的才需要在後續給予救濟,也更確定。
認爲不用作此保留的考慮主要是:締約國加入《公約》,《公約》即成爲該國法律淵源。當事人對于可執行財産地所在國的法律應當遵守。
當事人簽訂此類和解協議時,應當知道這一後果,即締約國可以通過強制執行對這類和解協議予以保障,與締約國國內司法實踐對其他和解協議的保障程度沒有關系。
互惠保留
公約沒有“互惠保留”,是否會導致締約國與非締約國權利義務不平衡?這就涉及對兩個問題的分析。
一是“互惠”不好確定。法院判決和仲裁裁決中的“互惠”比較容易確定,前者涉及判決地和執行地,後者則涉及裁決地和執行地。在調解中,協議是雙方意思自治的體現,強調“調解員(或機構)所在地”“調解協議簽署地”或其他標准意義不大,並且可能帶來混亂。
考慮以協議一方或雙方營業地在外國的該“外國”爲標准互惠,遇到外-外-中(執)情形,若爭議雙方的營業地中,一個是締約國,另一個不是締約國,就不好確定以誰爲標准互惠了。
二是“互惠”保留實質上未必會帶來“互惠”的效果。在“中-外-中(執)”型和解協議中,如果尋求救濟的一方是營業地在中國的企業,根據上述標准進行互惠保留,恐怕會有“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風險。
究其根源,《公約》讓爭議多一種渠道得到有效解決,就是給締約國帶來的最大的“實惠”,或者說是“惠而不費”。
執行壓力與派生訴訟壓力
加入《公約》,是否會承擔更多的強制執行義務,給司法資源帶來壓力?
筆者認爲,執行義務並未增減,但短期內可能帶來更多執行申請,但由于財産的執行管轄權屬于締約國,如要解決爭議,執行的義務並沒有增加或減少。
可以確定的是,加入《公約》,多了一個途徑解決爭議。在同一時間段內,由于更多的爭議解決了,按照相同的概率,確實可能帶來更多的執行申請。但是,這些爭議如果不通過調解解決,恐怕還是要走訴訟、仲裁這兩種既有途徑,只不過會在一個更長的時間段裏來申請執行,且訴訟的壓力與可以通過調解有效解決相比會更大。
《公約》對于履行和解協議帶來震懾作用。《公約》賦予了調解與訴訟、仲裁同等的執行力,其對協議雙方嚴格履行和解協議的震懾作用,與其提供的強制執行救濟相比,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甚至震懾的意味更濃。所以,從爭議得到確定解決數量恒定的角度講,加入《公約》無疑是可以減輕司法資源壓力的。
調解的過程已經分擔了部分審查義務。不可否認,《公約》對于准予救濟的審查並沒有作出詳細規定,第四條規定了主管機關審查救濟請求的要求,第五條中不予救濟的情形則需要主管機關進行判斷。
但是參考國內類似的爭議解決方式,主管機關本就需要盡到一定的審查義務。如果不通過調解,而是將爭議作爲訴訟案件來解決,恐怕締約國主管機關需要承擔更多的審查義務。考慮到訴訟、仲裁的對抗性相對更強,雙方自行執行的可能性更低,申請強制執行的幾率更高。
虛假調解
有人擔心調解的門檻太低,《公約》對于調解員的資質、機構調解沒有要求,可能會給虛假調解帶來溫床,用公權力來保障虛假調解得到強制執行不太妥當。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不是“虛假調解”,也有其他途徑執行。《公約》調整的是具有國際性的部分商事爭議,爭議雙方對于可執行的財産本來就有權處分。
即便不適用《公約》進行救濟,雙方也可以將此和解協議視爲合同履行並得到司法救濟,或者通過仲裁對和解協議加以確認。從途徑來講,就算不適用《公約》也依然具有可執行性。
《公約》規定了不予救濟的情形,與《紐約公約》相似。如果依據《紐約公約》不予認可與執行,依據《公約》也得不到救濟。可以看到,欺詐、脅迫、違反公共政策、違反執行地法律規定等情形本身就不屬于《公約》救濟的範圍。
執行機制本身也有救濟途徑。例如案外人提出執行異議。在執行層面的救濟,通過調解與通過訴訟、仲裁申請執行是一樣的。
調解員資質與虛假調解也沒有必然聯系,且對調解員素質要求更高。調解達成和解協議,是當事雙方的合意,調解員無論有何資質、屬何機構,都不能代替爭議雙方作出決定。換句話說,如果爭議雙方裏應外合想要虛假調解,也不是對調解員的資質與機構進行要求就能夠解決的。
調解達成和解協議的難度與訴訟、仲裁相比更大,訴訟、仲裁無論如何都會産生一個結果,但是調解卻未必可以産生一個和解協議。其中的難點就在于如何讓有爭議的雙方達成一致,調解員的素養、技巧、公信力等因素缺一不可。所以雖然《公約》對于調解員沒有資質要求,爭議雙方卻在實際上用腳投票,實現市場的優勝劣汰。調解員通過“不正式”“非常態”方法進行調解,恐怕很難讓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如構成《公約》第五條“拒絕准予救濟的理由”規定的情形,可以不予救濟,特別是其中對調解員違反相關准則及披露義務也都作出了相應規定。
當然,這也啓示我們,國家應著力發展調解員隊伍,促進調解行業發展。
可以預見到《公約》生效後,我們在“中-中-外(執)”“中-外-外(執)”“中-外-中(執)”型和解協議中具有語言優勢。如我國成爲締約國,還會因爲可執行財産在我國,帶來一些便利執行銜接的優勢。從這個角度講,應當考慮加入《公約》,讓我國調解行業盡早得到更多實踐機會,培養競爭力,避免贻誤發展先機。可以考慮從促進調解行業發展的角度,例如,通過及時公布導致拒絕准予救濟的調解員名單等方式,方便市場公正判斷選擇,促進良性競爭,讓我國的調解行業具有競爭優勢。
救濟的不確定性
有人擔心,一旦《公約》生效,即便調解達成的和解協議在一個締約國拒絕准予救濟,但是在另一締約國仍然可能准予救濟,這會對當事人産生不確定性,也會對拒絕救濟的締約國産生不確定性。
在這種情況下,應了解締約國保留情況。由于締約國可以選擇是否保留“當事人明示適用”,如果當事人沒有明示適用《公約》,有的締約國就可以直接予以救濟,有的締約國就未必予以救濟。但這並非不確定,只是需要當事人了解締約國的保留情況。
不同締約國准予救濟的情況本就允許不同。如果當事人在不同的國家有可執行的財産,對于某締約國而言,是否予以救濟是確定的,該締約國具有管轄權。其他締約國的執行情況與該締約國在理想狀況下應當一樣,但也可能不同,不能將其歸結爲是由《公約》或調解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因爲其他爭議解決方式的執行也會存在相同的問題。
此外,可提供判決、仲裁外的確定路徑。對于我國法院調解不能通過《公約》解決的問題,恐怕這也不是《公約》要解決的問題。《公約》是在判決、仲裁之外,提供第三種路徑並使之具有確定性,不適用通過其他途徑解決的爭議,實際上也爲《公約》帶來了更多的確定性。
加入時點
有觀點認爲,對于何時加入《公約》應持“觀望”態度,筆者擬從加入後的受益點及“觀望”是否更有利的因素來分析加入時點的問題。
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總結出加入後的受益點如下:一是和解協議雙方可以多元解決爭議,降低爭議解決成本。二是營業地或可執行財産地在締約國的企業,可以因爭議解決便利,激發企業活力,並在國際經貿合作中獲得優先合作機會。三是締約國因提供爭議解決便利,可改善營商環境、彰顯開放形象、節省司法資源。四是締約國調解行業可在加入後因爲與可執行財産地的密切聯系,獲得更多實踐機會,以此獲得發展。
總體來看,因上述擔憂而“觀望”的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而國內各項相關制度的銜接、短期的執行與派生訴訟壓力,則恐怕是只要加入就會面臨的問題,這並不是“觀望”就能夠解決的。實踐中可以考慮在簽署後、批准前的時間裏,做好必要制度銜接的准備。新事物自然會帶來不確定風險,但看到《公約》生效並總結各締約國實踐經驗後再考慮是否加入,恐怕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放棄加入會帶來的益處。是否值得放棄這些利益來“觀望”,是需要客觀對待的。
其他
對于國有企業在“一帶一路”投資合作的爭議解決,《公約》可以帶來巨大利好的判斷,需要一些前提。
首先,爭議雙方的可執行財産地能夠成爲締約國。
其次,還要考慮公約的“商事保留”情況,包括我國是否考慮此種保留。
再次,實踐中國有企業是否願意通過此方式解決爭議,有一些現實問題需要解決。例如,誰來承擔和解協議得到的“解決”比“應收賬款”更少的“國有資産流失”的責任問題,是否要在簽署此類和解協議之前獲得履行出資人職責的相關部門審批等。
◆ ◆ ◆ ◆ ◆
作者:範怡娜
來源:法制日報
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中國公司法務研究會!
投稿或合作,請聯系喬女士:1891015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