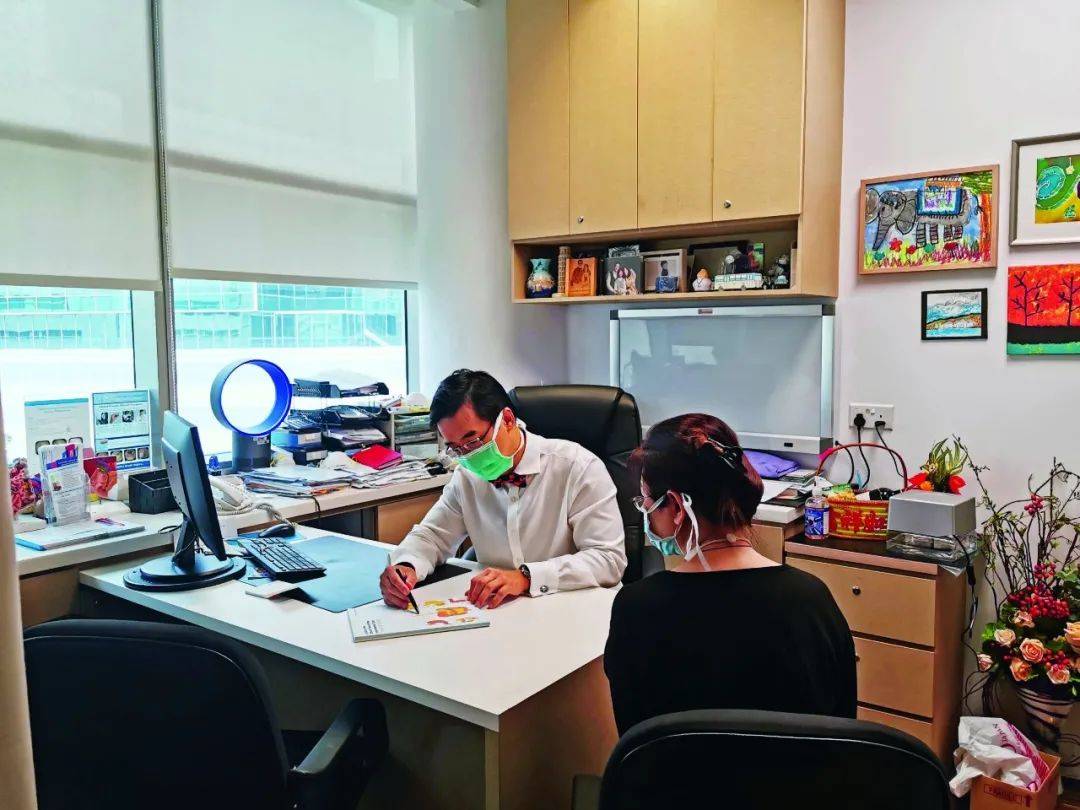韋俊韬醫生
每個成功者的背後,是無數看不見的付出和努力的結集。
主攻腸胃內窺鏡檢查及肝膽疾病的韋俊韬醫生(51歲),原籍香港,在伊麗莎白諾維娜專科中心開設腸胃及肝膽專科診所,也經常在本地媒體分享有關腸胃醫療知識,解答聽衆讀者的疑惑。
他17歲獲新加坡政府頒發獎學金漂洋過海,到萊佛士初級學院念高中,考進國立大學醫學院,完成內科專科培訓後,獲衛生部獎學金到美國專攻肝髒移植一年。回國大醫院腸胃科服務後,曾參與“沙斯之疫”前線醫療工作。2006年,他加入陳凱澤的亞洲肝髒疾病及移植中心,六年後開設私人診所。
新加坡,是他生活最久的地方,已是他的紮根處。
步入人生下半場,回首點滴,會有不一樣的抉擇嗎?
俗話說,時間花在哪裏,成就就在哪裏。
步入韋醫生的診所,牆上張貼著十多張中英文媒體的專訪和醫科專業證書。
每一張,見證著他不曾松懈的努力,驗證了時間力度與成就張度對應的人生道理,更反映出家庭教育對成就子女未來的無形力量。
家庭教育的影響
韋家是人才輩出的家庭。韋父(韋應錦,78歲)裁縫出身,韋母(蔡錦霞,72歲)是家庭主婦,四個兒女中,女兒是老大,韋俊韬是老二,下有兩個弟弟。除了當醫生的女兒仍在香港生活,三個兒子都在新加坡成家立業。老三韋俊行是內分泌科顧問醫生,老幺韋俊業是新加坡國家美術館人力資源高層。
一門俊秀,秘訣是什麽?
韋家並不富裕,在老家香港,一家六口擠在250平方英尺(約23平方米)的公屋,樓上住家,樓下是韋父的洋服店。家裏沒有廁所,公廁在10米外,大概要走過25家店屋才到達。但父母總是把最富營養的食物送入子女口中。
韋父10多歲從中國廣州逃到香港,沒受過正規教育,但他視書如寶,看書多到能與韋俊韬討論醫藥課題;吃飯時不忘閱讀鋪在桌子的報紙新聞;出國旅行前,會預先閱讀相關書籍。
自我充實之余,韋父“窮則變、變則通”的生活態度,造就韋俊韬積極樂觀的抗挫能力。洋服店生意不理想,韋父便廣發傳單給附近的辦公樓,以優惠價裁制制服。韋俊韬說:“父親總是不停地動腦筋,不斷改變自己,在他眼裏,沒有什麽是做不到的。”
韋父重視生活磨砺,經常告訴兒女,不要怕別人看不起自己,最重要的是不斷求上進。
出國旅遊時,韋父盡量以有限的旅費,選擇到比香港先進的國家,“他要我們看看別人比香港優秀的地方,讓我們認識自己的不足,激勵我們的上進心,如果我們只去旅費便宜但較落後的地方,可能會以爲香港是最好的,産生不可一世的心態。”
生活中的小點滴,顯現韋家教育的大不同。
韋俊韬盡量抽空,每個星期帶妻兒與年邁父母吃飯聊天。
一個笑話笑三次
“每次我的高中同學用英語講笑話時,我都會笑三次。第一次是當他們開口說笑話,我附和著笑;第二次是他們解釋時,我邊聽邊笑;第三次是我真正明白個中含義,坦然開懷大笑。”
自我調侃的豁達,是韋俊韬多年來努力融入新加坡英語環境換來的自信。
自诩遲開竅的韋俊韬,中學就讀于著名的香港華仁書院,香港前特首曾蔭權和著名歌手李克勤都是他的學長。中三以前,他的成績只屬中上。中三開竅後,名列前茅。
中五那年,他頂著相當于新加坡O水准八科優異的光環,獲頒新加坡政府獎學金到萊佛士初級學院念高中。
“剛來時,我的英文底子較差,爲了提升自己,每天閱讀英文報章。”
就如許多在異鄉落地生根的人一樣,面對陌生的用語習慣和環境,他硬著頭皮開口多說。說錯再學,絕對是迅速掌握新語言的不二之法。
英語之外,他還得面對另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語言——華語。
“我能寫也能看懂華文,可是我不會說華語。香港說的是廣東話,但新加坡不是人人都說廣東話。當年我就追華語新聞和華語電視節目惡補。”
說到講華語的趣事,他自嘲說:“每次我上電視節目錄制《小毛病大問題》時,節目主持李國煌就會作弄我的香港腔華語,說我把眼睛和眼鏡等混著說。”
撇開初期的用語不適,韋俊韬處處感受到新加坡人對外地人的包容及接納。在萊初時,逢年過節,班上同學和老師會邀他上門做客,品嘗家常小煮。
剛來新時,校方安排他住在武吉知馬的華中宿舍,同住的有馬來西亞和香港學生,彼此照應,分享生活小點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當年沒有互聯網,越洋電話又很貴,幾個月才打電話給父母一次,周圍的朋友就是最佳的生活夥伴。”
1993年,父母帶著兩個弟弟來新加坡定居,並在牛車水一帶開洋服店,靠著積蓄和在香港行醫的大姐補貼家用。幾年後,兩個弟弟完成學業出來工作,父親結束小本經營,惬意退休。新加坡,早已成爲韋家的家。
由港風轉爲新加坡派
屈指一數,扣除去美國一年的生活,韋俊韬在新加坡住了33年,他對新加坡,比對香港還習慣和熟悉。
“我娶了個新加坡太太,兒子在這裏受教育,吃著小販中心的食物,說著新加坡式英語,從不吃辣到現在愛吃辣,最拿手的好菜是黑胡椒螃蟹,最常點的菜是老婆愛吃的三峇空心菜。”
愛烹饪的韋俊韬醫生,趁新冠病毒阻斷措施期間,大顯身手,烹煮太太愛吃的黑胡椒螃蟹。
念國大醫學院一年級時,他申請成爲新加坡永久居民。幾年後,他接到入籍新加坡的邀請信,“當時我一些馬來西亞朋友說,如果拒絕,以後就很難申請爲新加坡公民。”
順水推舟,他現在連自己何年入籍新加坡都不太記得,“我已經本土化了。”
當然,間中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記得我來新加坡的第一個物理考試得了滿分。當時我的作風還很香港,同學問我考得怎樣,我回答說,‘很簡單,真不明白爲什麽有人不及格’,結果這句話,讓我樹立很多敵人,一名不認識的女同學還特地來看我是何方神聖!”
他說,香港和新加坡存在著一個有趣的文化差異——香港人喜歡“吹大”,新加坡人習慣“吹小”。繳了學費後他學乖了,每次被人問起做得如何,他總會一臉抱歉地說:‘還好啦、沒有死、OK loh!”
韋俊韬補充說:“香港人說話的聲量較大,新加坡人習慣較小聲說話;香港人走路和說話節奏比新加坡快很多,新加坡華人也不太說廣東話,與新加坡朋友相處,不是說英語就是華語。”
對那些剛到新加坡的外地人,韋俊韬認爲一定要擴大自己與本地人的接觸面及機會,可以通過工作、教會、社交活動和學校的課外活動團體等結交新朋友,不能僅限與同鄉交流,如此才會對新加坡産生家的溫馨感。
醫生是個廣受世界各地歡迎的專業人才,即便不移民他國,回到香港行醫,收入也比本地同等級的醫生高出兩三倍。移民或離開,曾否是選項之一?
韋俊韬不加思索說:“除了南美,我到過許多國家和城市,我敢說新加坡是最適合工作、生活和養兒育女的城市之一,政府對人民的照顧周到。在新加坡住久了,就很難回香港生活,香港人多屋小、又沒停車位,已經無法適應得了。”
人生上半場已過,韋俊韬總是心懷感激。
在忙碌生活中,能與妻兒一起騎腳踏車做運動,是韋俊韬最開心的事。
韋俊韬醫生周末有空時,會陪孩子揚帆出海,享受親子時光。
擔心本地醫學界前景
2003年底,當韋俊韬完成肝髒移植專科從美國回新時,以爲會加入醫院的肝髒專科部。不料,沙斯肆虐,當時的部門主任王建忠副教授(前衛生部醫藥服務總監)就安排他負責國大醫院的沙斯部門,投入“沙斯之役”。
回想起全身防護的那段日子,他說:“開始覺得這個病毒有點棘手,但幾個星期後,我們對沙斯已有更多認識,知道它的死亡率高,每個人都需認真慎重地穿戴全套防護裝備,保持良好個人衛生,避免受感染並傳染給同事和家人。當時我想,如果穿得這麽密實也受感染,那麽社區裏其他人遲早會受感染而死,所以不會對站在前線有所恐懼。”
2019年底,新冠狀病毒出現,韋俊韬沒有走上前線。不過,當他看到中國與意大利等國的醫院擠滿大量病患的慘狀時,內心又再緊繃。
所幸隨著疫情發展及醫藥科學的研究,知道該病毒死亡率不如沙斯可怕,保持社交距離、采取阻斷措施及個人防護裝備都能發揮控制疫情的效力,他多少安心下來。
倒是疫情讓世界各國采取鎖國封城禁飛等阻斷措施,讓他擔心本地醫藥界的前景。封城禁飛首先嚴重打擊那些依靠海外病患的本地私人診所及醫院,尤其從印度尼西亞和孟加拉等國前來問診的病人銳減,迫使一些私人專科診所另謀出路。
對韋俊韬的診所而言,影響最大的不是只占總病患人數不到一成的海外病患,而是本地人在疫情期間避看醫生,醫生又不能像過去一樣到不同的醫院或診所看診,以致診所病患減少一半。
每個病人或是最後一個病人
放慢說話速度,讓病人輕松問診。
“每個病人,都可能是我最後一個病人。”
這句話出韋俊韬醫生之口,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行醫超過25年,他得出的經驗是,需要專科服務的病人,一般只找一兩個醫生看病。如果專科醫生無法成爲病患或同行推薦的首三名醫生人選,就難以競爭生存。
那他是如何終身學習增加競爭力?
自我鞭策及終身學習是必備條件。不論多忙多累,他每天都會抽出至少半小時,沉浸書海,閱讀醫學研究報告。
“以內窺鏡爲例,過去我們得到海外進修,學習新方法,現在居家上網就能觀摩學習,許多醫科學術報告或期刊也免費供人閱讀。”
小小內窺鏡,大大學問。韋俊韬醫生操作了至少10年,至今仍不懈地跟進及提升這方面的技巧。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韋俊韬深明此理。他經常反省,檢討什麽地方可以改善。“每個病人都不一樣,每做完一次內窺鏡,我會加以檢討,精益求精。只要醫壞了一人,就會一傳十、十傳百,再也沒有病人上門了。”
各行各業難免會有一些良莠不齊的情況。“有的醫生收費過高,有的只說病人愛聽但不盡真實的話,有的進行不必要的檢驗以增加收費等。其實,有醫德的醫生不需要打,病人就是活招牌。”
然而,他不是一開始就懂得拿捏看診輕重。初期在國大醫院獨立看診時,有段時間常接到病人投訴,原來他說話太快,讓病人有種被趕鴨子的急迫感。
“當時我的主管醫生林成義教授(現任國大醫院腸胃與肝髒科高級顧問醫生)就贈我一句看診名言——在看診結束前,問病人‘還有其他問題嗎?’這個問題,是引導病人說出隱藏于心或羞于啓齒的疑慮。結果,那之後再沒接到病人的投訴了。”
還有一次,他出國開會,淩晨1點才回到新加坡,第二天出席部門醫務早會遲到半小時。林教授一把拉他到房裏訓了一頓,“林教授說,初級醫生們看到主管經常遲到,就會有樣學樣,形成不良的職場風氣。我那時才剛升爲顧問醫生,難免有點意氣風發,幸好他提醒。即使我已離開國立醫院多年,看到我做得不好,他還是會打電話指點我。”
對林成義教授的指點,韋俊韬心懷感激,“沒有他和楊啓源教授(現任國大高級副校長)的提拔,就沒有今天的我。”
訪問過程中,帶著口罩的妻子曾美珠進入診室,讓韋俊韬過目重要文件。丈夫自我要求這麽高,是否對她形成壓力。負責打點診所大小行政事務的曾美珠打趣說:“不會有壓力,因爲我也要求做到最好,如果他做得不夠好,我也會提醒他。”
韋俊韬馬上接口說:“世上只有太太會告訴丈夫什麽地方有待改進。”
那她最希望丈夫給她什麽,曾美珠笑著說:“他的時間!他是個工作狂,八成時間工作,只留兩成給家庭和我們唯一的11歲兒子。”
至于他什麽時候打算退休,以便和太太重溫在美國深造期間,朝九晚五准時回家、周末休息旅遊的好時光,他笑說:“你知道的啦,我是工作狂。我想,只有當我能力不夠的時候,才會退休吧!”
可是,一個不停反思、堅持今天比昨天做得更好的人,怎可允許“能力不足”的降臨?
沒有韋父謙卑上進的身教,沒有韋俊韬自我鞭策的精神,新加坡就缺了一位肝髒移植和腸胃疾病專科醫生,更少了願意義務解答報章讀者和電台聽衆對腸胃疾病的疑惑的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