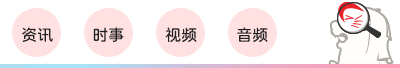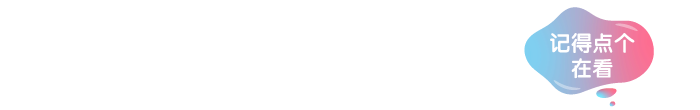我曾經想過,我的童年記憶自那一趟從怡保南下新加坡的夜間火車開始。
當年新生學校那椰樹環繞著校舍的畫面已然遠去,峇踏,已無迹可尋。(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1. 我曾經想過,我的童年記憶自那一趟從怡保南下新加坡的夜間火車開始。那時妹妹、弟弟還未出世,爸爸媽媽帶著分別爲五歲、四歲、三歲的姐姐、哥哥及我,就這樣全家從怡保一路坐火車南移到新加坡。
與其說,我記得的是那班夜行列車,不如說,隱約浮現在腦中的是自己在火車上一路哭泣的畫面。那段記憶就如拼貼出來的蒙太奇畫面,偶爾在腦中閃現。
我也曾經想過,對于當年那個三四歲的小女孩來說,全家坐上南下火車之際,之所以不停哭泣,興許是突然遠離熟悉的生活與玩伴。
由于祖父母過世早,在怡保的時候,我們一家與外公、外婆及舅舅全家同住,突然就離開了熱鬧哄哄的大家庭生活,即便那年僅有三歲,甚至更小,也會不舍吧。但那麽傷心,是否也在童稚的歲月裏有所感知,從此告別怡保這塊出生之地?
我也曾問媽媽,我們家當年爲何要遷離怡保南下?媽媽對回憶過往沒多大興趣,仿佛在敷衍我,只淡淡地說了句:那時候很多人都是這樣,從聯邦跑到新加坡來的。
可我一直困惑,爲何爸爸一直到去世都沒有申請爲新加坡公民,也許,年少即自福建下南洋討生活的父親,他心中認同的家國,不在彼也不在此,不在新加坡,也不在馬來西亞,一直是他心中那一片永遠的故裏。
2. 也不知爲什麽,我們在新加坡的第一個家是在島嶼東部,一個叫做峇踏(Batak)的馬來村落。這些年來,雖然心中總有個疑問:Batak,在馬來語裏究竟是什麽意思?但似乎總是想想即忘,沒真正放在心上。一直到最近,一天早上,突然想要打個電話請教馬來文學翻譯家妙華大姐,這才知道,“Batak”大多指分布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北部的巴塔克人。那麽,峇踏,是不是過去巴塔克人從印尼移居到新加坡的落腳處?或那曾是巴塔克人聚居的地方?
在峇踏,我們家周圍人煙並不稠密,雖說是馬來甘榜,但左鄰右舍除了馬來人,還有華人,其中也有福建人、潮州人和廣東人。我們家對面是獨門獨戶的潮州人家,他們家院子大,種了紅毛榴梿、紅毛丹等果樹,還養了幾頭灰褐色羽毛的家鵝。那些看起來呆頭呆腦的大鵝,卻一只只盛氣淩人,有事沒事,看到人就伸長脖子,撲打著翅膀追著人咬,俨然村中惡霸。
對面鄰居有時將家鵝關在自家院子裏,有時讓它們走出院子橫行霸道。大鵝在路上招搖的時候,我們就躲得遠遠的,大人們都說,鵝喙銳利,被咬一口肯定痛死了。可我從小不明白,憑什麽鵝見人就咬?年歲漸長,想起甘榜裏那幾只追逐行人的家鵝,不禁要想:大鵝如此凶猛,是沒有安全感,害怕自家地盤被侵占,所以先發制人?又或,本性就好攻擊,逢人就想欺負?
離我家不太遠,有一家步行約20分鍾可抵達的中央戲院,小時候喜歡的電影《江山美人》就是在那裏看的。夜裏天氣好的時候,媽媽還會帶我們到戲院附近的pasar malam(夜市)閑逛。到了夜市,我們總是大有收獲,小時候家裏的連環圖書如《西遊記》等等大多是在夜市裏的書攤買的。
這輩子讀的第一所學校新生學校也在峇踏一帶的馬來甘榜裏。記憶中,學校前後左右搖曳著椰樹與果樹,附近還有馬來人家的浮腳木屋。校舍建在微微高起的半山坡上,我們每天就在山坡上上下下。
我曾請教本地文史研究者李國梁,新生學校究竟是在如今什麽地方。國梁果然不負所托,他後來告訴我,是在惹蘭友諾士一帶。換言之,過去所說“峇踏”,也即目前車如流水的惹蘭友諾士一帶。歲月改變了地貌,也改變了人文景觀,當年那椰樹環繞著校舍的畫面已然遠去,峇踏,已無迹可尋。
回想起來,1960年代初期,那還是個華文教育昌盛的年代,不但馬來甘榜裏有華校,學校裏甚至還有馬來同學,當時也不知這些馬來同學來自哪個年級,哪一班,不知什麽原因,被父母送來華校就讀。
第一次那麽近距離看到政治人物也是在新生學校上學的時候。小學三年級那一年,當時初任總理的李光耀到了我們學校,爲平靜樸素的甘榜小學掀起了不小的漣漪。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1963年年底,新加坡舉行立法議會大選,也就在那一年,李光耀開始了他一連串的下鄉訪問,位于馬來甘榜的新生學校應該也是他在大選前探訪民情、拉選票的行程之一。
我對于建國總理那次的下鄉訪問沒太多記憶,只記得那一天,學校突然就氣氛熱烈起來,迎接總理的時候,每人拿著一面小邦旗,站在學校門口的大路邊,興高采烈地列隊歡迎。
比我年長兩歲的姐姐記得比我多,有一回不知爲何談起童年往事,姐姐無意間說了句:當時看李光耀覺得他很高。我沒搭腔,因爲這不在我的記憶畫面裏,或當時根本不在意什麽大人物到訪,心思都被學校那異乎日常的歡騰感染,那是好玩的成分多過一切。樸實的年代裏,小孩的快樂也是簡單純粹的。
但我與新生學校的緣分僅有一半。1964年7月,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一場突然爆發的種族騷亂,突然間破壞了峇踏村民原本和諧共處的氛圍,也間接影響了我的童年生活。
騷亂的時候,全島戒嚴,街上不時有軍警巡邏,氣氛十分緊張。可我印象最深的是,半夜裏常被來勢洶洶的馬來鼓聲驚醒,那鼓聲,聽來急促,聽了教人不安,當時也問過爸媽,半夜裏爲何有鼓聲?卻總是沒有答案。但有一回,媽媽在院子裏與隔鄰的阿姨交頭接耳,我聽到鄰家阿姨說了,馬來鼓聲響起,象征他們在召集人馬。
夜半鼓聲帶來的緊張氣氛持續了好些天,爸媽越來越感焦慮。那天,我們一家子終于倉惶離開了南下新加坡後生活了六年的馬來甘榜。當時妹妹已出世,父母親帶著四個孩子,先是寄居在父親的多年好友周叔叔家裏,兩個月後,搬到華人聚居的大成巷。
而我們家,就此告別了那個叫“峇踏”,目前已不複存在的馬來甘榜。回想起來,在我的童年記憶裏,這夜半鼓聲就好比那南下的列車,是童稚歲月的某種標記,也是那個年代,某個時間點的印記。
3. 因爲騷亂與搬家,小學四年級還沒念完,懵懵懂懂間被逼離開了新生學校,轉校到坐落在大成巷盡頭的鳳山學校。對于自己如何適應新學校與新生活,其實我已記不得了。
雖然同樣都是華文小校,可因爲坐落點的關系,鳳山學校和新生學校在氛圍與環境上相差太大。和新生學校蕉風椰雨式的甘榜風情不同,鳳山學校是一所典型的華人鄉村學校,緊挨著學校的是座華人老廟鳳山宮九皇爺廟,至今也仍記得,廟宇附近還有一棵氣根盤錯的老榕樹。
很久之後我才知道,早在1920年代,鳳山學校就是由九皇爺廟創辦的,學校最初還是從私塾開始,一度靠信衆的香油錢辦學。
九皇爺信徒衆多,每年農曆九月的九皇誕是鳳山宮一年一度的大事,在鳳山學校的日子,我對九皇誕慶典從陌生到熟悉,到了後來,甚至期待每年慶典帶來的熱鬧歡騰。
九皇誕慶典期間,廟裏香火特別鼎盛,周圍都立起黃旗、黃布條。廟裏出入的信衆,身著白衣白褲,腰纏黃布條,我也常看到一些同學,手上系著據說可保平安的黃色布繩。
九皇誕期間,大成巷村人大多連續茹素九天或三天,大人們說,那是吃“九皇齋”。慶典從農曆八月最後一天的迎銮開始,然後在廟前連續演上十個晚上的酬神大戲,一直到送九皇爺回銮。
九月初九,九皇爺回銮的晚上,八九點左右,送駕遊行的隊伍浩浩蕩蕩自九皇爺廟出發,銮轎、花車、鼓樂、龍獅隊,一路鑼鼓喧天,沿著大成巷,往巴耶利峇上段的方向遊行,一路送九皇爺往東海岸海邊,完成送神出海的儀式。九皇爺銮轎由幾個白衣大漢擡著,一路前行一路晃動,村裏人紛紛在門前擺上香案和供品,當銮轎經過自家門前的時候,點上一束清香膜拜。
從小耳聞目睹聲勢浩大的遊神賽會,感受到民間對九皇大帝的信仰和崇拜。就像那盛大而隆重的九皇爺慶典,年複一年,年年锲而不舍。後來漸漸知道,九皇爺信仰不只存在大成巷,在本地不同地方都可找到九皇爺廟,它甚至不只是新加坡的民間信仰。九皇爺,它還是馬來西亞、泰國敬畏的神明。信徒們相信,九皇大帝能保佑家國風調雨順,只要誠心禮拜就會得福消災。
一直好奇于九皇爺的身份和起源,年歲增長,斷斷續續讀了一些關于九皇大帝的資料,那些衆說紛纭的民間傳說,經過不同方式的傳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無以判斷,也無需判斷。有些傳說將九皇爺與洪門會、天地會連在一起,說九皇爺是九位反清複明義士,甚至有的說九皇爺指的是乾隆年間天地會創始人萬雲龍和他的兒子、結義兄弟等等。也聽說過,九皇大帝是道教信仰中的星神,是北鬥七星星君: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加上左輔、右弼兩星君的合稱。
讀九皇爺資料,並非想做研究,純屬好奇,對我而言,九皇爺的曆史和來源其實並不重要,我想知道的是,九皇大帝爲何如此受民間崇拜?而我知道,這是個沒有標准答案的問號。
歲月流逝,城市變遷,童年時代就讀過的兩所鄉村學校,一所在馬來甘榜,一所在華人村落,兩所學校各有特色與那個年代的象征意義,也在特定的年代裏,肩負起春風化雨的使命,但終究也像全島所有華校一樣,船過水無痕,消失得無影無蹤。我記得,我是在鳳山學校讀書時,開始懂得寫作、投稿,第一篇刊登在報章上的作文,還是在校長、老師們的鼓勵下,投稿到《星洲日報》去。
4. 打從九歲開始,住了十余年的大成巷,一直是個有故事的地方。這些年來,大成巷的故事仿佛說也說不完,道聽途說者有之,繪聲繪影者有之,人們津津樂道于大成巷的私會黨曾經如何猖獗,黑幫如何橫行,尤其是傳說中的千面大盜林萬霖,槍法如何神乎其技,混迹黑道時如何神出鬼沒,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傳說,在坊間口耳相傳,大成巷多了幾分傳奇。
1960年代的大成巷充滿市井生機與生活氣息。(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也許因爲我們家並非世居大成,甚至可以說是大成巷的外來者,沒經曆過傳說中大成巷黑幫猖狂的日子。我也曾經查過資料,爲大成巷增添上神秘色彩的千面盜,其實家在巴耶利峇機場一帶的惹蘭紅燈,與真實範圍內的大成巷有一段距離。因爲背負著黑幫與大盜之名,當年的“大成人”仿佛被貼上標簽,常令人爲之側目,外地人平素無事,也不會輕易走進去。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記憶裏的大成巷是個實實在在,彌漫著人間煙火、市井氣息的地方。大成巷雖以“巷”之名,卻不是一般的橫街窄巷,它也不僅是一條街,一個聚落,而是由一路上不同小村落交彙而成,許多人不知道的是,來到大成巷的中間地段,還有一個馬來甘榜,一兩家由馬來人經營的雜貨店。我是在後來聽大人們說的,1964年種族暴動的時候,大成巷裏的馬來人卻未受影響,安然地在甘榜裏與華人共處。
大成巷並非窄巷,卻是條長“巷”,頭尾兩端,大約兩三公裏長,前端路口面向巴耶利峇路上段,從路口一直往前走,到了尾端則是機場路。在大成巷的時候,我每天在長巷來來去去,讀鳳山小學的時候,每一天,我從家裏朝大成巷尾端機場路的方向,以大約20分鍾的路程步行到學校。上中學之後,我每天從家裏往巴耶利峇上段方向走向車站,腳程大約也是20分鍾。
大成巷路口是個市集,不論白天或晚上,這個面臨巴耶利峇上段的市集是整個大成巷最熱鬧喧囂的地方,除了巴刹,市集兩旁麇集著酒莊、米棧、雜貨店、洋服店、縫紉班、理發店、書店、咖啡店、火炭店、會館(公館)、醬油廠、西藥房、中藥鋪,還有個社會主義陣線開辦的幼稚園。至今叫村民特別懷念的是,市集裏五味雜陳的路邊攤,從山瑞炖湯、羊肉湯、沙爹米粉到福建鹵面、廣東雲吞面、潮州糜、肉骨茶、海南咖喱飯、豬肉粥等等,都是能輕易勾起味蕾記憶的老味道。
從市集往裏走,除了住家,還有散布其中的家庭式工廠、手工作坊,寺廟、學校、聯絡所,記憶中,老字號餅家寶源、泰利餅家半個世紀前都在大成巷起家;再往裏走,大成巷支路裏,還有外人鮮少探秘的鄉村池塘、椰林、雞寮、豬欄、菜圃。
我當然記得,弟弟是在大成巷家中出生的。我們家在大成巷的一條岔路上,附近有三片大小不一的池塘,其中一個池塘離我們家僅數碼之遙。池塘位于椰林裏,每天早上,我貪走捷徑,穿過椰林小路去上學,總會看到一些鄰家婦女,在晨曦中,蹲在池塘邊洗滌衣裳。
往椰林裏向上走,離我家15分鍾路程,在金泉路一帶,有家名字很美的玫瑰露天戲院。愛看戲的媽媽,帶著我們,在玫瑰戲院看了《劉三姐》《養鴨人家》《婉君表妹》等當年紅極一時的電影,那個年代的影片,就如鄉村裏的露天戲院,淳樸卻令人懷念。
“玫瑰”雖離我們家不遠,但要到戲院去,要穿過池塘,走在凹凸不平的椰林路上,多少個夜黑風高的晚上,爲了看電影,我們就這樣,一腳高一腳低,穿過池塘與椰林,勇往直前,往玫瑰戲院前行。
說是城市重建的緣故,大成巷村民到了1970年代末紛紛遷出區裏,長長的,曾經聲名遠播的大聚落,就這樣一步步走進曆史。現在偶爾開車到了巴耶利峇路、巴耶利峇上段與機場路交接處,看到昔日大成巷一帶盡是商業大樓與工業廠房,那裏有座辦公大樓直接取名“ Tai Seng”,周遭數條大路、支路也以Tai Seng命名,從其中一條“大成道”一直往前走,可直通目前也已改頭換面的金泉路。可是,單憑Tai Seng兩個字,就是我們留給後世的記憶?年輕一代可知道什麽是“Tai Seng”?曾經,那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而我知道,記憶中那個有華人村落,有馬來甘榜,有家庭作坊,有人養豬,有人種菜,有椰林、魚池,曾經市集喧囂,商店、路邊攤林立,充滿市井生機的大成巷已蕩然無存,任人憑空遐想,有意無意間,以“大成”之名編織黑幫傳奇。
歲月流逝,城市變遷,童年時代就讀過的兩所鄉村學校,一所在馬來甘榜,一所在華人村落,兩所學校各有特色與那個年代的象征意義,也在特定的年代裏,肩負起春風化雨的使命,但終究也像全島所有華校一樣,船過水無痕,消失得無影無蹤。
相關閱讀:
-
剛遭受祝融之災的新加坡龜嶼拿督公廟有段獨特曆史,史記靈驗異常
-
新加坡獨立前的146年,法國人在這裏留下哪些曆史性標記,我們在他們的文獻裏又以什麽姿態出場?
-
新加坡實裏達機場附近有座從未對外開放的神秘老建築,今年你終于可進去參觀
作者:張曦娜
新加坡魚尾文 新加坡《聯合早報》旗下産品 – 帶你了解新加坡原汁原味的風土人情,領略小島深處那些鮮爲人知的文化魅力~ 5199篇原創內容 Official Acco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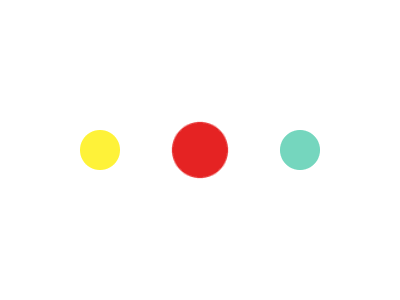
關注新加坡魚尾文視頻號
收看獨家訪談、特約節目
了解本地新聞、疫情資訊
新加坡魚尾文 ,贊 3
新加坡魚尾文推薦搜索關鍵詞列表:冠病疫苗騎行新加坡Omicron
一只愛生活、文藝範的小魚尾獅帶你了解新加坡原汁原味的風土人情領略小島深處那些鮮爲人知的文化魅力~ 新加坡《聯合早報》旗下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