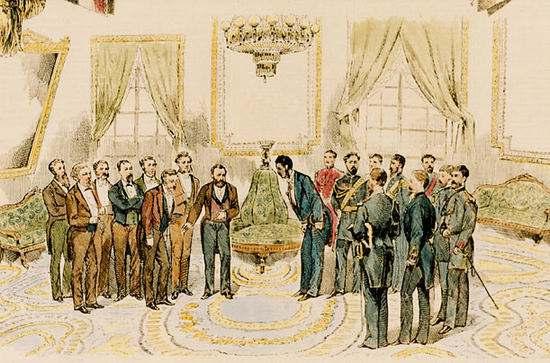1932年那個山窮水盡的夏天,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象一座深陷敵圍的歐洲小國京城。自從五月以來,大約有二萬五千名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攜家帶口,身無分文,紛紛在市內的公園,垃圾堆積處,沒主的貨棧,歇業的鋪子,揀個地方住下。他們時而上軍操,時而唱戰歌,有一回還由一位獲得榮譽勳章的老兵率領,扛著褪色的布縫的國旗沿著賓夕法尼亞大道遊行,十萬市民默默在兩旁看著。不過,他們大部分時間只是在等待,在發愁。經濟蕭條已經幾乎整整三年了,這些退伍軍人是來請求政府救濟的。這筆錢是1924年的《重訂補償法》規定要發的,但是得等到1945年才到期;假如現在發,他們每人就可以拿到大約五百美元。這些人,報刊的編輯在標題中叫做“補償金大軍”、“補償金遊行隊”,他們自稱爲“補償金遠征軍”。
“遠征軍”裏邊的人原是希望國會采取措施的,可是國會沒理睬他們。于是他們便向胡佛總統呼籲,懇求他接見由他們的領導人組成的代表團。沒想到這個胡佛總統居然傳下話來,說太忙了,不能見,接著便把自己跟市區隔絕。總統原定要去參議院的,現在改變了計劃;白宮的周圍加派了警察日夜巡邏;自從停戰以來,總統府的大門頭一回用鐵鏈鎖上了。《紐約每日新聞》報上有一條標題說:“胡佛深鎖白宮中”。可是他還不止這樣。街上設置了路障;總統府四周一條馬路以外就封鎖了交通。有一位獨臂退伍軍人,因爲執行糾察任務,想穿過警戒線,結果被痛打一頓。
當年美國政府這樣如臨大敵,似乎是由于心慌意亂,窮于應付,這才小題大做的。這些退伍軍人手無寸鐵,隊伍裏也不讓過激分子參加;盡管明明在挨餓,也沒有公開行乞。他們力量其實很薄弱,不能成爲什麽成脅。《巴爾的摩太陽報》有一位三十四歲的記者,名叫德魯·皮爾遜,他描寫那些退伍軍人,說是“衣衫褴褛,筋疲力盡,神情木熱,滿臉愁容”。他們困守多日,越來越難以堅持了。衛生部門有一位檢查員認爲退伍軍人住地的衛生情況“極端糟糕”。他們的臨時食品供應大都靠捐助:支持者用卡車給他們運來了食物;一個同情他們的面包商每天用船運來一百個面包;另一個面包商送來了一千個餡餅;退伍軍人協會捐了五百美元;他們自己在格裏菲思體育場舉行拳擊比賽,又籌得二千五百元。所有這些來西都是很靠不住的。政府實際上一點忙也沒幫過。當時華盛頓警察局每天給這些不速之客送了些面包,咖啡、燉菜,一天收費六分,胡佛因之大發雷霆。到了8月中旬,酷暑氣溫達到了全年的頂點,水源日枯,苦況更甚。
那時,英國外交部是把華盛頓市劃歸“亞熱帶氣候地區”的。各國使節因爲華盛頓氣溫高,濕氣重,都討厭這地方。這裏,除了鬧市裏有少數幾家戲院在廣告上說有“冷氣”外,別的房子都沒有空氣調節設備。一到夏天,華盛頓到處是涼篷,遮陽走廊,賣冰的手推車,乘涼用的躺椅和地席,而且,用官方遊覽指南的話來說,這裏還是“一個研究昆蟲的絕妙處所呢”。“遠征軍”一無涼篷,二無簾幕,飽嘗酷暑之苦。先前他們的先頭部隊進人市區時,正是鮮花盛開,春色滿園時節,而今到了7月,木蘭花和杜鵑花都早已凋謝,櫻桃樹也只剩下禿枝了,連大地似乎也變得冷酷無情。退伍軍人們的樣子,活象沙漠中的流浪者。鬧市的店鋪老板們抱怨說:“來了這麽多窮小子,生意都受影響了。”說實在的,要說他們對國家有什麽威脅,充其量不過如此而已。
說“遠征軍”危險,這絕對是無中生有;可是說華盛頓長期以來在國際上默默無聞,一味依賴歐洲,這倒是有根據的。當時在全世界六十五個獨立國家中,只有一個是超級大國:英國。英國國旗昂然飄揚在地球四分之一的可耕地上–在歐洲、亞洲、非洲,在北美、中美、南美,在澳大利亞、大洋洲、西印度群島。凡有日照之處,就有英國旗在,這話是不假的。大英帝國統治著四億八千五百萬人。人們談到什麽東西很穩固,就說“堅固如直布羅陀,”或者“牢靠如英格蘭銀行。”當時一英鎊兌換美元四元八角六分,所以英格蘭銀行在金融界信用最高。那時只有少數幾個不甚出名的飛行員和一個撤了職的名叫米切爾的美國將軍才夢想要發揮空軍的威力:至于一般人重視的還是海軍,實際上也沒有一條重要國際航道不在倫敦政府的控制之下。直布羅陀海峽、蘇伊士運河、亞丁灣、新加坡海峽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國海軍部控制。福克蘭群島的英國海軍站掌握了麥哲倫海峽,甚至巴拿馬運河也是在皇家加勒比海艦隊的監視之下。結果是,美國就象英國的直轄殖民地一樣,完全在皇家海軍的保護之下。倫敦勞埃德保險公司表示,他們願以500對1的賠償率擔保美國不受侵犯。《幸福》月刊向讀者保證,“不管軍艦開得有多快,飛機飛得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永遠是可靠的屏障,過去如此,將來亦複如此。”該刊認爲,自美國有史以來,英國海軍一直稱霸海上,將來還要稱霸下去。
華盛頓政府的想法也是一樣:美國沒有大國的地位,大國的抱負,大國應有的龐大的機構。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村野;至于其他季節,更沒有人記得它了。論城市的規模,華盛頓在全國居第十四位。紐約是金融中心,國內多數重大問題都得在那裏作出決定。每當要求聯邦政府采取什麽行動的時候,曼哈頓區那些大企業的律師就都到這裏來,給在他們卵翼之下的共和黨出謀畫策。柯立芝總統通常到吃午餐時就辦完了一天的公事。胡佛是第一位在辦公桌上安起電話機的總統,因而轟動一時。他還用了五個秘書–以前曆屆總統誰都沒有需要一個以上的秘書的–並有一套複雜的按鈕系統來喚他們。
現在的國務院大廈所在地霧谷,原是黑人貧民區。現在五角大樓的所在地則是當時的農業試驗站,因而頗具華盛頓郊區的特色。《星期六晚郵報》說過:“就在這個全國立法中心附近,竟有大片土地還在莊稼漢手中呢。”這時政府所用的外事人員,總共還不到兩千名。從白宮跨過一條馬路,就到了今天大家熟悉的所謂行政大樓,有數不清的欄杆、高閣和圓柱門廊,式樣粗俗,外觀倒還整潔。在這麽個有雙重坡度的大屋頂底下,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竟能都在一起辦公,豈非怪事。事實上,1929年一場大火燒了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以後,胡佛和總統府人員統統都搬進了行政大樓來,同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在一個樓裏辦公,也沒有誰感到擁擠。那時是不講究排場的。後來總統的軍事顧間、社交秘書所在的白宮東翼,當時還沒有興建。特工處還不曾把行政大樓西路封鎖起來,這是一條普通街道,平時在離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不遠的地方就可以停放汽車。有時有人走訪國務卿,國務卿就在大門口相迎。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也在行政大樓的同一層樓上辦公。他和他唯一的副宮只隔著一扇木條門。將軍有事需人幫忙,只要喊一聲“艾森豪威爾少校”,艾克就飛跑過來了。
《幸福》月刊有一位作者寫道:麥克阿瑟將軍“生性腼腆、對于抛頭露面的事,從心裏就不樂意。”這是胡說八道。即使在當時,麥克阿瑟一談到他自己,也已經用第三人稱了,一邊講話,一邊揮舞著他那長長的煙嘴。他還在辦公桌背後豎著一面十五英尺高的紅木框鏡子,使自己的形象顯得格外高大。艾森豪威爾後來回憶住事時說,只要麥克阿瑟感到有人對他不夠尊重,就“發起脾氣來,破口大罵人家好耍權術,不懂禮貌,亂出主意,出爾反爾,狂妄自大,違反憲法,神經遲鈍,麻木不仁,如今世道真是見鬼,等等。”這也難怪。那時職業軍人的日子確實不好過的。從下級軍官逐級升到上校,只能靠年資:在三十年代初期,從上尉爬到少校,要整整熬二十二年。除了眼看著日曆一張一張撕下來之外,再沒有別的事可做了。由于悶極無聊,艾森豪威爾幾乎想解甲歸田;就是在這些年頭,他養成了閱讀斯特裏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驚險小說的習慣,天夭看《西部雙槍將》、《西部故事》、《驚心動魄的西部》、《牧牛騎士短篇小說集》之類的書。在波托馬克河彼岸的邁爾堡,人們還常見小喬治·S·佩頓(他從1919年起就是少校了)每到星期三、六下午四點就出來打馬球。他騎著自備的馬參加賽馬,先後贏得了四百條獎帶、二百只獎杯。這時他已經以用珍珠鑲在左輪手槍柄上而遠近聞名了;他還搞越野賽馬、獵狐、射鳥練習,還有飛行。但是佩頓少校跟艾森豪威爾少校不一樣,他是個有錢人。
按當時的兵員計算,美軍在世界上居第十六位,居捷克斯洛伐克、士耳其、西班牙、羅馬尼亞、波蘭等國之後。他們甚至不能跟南斯拉夫的十三萬八千九百三十四名陸軍好好較量一番,當真兩軍對壘,准會一敗塗地,因爲麥克阿瑟手下的大部分官兵不是在做機關工作,就是在毗鄰墨西哥的邊境上巡邏,或是駐守著美國在海外各處的屬地。參謀長手頭只留三萬部隊,比1776年英主喬治派來鎮壓北美殖民地革命的兵力還少。
美國陸軍的質量更是壞得驚人。當時軍費僅僅約爲今天的龐大開支的千分之二點五上下,所謂一分錢,一分貨。《幸福》月刊說美軍是世界上“裝備最差的”軍隊,對此誰也沒有不同意的。在緊急的關頭,麥克阿瑟能夠投入戰場的只有:一千輛坦克(統統是過了時的),一千五百零九架飛機(其中最快的每小時只能飛二百三十四英裏),以及唯一的機械化團(當年春天才在諾克斯堡編成,由騎兵開路,戰馬有防芥子毒氣的護腿)。有一位作者報道說,美國軍隊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個氣喘喘地咧著大嘴,穿著不合身的軍服,歪歪斜斜扛著一杆老掉牙的步槍,在廣大無邊的國土上沒完沒了地走來走去。”
麥克阿瑟是全國唯一的四星將軍,下邊也沒有三星將軍。他是參謀長,年薪一萬零四百美元,在邁爾堡有一座公館,軍隊裏唯一的一輛高級臥車供他專用。在他的副官看來,參謀長的地位真是高不可攀;那時艾森豪威爾少校的年薪不過三千美元,由于替參謀長在國會裏遊說,他經常跑國會;但他的長官從來不讓他借用車子。坐出租汽車的錢也不給,因爲當時整個華盛頓官場都還沒有零用費這個開支項目。艾森豪威爾日後常說當時他要走到門口,填一張申請表,才能領到兩張電車代金幣,然後站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等候從普萊森特山開來的電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