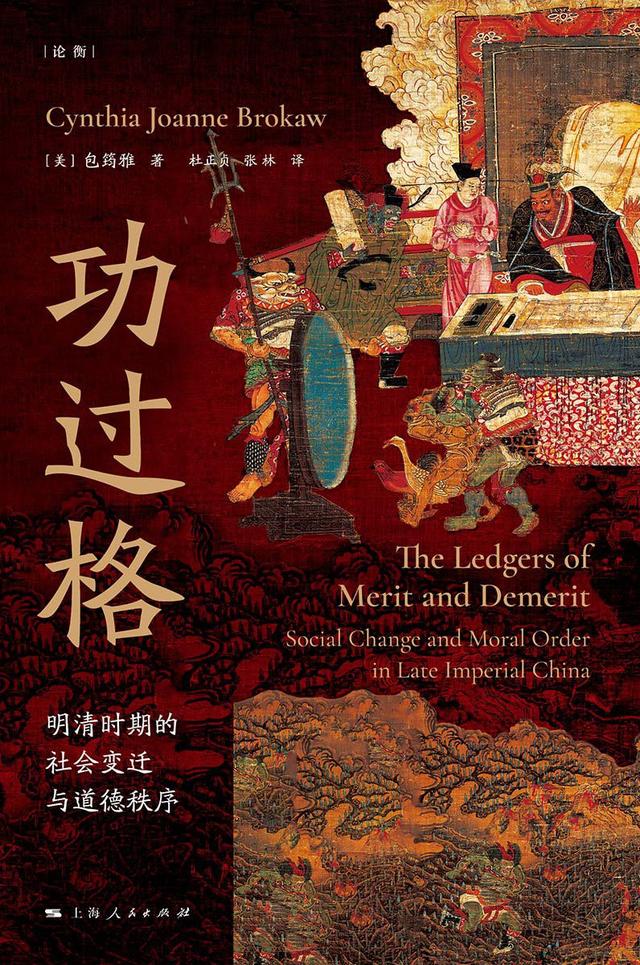李子歸
包筠雅(章靜 繪)
功過格是一種廣泛流傳于中國古代民間社會的善書,它通過列舉善惡行爲、量化功過等抽象概念來指導人們的日常道德實踐。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的著作《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集中研究明清嬗變時期功過格廣泛流行的社會現象,是非中文世界第一部詳細探討該問題的專著。包筠雅于1984年從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後任教于範德堡大學、俄勒岡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現爲美國布朗大學曆史和東亞研究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社會文化史、書籍史研究,所著《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在學術界産生廣泛反響,先後被譯介到國內。
《功過格: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與道德秩序》,[美]包筠雅著,杜正貞、張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318頁,75.00元
《功過格: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與道德秩序》這本書是您博士論文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您當年爲什麽會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功過格産生興趣?
包筠雅:我最初想要研究功過格的原因和後來支撐我研究下去的理由不太一樣,我對社會史和思想史領域非常感興趣,我想知道人們相信什麽,他們思考的方式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許多美國學者一樣,對中國傳統社會中非精英的社會成員的信仰和生活有興趣,換言之,我有興趣的是那些沒有受過很多教育,也並不擁有很多社會資源的普通人——我至今仍對他們有濃厚的興趣。功過格兼有思想史和社會史兩方面意義,因此給我一個良好的契機。功過格之中蘊含著一種超自然報償體系的觀念,這屬于思想史領域,而功過格教人如何積累功德,以求福報,又是一種指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手冊。
但是很快我就發現自己錯了。我本以爲功過格是研究流行思想(popular thought)的史料,但功過格實際上還是精英階層的成員創作的,因此不能被拿來直接當做反映民衆(commoner)觀念的材料。
另一方面,當時我對中國的善書非常感興趣,我讀了酒井忠夫先生的著作,一開始讀的是英文的文章“The popular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他在文中談到了功過格這種善書,後來我讀了他的名著《中國善書研究》,深深被功過格吸引,因爲這種類型的善書主張道德可以量化,可以計算,這令我充滿興趣,也充滿疑問。量化道德究竟意味著什麽?以及道德的量化如何影響人們對善行的看法?這就是我對功過格産生研究興趣的原因。
在《功過格》這本書中,袁黃(1533-1606,1586進士)是一個獨特的形象,他在宦途走到盡頭之後,投身于出版業,對晚明功過格的流行有很大影響。袁黃的“立命”觀念帶有某種革命性的啓蒙色彩,您認爲他是反映了當時一種普遍的潮流,還是所處社會的一個異類?
包筠雅:我想袁黃可能二者皆是。首先袁黃屬于陽明學派中的一個比較激進的分支(泰州學派),在他的“立命篇”中,袁黃主張人可以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決定自己的命運。他是晚明一股大思潮中的一員。他也參與功過格以外的出版活動,例如舉業書。舉業書雖然不是爲了底層民衆設計的,但這一類書的確有效地幫助了很多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普通人提高了在科舉考試中的表現。但是他在功過格中展現出來的觀念,未必能夠得到王陽明的認可。他的主張也是有矛盾的,人要行善而不圖回報,但是如果不圖回報又如何會去計算自己積了多少功德?陽明學派的其他成員肯定也察覺到其中的矛盾,劉宗周就反對袁黃對功過觀念的解讀(劉宗周主張只記錄自己的過錯,來避免有意識的積功圖報)。
另一方面,袁黃的家庭背景很不尋常,他可以說是精英階層的外來者(outsider)。他的祖上曾經因爲反對朱棣篡位而被禁止參加科舉長達三代。到了袁黃這一輩,他是第一位有資格參加科舉的子孫,他身上有相當的壓力,這也是他不同尋常的一方面。
您的書中勾勒出了明清之際功過格觀念的變化,它從一種帶有“立命”色彩、挑戰等級制度的思想萌芽,轉變成爲一種維護社會穩定的道德指南,您認爲發生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什麽?應當如何看待這種轉變?
包筠雅:轉變的原因就在于這本書的標題——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袁黃所在的江南地區,是一個充滿生機活力的地區,有很多非精英階層的人,善于把握社會機遇,變得富有,跻身上層社會,社會充滿商機和流動性,這樣的社會環境,很適合袁黃“立命”的觀念。但同時,十七世紀早期也存在著很明顯的社會緊張。佃農抗租的情況頻頻發生,最終還爆發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最終推翻了明朝。因此這也是一個充滿騷亂的社會。明亡清興,這種變化對士大夫階層來說是一種慘痛的轉變,似乎也是一種啓示,證明他們沒有恪盡職守,使社會安穩有序。因此在清代早期的士大夫之間有一種反思的情緒,反思到底哪裏出了問題,爲何漢人王朝會被滿人取代。《桃花扇》就凝聚了這種反思,還有顧炎武。反思的一個結果是認爲這是由于激進的陽明學派文人拒絕履行自己治理百姓的職責。因此清代初年對這種新的思潮有一種反動,否認晚明陽明學派對儒學的诠釋,而回歸一種更傳統、更保守的儒家哲學當中。社會秩序和禮儀再度得到強化。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流動性是不被鼓勵的。社會應當回歸正軌,就要求人們應當恪守本分。所以功過格從強調“立命”,即決定自己的命運,轉向了勸說安分守己,維系等級制度,維護社會穩定。所以我認爲是明清更叠之際的一系列社會政治劇變,導致了功過格社會功能的變化。
另外,功過格還有一種轉變,袁黃聲稱積善可以帶來現世的報償,而清初的功過格許諾的報償是超越此世,體現在後代身上。這種來世報償的觀念有點像是恢複到了十二世紀初功過格剛形成的時候。人們積善不是爲了此世的世俗報償,而是爲了子孫能夠獲得福報。這並不是說袁黃否認積善可以福澤子孫,他只是更強調此世的報償。
功過格的起源和它的超自然福報觀念有宗教信仰的背景,而在明清時期功過格成爲維持社會穩定的道德指南,從這個意義上,您能否談談傳統社會中世俗權威對宗教的改造?
包筠雅:整個功過格體系的基礎是對超自然報償(supernatural retribution)的信仰。袁黃在《立命篇》中的表達反映出他的確相信。清代早期的功過格,鼓勵社會穩定的前提也是這種超自然報償的觀念。不過清代許多士大夫並不相信,只是覺得它有用。清代的功過格序言中,一些作者會說我並不相信,但我認爲功過格的信仰觀念可以促使一般人遵守秩序,安分守己,這很有用。
功過格的普及主要是文人階層的推動,政府或許會不時給予支持,但據我所知並沒有有意推廣。明太祖朱元璋頒布過《大诰》等書,這些書雖然不是功過格,但帶有一種廣義的勸善教化作用,並且許諾如果遵從書中的規定,將會有某種回報,因此或許可以說政府也有一些推動善書普及的作用。順治年間皇帝曾谕令刊刻《太上感應篇》頒賜群臣。清代一個版本的《太上感應篇》也包含一篇告訴地方官員如何教導百姓的文字,所以地方官可能用過這些文本來教化百姓。
我沒有看到過關于政府審查或銷毀功過格的記錄。當然有不少批評功過格的人,但功過格並不是帶有造反性質的文本。盡管袁黃鼓勵利用功過格跻身社會上層,但功過格本質還是勸人向善,追求世俗的回報。清政府進行的是另一類的審查,審查的是那些有政治威脅或者不道德的文本。而對書籍質量的審查,主要針對的是舉業書。不過雖然我沒有見到過,不表示政府審查功過格的情況從未出現過。希望撲滅迷信的反而更多是現代政府。我還見過一種1920年代的功過格,指導使用者如何成爲一名合格的共産主義者,可見功過格這種形式在不同時代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功過格在明清士人之間很流行,它的實際道德教化效果如何?
包筠雅:有關功過格閱讀情況的證據是零散,甚至是主觀的。這本書出版之後,我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反饋,不少人記得自己在上海或者新加坡的祖母曾經有一本功過格。書裏還有一個例子,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滿鐵調查部在華北調查時發現,窮苦的華北農民家裏幾乎沒有任何書,如果有的話,就是這種廉價的功過格。我也在日本的圖書館裏見過有使用痕迹的功過格,有人在功過格中記下一些自己積功的數字。出版功過格也被當作一種功,不過出版的數量不能當作被閱讀的數量。這些都是軟證據(soft evidence),證明功過格的確被廣泛地閱讀、使用過。
但是這也引起一個有趣的問題,功過格是如何被使用的?功過格排版的方式不大相同,我見過一些是按照月份來排列的,每一天都對應的“功”欄和“過”欄,月末有一個合計。這是一種比較簡單的排版,使用者只需要填寫基本的數值。我還見過一些功過格排版是網格狀的。還有些功過格沒有表格,只有文本,使用者必須自己記錄。但人們寫下的是數字,而非自己做了什麽。
這就引起了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人們很容易利用功過格做博弈(gaming),去做很多微小的善事,以功過格的標准獲得一個很高的分數,來抵消自己的大惡。喬治·奧威爾的小說《緬甸歲月》中就有這樣一個角色,他相信超自然報償,因此不斷地向寺廟捐錢,認爲只要自己捐夠了錢,就能消除自己做過的惡事。
所以很難衡量功過格對人的道德境界有何影響,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美國的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雖然沒有發明過類似功過格的東西,但他的確說過,人應該在一天結束的時候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爲,並且記錄下來,成爲一本約束自己的冊子。盡管功過格本身有很多問題,但我們卻能夠看到這種道德自我約束的生命力,不僅限于傳統中國。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一些中國研究的主流範式和經典論爭,如何影響了您?
包筠雅:我在書中並沒有刻意去回應這些問題,但這些議題是無法回避的,它們充斥在當時的學術氛圍之中。我在研究生期間的同學們都有興趣思考如何推翻“停滯論”,因此我的研究主題也是想要反映變革而非停滯。功過格這類善書也的確存在重大的變化,它們看上去或許雷同,但是在差不多一個世紀的時間裏,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關于明清時期中國是否存在過一個“資本主義萌芽”的辯論,在當時也非常有影響。這並不是因爲最後討論出了是或者否的結論。這個辯論的前提條件是很值得懷疑的,亦即中國必須經過一個資本主義階段才能夠進入社會主義,而且,晚明社會的經濟推力未必就是資本主義。但是,圍繞著這一問題的一系列出色的研究,使人們注意到當時中國社會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和經濟形態,此前並沒有被好好研究,因此這一系列辯論極大推動了經濟史領域,盡管我並非經濟史學者,但是從經濟的角度探討社會發生的變革,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也很受本科時候的老師柯文的影響。他強調研究中國的曆史要從中國自身出發,而不是以西方的眼光和標准來審視中國。史華慈教授是我在哈佛時的導師,他是一位才華過人的思想史家,我也非常喜歡他的課。在當時美國史學界有一種流行的做法是將中國的思想家與西方思想家進行類比,看看某位中國思想家最類似哪位西方思想家。因此有文章將王陽明和海德格爾相比,或者與哈貝馬斯相比。而史華慈教授沒有這麽做,他正是那種從中國自身的曆史脈絡出發,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
日本學者的研究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的博士論文基本上是在日本完成的。在東京大學,我跟隨酒井忠夫先生進行研究。東京大學在社會經濟史方面有很深的傳統,我在那裏學到了很多,包括傳統中國土地租佃關系、晚明佃農抗租運動等等。盡管功過格和租佃關系的聯系不是那麽直接,但是當你對産生文本的社會環境(context)了解更多,比如寫書的時候大概發生過什麽事情,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它。頻發的奴變使很多精英階層的文人擔憂,他們擔心社會秩序崩潰,這也影響到了他們如何看待和使用功過格。
酒井忠夫先生也在尋找材料方面給予我巨大的幫助。在那個年代(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人到中國做有關中國的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功過格這種圍繞著超自然功報信仰的善書研究,涉及“封建迷信”,更加不妥。還好有很多明清功過格收藏在日本,因此我得以在日本接觸到許多珍貴的史料。日本的藏書有些是日本殖民過程中從中國收集的,這很令人遺憾。在這本書(《功過格》)出版之後湧現了大量有關功過格的研究,毫無疑問地證明,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圖書館中還收藏著大量功過格,數量一定比我在書中研究的要多得多。不過日本學者提問的角度和中國學者有所不同,他們感興趣的問題有時候未必是中國學者有興趣的,因此某種程度上,日本的藏本對中國圖書館的藏本是一種補充。
所以,我求學的時代,周圍環繞著如何研究中國的充滿活力的新觀念,而我在東京大學又學到了如何去做嚴謹、細致的研究,我想我是非常非常幸運的。
從本書的結論和您此後研究興趣的轉變都可以看到1980年代新文化史和歐洲書籍史對您的影響,您此後也更多地關注書籍史和印刷文化相關的問題,您可否談談研究興趣向書籍史的轉變?
包筠雅:有兩件事推動我從研究功過格轉向研究書籍的社會史。其中一個推力是我認爲這本書做得不好的地方。在全書的最後,我談到了一點功過格的出版、流傳和閱讀,我發現自己只有一些零星的材料,而且不是很系統。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大問題,爲了衡量功過格的影響,我們必須掌握書籍生産的情況,在哪裏刊刻、在哪裏出售、有哪些版本、如何流傳,我發現這一部分的曆史,但當時並沒有完成。
第二個推力就是你所說的書籍史(histoire du livre),我當時也大量閱讀歐洲書籍研究的著作,包括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和其他許多學者。我想,書籍在傳統社會如此重要,爲什麽沒有學者像研究歐洲書籍對歐洲社會的影響那樣,去研究中國的書籍呢?其實當時有很多相關的研究,只是我沒有注意到。比如東京大學的大木康先生。中國學者研究書籍是從書目文獻、版本學的角度,這在中國有幾個世紀的悠久傳統,但這種取徑研究的是與歐洲書史或書籍社會史完全不同的問題。我熱愛書籍,因此我想開拓這個非常有趣的研究領域。當然,中國和歐洲的曆史條件不同,因此也不可能提出完全一樣的問題,但的確有一些問題是相通的。
書籍文化(Book Culture)和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這兩個關鍵詞經常出現在您的研究題目之中,請問這兩者之間的側重點有何異同?
包筠雅:書籍文化和印刷文化史緊密相關而又不同。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學者,使用的時候有時不夠嚴謹,因此的確有必要區分它們各自是什麽。印刷文化應當囊括了所有的印刷品,當然包括印刷書,但也包括報紙,單張印刷品例如年畫、宗教形象、名片、廣告等等,多數印刷品應當都屬于印刷文化的範疇。而書籍文化,當然也包括用一切印刷方法(木雕版、活字、石印、鉛印)制作的印刷書,但是也包括手抄本。這兩個概念之間當然存在一些重疊。此外,印刷文化包括了許多曾經流行在東亞的印刷技術,從十九世紀以前的木雕版,金屬及木、陶活字,到十九世紀以後進入東亞的機械化活字印刷、石印、鉛印,以及現在的數字化印刷技術,印刷文化囊括了一個廣闊的技術領域,技術也影響了人們如何接受、閱讀文本。
您的這本《功過格》從英文版面世到中譯版再版,已經過了三十年的時間,如果您有機會爲中譯再版寫一篇序言,您會寫什麽?
包筠雅:我想我會寫我們剛才討論到的這些問題,關于功過格的觀念和實踐,以及在當代,人們如何繼續使用它。在當代中國和美國仍然有一些東西體現著這種量化道德和功過報償的觀念。中國有征信體系和社會信用評分系統,而在美國有信用報告系統(Credit Reporting System),也是一種用數字量化道德水平的體系。當一個人需要買房、買車的時候,銀行會核對這個數字,來評估這個人是否在經濟方面有責任心,值得信賴,這些將道德品質量化的做法,不僅存在于傳統中國社會。征信體系沒有任何超自然信仰意味,美國的信用評級也不帶宗教色彩,這些完全是世俗的體系,但是其中有一些共通的觀念,認爲數字可以代表一個人的品質,這仍然是非常有趣的。
您最近在進行有關清代西南地區書籍文化和清代蜀學的研究,可否向《上海書評》的讀者簡要介紹您的研究進展和發現?
包筠雅:我目前在進行的主要研究項目有兩個,但是因爲疫情的緣故,我無法到中國去,不得不緊急刹車。其中一個研究是關于十九世紀末成都的尊經書院。尊經書院1874年由張之洞和一些地方士紳創立,一開始是向四川學生傳授漢學,書院也出版經學書籍,後來轉向治公羊學,1898年尊經書院參與了維新變法運動,開始出版書院的期刊《蜀學報》,《蜀學報》的內容涵蓋相當廣泛,有關于變法改革的,有上谕,也有文章討論儒家道德倫理,西方的法律政治等等,是一本有趣的刊物。二十世紀初尊經書院並入了現代高等教育的學校系統。
我有興趣研究尊經書院的出版史,它反映出尊經書院都向學生教授過什麽,此外我也對在尊經書院讀書的人有興趣。尊經書院在培養學生通過科舉考試方面卓有成效,學生中的一些人後來成了晚清相當重要的官員。當他們離開四川,到北京做官,接觸到更宏觀的國家政策的時候,卻致力于形成一種名爲“蜀學”的區域性的學術流派認同。他們中的成員也競相去定義何爲“蜀學”。簡而言之,這個項目既研究出版,也研究人,是一個很有趣的項目。
我的另一項計劃是繼續江西浒灣的商業出版研究,我將繼續研究坊刻和大衆出版。我上一次訪問中國是在2017年,原本計劃2020年再度訪問中國,不過後來疫情全球爆發,我的研究項目也不得不暫停,這很令人沮喪。希望一切都能盡快好起來。
(感謝布朗大學曆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張烨凱先生、 澎湃新聞編輯黃曉峰先生的協助。)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