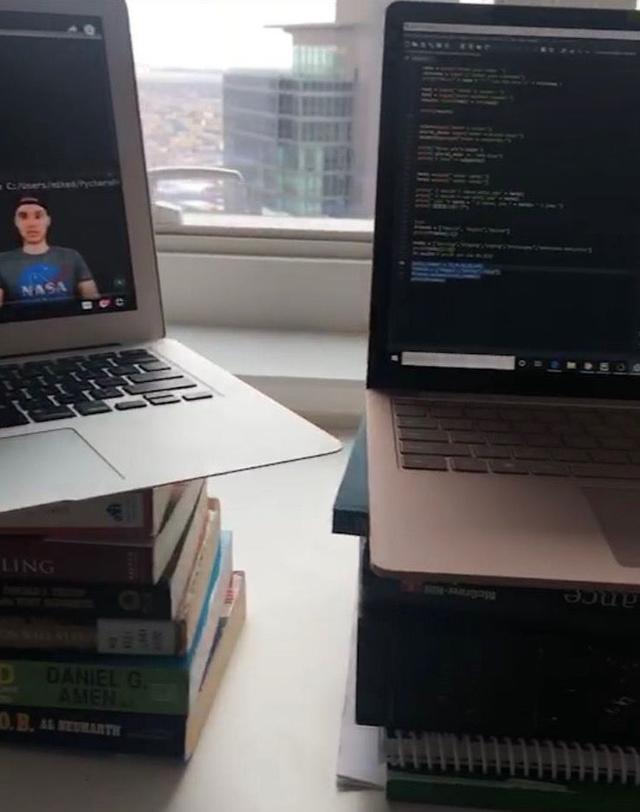“新冠疫情,中國打上半場,國外打下半場,中國留學生打全場。”在很多在外的中國留學生看來,這不是一句調侃,而是他們生活的真實寫照。
無法再進入的實驗室、中斷的畢業設計、搶空的超市、取消的航班、封鎖的城市、各國民衆對待疫情的態度……疫情之下,留學生在當地經曆了世間百態。
他們之中,有人乘坐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小心翼翼輾轉回國;有人選擇在當地留守,陪心愛之人度過漫漫長假。這次難忘的經曆,讓這些留學生感受到人類命運緊緊相連,對生命、親情,都産生了新的認知。
中斷的畢業設計
英國一年制的碩士項目往往在四月中旬第二個小學期末結課。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碩士生林伶的不少同班同學早早訂了回國機票,准備實習、找工作,待七月份第三小學期結束時再回到英國參與畢業設計答辯。
林伶打算第三學期留在英國做畢業設計,主題是制作一個倫敦電子地圖。在她的構想裏,電子地圖的用戶是到倫敦旅行的各地遊客,地圖可以爲他們推薦倫敦當地人心中的美食。林伶是廣東順德人,紀錄片《尋味順德》火起來後,常有外地朋友到順德旅行,尋找美食。好客的林伶只帶朋友們去吃順德人認准的老店。朋友們告訴林伶,雖然是外來客,有當地人的推薦同樣能吃到最“正”的美味。
林伶來倫敦後也曾想尋找當地最地道的美食,但旅遊網站上多是旅客的推薦,加上課業繁重,她很少有時間去了解普通倫敦人的生活。“整個碩士項目的學生裏沒有一個英國人,老師也來自世界各地。一年到頭,總覺得自己對英國、對倫敦沒了解多少。”
畢業設計給了林伶機會。制作地圖需要林伶的團隊進行大量的實地調研,了解目標用戶的需求和倫敦城的實際情況。在她看來,這成爲了解倫敦生活的絕佳機會。“我們要去做訪談,和很多普通倫敦人訪談,了解他們最愛倫敦的哪些部分。他們向遊客推薦的才是真正的倫敦。”
然而,新冠疫情在英國蔓延,林伶只能暫停畢業設計計劃。具體如何調整,還需要和老師、組員商量後再做決定。“不能做期待中的畢業設計,還挺遺憾的。”
“我不敢回國,我怕我上學期期末考試挂科,如果回了國,再回來不知道會是什麽時候了。”朱赫是北京理工大學大四的一名學生,一年前,他報名參加了北京理工大學和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的交換項目,計劃在德國完成大四的課程及畢業設計。
3月中上旬是朱赫的期末考試周。“學習壓力非常大,每天只睡五個小時,白天除了吃飯就是學習。哪還有時間想疫情的事啊?”
3月中旬,結束了最後一科考試的朱赫突然“蒙了”。彼時,德國已有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2700余例,朱赫所在的達姆施塔特市也出現了確診病例,他才從昏天黑地的考試中驚醒,“現在想想,挺後怕的,之前沒做任何防護措施。”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德國的蔓延,朱赫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他無法再按照原計劃,每天去實驗室跟隨導師完成關于複合材料力學的畢業設計,而是居于家中看論文,以及自學一些工程模擬軟件的操作,“現在肯定是做不了實驗了,先多做做功課,希望疫情過去之後能提高研究效率。”
朱赫介紹,根據學校規定,他需要去學校的機械中心注冊後,才可以開始畢設創作。然而,新冠疫情暴發後,學校就關閉了。“我已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完成了注冊,同時,論文期限最多只有五個月,現在距離答辯只剩下三個月,每天都盼著疫情早點過去,我好回實驗室繼續做實驗。”
“和我一起過來的還有幾個同學,他們中有的人打算繼續在德國讀碩士,這部分同學現在已經回國了。”朱赫的導師和他說,一定程度上他有延期畢業的可能。而朱赫畢業後的計劃是到英國攻讀碩士學位,如果無法按時畢業,他後面的日子將會麻煩得多。
回與不回的糾結
除了畢業設計受到影響,這些在外中國留學生們也擔心自己被感染了。
爲了減少被感染的可能,林伶選擇閉門不出。她住學校的宿舍,那是一個en suite(套間)房型,每個臥室都有獨立的衛生間,大部分日常起居都可以在臥室中完成。但她需要和另一間臥室的同學合用廚房,這是她最擔心的地方。 “疫情這麽嚴重,室友依然照常出門,合用廚房難保不會造成交叉感染。”
學校在3月23日已經改上網課。林伶每天待在宿舍狹小的空間裏,除了上網課再也無事可做。英國的疫情蔓延迅速,這讓她漸漸有些焦慮。回國?目前已很難買到直飛的機票,多次中轉、航程較長的航班勢必會增加感染的風險。不回國?宿舍空間狹小,長期居家生活容易導致焦慮情緒,英國當地疫情也很難說什麽時候結束。
權衡再三,林伶買了3月26日經由莫斯科中轉的航班回國。當她收拾好行李,並將宿舍裏儲備的“存貨”送給了其他人,等待回國之時,3月22日,俄羅斯政府宣布,3月23日起,俄羅斯將臨時限制與所有國家的空中交通。除撤僑包機外,與每個國家僅保留一條航線。
這個消息讓林伶所在的同學群炸了鍋,她身邊的中國同學有三分之二計劃回國,不少人買了同一趟經莫斯科中轉的航班。“打了好多電話,但是對方就是不回應是不是要取消航班。”與此同時,不少國家也開始對非持有本國護照的旅客進行入境和轉機限制,一旦中轉莫斯科的航班取消,留給中國留學生們的選擇只有全程超過三十小時、中轉兩到三次的航線“曲線”回國。林伶等人把這樣的航班稱爲“死亡航班”,“大家回國都是全副武裝,盡量避免吃東西、喝水、上廁所,三十個小時的航班保持這樣的狀態我們肯定會虛脫。”
“最好的情況是從莫斯科回國的航班沒有取消。即使取消了,希望還有航班把我運回倫敦,好歹還有個睡覺的地方。”林伶說。
“現在剩下五張票,你要不要收拾行李馬上回來,快點答複我。”3月15日,美國福特漢姆大學碩士生邱邱接到母親的電話。而前一天,福特漢姆大學宣布了線上授課將持續到春季結束的消息,此時回國對邱邱來說,成爲一個合理的選擇。
“我真的想過這個問題很多次,但沒有想到我要去面對它。”邱邱的男友一臉平靜又疑惑地望著她。看著他的眼睛,邱邱始終沒辦法對電話另一端、位于大洋彼岸的媽媽說一個“好”字。“如果我走了,我跟這個在乎的人是不是就這樣分開了?”
挂了電話,邱邱心裏第一次有了不知所措的慌張。彼時,紐約大部分學校已經停止線下授課,大部分公司已經實行在家辦公。超市裏肉蛋奶每天都幾乎被一掃而光,邱邱訂購的食物送到手裏的只有不到10%,口罩等防護物品基本買不到。通過小區的郵件,邱邱得知她所住的樓裏,也出現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如果現在不走,會不會有食物買不到,交通封鎖,想走走不了的那一天?如果我被感染了怎麽保證存活條件?”邱邱陷入了糾結,但最終她選擇留守紐約。作爲金融專業學生,她一邊盯著金融市場在病毒危機下呈現的全球震蕩,一邊讀著一本講逆境中成長經曆的書。
3月14日,邱邱所在的福特漢姆大學宣布線上授課將持續到春季結束,邱邱每天在宿舍裏上網課。受訪者供圖
回國的安與不安
3月15日,蔡曉從加拿大溫哥華回到了祖國。蔡曉運氣不錯,買到了直飛航班,航班在廈門降落,蔡曉填報完身體健康狀後再乘另一航班到最終目的地——山東濟南。
蔡曉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大四的學生。當地時間3月14日,學校正式停課。但在之前,蔡曉去上課時就注意到,身邊不少中國同學都在討論如何買機票回國。“三月初,溫哥華直飛國內的機票就已經很緊張了,到了三月中旬,回國航班基本已經賣光了。”
爲了避免長途飛行中的交叉感染,蔡曉戴上了口罩。等她到了機場發現,不少回國的留學生全副武裝,不僅戴多層口罩,還穿著防護服,戴著護目鏡。而在溫哥華機場,防控疫情的氣氛已經趨于緊張。在值機的服務台處需要測量體溫,而在安檢前還需要測量一次。“登機時又測了一遍,路上測了一遍,下飛機又測了一遍,反反複複很多次。”
溫哥華到廈門需要飛行12個小時。蔡曉發現,以往飛機餐的餐盤變成了一個外賣盒,裏面有能量棒、巧克力、水果罐頭等已被密封的食物,除了熱水,其他飲料都改爲密封包裝。但12個小時的航程中,很少有乘客吃東西或喝水。大家無人摘下口罩,也鮮有人互相交談。
蔡曉注意到,乘務員戴著雙層橡膠手套和口罩,每個衛生間前都有乘務員值守。蔡曉去衛生間前乘務員遞給她一雙手套,並要求她戴上,出來後又指導她把用過的手套扔到一個指定的袋子裏,並給她的雙手消毒,“使勁兒讓我擦手”。
飛機落地後,機組通知所有人員不要走動,等待檢疫人員上機檢查。“檢疫人員給從美國回來的人單獨貼了標簽,讓他們先下機。之後機上廣播要求旅客以每三排爲單位下機。”
蔡曉在飛機上填寫了健康申報表,下飛機入海關,共有三批工作人員幫她檢查。“幫我檢查表填的對不對,有沒有填好。海關那裏的自動測溫裝置也能監控我們的體溫。”而在國內航段,蔡曉一上機就收到了乘務員發放的消毒濕巾和手套。飛機落地後,機場有專門的工作人員在境外歸國人員申報點幫助蔡曉申報。
目前蔡曉正在濟南市的集中隔離點,即將結束隔離。她已經通過了核酸檢測,每天需要報備三次體溫。“這半個月覺得很溫馨,從航班到隔離點,工作人員的工作實在是太細心了。”
“盼著回家,盼著重返‘自由’。”從隔離酒店的窗戶向外望,北京街上漸漸有了春的生機。此時,悉尼大學畢業生袁林正在北京海澱區一家酒店進行隔離,如果沒有疫情的發生,他原本計劃在三月底續簽工作簽證,繼續在悉尼從事教育相關的工作。
疫情的發生加速著袁林的回國計劃。3月初,他購買了從悉尼回國的機票,“留在這裏不是一個安全的選擇,工作辭了,簽證也不續簽了,以後在家鄉找工作吧。”
袁林回憶,返回中國的飛機上,座位幾乎被坐滿。“大多數乘客是中國人,都知道疫情有多嚴重,所以大家也都很謹慎,全程除了吃飯,不會摘下口罩,就怕有傳染風險。”
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時,袁林産生了久違的安全感。“首都機場的體溫檢測很嚴格,入境管理也很嚴格,我一下飛機就被帶去隔離酒店了,除了乘客和穿著防護服的管理人員外,這些天我沒再見過其他人。”
回國之前,袁林在悉尼拍攝了一些視頻素材。這些天,袁林經常通過剪視頻的方式度過隔離期間無聊的日子,他也經常回憶起在澳洲求學的時光。“恍若隔世。”
蔡曉在集中隔離點的飯菜。 受訪者供圖
疫情之下:很難在當地人臉上看到焦慮
讓袁林選擇回國的原因之一——當地人對疫情的態度。
“面對疫情,我覺得澳洲人是恐慌的,澳洲剛開始有新冠肺炎病例時,我在這邊就已經買不到口罩了,卷紙也買著很困難。”但當地人對聚會的熱情又讓袁林感到不解。
回國前,想到短期內不會重返澳大利亞,袁林戴上口罩,去悉尼歌劇院、邦迪海灘等地,拍攝了大量視頻素材,渴望以此銘記這兩年在悉尼的留學時光。讓他意外的是,“歌劇院邊上的草坪,酒吧裏,都有大量聚會的人,他們不害怕嗎?”
拍攝素材期間,袁林也經受了來自旁觀者的非議。“有一次,我在橋邊拍攝的時候,一個經過的司機看我戴著口罩,搖下了車窗,對我喊了一句‘Virus’(病毒),又搖上車窗開走了。”這些場景讓袁林産生了一種剝離感,“也許回國會更好過一些。”
疫情之下,德國斯圖加特大學碩士生陳思選擇留在德國,3月25日是他本學期最後一門考試,但是隨著學校停課,考試也隨之取消。他把外出次數減少爲7-8天一次,每次外出采購一些水果、蔬菜和日用品,礦泉水等較重的日用品則通過網絡購買。
斯圖加特是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首府和第一大城市。陳思告訴記者,巴登-符騰堡州已經成爲德國疫情第二嚴重的州,有超過4000例確診病例,其中斯圖加特有100多例。但在斯圖加特的街上,卻很難看得出人們因疫情而焦慮。陳思住所附近的街區也似乎和往日沒有什麽兩樣,“很多德國家庭還是在室外散步、玩,和疫情前的狀態很類似”。
疫情期間,陳思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過不少其他國家超市中廁紙、水被一搶而空的圖片。但在斯圖加特,當地超市中的水果、蔬菜、肉類以及包括廁紙在內的日用品供應相對充足,唯一短缺的商品是面粉。“可能大家囤了面粉做面包,但面包還能買到,不過口罩已經買不到了。”
此外,疫情的影響在一些細節上還是得以體現。陳思坐地鐵去超市采購時發現,以往滿滿當當的地鐵車廂如今只有零零星星幾個人。而在斯圖加特市中心,街道上的人流量也明顯減少。
實際上,斯圖加特當地人對疫情的態度直到近兩周才開始緊張起來。3月初時,仍然有德國同學與陳思開玩笑,說亞洲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歐洲人可以不用害怕,“我覺得匪夷所思,但他們還讓我放松些,說是科學家說的。”
3月8日,德國衛生部長延斯·施潘曾建議取消一千人以上的群體活動。但令陳思哭笑不得的是,一些一千人以上的音樂會觀衆人數被組織者削減至999人,音樂會仍按期進行。3月9日,斯圖加特還舉辦了一場和比勒菲爾德的德甲比賽。官方只是敦促球迷注意預防措施和衛生規則。
陳思是一名攝影發燒友,在他的社交平台上,經常能看見他用相機記錄下的德國街頭。從3月20日起,斯圖加特政府建議市民無故不要出門。陳思告訴記者,實際上如果拿相機去拍照被發現會被罰款。“以前很喜歡走街串巷搞街頭攝影,現在只能偷偷去樓下的小樹林拍拍風景了。”
陳思最擔心的是,斯圖加特大學對于校園內確診病例的披露並不及時。“上周學校一個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被確認,但學校四天之後才在官網發布了消息。”陳思未雨綢缪,專門去了解一旦感染新冠肺炎需要如何就醫。他告訴記者,中國駐德國大使館開通了24小時咨詢熱線,留學生、華人可以通過撥打熱線電話了解自己的症狀是否可能是新冠肺炎。“如果真的出現了症狀,我們第一選擇肯定是打給大使館,因爲是中文服務,不用擔心語言的障礙。”
除了大使館的咨詢熱線,德國當地民衆還可以預約家庭醫生進行初步的檢查來判斷自己是否感染。陳思告訴記者,即使要進行咽拭子取樣,他們可以去指定地點通過一個窗口由家庭醫生完成檢測采樣,“就像外賣窗口一樣,全程無接觸。”
“周圍的人怎麽一點都不急呢?”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就讀的碩士生楊靜也有相似的困惑。
1月底,已有新冠肺炎病例在新加坡出現。“我看到超市裏有人在排隊買口罩,口罩都被搶空了,但是很奇怪,街上都很少見到有人戴口罩,戴口罩的都是中國人。”楊靜說,當地人對待新冠疫情的態度是“割裂”的,一方面大家會去超市裏搶購口罩、衛生紙等物品,另一方面又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態度,新冠肺炎疫情很少成爲人們日常談論的話題。
“疫情蔓延到全球後,美國、英國、德國等國家的學校紛紛宣布取消面授課堂,3月中旬,南洋理工大學校園內已出現兩名新冠肺炎感染者,但我們遲遲不停課。”楊靜看到,她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學依然在堅持面授課程,防護措施也沒有她期待中那樣完善。“學校只取消了50人以上的面授課程,我所在的班級有40余人,全部的課程、考試都在照常進行,我的室友是學電氣專業的,他們還在照常做實驗。”楊靜說,南洋理工大學的教室門口,張貼了二維碼,學生在在進入教室前可以掃描二維碼,填寫表格記錄個人信息,以便追蹤潛在接觸者。但“是否填寫完全是出于自願的,我有事著急上課,就會忘了填。”
臨近期末,楊靜又多了一重心理壓力。“在家實在學不進去,白天我通常會去學校的圖書館學習,到了期末,圖書館裏的學生更多了,而且大家經常擠在一張桌子上學習。”楊靜清楚地記得,有一次在圖書館學習時,對面一位亞裔同學接連打了好幾個噴嚏,但沒有人覺得異常,反而是楊靜戴著口罩行走在圖書館時,周圍的人會自覺遠離她,有時還會投來鄙夷的目光。“他們覺得,只有患者才會戴口罩。”
“我們學校在新加坡的郊區,從圖書館的樓頂上看,能看到柔佛海峽。”3月17日,楊靜看到新加坡鄰國馬來西亞宣布封國的消息,她又陷入了緊張情緒,去超市買了米、面、肉制品、雞蛋和蔬菜,又買來了洗手液和卷紙,以防萬一。
疫情之下,楊靜在新加坡的日子還能照常過,只是會在上下學的路上避免人群聚集的地方。前幾天,她收到學校發來的郵件,南洋理工大學終于要全面進行網絡授課了,但考試形式將維持不變。“我們學校已經出現9例新冠肺炎患者了,他們怎麽就不著急呢?”楊靜哭笑不得。
受疫情影響,原本熱衷街頭攝影的陳思只能偷偷到住處樓下的小樹林裏拍風景。 受訪者供圖
相隔千裏的牽挂
“新冠疫情,中國打上半場,世界打下半場,留學生打全場。”雖然這只是一句對留學生的調侃,卻有留學生表示,“打全場”幾乎是他們的真實狀態。
“有時候,相比于在千裏之外擔心家人,我甯願自己處在一個較爲危險的地方,會有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中國疫情嚴重的那些天,楊靜幾乎每次看新聞都會哭,擔心家人感染。她幾次情緒崩潰,給家裏打電話的頻率是平時的三、四倍,反複叮囑家人不要出門,不要聚集,戴好口罩。還通過網絡捐款的形式,爲中國抗疫出了一份力。
看到中國的疫情有好轉,楊靜緊張的心情開始有所放松。轉眼再看看自己所在的新加坡,新冠肺炎病例開始以每天十幾例、幾十例的速度增長著,又變成了家人不停給她打來電話,叮囑她戴好口罩,減少出門次數。
袁林的愛人家在湖北宜昌,澳大利亞疫情暴發前,袁林和愛人每天都盯著疫情滾動數據。“看著國內增長數字,心都碎了。”
朱赫收到了來自母校的關懷。3月20日,他收到了北京理工大學國際處的通知,學校將爲在海外交換的學生寄出一批口罩。
中國疫情發生時,邱邱和她的同學在紐約想方設法爲國內的同胞寄送口罩。“我們聯系了紐約很多廠家,對接國內負責接收、發放這批口罩的人員,飽經周折,才把口罩寄送回國內。”而今,卻是邱邱的媽媽想方設法從國內爲身在紐約的秋秋寄送口罩、防護服等物品。“這種感覺挺神奇的,疫情之下,人類命運緊緊相連,親情的定義也更加豐富。”
3月22日,紐約宣布封城。從住處的陽台向外望,紐約昔日繁華的街道上已不見人影,邱邱將在這裏度過一個充滿未知的“長假”。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林伶、朱赫、邱邱、蔡曉、袁林、陳思、楊靜均爲化名)
新京報記者 樊朔 戚望 編輯 潘燦 校對 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