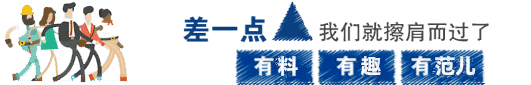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IPP評論(IPP-REVIEW)是鄭永年教授領導的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無論就中國曆史還是就世界曆史而言,這個時代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時代。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乃至政治轉型。就經濟而言,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初一個貧窮的經濟體躍升爲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從一個幾乎處于封閉狀態的經濟體,轉型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大國,並且已經俨然成爲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領頭羊。
中國知識界進入一個悲歌時代
而這些變化的背後,是從原先計劃經濟向中國自身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就社會發展而言,這些年裏中國已經促成了數億人口的脫貧,同樣爲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迹;盡管還有很多窮人,但人均國民生産所得也已經接近9000美元。
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也同樣顯著,包括人口壽命、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後建立起來的制度經受住了各種挑戰,化解了各種危機;盡管仍然被西方簡單地視爲權威主義體系,但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顯現出其高度的韌性和靈活性,與時俱進。
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實踐,需要人們來解釋,來提升,概念化和理論化,從而創建出基于中國經驗之上的中國社會科學體系。很顯然,這是中國知識界的責任。這個責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國知識界的偉大時代,但現實無比殘酷,當中國成爲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實驗場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則進入一個悲歌時代。
說是知識的悲歌時代,倒不僅僅是因爲權力、金錢和大衆對知識史無前例的鄙視,也不是因爲知識常常被用來點綴、成爲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爲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今天知識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識創造者本身對知識失去了認同,知識創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體地位,而心甘情願地成爲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國大學衆多,每年都有很多校慶,不過一次次校慶就是對知識的一次次羞辱。
有些知識人要名利雙收
每次校慶,大家無一不是以培養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獨說不出來的就是,沒有一個大學已經培養出一位錢學森生前所的說“大師”。實際上,今天大學或者研究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公共論壇乃至學術研討會,人們都已以邀請到大官大富爲目的,而知識本身則是極其次要的、可有可無的陪襯物。
知識體系是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沒有這個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難在世界上生存和發展,至多成爲未來考古學家的遺址。從知識創造的角度來看,正是偉大的知識創造和造就了文明。在西方,從古希臘到近代文藝複興再到啓蒙時代,這是一個輝煌的知識時代,沒有這個時代,就很難有今天人們所看到所體驗到的西方文明。中國也如此,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陽明等,鑄造了中國文明的核心。
就知識創造者來說,知識創造從來就是個人的行爲。盡管有些時候也表現爲群體知識,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但群體知識仍然是基于個人知識體系之上,只是一些學者之間有了共識,才形成爲互相強化的群體知識。
同時,在中國“學而優則仕”的政治環境裏,知識表面上是政府知識分子(也就是“士”)這個階層創造的,但應當指出的是,政府從來不是知識的主體。
當然,這並不是說政府在知識創造過程中就沒有責任,政府既可以爲知識創造有利、有效的環境,也可以阻礙知識的創造。因此,從知識創造者這個主體來反思當代中國的知識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說,我們要回答“我們的知識創造者幹什麽去了呢?”這個問題。
一個一般的觀察是,在中國社會中,曆來就是“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爭智于孤”。這裏,“爭名于朝”是對于政治人物來說的,“爭利于市”是對商人來說的,而“爭智于孤”則是對知識人來說的。今天的知識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現代知識人已經失去了“爭智于孤”的局面,而紛紛加入了“爭名于朝”或者“爭利于市”,有些知識人甚至更爲囂張,要名利雙收。
很多知識分子對大官吹牛拍馬
爭名于朝。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從前是“學而優則仕”,從學的目標就是從官,並且兩者沒有任何邊界。現在從學的目標已經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論上說)了從官,並且兩者之間有了邊界。盡管大多知識人士爲官了,但“爲官”的心態仍然濃厚,因此還是通過各種變相的手段爭名于朝。當然,這背後還有巨大的“利益”。競相通過和“朝廷”的關聯來爭名,這個現象隨處可見。
一些學者給政治局講一次課就覺得自己非常了不得。今天在做智庫評價指標時,人們以爭取到大領導的批示和認可作爲最重要的指標。更有很多知識分子對大官竭盡吹牛拍馬之功能。無論是被邀請給政治局講課還是文章拿到了領導的批示,這可以是一個指標,但並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標。知識有自己的指標。如果知識人以這些東西來衡量自己的知識的價值,那麽不僅已經是大大異化了,而且很難稱得上知識。
爭利于市。這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個新生事物。傳統上,從理論上說,知識分子和商業是遠離的。從認同上說,知識分子顯得清高,不能輕易談錢的問題;從制度層面來說,“士、農、工、商”的社會安排把知識分子和商隔離開來。當然,在實際層面,兩者也經常走在一起的。不過,現在情形則不同了。知識分子以其利益爲本、以錢爲本,公然地和企業走在一起,各個産業都“圈養”著一批爲自己說話、做的知識分子。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房地産業。中國的房地産能夠走到今天這麽荒唐的地步,不僅僅關乎房地産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關乎于這個産業“圈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因爲這些人的每一步都在論證著政府房地産市場政策的正確性,推波助瀾,而非糾正錯誤。
知識付費與知識的未來
在現代社會,除了和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發生關系,知識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來爭名利。例如,爭名于“名”,即通過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嘗不可,而且也是知識生産和創造的手段。不過,在今天的中國,人們不是認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據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隨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陽明。王陽明是個大家,現在被炒得很紅火。不過,很遺憾的是,沒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陽明,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現在的情況延續,“陽明學”很快就會演變成一種庸俗不堪的宗教,不僅靜不了人們的心,反而會攪亂人們的心。
這種現象在所謂的“國學”處處可見,人們所期望的國學精華沒有出現,而那些“牛、鬼、蛇、神”則已經泛濫成災。中學如此,西學也如此。例如馬克思。在世界範圍內,今天的中國擁有著最大群體的馬克思研究機構和馬克思研究者,因爲馬克思幾乎已經成爲官方的“國學”。但是認真去讀一下這些機構和學者的産品,有多少人懂馬克思。馬克思只是他們的政治,只是他們的飯碗。
在互聯網時代,知識更是具備了“爭名利于衆”的條件。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知識人通過互聯網走向了“市場”,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識“商品化”。當然更多的是充當“販賣者”,即沒有自己的知識,而是販賣人家的知識。互聯網是傳播知識的有效工具,但這裏的“販賣”和傳播不一樣,傳播是把知識大衆化,而“販賣”的目的僅僅是爲了錢財。
看看眼下日漸流行的“付費知識”就知道未來的知識會成爲何等東西了。另一方面,互聯網也促成了社會各個角落上的各種各樣的“知識”(宗教迷信、巫術等)登上“學術舞台”,並且有變成主流的大趨勢,因爲衡量知識價值的是錢、是流量。
而後者的力量如此龐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識分子都是在爭流量,爲此大家爭俗、爭媚,媚俗和流量無疑是正相關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會影響力等同起來。這就不難理解,即使官方媒體也和衆多自媒體一樣,堂而皇之地媚俗。
名利只應該是知識的副産品
古今中外真正的學者沒有一個是爭名爭利的,有很多爲了自己的知識尊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曆史上,不乏知識人被權力和資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來才逐漸有了言論自由的保障。對大多數學者而言,名利並非是追求而來的,而僅僅只是他們所創造知識的副産品。
很多學者生前所生産的知識,並沒有爲當時的社會所認可和接受,窮困潦倒。那些能夠遠離名利的學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毛澤東曾經評論過屈原,認爲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爲被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産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引自鄧力群著《和毛澤東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文)。
一旦進入了名利場,知識人便缺少了知識的想象力。一個毫無知識想象力的知識群體如何進行知識創造呢?一個沒有知識創造的國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爲知識之于民族和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近來自上到下都在呼籲知識的創造、創新。爲此,國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財政資源,培養重點大學,建設新型智庫,吸引頂級人才等。但現實情況極其糟糕,因爲國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場越大;名利場越大,知識人越是腐敗。
最近,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稱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近代大學,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補充的是,不僅沒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學,而且也遠遠落後于傳統書院制度。實際上,無論是近代大學還是傳統書院,重要的並不是大學制度或者書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學和書院的主體,即知識人。
有了以追求知識的知識人之後,這些制度就自然會産生和發展;而在缺少知識人的情況下,最好的大學和書院也只是一個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識人自願墮落的情況下,這類居所越好,知識越遭羞辱。
知識圈在下行,知識也在下行。盡管預測是危險的,但人們可以確定的是,如果這個方向不能逆轉,那麽中國很快就會面臨一個知識的完全“殖民化”時代,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道理很簡單,人們已經不能回到傳統、不需要那麽多知識的時代,知識是需要的,但人們因爲沒有自己的知識,那麽只好走“殖民”路線,即借用和炒作別國的知識。
在很大程度上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走的就是這個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數十年可以想象的。
對此,你怎麽看?
歡迎給小編留言!
覺得不錯請點ZAN!
領導說了,
您點一個
小編的工資就漲五毛!
這5篇文章你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