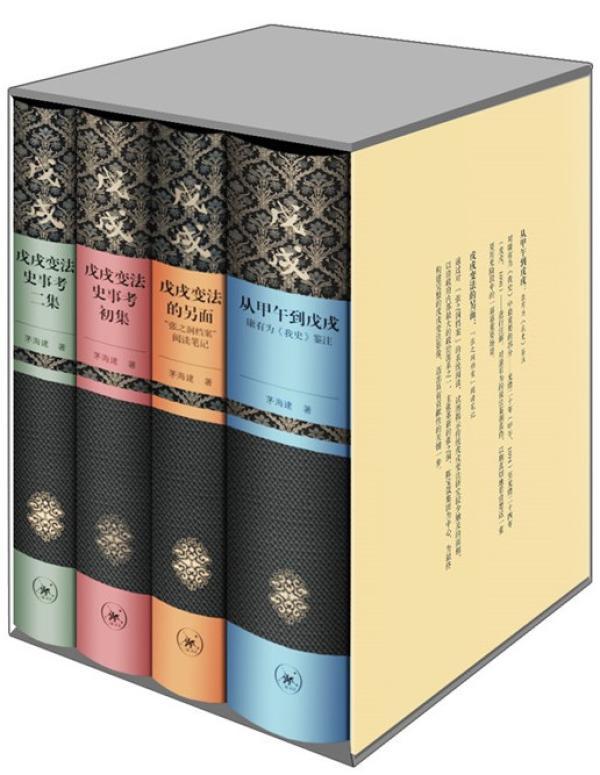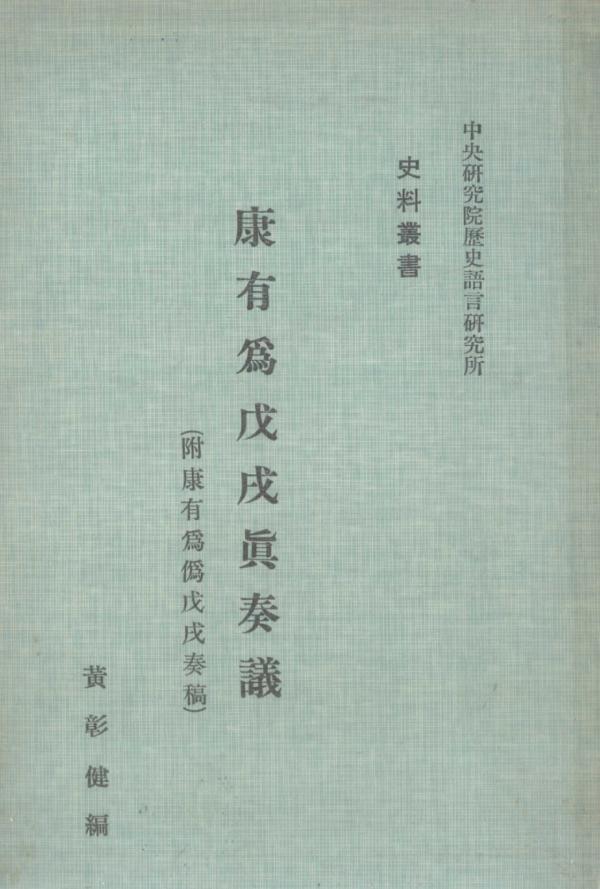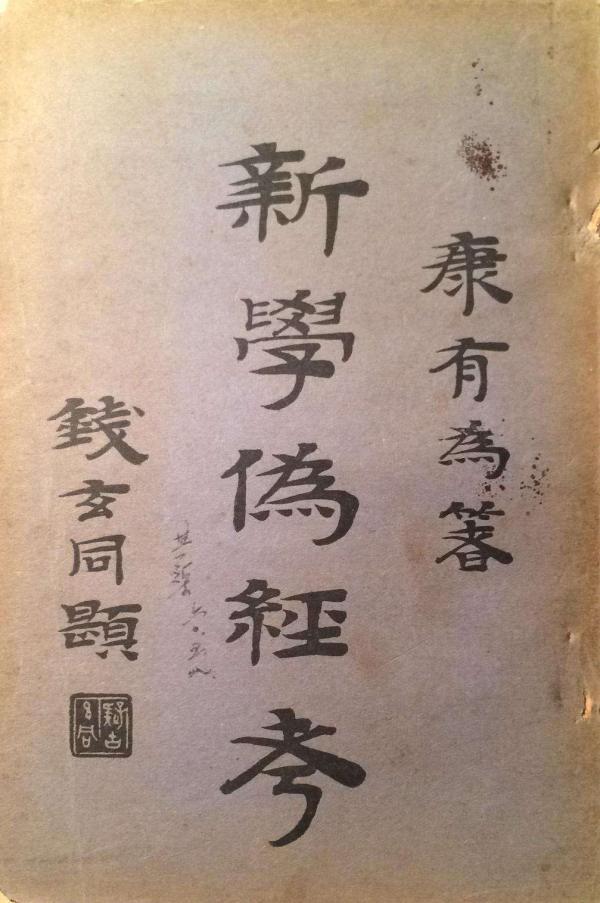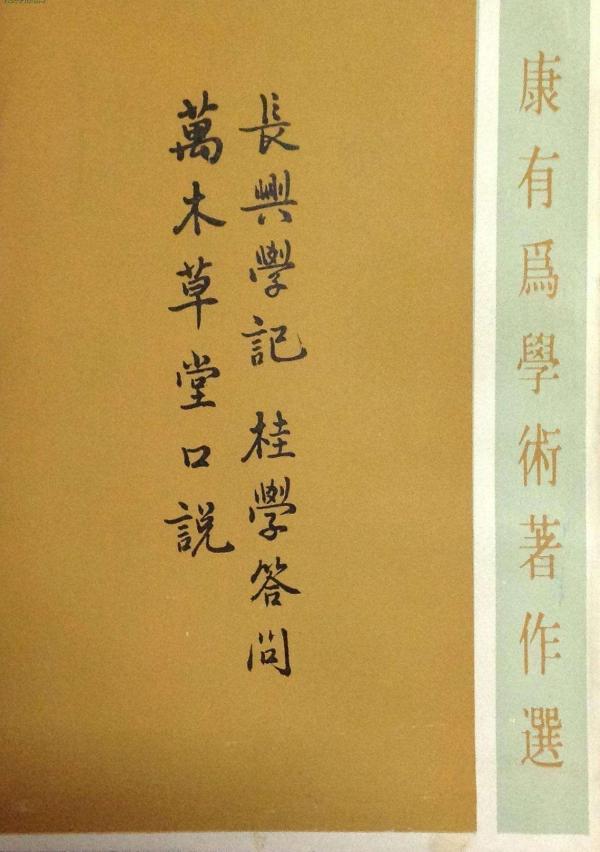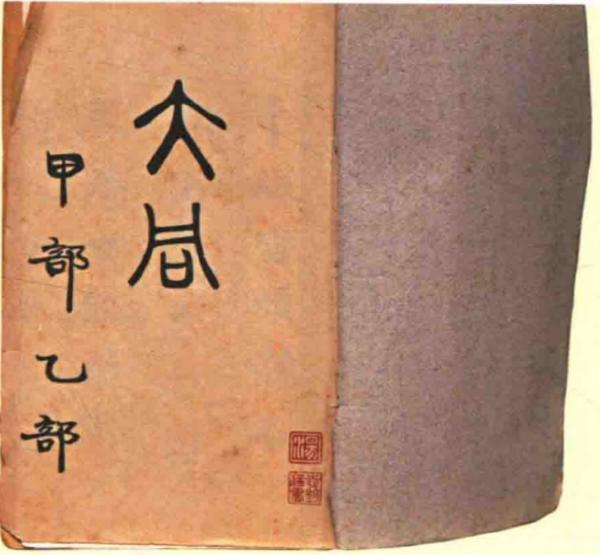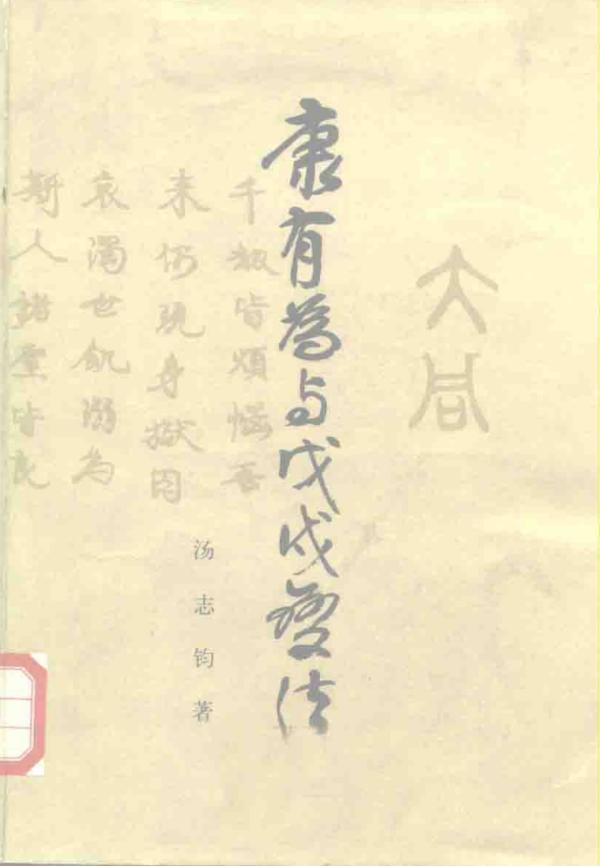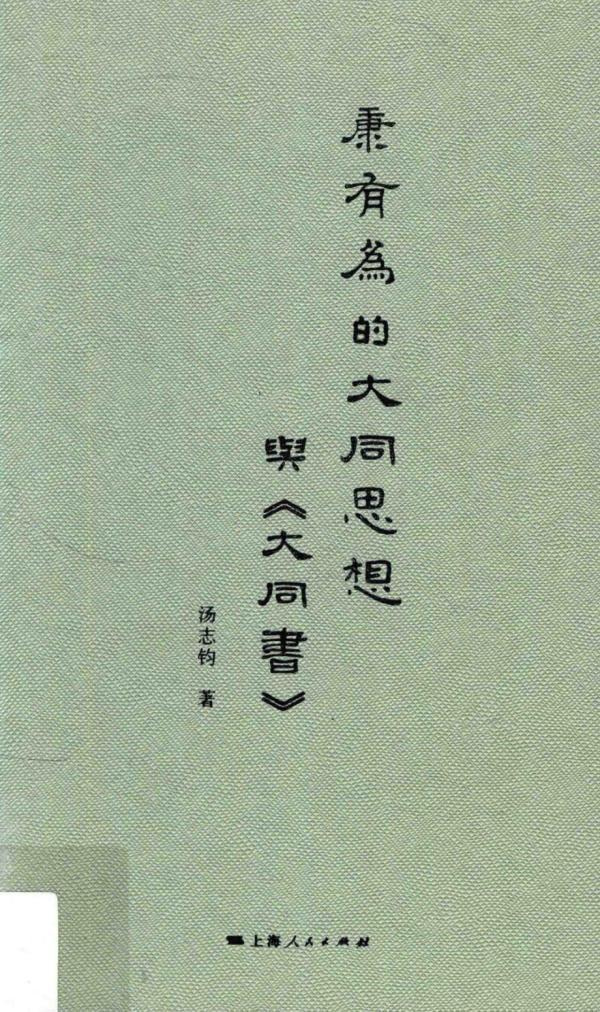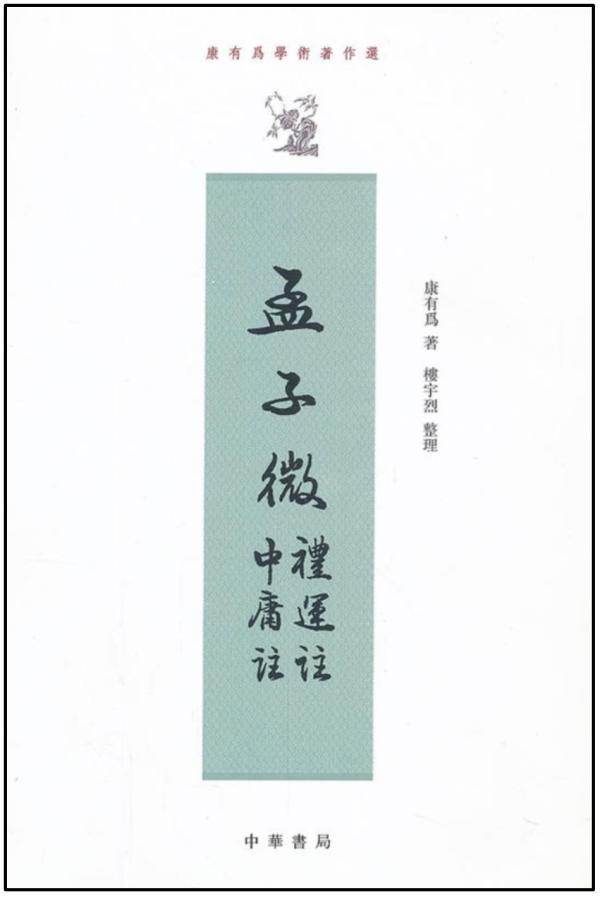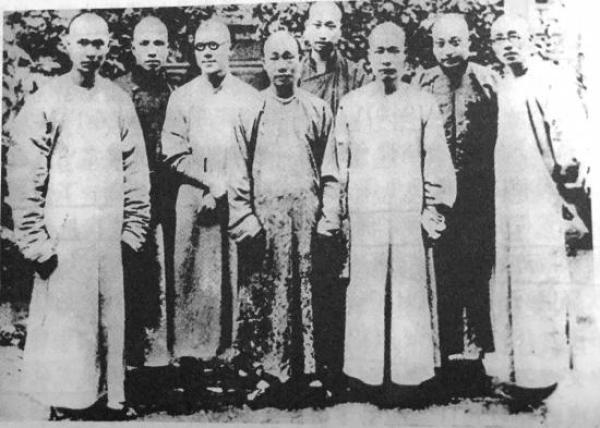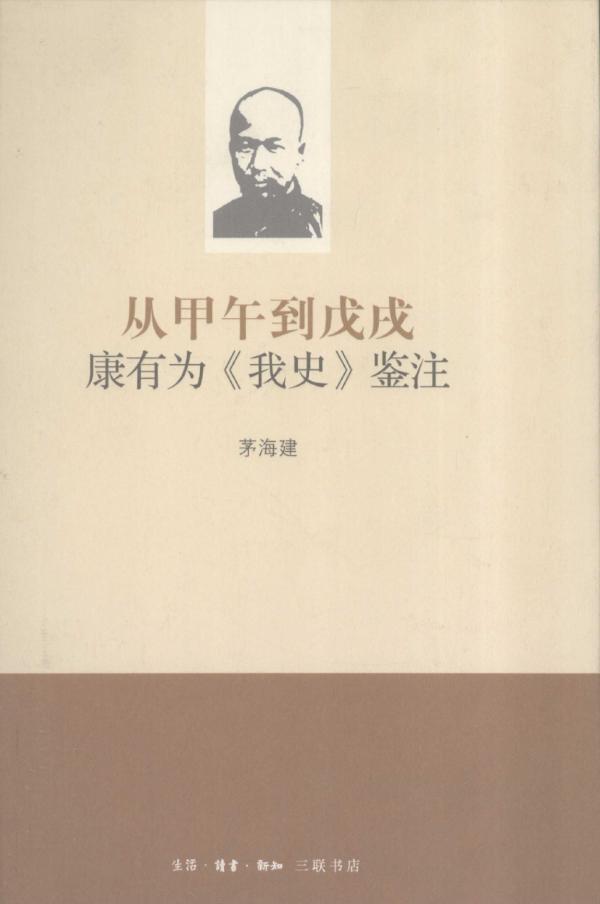按:本文系作者2018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聯合舉辦的講座上的發言。
康有爲
當三聯書店的編輯告訴我,這次推廣會放在北大時,我心中怦然一動。我離開北大剛好十年。當年在北大時,對北大的景物關注度不夠。有一年,我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對我說,很懷念北大二院(曆史系)的紫藤,我聽了很詫異,回來後才看到二院的紫藤花盛開。
今年是戊戌年,戊戌變法兩個甲子,北京大學是變法的産物,也就是北大的一百二十周年。再過兩個星期,6月11日,正是“百日維新”的起始日。離開北大後回北大講戊戌,感覺上是有點奇特,當然也只是巧合而已。
《茅海建戊戌變法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6月出版,395.00元。
問題的發生
康有爲的“大同三世說”,是我最近講的比較多的題目,是近幾年最爲關注者。我寫了幾篇非常學術性的論文,字數加起來大約有三十萬字,十分繁瑣。我在這裏盡可能講得不那麽學術,盡可能簡要明白一些。
大約在五年前(2013),我准備寫一篇關于康有爲戊戌時期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的論文。這項研究的起因是,既然台北的史語所研究員黃彰健院士已經證明康有爲《戊戌奏稿》作僞,既然中國人民大學孔祥吉教授等人已經發現《傑士上書彙錄》和許多康有爲的原始奏折(其中一部分是代他人所擬的),稱戊戌變法是“君主立憲式的改良主義運動”,失去了基本史料根據;那麽,戊戌變法的性質究竟是什麽?我想以可靠的檔案與文獻爲基礎,重新梳理一遍,得出新的結論來。爲此,我制定了一個計劃,申請了一個項目,准備用一年半的時間,寫一篇五到十萬字長篇論文。我得到了一筆小的資金支持。
黃彰健編:《康有爲戊戌真奏議》,“中研院”史語所,1974年3月出版。
孔祥吉編著:《康有爲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可是,研究進行沒多久,就卡殼了。我遇到了兩個難題。
一、1898年(戊戌)之前,康有爲完成了兩部重要的著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這兩部書的內容大約是:儒家的《六經》皆存世,即“今文經”,秦始皇並未焚盡;所謂“古文經”,皆是僞經,是西漢時領校“中秘書”(皇家藏書)的官員劉歆所僞造,目的是爲王莽的“新朝”服務。此即“新學僞經說”。中國的早期曆史“茫昧無稽”,堯、舜、文王等“文教之盛”,皆是孔子“托古”的創造,其目的是以民間“素王”身份來“改制立教”。不僅《春秋》爲孔子所創,《詩》《書》《禮》(《儀禮》)《樂》《易》,也都是孔子自我創造出來的。此即“孔子改制說”。
“新學僞經說”“孔子改制說”雖然非常大膽,也非常極端——按照康有爲的說法,古文經是劉歆僞造的,服務于“新朝”,今文經是孔子創造的,以能“改制”,中國的傳統經典皆是孔子和劉歆兩人僞造出來的,中國的早期曆史也是由他們兩人僞造出來的——但若從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來看,兩說皆是思考與探索的過程,而非爲最終的結論。用今天的說法,屬于“中期研究成果”。如果僅僅用“新學僞經說”“孔子改制說”去解釋當時的康有爲,那麽,他只是一個比廖平更極端的學者,不會那麽熱衷于政治活動:不會去自辦萬木草堂,不會去自辦各類報刊,如《強學報》《時務報》《知新報》,不會到廣西去講學,也沒有必要去辦強學會、聖學會、保國會之類的政治性組織,更沒有必要再三再四地給光緒帝上書。他當時的政治思想與政治目標究竟是什麽?
《新學僞經考》
《孔子改制考》
二、從康有爲在戊戌時期所上奏折來看,向光緒帝提出的政策設計大體上是西方式的,或用西方的曆史來說事;但從康有爲的著述來看,如前面提到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從康有爲的講學內容來看,如《長興學記》《桂學問答》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萬木草堂門生筆記,卻很少有西方思想與制度的內容,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的思想,相當多的部分屬經學。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是《實法公理全書》,談的是人的權利與民主制度,然其根據也不是西方思想與制度,而是西方數學中的“幾何公理”。1891年,康有爲與廣東大儒朱一新有一場論爭,康在信中說:
……緣學者不知西學,則愚暗而不達時變;稍知西學,則尊奉太過,而化爲西人。故仆以爲必有宋學義理之體,而講西學政藝之用,然後收其用也。故仆課門人,以身心義理爲先,待其將成學,然後許其讀西書也。然此爲當時也,非仆今學也。
“必有宋學義理之體,而講西學政藝之用”,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體西用”的說法,不僅早于孫家鼐(見其奏折,1897),更早于張之洞(《勸學篇》,1898)。
康有爲是戊戌變法的主要推動者,戊戌變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但這個推動者卻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與制度。他不懂任何一門外國語,也沒有去過外國,他能得到的外部資料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等機構、西方傳教士等人翻譯的西書,其中以聲光化電、機器制造爲主,關于西方思想、制度、經濟與社會學說的書籍相當有限。他可能也看過一些日本譯書,從目前的研究來看,若真讀書,數量也是相當有限的,且有自我的理解。
《長興學記》《桂學問答》《萬木草堂口說》
如果從更寬泛的角度來看,上面說的兩個問題,實際是一個問題:康有爲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學知識(“新學僞經”“孔子改制”)與有限的西學知識來推動中國的改革?如果再深入一步,又可提出這樣的問題:即康有爲作爲一名晚近的進士,其官位僅是工部候補主事,在京城地面中盡管大聲說話,也無人聽得見。他能進入政治舞台的中心,純屬偶然,不是由他來決定的。如果不能進入政治舞台的話,他的政治抱負又是什麽呢?
我由此被卡住了,研究進入了瓶頸。2015年7月,我到京都住了一個月,試圖開一點思路,結果毫無效果。曆史學是以史料爲基礎的,沒有史料的突破,思路又有什麽意義呢?曆史學是不那麽浪漫的。
恰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了梁啓超《變法通議》的進呈本(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便轉過頭來研究梁啓超的著述。正是在梁的著述中,我看到了光明——康有爲在戊戌時期的“大同三世說”。
《大同書》的寫作時間:康有爲與梁啓超的說法
康有爲無疑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最偉大的中國人之一,最重要的政治功績是1898年的戊戌變法,但他也給曆史學家留下不小的麻煩。他指責劉歆造假,贊揚孔子創造,他自己的文獻也有作僞之處。前面提到的《戊戌奏稿》,就是典型的一例。
康有爲的另一大作僞是在《大同書》寫作時期上“倒填日期”。1919年,康寫《大同書題辭》中稱:
吾年二十七,當光緒甲申,清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銀塘鄉之七桧園澹如樓,感國難,哀民生,著《大同書》……
《大同書》,長興書局,1919年版。
《大同書題辭》
“甲申”,1884年,是年有中法戰爭。康在《大同書》緒言中,也有相同的說法:“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對此,上海曆史所的湯志鈞教授已證明其僞,說明該書是康有爲在南洋槟榔嶼、印度大吉嶺時寫的,以後屢有修改。由于湯志鈞教授的這一貢獻,學術界大多不再將“大同”作爲康有爲戊戌時期的政治思想。
比較有意思的是康有爲頭號門生梁啓超的說法。1901年,梁啓超《清議報》第一百冊發表《南海康先生傳》,稱言: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發明改制之義……次則論三世之義。春秋之例,分十二公爲三世,有據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據亂升平,亦謂之小康,太平亦謂之大同,其義與《禮運》所傳相表裏焉。小康爲國別主義,大同爲世界主義;小康爲督制主義,大同爲平等主義。凡世界非經過小康之級,則不能進至大同,而既經過小康之級,又不可以不進至大同。孔子立小康義以治現在之世界,立大同義以治將來之世界,所謂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也。小康之義,門弟子皆受之。……大同之學,門弟子受之者蓋寡。……先生乃著《春秋三世義》《大同學說》等書,以發明孔子之真意。
按照這個說法,康有爲已著《春秋三世義》《大同學說》等書,並將之傳授給梁啓超等少數門生。1911年,梁啓超出版由其親筆抄寫的《南海康先生詩集》,在《大同書成題詞》後作了一個注:
啓超謹案:先生演《禮運》大同之義,始終其條理,折衷群聖,立爲教說,以拯濁世。二十年前,略授口說于門弟子。辛醜(1901)、壬寅間(1902)間避居印度,乃著爲成書。啓超屢乞付印,先生以爲方今爲國競之世,未許也。
這個說法與前說有了不同。“二十年前”爲1891年,梁啓超剛剛入門,只是“略授口說”;“著爲成書”的時間是1901-1902年。這也是湯志鈞教授推翻1884年說的主要證據。1921年,梁啓超出版《清代學術概論》,稱言:
……有爲以《春秋》“三世”之義說《禮運》,謂“升平世”爲“小康”,“太平世”爲“大同”。……有爲雖著此書,然秘不以示人,亦從不以此義教學者,謂今方爲“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于洪水猛獸。其弟子最初得讀此書者,惟陳千秋、梁啓超,讀則大樂,銳意欲宣傳其一部分。有爲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爲,後此萬木草堂學徒多言大同矣。而有爲始終謂當以小康之義救今世,對于政治問題、對于社會道德問題,皆以維持舊狀爲職志……啓超屢請印布其《大同書》,久不許,卒乃印諸《不忍雜志》中,僅三之一,雜志停版,竟不繼印。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1921年2月出版。
梁啓超又稱其在萬木草堂已經讀到了康“秘不示人”的著書。三個時間,三個說法,如果相信梁啓超的說法是真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一、康有爲已將“大同學說”的部分內容傳授給梁啓超;二、康在戊戌時已有著書,如梁先前所說的《春秋三世義》《大同學說》,但絕不是後來我們看到的《大同書》。
“大同三世說”的主要內容
湯志鈞教授證明了《大同書》是康有爲在槟榔嶼、大吉嶺時所寫的,但他同時認爲戊戌時康已經形成了“大同三世說”,主要證據是《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和《禮運注》。《禮運注》的成書年代也有點問題,現有的證據說明,該書也是康在大吉嶺時完成的。
湯志鈞:《康有爲與戊戌變法》,中華書局,1984年10月出版。
湯志鈞:《康有爲的大同思想與〈大同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由此再來檢視《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康有爲確實提到了“大同三世說”,但十分簡略。我這裏舉兩個例子。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爲稱:
堯、舜爲民主,爲太平世,爲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爲極者也……孔子撥亂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實,可知“六經”中之堯、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春秋》始于文王,終于堯、舜。蓋撥亂之治爲文王,太平之治爲堯、舜,孔子之聖意,改制之大義,《公羊》所傳微言之第一義也。
在萬木草堂講學時,康有爲稱“堯、舜如今之滇、黔土司頭人也”;又稱:“堯、舜皆孔子創議。”(黎祖健:《萬木草堂口說》)此處說“堯、舜爲民主,爲太平世”,即孔子創造出堯、舜,聖意在于“太平之治”;孔子又創造出文王,是爲“撥亂之治”,“以行君主之仁政”。以“孔子改制”講“大同三世”,這裏面的意思,若不加解釋,不易察覺。我仔細查看《孔子改制考》,與“大同三世說”相關的內容,僅僅找到六條。在《春秋董氏學》中,康有爲稱:
三世爲孔子非常大義,托之《春秋》以明之。所傳聞世爲據亂,所聞世托升平,所見世托太平。亂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備也。大義多屬小康,微言多屬太平。
康的這一說法,是對《公羊》派“三科九旨”的擴展,加上《禮運篇》中“小康”“大同”的內容。我仔細查看《春秋董氏學》,與“大同三世說”相關的內容,僅僅找到五條。《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講的是“孔子改制”的內容,“大同三世說”不是兩書的主題。若不是特別的挑選,這十一條內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放過去了,且僅看此十一條內容亦難窺全豹。
康有爲的“大同三世說”,是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一種普世性解說。按照康的說法,這一學說是由孔子創造,口傳其弟子,藏于儒家諸經典和相關史傳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傳》《禮記》(尤其是《禮運篇》《中庸篇》和《大學篇》)《易》《孟子》《論語》等文獻,以留待“後聖”之發現。泰西各國對此學說亦有所體會,亦有所施行。
從1900年夏天起,康有爲先後旅居南洋槟榔嶼、印度大吉嶺,至1903年春夏之交時才離開。在此兩年多中,他遍注群經——《〈禮運〉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大學〉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說”的著述。
《〈禮運〉注》《〈孟子〉微》《〈中庸〉注》
如果用最爲簡約的方式來說明“大同三世說”的基本概念,可謂:一、據亂世,多君世,尚無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禮運,削臣權;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運,削君權。“大同”雖是孔子創造出來的理想世界,但其時不可行,只能以“小康”來治世,只能待之于後人來實現。對此,康在《〈禮運〉注》中稱言:
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之道皆無徵而可傷。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澤,久積于心乃觸緒大發,而生哀也。孔子于民主之治,祖述堯、舜,君主之治,憲章文、武……其志雖在大同,而其事祇在小康也。
需要注意的是,康有爲在槟榔嶼、大吉嶺精心著述時,閱曆與見識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1898年9月他離開北京南下,在上海由英國軍艦接往香港,然後去了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新加坡。從思想史的角度來分析,戊戌前後康的“大同三世說”思想可以作爲一個整體來看待;但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若不加以嚴格的區別,會有致命的缺陷——我的目的原本是要證明戊戌變法的性質,由此來證明戊戌時康有爲的政治思想;若以康在槟榔嶼、大吉嶺時期(即戊戌之後)的著述,來說明戊戌時康有爲思想,是不可能精確、不可能具有說服力的。也就是說,除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中十一條內容外,我找不到更多的1898年9月之前的材料,來說明戊戌時康的“大同三世說”。
我就在這個關鍵點上被卡住了。
康有爲在芝加哥
康有爲及家人朋友在蘇格蘭阿伯丁女子學校的合影
由梁渡康
前面提到,梁啓超在1901、1911、1921年三次著述中談到康有爲的“大同學說”,說法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康在萬木草堂向梁傳授過“大同學”。從梁入學時間來看,應是1891-1896年,即光緒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梁爲十八到二十三周歲。康的思想有沒有影響到梁呢?
前面提到,我因發現梁啓超《變法通議》進呈本,開始集中閱讀梁啓超的著述,其中大部分是再次閱讀。由于閱讀時的立場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從梁的許多著述中都看到了“大同三世說”,尤其是《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湖南時務學堂初集》。
梁啓超
1896年11月,梁啓超在《時務報》上發表《古議院考》,說明中國古代就有議院的思想,甚至有相當于議院的制度,結果受到了嚴複來信的嚴厲批評。梁給嚴回了一信,用“大同三世說”的思想來自我辯護,並提出了反批評。年輕的梁啓超(二十四周歲),意氣風發,僅僅回信尚覺不滿足,又在1897年10月在《時務報》第四十一冊上發表《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將與嚴複的討論公開化。該文起首便直接、明確地闡述康有爲的“大同三世說”:
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爲政之世,二曰一君爲政之世,三曰民爲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這是“大同三世說”在報刊上第一次完整的表述,梁啓超將之分爲“三世六別”。在批判了多君世的罪惡後,梁稱從多君世轉爲一君世是孔子的貢獻:
孔子作《春秋》,將以救民也,故立爲“大一統”“譏世卿”二義。此二者,所以變多君而爲一君也。變多君而爲一君,謂之“小康”。
梁啓超繼續指出,“三世”是各國必經之路,中西之間並無區別,並不以其是否有議院的“胚胎”而致道路之不同(即嚴複來信中的觀點):
……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間必經一君之政,乃始克達。所異者,西人則多君之運長,一君之運短;中國則多君之運短,一君之運長(此專就三千年內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歸民政,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此猶佛法之有頓有漸,而同一法門。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來殺機寡于西國者,則小康之功德無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一君之政即爲“小康”,中國的前途與“西人”一樣,是“同歸民政”(民主)。在該文的最後,梁啓超談到了世界的前途:
問今日之美國、法國,可爲太平矣乎,曰惡,惡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國言之,則可謂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國而言,則可謂爲一君之世;然合全局而言,則仍爲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國,各私其種,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財。度支之額,半充養兵,舉國之民,悉隸行伍。耽耽相視,龁龁相仇,龍蛇起陸,殺機方長,螳雀互尋,冤親誰問?嗚呼!五洲萬國,直一大酋長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見群龍無首,吉。”其殆爲千百年以後之天下言之哉?
梁啓超對僅僅只有美國、法國實行總統制(民政世)是不滿足的,若從世界的眼光來看,仍是“多君之世”,“直一大酋長之世界焉耳”。他那指責現實的筆法——“各私其國”“耽耽相視”——暗地裏卻描繪著那個無總統、無國家、無戰爭、無私産的“天下爲公”“不獨親其親”的未來畫面,真正的“大同”是世界性、全球性的。“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一句,典出于《春秋公羊傳》最後一句:“……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意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康也很愛引用,見後)梁暗暗自诩他們這個以康爲導師的小群體是能真正解讀《春秋》微言中所含“大同之意”的“後聖”。“見群龍無首”一句,典出于《易·乾卦》:“用九,見群龍無首,吉。”梁將之解釋爲“大同三世說”中最高階段——民政世(太平)之“無總統之世。”
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梁啓超去了長沙,擔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康門弟子韓文舉、葉湘南、歐榘甲擔任分教習。
時務學堂教習:左起葉湘南、譚嗣同、王史、歐榘甲、熊希齡、韓文舉、唐才常、李維格。
康門弟子掌握的湖南時務學堂,所授內容不是一般的“時務”,而是“康學”。梁啓超爲此制定了《學約》,並寫了指導性的《讀〈孟子〉界說》《讀〈春秋〉界說》。時務學堂學生每天要讀規定書目,主要是《孟子》和《春秋公羊傳》,若有問題提出,由教習予以答複,若有心得寫下來,即“劄記”,由教習加以批語。時務學堂內部材料雖不能全見,但在1898年春,已將梁啓超的《學約》、《界說》、學生與教習的問答(部分)、學生的劄記與教習的批語(部分)合刊了一部書,共四卷,名爲《湖南時務學堂初集》,今存世不多。當我讀到《湖南時務學堂初集》,非常興奮。梁啓超在時務學堂中大力宣傳“新學僞經說”“孔子改制說”和“大同三世說”。
《湖南時務學堂初集》中涉及到“大同三世說”的地方非常多,我這裏因時間關系只能舉一個例子。湖南時務學堂學生李炳寰以《孟子》中“仁義”一義作劄記,推及世界“大同”,梁啓超作批語稱:
說得極好。利梁一國而天下不收其利六語,非通乎《孟子》者不能通。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國,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輩今日立志,當兩義並舉。目前則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國,他日則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極也。救全球而必先從中國起點者,義也。“仁者人也,義者我也。”大同近于仁,小康近于義。然言大同者固不能不言義,言小康者固不能不言仁。韓先生因汝問大同條理,而以“本諸身,征諸庶民”答者,正明以義輔仁之旨。由身以推諸民,由中國以推諸地球,一也。故今日亦先從強中國下手而已。至所謂大同之道與大同之法,五百年以內,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窮思極慮,淵淵入微以思之,其條理極詳,至纖至悉,大約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鄙人等侍先生數年,尚未能悉聞其說,非故秘之不告也。先生以爲學者之于學也,必須窮思力索,觸類旁通,自修自證,然後其所得始真。故事事皆略發其端,而令鄙人等熟思以對也。今鄙人與諸君言,亦如是而已,將以發心靈、濬腦氣,使事事皆從心得而來耳。不然,亦何必吞吐其辭乎?諸君幸勿誤會此意。若欲有所憑藉,以爲思索之基,先讀西人富國學之書及《佐治刍言》等,以略增見地,再將《禮運》“大道之行也”一節熟讀精思,一字不放過,亦可略得其概。至所雲起點之處,西人之息兵會等,亦其一端也。(《湖南時務學堂初集》,第二冊,《劄記》卷一)
師生所言的內容,皆是“大同三世說”。梁啓超仍是從“仁、義”出發,談到了大同、小康。他沒有直接回答問題,只是宣稱康有爲對“救全球”的大同道、法,已經窮思極慮,條理極詳,西方各國目前對康有爲所思之條理,已實行者一二,未實行者八九,要求李炳寰通過自修來自證。“富國學之書”,大約是指《富國策》,與《佐治刍言》皆是西方政治經濟學著作。梁讓李炳寰以此爲基礎,再“熟讀精思”《禮運篇》中“大同”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一段話,正是“大同三世說”的核心內容。李炳寰若“一字不放過”的“窮思力索,觸類旁通”,所得出的結論只能是——西方學術爲“大同三世說”提供了佐證——這正是梁啓超希望得到的教學效果。
由梁渡康,恰好合璧。
梁啓超
康門其它弟子的言說和梁鼎芬的評論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還談到:“其弟子最初得讀此書者,惟陳千秋、梁啓超,讀則大樂,銳意欲宣傳其一部分。有爲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爲,後此萬木草堂學徒多言大同矣。”除了已經去世的陳千秋和梁啓超外,康有爲的其它弟子對“大同三世說”也有所了解,“多言大同”。
康門弟子的著述,大多尚未整理編集,但康門弟子在《知新報》和《時務報》上發表了許多政論文章。爲了驗證梁啓超的說法,我將《知新報》《時務報》重讀一遍:康門弟子九人(不包括梁)在《知新報》發表了五十八篇政論文,康門弟子三人(不包括梁)又在《時務報》發表了九篇政論文;有些是類似梁啓超《變法通議》那樣的大文章,多期連載。也就在這些文章中,我又看到了忽隱忽現的“大同三世說”的痕迹。
《時務報》
我這裏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康有爲的大弟子徐勤,其在康門的地位,僅次于陳千秋、梁啓超。他在《知新報》上發表《地球大勢公論》,稱言:
……故天下之勢,始于散而終于合,始于塞而終于通,始于爭而終于讓,始于愚而終于智,始于異而終于同。古今遠矣,中外廣矣,要而論之,其變有三:
洪水以前,鳥獸相迫,昆侖地頂,人類自出。黃帝之子孫,散居于中土;亞當之種族,漫衍于歐東。創文字,作衣冠,立君臣,重世爵。由大鳥大獸之世,而變爲土司之世。其變一。
周秦之世,地運頓變,動力大作。爭奪相殺,而民賊之徒徧于時;兼弱攻昧,而強有力者尊于上。贏政無道,驅黔首以爲囚;羅馬暴興,合歐西而一統。由土司之世,而變爲君主之世。其變二。
百余年間,智學競開,萬國雜沓。盛華頓(華盛頓)出,而民主之義定;拿破侖興,而君主之運衰;巴力門立,而小民之權重。由君主之世,而變爲民主之世。其變三。
故結地球之舊俗者,亞洲也;開地球之新化者,歐洲也;成地球之美法者,美洲也。(《地球大勢公論·總序》,《知新報》第二冊)
“大同三世說”反映的是世界的變局,徐勤的著眼點也是世界的。他沒有用“據亂”“升平”“大同”之詞彙,而代以“酋長”“君主”“民主”之三變。“洪水”“地頂”“地運”“動力”也是康有爲講學時使用過的概念。
其二是康有爲的弟子劉桢麟。他在康門中的地位不高,但在《知新報》的金主、澳門賭商何連旺家中授館課其子。康門弟子中,他在《知新報》發表的文章最多。其文《地運趨于亞東說》連載于《知新報》,第七、八冊,多處涉及到“大同三世說”。在該文結尾,他呼喚著“大同世界”的到來:
嗚呼!嘗聞之南海先生之言矣:世界之公理,由力而趨于智,由智而趨于仁。上古千年,力之世也;中古千年,智之世也;後古千年,仁之世也。力之世,治據亂;智之世,治太平;仁之世,治大同。今其智之萌芽乎,夫大地萬國,寐覺已開,中土蚩氓,蒙翳漸辟,遠識之士,競馳新學之途,杞憂之儒,群倡開化之術。吸籲所接,或有動于當途;阖辟所關,即不朽之巨業。匪一隅之偏局,實萬國之同風。乘朕兆已萌之後,爲有開必先之舉。將豈徒一國、一洲蒙靡穹之利賴欤,其將以是期之百千年後,凡我圓顱方趾之倫——黃人、白人、紅人、黑人、棕色人、半黃半白淡黑人、不可思議之諸色人——鹹被此靡穹之利賴焉,而爲智、爲仁之世界,均于是起點也,而又何東、西之有耶,而又何趨、變之有耶?
劉桢麟清楚說明了前、中、後三世,分別崇尚力量、智慧和仁愛。他將“小康”誤說爲“太平”。他認爲,當今“智”已“萌芽”,其後的發展趨勢將不可抵擋;當此“朕兆已萌”,“百千年後”,人類(即“圓顱方趾之倫”)將不分國家、不分洲別、不分膚色,共同經由“爲智”而進入“爲仁”的世界。到了那個時候,東、西可不必分,趨、變可不必論。這是康有爲及其黨人所認定的“世界之公理”“不朽之巨業”。
《知新報》
康門其它弟子,關于“大同三世說”的言論還有許多;但若從總體來看,所言“大同三世說”只占其全部著述的較小篇幅,其深度遠遠比不上梁啓超。既然公開刊刻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中都有“大同三世說”的內容,康有爲也沒有必要在萬木草堂保密不說,只是所說的內容與深度,要遠遠少于對陳千秋、梁啓超之傳授。
康有爲的同鄉、昔日好友梁鼎芬,時任張之洞的大幕僚,戊戌變法期間與康決裂。在康逃亡日本後,他以“中國士民公啓”之名,作《康有爲事實》,由張之洞交給來訪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以能讓日本驅逐康。其第三條稱:
康有爲之教,尤有邪淫奇謬、不可思議者,其宗旨以“大同”二字爲主(其徒所設之局、所立之學,皆以“大同”爲名),創爲化三界之說:一化各國之界。謂世間並無君臣之義,此國人民與彼國人民一樣,古人所謂忠臣、義士,皆是多事。一化貧富之界。富人之財皆當貧人公用,此乃襲外國均貧富黨之謬說、小說戲劇中強盜打富濟貧之鄙語。一化男女之界。謂世界不必立夫婦之名,室家男婦皆可通用。將來康教大行後,擬將天下婦女聚在各處公所,任人前往淫亂。生有子女,即籌公款養之,長成以後,更不知父子兄弟爲何事。數十年後,五倫全然廢絕,是之謂“大同”(少年無行子弟,喜從康教者,大率皆爲此爲秘密法所誤也)。其昏狂黩亂,至于此極,乃白蓮教所不忍言,哥老會所不屑爲。總之,化三界之說,一則誨叛,一則誨盜,一則誨淫。以此爲教,不特爲神人所怒,且將爲魔鬼所笑矣。或疑此條所談太無人理,康教何至于此?不知此乃康學秘傳,語語有據,試問之康徒便知。若有一言虛誣,天地鬼神,實照鑒之。(見《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一卷,第一冊,有校正)
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2014年3月初版。
梁鼎芬又從何處得知康有爲此類“秘傳”的“大同”思想?他賭咒發誓稱“語語有據”,很可能得自于“康徒”。就“化三界”而言,對照此期梁啓超及康門弟子在《時務報》《知新報》和時務學堂中的言說,“一化各國之界”可以成立;對照康有爲先前和後來所著的《實法公理全書》《〈禮運〉注》《大同書》及梁啓超在《清議報》上發表的《南海康先生傳》,“一化貧富之界”可以成立;對照康後來所著的《〈禮運〉注》《大同書》,“一化男女之界”也有部分內容可以成立,只是稱康門弟子“爲秘密法所誤”,當屬梁鼎芬並無根據的誣詞。
從康有爲在《孔子改制考》等書中的簡說,到梁啓超的多種著述,再到康門其他弟子的言說以及康政敵的評論——除了梁鼎芬的評論外,所有的材料都是1898年6月(即“百日維新”起始時)之前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康在戊戌時確有“大同三世說”的思想。
當我將相關的論文寫完,時間已過了五年。我才完成了證明的過程。
創制立教
對康有爲來說,從“新學僞經說”到“孔子改制說”,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其最終的結論,應當是“大同三世說”。從“大同三世說”再到《大同書》,是康有爲思想發展的又一個階段。兩者之間的聯接性是比較明顯的,而兩者之間的最大差別在于:康不再宣稱該學說由孔子原創,藏于經、傳、史等典籍之中,是他通過“微言”而發現的“大義”;而是自由奔放地直接說明他對未來社會的設計,那種曆史命定論的色彩也有所淡化。
錢定安校本《大同書》,1935年出版。
“新學僞經說”“孔子改制說”“大同三世說”皆是學理,不太可能直接運用于政治。康有爲雖然有參與高層政治的企圖,但他唯一的辦法是上書。通過上書而獲得皇帝青睐的機率是很低的;而“新學僞經說”“孔子改制說”“大同三世說”這類學理在高層政治是不可能通過的,尤其是“大同三世說”,其目標是改皇帝爲民主,最終要消亡國家,實現世界大同。清朝的皇帝又怎麽可能對此認同呢?
康有爲創造這些學理,目的是“創制立教”。在萬木草堂,他對其門徒直白地說:
孔子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可得見乎?書者,六經也;言者,口說也;意者,聖人所未著之經,未傳諸口說者也。然則,聖人之意一層,猶待今日學者推補之。(黎祖健:《萬木草堂口說》)
康多次說明,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和《易》。《春秋》記事,其主旨不在事而在于義,其義理由孔子口說而由弟子相傳,《公羊》是最主要的一支;但《春秋》中的許多義理,《公羊》未能明,甚至董仲舒、何休都未有解。至于《易》,全是義理。此即“猶待今日學者推補之”。康此處所稱“今日學者”,即是康本人。這種不見于經、傳,甚至不見于董說何注的孔子思想,可以說是康的自我理解、自我體會,也可以說是康的自我發揮。康可以將其思想附托孔子的名下,“托孔改制”。他又對其門徒說:
地球數千年來,凡二大變,一爲春秋時,一爲今時,皆人才蔚起,創制立教。(張伯桢:《康南海先生講學記》)
此處的“春秋時”主要是指孔子,而“今時”又可見康的自期,他要仿效孔子“創制立教”。康常引用《中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公羊傳》“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頗有自許之意(見《〈中庸〉注》《〈孟子〉微》)。康還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稱: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煥炳瑩晶。予小子夢執禮器而西行,乃睹此廣樂鈞天,複見宗廟百官之美富……
他這些話講得很明白,他是受命于天的。
當時的文士章太炎,對康有爲創教的設想有所揭示。1897年,他寫信給老師譚獻的信中稱:“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爲教皇,又目爲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他在《自訂年譜》稱:1897年“春時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而馮自由後來記錄章太炎對梁鼎芬的談話稱:“只聞康欲作教主,未聞欲作皇帝。實則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異;惟欲作教主,則未免想入非非。”(《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而梁鼎芬在前面談到的《康有爲事實》中又稱:
康有爲羨慕泰西羅馬教王之尊貴,意欲自爲教王,因創立一教,謂合孔教、佛教、耶蘇、希臘教四教而爲一,自命爲創教之聖人,其徒皆以聖人稱之。其徒黨有能推衍其說者,則許爲通天人之故,聞者齒冷。康所著書內有《孔子爲改制之王考》一卷(上海有刻本),稱孔子爲教王,諷其徒謂康學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
梁鼎芬的說法也是相當肯定。即便從康有爲這方面的材料來看,也是相當清楚的。他在《孔子改制考》一書起首便稱: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爲神明,爲聖王,爲萬世作師,爲民作保,爲大地教主。生于亂世,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界之義,而注意于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
其中“黑帝乃降精”,見《春秋演孔圖》,屬緯書,稱孔子的母親在夢中與黑帝相交而生孔子。康引緯書言“黑帝降精”,否認孔子的人間生父,有意模仿基督教的“聖誕說”。康辦《強學報》,用的是孔子紀年;又命梁啓超在《時務報》上也用孔子紀年,梁因阻力太大而未能辦到。這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爲上奏光緒帝,要求建立孔教會。
光緒、康有爲、梁啓超合成圖。
根據《孔子改制考》,孔子“創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兩項:一是創制經典,二是傳教于門徒。《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再加上“大同三世說”,“小康”“大同”之制,經典的創制已初步完成。康主持的萬木草堂,已有相當的規模,其門徒張伯桢稱:“同學凡百余人。”(《康南海先生講學記》)康又到廣西去講學,梁啓超等人去湖南主辦時務學堂,亦可視之爲“傳教”。
根據《孔子改制考》,從春秋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即孔子創制立教至改制成功,經曆了數百年的時間,並規範了“百世之後”的政教禮儀。基督以十二使徒傳教于天下,孔門有十哲七十二賢人,都不是一代人的事業。康此時若真心有意于“創制立教”,也不會太注重于當下。大約在1897年春,梁啓超在上海寫信給康有爲:
……尚有一法于此,我輩以教爲主,國之存亡,于教無與。或一切不問,專以講學、授徒爲事。俟吾黨俱有成就之後,乃始出而傳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之志,但一切已辦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學算、讀史,又讀內典(讀小乘經得舊教甚多,又讀律、論),所見似視疇昔有進,歸依佛法,甚至竊見吾教太平大同之學,皆婆羅門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所憑依,奈何。(《覺迷要錄》,錄四)
梁此中談到的“教”,是超越國家的,即“國之存亡,于教無與”,說的就是“大同三世說”。梁讓康“專以講學、授徒”,當萬木草堂學生學成後,出而傳“大同三世說”之教。梁對其掌握的“教”義仍不滿足,想通過“入山數年”以補足。梁又通過數學、曆史和佛教經典的學習,自覺“歸依佛法”,甚至對“吾教太平大同之學”一度産生懷疑,覺得“所學失所憑依”。梁的這一封信,是戊戌政變後從康有爲家中抄出來的。內容大體相近的梁信,還有一封。
康有爲“創制立教”,是想當教主;當然,如果有可能,也想當帝師。今天的人們看到了曆史的結局,他沒有當成教主,也沒有當成帝師,而是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期當了光緒帝的重要謀士。由此再來看看他自己的說法。1898年冬,康在日本寫《我史》,這是他第一部人生總結,也正處在人生的低谷期。康稱,百日維新的關鍵時刻,其弟康廣仁勸其“不如歸去”,回鄉授學,用康廣仁的話來言其志:
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中國,殺身無益。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爲〈我史〉鑒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5月初版。
根據梁啓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的批語:“目前則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國,他日則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康的志向不僅僅是“救中國”,而在于“地球”。康又稱,戊戌政變前他從北京到天津、煙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難不死,必有其因:
……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無所濟。而曲線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來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絕耶?“聚散成毀,皆客感客形”,深閱死生,順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此四十年乎,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並出,新理大發之日,吾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爲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吾皆遭逢其會,而自爲之。學道愛人,足爲一世,生本無涯,道終未濟……
保救大清皇帝會加拿大成員,康有爲在其中。
我以前每讀至此,總覺得康在造作;然讀到梁啓超等人關于“大同三世說”的諸多著述,才隱約地感到,康也未必矯情,或真以爲自己天降大任、使命在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