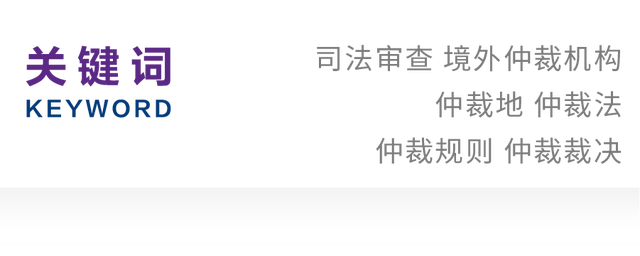王生長 國際商事仲裁理事會(ICCA)的理事、顧問,法學博士
內容摘要:就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而言,“龍利得案”解決了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的仲裁協議效力問題,“大成産業案”明確了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不涉及仲裁市場開放問題,“布蘭特伍德案”按照仲裁地標准爲確定此類仲裁裁決的籍屬和執行依據提供了指引。在中國仲裁法修訂時,應當對標國際先進規則,確立處理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的一系列法律規則,營造法治化、可預期的仲裁環境,爲使中國成爲國際上受歡迎的仲裁地而不斷努力。
關于境外仲裁機構能否在中國內地仲裁問題,多年來意見紛纭。問題的主要結症是對我國仲裁法第16條如何理解適用,即在仲裁法第十六條項下作爲有效仲裁協議必備要件之一的“選定的仲裁委員會”是否可以從寬解釋爲包括了境內外的仲裁機構;進而言之,如果境外仲裁機構可以視作仲裁法第16條下“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在內地管理仲裁程序,那麽它們在內地作出的仲裁裁決是什麽性質的裁決,在中國法院依據什麽法律條文申請執行。
2013年以來,通過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活動,圍繞這個問題的迷局逐步明朗,司法機關的實踐漸趨一致,境外仲裁機構在內地仲裁已經可以破冰起航,即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鑒于此,本文簡要回顧在過去幾年中有標志性意義的三個司法案例,並就在仲裁法修訂時如何妥善處理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的一系列法律規則,營造法治化、可預期的仲裁環境提出意見建議。
一、2013年3月的“龍利得案”
(一)案情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申請人安徽省龍利得包裝印刷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BP Agnati S.R.L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案的請示的複函》顯示:
安徽省龍利得包裝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龍利得公司”)與BP Agnati S.R.L及江蘇蘇美達國際技術貿易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28日簽署了一份《銷售合同》。該合同第10.1款約定任何因本合同引起的或與其有關的爭議應被提交國際商會仲裁院,並根據國際商會仲裁院規則由按照該等規則所指定的一位或多位仲裁員予以最終仲裁,“管轄地”應爲中國上海,仲裁應以英語進行。此後,因履行合同發生爭議。龍利得公司遂向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合肥中院”)確認前述仲裁條款無效。
龍利得公司認爲,上述仲裁條款因違反中國仲裁法的相關法律規定而無效,理由是:首先,國際商會仲裁院不是中國仲裁法項下的仲裁機構,約定將爭議提交給其仲裁不構成有效仲裁條款;其次,國際商會仲裁院在中國進行仲裁違背了中國的公共利益,存在侵犯我國司法主權之嫌;其三,即便國際商會仲裁院在中國境內作出裁決,該裁決也應屬于仲裁法規定的“內國裁決”,不能依據聯合國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受到承認與執行。
合肥中院審查後認爲:首先,該仲裁協議在約定仲裁機構爲國際商會仲裁院的同時,又明確約定仲裁管轄地爲中國上海,但關于國際商會仲裁院等國外仲裁機構能否在中國境內從事仲裁活動,仲裁法並未明確規定。盡管如此,當事人既然選擇在中國內地進行仲裁,該仲裁從法律意義上說應當屬于國內仲裁,並非紐約公約規定的“非內國裁決”。其次,根據仲裁法第10條的規定,仲裁在中國是需要經過行政機關特許才能提供的專業服務,而中國政府也未向國外開放中國的仲裁市場,故外國仲裁機構依法不能在中國境內進行仲裁。因此,合肥中院認爲國際商會仲裁院並非符合仲裁法規定的仲裁機構,約定將爭議提交給其仲裁的仲裁協議不是有效的仲裁條款。
合肥中院將前述意見上報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後,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過審查,內部形成了兩種不同意見。多數意見認爲,涉案《銷售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涉案仲裁條款中具有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和約定的仲裁事項,並選定了明確具體的仲裁機構,系有效的仲裁條款,合肥中院以國際商會仲裁院等國外仲裁機構不能在我國境內從事仲裁活動爲由確認涉案仲裁條款無效是錯誤的,缺乏法律依據;少數意見贊同合肥中院的意見,認爲仲裁在中國是需要經過行政機關特許才能提供的專業服務,中國政府並未向國外開放我國的仲裁市場,故國外仲裁機構依法不能在我國境內進行仲裁,因此涉案《銷售合同》約定的由國際商會仲裁院進行仲裁的條款因違反仲裁法的規定,應屬無效條款。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答複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在給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複函中答複如下:
“本案爲確認涉外仲裁協議效力案件。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因合同而發生的糾紛由國際商會仲裁院進行仲裁,同時還約定‘管轄地應爲中國上海’(PLACE OF JURISDICTION SHALL BE SHANGHAI, CHINA)。從仲裁協議的上下文看,對其中‘管轄地應爲中國上海’的表述應當理解爲仲裁地在上海。本案中,當事人沒有約定確認仲裁協議適用的法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幹問題的解釋》第16條的規定,應適用仲裁地法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來確認仲裁協議的效力。
仲裁法第16條規定,仲裁協議應當具有下列內容:(一)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項;(三)選定的仲裁委員會。涉案仲裁協議有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約定了仲裁事項,並選定了明確具體的仲裁機構,應認定有效。同意你院關于仲裁協議有效的多數意見。”
(三)簡評
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龍利得案”的答複中首次明確表示國際商會仲裁院是當事人選定的“明確具體的仲裁機構”,符合仲裁法第16條關于“選定的仲裁委員會”的規定,滿足了中國法關于仲裁協議須選擇機構仲裁的要求。這是一個有突破意義的標志性案例,它終結了此前一直存在的關于境外仲裁機構是否可被視作仲裁法第16條“選定的仲裁委員會”的爭論,在司法實踐中確認了當事人約定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的仲裁協議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在此案中的答複也開闊了人們對于仲裁法第16條的審視角度。仲裁法第16條的主旨是希望當事人約定仲裁時選擇進行機構仲裁而非臨時仲裁,其中“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固然可以在狹義上理解爲國內重新組建的仲裁委員會和已經存在的涉外仲裁委員會,但該條並沒有明確排斥境外的仲裁委員會。最高法在答複中將仲裁法第16條“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從寬解釋爲“明確具體的仲裁機構”,是對仲裁法立法本意的補充闡釋,是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對法律規定的不明確之處拾遺補缺。由于當事人的仲裁意願明確真實,法院對法律規定從寬解釋以確認仲裁協議效力,也體現了法院支持仲裁的司法政策。
由于請示範圍所限,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的答複中並不涉及國際商會仲裁院在上海仲裁後其作出的仲裁裁決屬于什麽性質的裁決(是外國裁決、非國內裁決還是中國裁決),以及在內地是否有執行的法律依據問題。這些問題,也只能留待後來在合適的個案中解決。
二、2020年6月的“大成産業案”
(一)案情
2012年8月7日,大成産業氣體株式會社(以下簡稱“大成株式會社”)和普萊克斯(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普萊克斯公司”)簽署的《承購協議》第14.2條約定發生爭議由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在上海仲裁。後大成株式會社、普萊克斯公司以及大成(廣州)氣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成廣州公司”)簽署了《補充協議(一)》,大成株式會社將其在《承購協議》項下的權利義務轉讓給大成廣州公司。
2016年3月,大成株式會社、大成廣州公司作爲共同申請人向SIAC提出仲裁申請。在仲裁過程中,針對仲裁庭多數成員作出的仲裁地爲新加坡的管轄權決定,當事人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和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訴庭興訟,案件名稱簡稱“BNA v BNB”。2017年8月30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BNA v BNB AND ANOTHER [2019] SGCA 84”判決,認爲提交至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在上海仲裁應理解爲仲裁地爲新加坡,新加坡法律爲仲裁協議適用法。2019年11月14日,新加坡最高院上訴庭作出“BNA v BNB & another [2019] SGHC 142”判決,認爲“在上海進行仲裁”一詞的自然含義就是將上海作爲仲裁地。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只約定了唯一的地理位置,這應當解釋爲當事人對仲裁地作出了選擇。因此“在上海仲裁”的文字含義即是指將上海約定爲仲裁地。當事人對仲裁協議適用法律的默示選擇是中國法律。但是上訴庭僅在上述的法律觀點上推翻一審法院的裁決,而並未就仲裁庭是否擁有管轄權發表任何結論性意見,這意味著判定本案仲裁協議效力的管轄權落到仲裁地上海的中國法院之手。
(二)上海一中院的裁定意見
2020年1月20日,兩名申請人向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確認仲裁協議效力之訴。2020年6月29日,上海一中院作出《民事裁定書》,在確認仲裁地爲上海、仲裁協議適用法爲中國法的基礎上,對本案仲裁協議效力作出了如下分析:
首先,外國仲裁機構在中國仲裁主要指外國仲裁機構適用其仲裁規則將仲裁地點設在我國的情況,由此進行的仲裁是機構仲裁,而非我國在紐約公約中聲明予以保留的臨時仲裁;其次,在“(2013)民四他字第13號”複函中,最高人民法院已經確認了涉外合同中約定發生爭議由外國仲裁機構在國內仲裁如其約定符合仲裁法第16條的規定則爲有效;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並未禁止外國仲裁機構管理仲裁地點在國內的仲裁;第四,對于具體案件,司法不能以立法不明爲由拒絕裁判,盡管仲裁法在立法之初並不全面且與國際商事仲裁存在脫節,但立法與司法應系相輔相成關系,被申請人有關仲裁法在立法層面沒有解決外國仲裁機構能否在中國進行仲裁的問題,並不能改變司法層面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釋的有效意思。
綜上所述,上海一中院認爲應確認申請人大成産業氣體株式會社、申請人大成(廣州)氣體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普萊克斯(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之間依據《液態及氣態産品承購協議》第14.2條、《液態及氣態産品承購協議補充協議(一)》形成的仲裁協議有效,當事人爲此發生爭議,應提交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根據其仲裁規則在仲裁地中國上海仲裁。”
(三)簡評
中國加入紐約公約所作的“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並不包含對臨時仲裁的保留,因此上海一中院的分析有其不准確之處。但除此之外,上海一中院在本裁定書中的分析值得稱道,它體現了司法支持仲裁的政策導向,堅持了裁判規則前後承繼有序、裁判標准統一的司法政策,並且具有順應仲裁發展趨勢的國際視野。對于外國仲裁機構能否管理仲裁地點在我國國內的仲裁這一問題,上海一中院觀點鮮明,指出這個問題不涉及我國仲裁市場是否開放的問題,法律上無明文禁止規定,最高法在“龍利得案”的司法意見必須堅持,順應國際潮流的做法應當允許。
上海一中院的裁定很好地呼應了“龍利得案”和新加坡最高法院在BNA v BNB案中的判決,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國法院支持當事人選擇境外仲裁機構來華仲裁的積極態度。但由于本案的司法審查範圍僅限于審查仲裁協議的效力,不涉及對仲裁裁決的司法審查,因此對于這類仲裁裁決的性質和執行依據問題,本案如同“龍利得案”一樣,無法給出答案。
三、2020年8月的“布蘭特伍德案”
(一)案情
2010年4月13日,布蘭特伍德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布蘭特伍德公司”)與廣東閥安龍機械成套設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閥安龍公司”)、廣州市正啓貿易有限公司簽訂購買鏈板式刮泥機的合同,其中第16條“仲裁”約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與本合同有關的任何爭議,雙方應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不能解決,應提交國際商會仲裁委員會根據國際慣例在項目所在地進行仲裁。”根據合同約定,項目所在地爲中國廣州。
2011年5月9日,布蘭特伍德公司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州中院”)申請確認案涉合同中的仲裁協議無效。廣州中院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2011)穗中法仲異字第11號《民事裁定書》,確認案涉合同中約定的仲裁條款有效。2012年8月31日,布蘭特伍德公司向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提起仲裁。2014年3月17日,國際商會仲裁院獨任仲裁員作出案件編號18929/CYK《終極裁決》。
2015年4月13日,布蘭特伍德公司向廣州中院申請承認並執行該裁決。布蘭特伍德公司認爲,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意見,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可以在中國境內進行仲裁活動,約定由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中國境內仲裁解決爭議的仲裁條款合法有效。根據中國法院的司法實踐,應當認定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作出的《終極裁決》是法國仲裁裁決,應按照紐約公約規定得到中國的承認與執行。如果法院認爲案涉《終極裁決》是由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我國香港的分支機構作出的,該裁決系香港仲裁裁決,也應根據《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的規定認可並執行該裁決。
閥安龍公司則認爲案涉《終極裁決》不應得到承認與執行。首先,根據中國加入紐約公約時作出的互惠保留聲明,由于案涉《終極裁決》系在中國廣州作出,不屬于“在另一締約國領土內作出的仲裁裁決”,故應當排除適用紐約公約而被拒絕承認和執行;其次,根據中國加入紐約公約時所作的保留聲明,中國並不允許外國仲裁機構在中國境內進行仲裁活動,而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並非中國仲裁法規定的仲裁機構,其在中國作出裁決,當事人無法申請由仲裁機構所在地的中國法院對其進行撤銷審查,不僅剝奪了當事人的合法程序權益,也侵害了中國的司法主權;其三,盡管紐約公約在“領域標准”之外還規定了“非內國裁決(或非本國裁決)標准”,但目前中國立法對“非內國裁決(或非本國裁決)標准”沒有明確規定,沒有采取以仲裁程序准據法來確定仲裁裁決國籍的模式,故也不應以“非內國裁決(或非本國裁決)標准”適用紐約公約;最後,仲裁條款的效力與對裁決的承認和執行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問題,適用不同的法律規範。綜上,盡管布蘭特伍德公司主張案涉仲裁條款有效,不能當然得出案涉《終極裁決》應被承認和執行的結論。
(二)廣州中院的裁定意見
就布蘭特伍德公司的申請,廣州中院作出如下裁定意見:
首先,案涉合同的項目地點在中國廣州市。廣州中院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的(2011)穗中法仲異字第11號《民事裁定書》已確認上述仲裁條款有效。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根據布蘭特伍德公司的申請,由獨任仲裁員組成的仲裁庭在仲裁地中國廣州作出案涉仲裁裁決。根據該事實,案涉仲裁裁決系外國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的仲裁裁決,可以視爲中國涉外仲裁裁決。案涉仲裁裁決的被申請人不履行仲裁裁決的,布蘭特伍德公司可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73條的規定向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財産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
其次,布蘭特伍德公司在本案中主張依據紐約公約或《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的規定申請承認及執行該仲裁裁決,其提起本案申請的法律依據顯屬錯誤,經多次釋明後又拒不糾正,其應自行承擔由此導致的相應法律後果。鑒此,本案不應作爲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依法應予終結審查。本案終結審查後,布蘭特伍德公司可依法另行提起執行申請。
(三)簡評
相較于“龍利得案”和“大成産業案”,本案在處理境外仲裁機構在內地仲裁問題上又前進了一大步。廣州中院不僅在之前的民事裁定書中確認國際商會仲裁院在廣州仲裁的仲裁協議有效,而且在仲裁裁決的執行階段還進一步明確了這類裁決的國籍屬性(籍屬)和執行裁決的法律依據。
關于裁決的籍屬,申請執行人布蘭特伍德公司原本希望法院采取“仲裁機構所在地標准”,走捷徑認定本案裁決爲法國裁決或者香港裁決,因爲本案仲裁機構總部或者受理案件的分支機構所在地分別爲法國和香港。若如是,則本案裁決可以視爲法國裁決或香港裁決,進而紐約公約或者內地和香港相互執行裁決安排得以適用。被申請執行人則提出本案裁決不屬于紐約公約第1條第1款項下的“非內國裁決”。廣州中院在本案中沒有回避裁決的籍屬問題。廣州中院既沒有按照“仲裁機構所在地標准”認定本案裁決爲法國裁決或香港裁決,也沒有認定本案裁決爲“非內國裁決”,而是認爲外國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的涉外性質的仲裁裁決,可以視爲中國涉外仲裁裁決。廣州中院的這一認定殊值稱贊:首先,這是中國法院首次明確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裁決的性質,具有標杆意義;其次,摒棄“仲裁機構所在地標准”,以“仲裁地標准”確定仲裁裁決具有仲裁地所在國國籍,符合國際仲裁的主流觀點,我國司法機關並未逆潮流行事或者置身于該潮流之外;第三,若將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的仲裁裁決視爲“非內國裁決”,將有可能無法逾越我國加入紐約公約時所作出的“互惠保留”,于執行無助益;退而言之,即使不考慮“互惠保留”而依據紐約公約解決裁決的執行問題,紐約公約也會因其本身的局限不能解決裁決的其他司法監督問題(例如,如何確定對仲裁裁決行使撤銷權的主管法院問題),因此“非內國裁決”的解決方案並不周延,容易顧此失彼。將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的仲裁裁決視爲中國的仲裁裁決,除有執行方便外,還可以解決對該類裁決的撤銷管轄問題。按照通例,仲裁地的法院對仲裁裁決的撤銷有管轄權。
關于裁決的執行依據,廣州中院也明確了,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的涉外仲裁裁決,可參照民事訴訟法第273條的規定向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財産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民事訴訟法第273條(以及第274條)原本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裁決”,本案法院曆經五年(從2015年4月13日立案至2020年8月6日作出本案裁定)提出此條文也可“參照”適用于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作出的涉外仲裁裁決,足見此一解決方案是我國法院審慎考慮後作出的務實選擇,爲以後同類案件的裁判和同類裁決的執行提供了明確的指引。按照本案的裁判理由進一步推理,境外仲裁機構在內地作出涉外仲裁裁決的撤銷,將也有參照仲裁法第70條和民事訴訟法第274條進行司法監督的可能。
以上三個案例相互之間的時間跨度不到十年,其所取得的進步卻意義非凡。它們都完成了同樣的任務,就是面對仲裁法存在的缺漏和當事人願意通過境外仲裁機構在內地仲裁的現實需要,如何順應國際仲裁的潮流,創造性地解決制定仲裁法時未曾明確的問題,讓當事人切實感到中國是一個可信任、可預期的仲裁地。最高人民法院、安徽高院、上海一中院和廣州中院在三個案例中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體現了人民法院支持仲裁、求真務實、填補缺漏、解決問題的態度。
從更加廣闊的背景來看,人民法院積極支持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的態度與國務院關于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爲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制度環境的工作總基調相吻合。2015年以來,國務院先後三次發文,就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特定地區開展業務活動問題提出了建設性的指導意見。
2015年4月8日,國務院在《進一步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中,提出要“進一步對接國際商事爭議解決規則,優化自貿試驗區仲裁規則,支持國際知名商事爭議解決機構入駐,提高商事糾紛仲裁國際化程度。探索建立全國性的自貿試驗區仲裁法律服務聯盟和亞太仲裁機構交流合作機制,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亞太仲裁中心。”2019年8月7日,國務院《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總體方案》進一步提出,“允許境外知名仲裁及爭議解決機構經上海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登記並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備案,在新片區內設立業務機構,就國際商事、海事、投資等領域發生的民商事爭議開展仲裁業務,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當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財産保全、證據保全、行爲保全等臨時措施的申請和執行。”2020年8月28日,國務院《關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建設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範區工作方案的批複》([2020)123號“]允許境外知名仲裁機構及爭議解決機構經北京市司法行政部門登記並報司法部備案後,在北京市特定區域設立業務機構,就國際商事、投資等領域發生的民商事爭議提供仲裁服務,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當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財産保全、證據保全、行爲保全等臨時措施的申請和執行。”
既然國家鼓勵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設立業務機構提供仲裁服務,那麽它們以內地爲仲裁地受理仲裁案件、管理仲裁程序和依法作出仲裁裁決就是題中應有之義。相應地,中國法院能夠執行該仲裁裁決也是合理的預期。可以想見,在外國法院看來,在中國領域內作出的仲裁裁決是中國的仲裁裁決。如果我們不認可這個現實,而是以“仲裁機構所在地不是中國”爲由將此類裁決打上“外國仲裁裁決”的標簽或者幹脆以“沒有法律依據”爲由一推了之,則很容易造成認知混亂,也會讓意欲在中國仲裁的當事人感到挫傷。
所幸的是,上述三個案例爲解決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的相關的問題開啓了綠色通道。“龍利得案”解決了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的仲裁協議效力問題,“大成産業案”明確了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不涉及仲裁市場開放問題,“布蘭特伍德案”按照仲裁地標准爲確定此類仲裁裁決的籍屬和執行依據提供了指引。三個案例中,司法機關均本著有利于仲裁的政策去靈活地、而不是機械地理解和適用仲裁法。
當然,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在修訂仲裁法時充分考慮司法實踐所取得的經驗,對標國際先進規則,確立處理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的一系列法律規則,營造法治化、可預期的仲裁環境,爲使中國成爲國際上受歡迎的仲裁地而不斷努力。
來源:《上海法學研究》集刊2022年第2卷(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