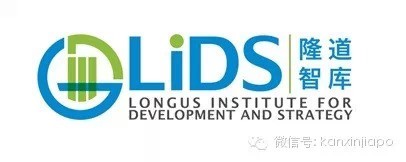國際政治往往是大國之間的政治(而非理性)博弈。因爲每一大國都是獨立的主權體,如果大國之間開始博弈,就很容易受很多非理性因素(例如民族主義和政治人物的個性等)的影響,博弈的結局並不見得就是博弈者原來所預期的,甚至相反。
很多迹象表明,中美兩國之間正進入這樣一種博弈狀態。中美都希望彼此的博弈會是雙贏而不是零和遊戲。就中國來說,早就提出了要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其本意就是要逃避曆史上一再出現的大國爭霸而導致戰爭的“宿命”。從這個角度說,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設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如果不能逃脫零和遊戲的博弈,兩國的沖突也爲期不遠了。
中美近來博弈最直接的起因在于東海和南中國海問題。它們並不直接涉及中美雙邊關系,兩國之間也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沖突。美國的深度卷入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美國和其同盟之間的關系,二是美國對中國的錯誤判斷,以爲中國要挑戰美國。無論在東海還是南中國海,中國實際上並非肇事者,而只是對他國(日本、越南和菲律賓等)行爲的反應。即使如此,美國選擇和其盟友站在一起。美國的選擇或許是因爲被盟友所綁架,或許是因爲要利用盟友來制約中國,或許兩者兼有之。但不管如何,這種選擇的心理基礎,是其與日俱增的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感。美國在成爲世界大國後,一直和其他大國爭霸,對大國爭霸學說深信不疑。因此,盡管中國選擇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無意把美國趕出亞洲,更無意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但美國的這種霸權信仰不可避免導致其對崛起中國的恐懼。
美國對中國的反應可以分爲官方和非官方兩個層面。盡管官方並沒有完全接受“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但的確認識到了中美關系的複雜性。因爲中美之間的高度互相依賴性(至少在經濟上),也是因爲中國並沒有蘇聯那樣的爭霸方案,美國意識到處理和中國的關系並非那樣簡單明了。所以,盡管官方有時也放出狠話,但反應還算節制,沒有想把中國推向對立面。就美國政府來說,只要稍微理性一些,就不會把中國推向對立面。一旦美國失去中國,這個世界很有可能演變成往日美蘇集團之間的冷戰狀態。如果中國離開了以美國爲主導的國際秩序,美國充其量也只是半個世界的霸主,而非全球霸主。
不過,非官方的強烈反應似乎顯示兩個國家關系的遽然惡化。自近代以來,美國國內一直存在著一個可以稱之爲“中國情緒”的東西:如果中國的發展(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符合美國人的理念和價值觀,美國就會充滿樂觀的中國情緒,甚至過度樂觀;但如果中國的發展不符合美國人的理念和價值觀,美國人就會對中國悲觀起來,甚至充滿敵意。再者,美國的“中國情緒”曆來就是導致美國改變中國政策的重要因素。今天的情形就是,不僅往日的反華和對華敵視的政治力量再次擡頭,而且傳統上被視爲是對華友好和同情中國的政治力量,也在急速改變態度。在學術和政策界,已經開始呈現出對華普遍的“冷戰情緒”。
沖突會是人類大災難
對中國來說,盡管很難控制美國內部所發生的變化,但如果建設不成新型大國關系,就會走向中美沖突的宿命。如果這樣,便會是個顛覆性錯誤。現實中,在中美關系上,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大多數人都會關注誰輸誰贏的問題,也就是零和遊戲。人們假定,一方的失敗就會是另一方的成功。實際上則不然。中美的沖突會是人類的大災難。往日美蘇冷戰之所以沒有演變成熱戰,根本原因在于兩大集團之間的核威懾。對今天的中國來說,無論是和美國的冷戰還是公開的沖突,都會是顛覆性的錯誤。如果要逃避兩國沖突的宿命,就要通過百倍的努力來建設意在逃避宿命的新型大國關系。
既然是博弈,就要充分了解博弈者和博弈的方法。不同的博弈者和博弈方法導致不同的結局。對中國來說,就是要在不同的博弈局面中爭取最好的局面。就中美關系來說,中國必須了解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諸種方法,和這些方法背後的政治力量。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可以概括成如下三種。
首先,圍堵、遏制。這是一種冷戰的方法,是美國對付蘇聯的。在美國的一些勢力看來,這個方法很有效,它不僅遏止了蘇聯的擴張,而且導致了蘇聯的解體。當然,對蘇聯來說則是大災難,使得俄羅斯直到今天仍然一蹶不振。盡管這種方法很難用于和美國互相依賴的中國,但美國國內不時會有人出來試圖使用這種方法來應付中國。
其次,接觸、融入。這在學術上被稱爲“社會化”,也就是被西方“社會化”。美國容許和鼓勵中國加入現存國際體系,接受西方制定的規則。美國使用這種方法消化了日本、德國等,冷戰結束之後也消化了屬于蘇聯陣營的東歐國家。美國也希望通過這種方法來消化中國的崛起。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對中國基本上也使用了這種方法。不過,中國和其他國家不同,讓美國感覺力不從心。
再次,把中國轉變成爲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承擔維持世界秩序的國際責任。這種方法也是中國所可以接受的。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樂意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但問題出在中國向誰負責。中國具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對國際責任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中國會履行自己而非美國所界定的國際責任。在很多方面,兩者並不見得一致。
因爲美國在使用所有上述方法上不盡人意,隨著中美關系大環境的變化,美國現在開始尋找新的途徑,制定新的對華政策。今天流行于美國政策市場的方法是傳統方法的延續,所不同的是哪種方法占據優勢。在對華政策上,今天美國存在如下幾個主要方法或者政策思維。
第一,現實主義派,以五角大樓爲主導。這派類似于“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發生之前的新保守主義。這一派強調要利用美國所擁有的強大軍事優勢,使用冷戰期間曾經對付前蘇聯的經濟方法,締結區域性的針對中國的戰略性貿易同盟;嚴格限制對中國的技術出口,尤其是可以轉化成爲軍事用途的技術;在各個領域(例如中國的邊疆、周邊和主權問題)爲中國的崛起制造麻煩等。美國認爲,中國過去數十年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爲美國向中國開放,接納了中國,給了中國搭國際秩序便車的機會。如果美國改變開放政策,就可以延緩甚至阻止中國的崛起。
第二,和平共處方法。這個方法有些類似中國本身所追求的方法,美國可以通過限制對台灣的武器出口,以獲取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和平承諾、通過要求同盟(日本、菲律賓等)的克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中國的核心利益(主權)要求、通過改革現存美國西方所主導的國際機構,讓中國擁有更大的權利和責任等等。
第三,求同存異法,美國一方面不會在美國認爲會損害美國關鍵利益的問題上同中國妥協,例如當中國的“擴張主義”損害到美國或者美國盟友的利益的時候,美國需要和中國對抗;另一方面在一些關鍵問題和中國進行合作,例如朝鮮核武器問題、伊朗核武問題、氣候和環保問題等等。
雙方缺失“戰略互信”
第三種方法多年來是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主調。現在的情況是,第二種方法很難在美國有市場,很容易被視爲是“親華”“出賣美國利益”。如果學界和政策界現在的“中國情緒”繼續下去,這種方法很快就會退出思想政策市場。第一種現實主義的方法上升得很快,有可能和第三種方法中的一些負面(對中國而言)因素結合起來,演變成對華政策主流。
中國對美國國內各種博弈者及其方法也不是沒有認識。中國實際的國際戰略,和美國所認知的中國國際戰略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中國也意識到,這種巨大的鴻溝的出現主要在于雙方缺失“戰略互信”。如果意識到這種“戰略互信”是在雙方互動過程中産生和發展的,中國不再是一個被動的角色,而是應當有所作爲,努力改變美國對中國的認知。
對中國而言,今後相當長時期的外部挑戰,就是如何管理美國的相對衰落及和這種衰落有關的戰略心理。在中國真正崛起之前,能夠對中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是美國,其他國家可能只給中國帶來很多麻煩。要減少、控制乃至消除美國的威脅,就要管理美國的相對衰落和衰落心理。
美國和大英帝國不同。大英帝國的世界領袖地位是打拼出來的,知道打拼的辛苦。因此,在知道了自己的衰落不可避免時,大英帝國便制訂了體面退出的機制。美國沒有經過多少打拼便成爲世界領袖。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互相戰爭,戰後沒有一個可以成爲領袖,美國便被邀請成爲領袖。戰後,在和蘇聯的競爭過程中,美國用冷戰方式輕易打垮了對方。其他地方區域性沖突或者戰爭,對美國只是維持秩序的次要問題,也就是其履行世界警察的職能表達。今天盡管美國相對衰落了,其霸權心態仍然堅不可摧,仍然具有充當世界領袖一百年的雄心。
中國要管理美國的衰落及其衰落心理,至少必須做幾件事情。第一,中國不僅必須避免和美國的軍事競爭和沖突,而且要搞一些比較大規模的軍事合作。沒有幾個大規模的軍事合作平台,兩國很難建立最低限度的軍事互信。第二,也是最爲重要的,中國要克制自己,不和其他國家(例如俄國)結成同盟。一旦軍事同盟形成,就會走上戰爭的不歸路,無論是冷戰形式還是熱戰形式。曆史上,所有重大的戰爭都是在兩個同盟之間展開的。中國應當堅持迄今爲止的“戰略夥伴”戰略,避免結盟戰略;前者是針對解決各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而後者則是針對第三國(即敵人)的。
第三,就美國內部力量來說,中國可以通過使用上述兩種方法,有效結合第二、第三方面的政策話語和力量,避免讓第一方面的話語和力量占據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
最爲重要的便是通過外部的更加開放,來促成內部的可持續發展,以實現真正的崛起。在美國對華政策趨硬的情況下,中國不僅不能搞民族主義,而且應當變得更加開放,不僅向其他國家開放,更向美國開放。只有實行比美國更加開放的政策,才能阻止上述第一種現實主義占據對華政策的主流。
新型大國關系的道路必須走下去,而需要政治家來構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是不會讓局勢這樣惡化下去,而走入兩國沖突的宿命的。
隆道智庫由鄭永年教授等人在新加坡發起,本文感謝鄭永年教授授權發布